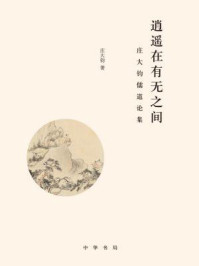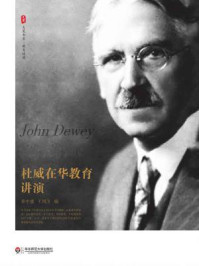前面已经写到过,达森草原不仅有牧人和畜群,还有狼、鼠兔和其他野生动物,它们也是这片草原的原住民,真正的土著。因为宿营达森草原,与一群老鼠比邻而居,我对它们便有了一些新的观察和认识。
当然,它们也在观察我们,人类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它们的法眼。对草原上人类头疼不已的种种变故,鼠族静观其变。
在它们看来,人类总喜欢瞎折腾,一会儿要翻开草皮,给草原垒上围墙,像城墙;一会儿又废弃草皮围墙换成铁丝围栏,把整片大草原分割成七零八落的碎片;一会儿要翻开草皮采沙开矿淘金子,把滋养草原的一条条河谷翻个底朝天,到处飞沙走石,连河流都钻进河床底下去了,死活不肯露面,几十年过去之后,那河谷里还时时发出一股恶臭,河中所有的鱼儿和水生物都死绝了;一会儿又要种草灭鼠和人工降雨,草没种出来,却把沙子翻出来了。雨倒是降下来了,可也给草原降下了无数的毛毛虫,现在不管是不是人工降雨,只要一场大雨过后,草原上到处都是黑油油亮晶晶的红头毛毛虫。

吉祥达森
而至于可恨的灭鼠——老鼠们心想,你人类凭什么要灭了我们鼠族。以鼠族在地球上几千万年的生存经验看,你们人类给我们鼠族当孙子还不够格呢,哼,几千万年!这几千万年还是你们自己说的,我们究竟在地球上生活了多长时间,除了我们自己,恐怕只有造物主知道。我们有的是时间和耐心——而你们人类未必有足够的时间,也许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尽快自救尚可,否则将自身难保——我们也有足够成熟丰富的战略战术来对付你们的那点儿能耐和伎俩……地球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会是谁的,不好说。
但可以肯定,最后的地球上绝不会只剩下人类。因为,所有地球生命都知道,假如地球上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人类,你们还能存活吗?妄想!不说了。多说不宜。最后,我们鼠族只想代表所有的地球生命奉劝一句:善待万物,万物才会善待你。利他才会利己。鉴于此,鼠族郑重声明:我们绝不称霸,但也绝不允许任何别的生命独霸地球。
当然,在别的生命看来,鼠族并没那么可恨,甚至很可爱。比如在狼族眼里,那些没有尾巴又幼小的生命就很可爱。狼族认为,它们甚至根本不是老鼠,总体上,它们应该归在兔子家族。虽然因为门齿无齿根,人类将兔子和老鼠都归到啮齿类动物,但是,兔子是兔子,老鼠是老鼠,不是一码事。据狼族的传说,兔子和老鼠原来也不喜欢到处开挖洞穴,它们所容身的地方,不过方寸之间,何苦要让自己大费周折呢?因为人类总喜欢在它们的洞口给它们下套放毒药,它们才开始四处广开洞穴,只为逃逸和活命,实属情非得已。
很久以后,人类世界的网络空间里有一篇文字流传甚广,单看其标题,你就能想见人类的出尔反尔。这篇原出《环境与生活》杂志、署名田野的文章,原标题是《不仅无过反而有功》,网络传播时,标题改成了《真冤!鼠兔为草原退化“背锅”60年,人家不仅无过,反而有功》。
鼠兔是一种害怕炎热而喜欢寒冷的动物,所以,它们一般都栖息在高寒地带,随着全球气候日趋变暖,它们也不断向更高寒的地带迁徙。正因为如此,我猜想,在青藏高原广袤的高寒冻土地带,鼠兔也许是最早定居于此并持续繁衍的动物。也许它们持续繁衍了几千万年之后,这里才出现了别的动物。
也许,它们最初迁居高寒冻土地带时,最后的冰川期还没有结束,它们是踩着厚厚的冰雪抵达这里的,而后住了下来。还因为地处高寒,这里冰川期结束的时间可能要比欧亚大陆其他地方晚得多,说不定直到5000年前后甚至更晚的年代,这里的冰川期还没有完全过去,大地还在厚厚的冰盖之下。
而人类一定是最后才出现在这里的动物,他们无法适应极度寒冷的气候。人类出现时,最后的冰川期早已结束。此前,几乎所有的动物都已在这里永久定居,并一直占据着种群繁衍的优势。直到今天,与众多物种比较而言,人类也肯定不是后来居上者。
2018年8月3日,在迪嘎盖草原拉姆德钦家门前的草地上,扎了一顶帐篷住下来之后,我在当晚的田野笔记中这样写道:
方圆5公里之内,至少有六七户牧人是我的邻居,人口数量不会超过40。这是人类,如果算上别的族类,我的邻居中至少还有一群牦牛和一群老鼠。哦,还有一只野鸽子——我没有看清,应该是一只鸽子。还有一只很大的乌鸦,像一只鹰那么大。当然,还有数量惊人的各种小虫子。因为刚刚扎好帐篷住下,别的,我还没顾上细看。毫无疑问,在所有邻居中,老鼠是数量最多的。大约两平方米之内就有一个鼠穴,我帐篷周围方圆50米之内,估计至少有50只老鼠——也许有300只甚至更多,具体的数量要看每个鼠穴中所居住老鼠的多寡。夜里,它们就会睡在我的地铺周围。
除了老鼠,距离最近的邻居是那一群牦牛,约80头。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它们会到草原上吃草,而夜晚,它们就住在我帐篷跟前。离我睡铺最近的不超过20米。如果夜里它们弄出点儿动静来,比如打个喷嚏或放个屁什么的,我都会听得一清二楚,甚至会听到它们反刍的声音。
傍晚,约7点到8点,我还拍了一阵老鼠。可能因为这里的牧人不怎么讨厌老鼠,这里的老鼠也不怎么怕人。看上去,这里只有一种老鼠——鼠兔。一种没有尾巴(或短尾)、长得像兔子的老鼠,与兔子和别的鼠类一样,均属啮齿类动物,至今已在地球上生活了7000万年之久。想来,在未来的很多天里,我还将继续与它们朝夕相处。
下午出去如厕,走了很远,就是找不到一个可以蹲下来而不让人看到的地方。小解还好,一般也不大顾及,只要不是当面就行,即使有人看到也不当一回事。而大解你总得顾及自己的颜面吧,可草原的空旷令你无处藏身。走很远去如厕时,感觉自己像做贼。
终于完事了。往回走时,我沿途仔细观察鼠兔的洞穴,竟发现鼠兔的厕所都建在洞穴外面,大多在一个凹陷的露天坑洼处。其厕所一般还都比较宽敞,还因为有足够的深度,隐蔽性好,一只鼠兔进到里面,从任何一个方向都不会看到它如厕的场景。想来,它们在如厕时也不希望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无论何种动物,如厕的场面都不雅。
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我从未看到过一只鼠兔(包括其他啮齿类动物)在大庭广众之下如厕的情景。其厕所也不在洞口,如厕时,鼠兔须穿过洞穴之间的一片空地。除了厕所,其他地方很少看见其粪便,说明鼠兔是一种不喜欢随处大小便的动物,所以也看不到“不得随处大小便,违者罚款”的警示标语。由此可以看出,鼠兔对环境卫生的重视和讲究。
其实,几乎所有鼠类和啮齿类动物都有这样的讲究。像俗称“瞎老鼠”的鼢鼠,虽然常年在地下生活,但其洞穴中也有专门的厕所或卫生间,从布局看,“瞎老鼠”对卫生间的讲究程度不亚于卧室和粮仓。其卧室大多居于中间位置,而卧室两侧分别是粮仓和卫生间。一窝“瞎老鼠”至少会有一处卫生间,也有两处和三处卫生间的——一户三卫的,想来应该会是一座鼠类的豪宅。
我看到两只鼠兔在自家洞口一边看风景,一边不时歪过头去看着对方,偶尔也会歪过头来瞅我一眼,像站在家门口说话的一对小夫妻那样。它们离我只有不到两米的距离。我静静地看着它们,大约有半分钟的时间。夕阳下,它棕灰色的皮毛闪闪发亮,尖尖的嘴唇快速蠕动着,像在咀嚼什么。那一对小耳朵总是直直地竖着,时刻保持谛听附近和远处动静的样子。
那一刻,我并未觉得它们有多么讨厌,甚至还觉得有点儿可爱,像一对精灵。我转身回到帐篷,去拿相机,我要给它们拍些照片。
我选了一支200毫米的镜头,觉得在这么近的距离,用这样一支镜头足以将一只鼠兔拍得非常清楚了。我重新站回到刚才的那个地方,发现那两只鼠兔还在那里,几乎没有挪动过,一只鼠兔的屁股还像刚才那样正对着洞口。我以为它们对我的举动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轻轻举起相机,准备拍摄。但是,当我将相机的取景框对准它们时,它们却一缩脑袋钻进洞穴里,不见了。
很显然,我的任何举动都没有逃过它们密切注视的目光。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想应该有一个多小时,我一直在帐篷周围的那一片草地上到处追着几只鼠兔给它们拍照。
可它们根本就没想着配合我的行动。它们不是一溜鼠窜,就是一缩脑袋溜进洞里。有好几次,我踩在一泡新牛粪上,差点儿把自己滑倒。我意识到,一直追着它们转不是个办法,就蹲下来,双膝跪地,相机一直架在鼻梁上,眼睛紧紧盯着取景框,严密监视着一个洞口,耐心等待,以为刚刚钻进洞里的那两只鼠兔会再次出现在洞口。可是,它们没有出现。我也坚持不住了,膝盖隐隐作痛,腰背也开始酸痛。
我站起身来,腰还没来得及伸直,它们却探出头来瞄了一眼,犹豫了一下,悠然踱出洞口,停下来重复刚才的那些动作。我以为机会来了,可是刚一端好相机,它们又一下子钻进了洞里……如此这般,折腾了好一阵子,尽管也把一只只鼠兔都装进了镜头,可没有一只鼠兔是拍得非常清晰的。
阿热啊克雪,这是藏语里一种鸟的名字,准确地说,后两个字才是鸟的名字,前三个字则是一种无尾鼠类的名字,就是鼠兔。鸟形似草百灵,疑为百灵鸟的一种。
也是在迪嘎盖草原,我才突然发现,鼠兔阿热啊(音读Ara)能发出百灵鸟一样清脆嘹亮的鸣叫,跟别的鼠类“吱吱”尖细的叫声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住在帐篷里,周边草地上到处都是鼠穴,我每天都有那么一些时候,可以静静地观察阿热们的一举一动。
我第一次听到阿热啊克雪这个名字,是在泽曲河上游河谷的一面山坡上。在《谁为人类忏悔》一书中,我曾写到过这段经历:

迪嘎盖的鼠兔
那些鸟儿在藏语中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阿热(啊)果雪(康巴方言中发阿热啊克雪之音——作者注),翻译成汉语就是老鼠的清洁工了。当地陪同采访的朋友说,这种鸟儿是专为老鼠打扫洞门的,它们常常扇动着一对小翅膀,把老鼠洞口的尘土扫去,还为老鼠承担警戒任务,为它们通风报信。我特意察看了一些鼠洞,果然没有尘土。再看那些鸟儿时发现,它们的确像是在围着老鼠生活。它们有翅膀,却并不飞高飞远,在地上跳跃时竟如鼠窜。便不禁叹为观止。老鼠何德何能,竟然将自己的领地从地下转入地面,进而还将自己的鼠爪伸向天空,征服了这些象征自由的精灵。它们对这些鸟儿施展了什么样的魔法,以致这些鸟儿甘愿俯首听命呢?人类费尽心思,也才教会几只鹦鹉学舌,或阿谀奉承或说脏话骂你。仅在这一点上,鼠类远比人类高明。
接着我还写下过这样的文字:
也许有一天,当这里最后一个牧人被老鼠赶离最后的草原时,这山下的滩地上说不定会黑压压一片,挤满了老鼠。可能会有一只统帅一样的老鼠蹲在这山冈上,望着那牧人远去的背影,哈哈大笑。它无疑是草原最后的胜利者,因为尽管人类征服了地球上所有的草原,它们却最终征服了人类。那时,整个草原上已没有了牧草生长,有的只是鼠类的咆哮和冲杀。如果弄不好,它们也会犯和人类一样的错误,毫无节制地繁殖自己的同类。而后,为了争夺没有牧草的黑土滩领地和生存空间,挑起鼠类之间的世界大战。说不定,也会出现像美国那般强大的鼠类帝国,对全球的老鼠们指手画脚,动辄出兵杀伐——那就是鼠类的不幸了。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反观人类,人类不是更不幸吗?人类最终可能会用自己的智慧将自己逼上绝路。
后来,我还陆续看到或听到过很多有关鼠兔和阿热啊克雪的故事,其中流传最广的是鸟鼠同穴的故事。据《甘肃志》记载:“凉州之地有兀儿鼠者,形状似鼠,尾若赘疣。有鸟曰本周儿者,形似雀,色灰白,常与兀儿鼠同穴而处。所谓鸟鼠同穴也。”另据《尚书·禹贡》记载:“鸟鼠之山有鸟焉,与鼠飞行而处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鸟名为‘鸟余’,其鼠为‘鼠突’,鸟似缀鸟而小,黄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处,各自生育,不相侵害……”除此之外,《山海经》《史记·夏本纪》等亦有相关记载。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有关鼠兔和阿热啊克雪的记载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些记述,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凉州之地有山,名曰鸟鼠山;另一层则说,有一种形似雀的鸟儿与一种短尾的老鼠同穴而处。至于文献中“兀儿鼠”“鼠突”则当是今天“鼠兔”的音变,其实,说的都是同一种动物。几千年以前,古凉州一带气候应该依然寒冷,适于鼠兔生存,而众多青藏高原的鼠兔,因为地处边远荒僻,其时,尚没有进入华夏族人的视野。
除了史书上的记载,鸟鼠同穴还有民间传说。鸟和鼠原本是一对恩爱夫妻,祖祖辈辈都居住在渭河源头,生活清苦,但为人善良忠厚。一天,妻子早起去担水,发现河边有两条蛇厮咬在一起,一条白蛇被一条黑蛇死死咬住,眼看就要被咬死了。妻子看着可怜,急忙从树上折了一根树枝把黑蛇赶跑了,白蛇得救,钻到河水里逃走了。当天晚上,妻子做了一个梦,梦见家里来了一个人,自称是渭河龙王的家里人。来人对她说:“你今天做了善事,救了我们家主人,我家主人要报答你,请你在鸡叫头遍的时候到渭河边上来。”
妻子半夜醒来,半信半疑,便约丈夫一同前去。男人比较懒,不太情愿,妻子要出门了,他才嘟嘟囔囔地从炕上爬起来。妻子到河边时,丈夫还在半山坡上。龙王的家人已经在河边等候了,一见面就嘱咐道:“此番前去,龙王会好好报答你。给金子,你不要要,给银子,你也不要要,你只要桌上的两把花扇子和那两颗玉石,就终生享用不尽了。”她一一记下。来人让她闭上眼睛,背着她下到河底,睁开眼睛时,她已经来到龙宫,一个受伤的老爷爷热情地接待了她,还摆了宴席招待她。
临了,他让下人端上一盘礼物给她,一看是金子,她没要。老人又让端来一盘礼物,是银子,她也没要。龙王就让她自己挑两件礼物,她就要了桌上的那两把花扇子和两颗玉石。龙王答应了,还派属下把她送上河岸。看见自己男人还在河边等,她就把经过说了一遍,还给他看了两样宝贝。她男人不喜欢花扇子,就接过了两颗玉石。正要细细看,妻子手中的两把花扇子一下变成了一对翅膀,妻子飞到天上去了。男人急了,想腾出手来拉住妻子,情急之下,把两颗玉石咬在嘴里,刚咬住,那两颗玉石却变成了一对尖利的门牙。
从此,妻子变成了鸟,男人却变成了老鼠,尾巴都没来得及长好。可好心的妻子总也忘不了过去的恩爱,便常常到鼠穴中与丈夫幽会……
从此,鸟鼠同处一穴,彼此相守和谐,老鼠打洞筑穴,鸟儿为其站岗放哨,还肩负清洁任务。
为了这个传说,我曾专程到渭河源头的鸟鼠山实地考察,在古凉州(今定西)一带走了两三天,均未发现鼠兔踪影,也未见着那种与鼠兔形影不离的鸟儿。鸟鼠山植被茂盛,植物种类丰富,其主要建群植物与青藏高原东北部及祁连山麓几乎没有分别。云杉、桦树、栎树、白杨当是主要乔木树种,灌木种类庞杂,栒子、黄刺、忍冬、柳类等属常见植物。山前的大片落叶松应该是后世人工种植的,树龄不会超过40年——也许是1998年之后种植的。
这样的环境并不是鼠兔喜欢的栖息地,与鼠兔相伴而生的鸟也难以生存。我在鸟鼠山只见过一种鸟,从羽毛的颜色和鸣叫声判断,应该是画眉的一种,与常见画眉不同的是,其头部和背部的羽毛多黑色。
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带鼠兔分布情况的变化看,一些低海拔地区今天已经看不到鼠兔,今天的定西(凉州)一带更看不到鼠兔了。虽然鸟鼠山还在那里,但鸟鼠已经远去——至少鼠兔已经远去,它们都已迁徙到更加高寒的高原腹地,在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尤为集中。那里气候寒冷,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这正是鼠兔喜欢的气候环境。
我听说,如需远距离迁徙,鼠兔还会将鸟儿当成坐骑,借鸟儿的翅膀飞翔。鼠兔有时候会从一个地方突然消失,而后出现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这是一种集体行为,这样的远距离迁徙时,鸟儿就是它们的运输工具,类似于人类世界的空中运输。
在迪嘎盖的那几天里,每时每刻,我周围都有一群鼠兔,或交头接耳,或鼠窜于鼠穴之间,或站在洞口鸣叫。其声如鸟鸣,清脆悦耳。不知道在骑着鸟儿飞行时它们是否也会鸣叫,如是,但凡听到那声音的人,一定会当成是鸟儿的鸣叫,而绝对想不到那是老鼠发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