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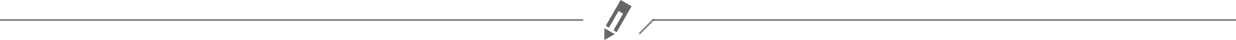
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扰动非常大,中国经济总量最晚在2035年超过美国。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北京
对于中国而言,2021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国的经济增速继续领跑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也已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下再次显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2021年对校外培训、互联网平台、加密货币等领域的大力监管背后,我们正迎来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历史时刻。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接受《北大金融评论》专访时指出,新冠疫情对经济活动影响超预期,特别是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非常大。而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能耗双控”和在一些领域竞争力的下降,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更紧迫的要求。虽然中国目前已经非常接近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但面向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北大金融评论》:新冠疫情发生近两年,如何评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高善文: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很大程度取决于疫情本身的发展。这包括病毒的传播、社交控制措施的影响、疫苗的研发和接种情况、治疗药物和技术的进展等。
从全球来看,各国疫苗研发和接种的速度很不平衡,不同的国家体制和文化对于社交疏离的推动、大规模人员流动的控制也有较大差异,各国经济受疫情影响的表现并不一致。
中国最显著的特点是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追踪和控制能力非常强,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的蔓延。但过去一年多,疫情仍呈现时断时续、小范围内偶尔发生的局面,叠加中国控制疫情的决心和力度,经济迄今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从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情况来看,它们虽没有中国政府这样的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但2021年以来其疫苗研发和接种速度非常快,经济活动也经历了强劲反弹,当然这些国家也出现了比较多的新冠关联的人口死亡。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无论是对于病例的追踪、隔离和控制,还是疫苗的接种,相对都更落后一些。
最近出现的病毒新变种传播很快,还导致疫苗效力下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不确定性,不过人们普遍相信我们不会重复2020年上半年的严重恐慌和经济冻结。
具体到疫情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影响。首先,疫情给人类的心理活动留下了一定的伤疤。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跟疫情之前相比,人们承担风险的意愿降低、消费倾向下降,经济活动进一步受拖累。
疫情期间,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住户部门提供了大量的补贴。但由于疫情导致的社会控制,大量由补贴形成的储蓄在当时并未被消费掉,这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增大,这一压力在长期之内如何管理和消化,值得人们观察。另一方面,当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后,疫情期间的积压需求是否会有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集中释放,这也需要去观察。
其次,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非常大。2021年美国美西港口持续拥堵、海洋运输费用急剧上升,都显示了全球供应链受到巨大扰动,而供应链迟迟不能恢复正常,在一定程度上是超预期的。
新冠疫情之后,全球供应链会有一定调整,供应链的调整可能与地缘政治有关,也可能与疫情造成的冲击所显现的供应链的脆弱性有关。因此,供应链的分散化、近岸化、本土化被认为是一个很可能正在出现的趋势。如果将这一趋势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在一些领域竞争力的下降联系起来,它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更紧迫的要求。
再次,从全球劳动力市场来看,相比疫情之前,在同样的失业率条件下,工资的上升会更快。求职者在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时,他们投入工作的积极性并不高。这也引发一定担忧,即我们是否正在形成一个由工资和物价上升相互循环的通货膨胀。
疫情对不同经济部门所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由于疫情都是近距离社交活动传播,在疫情期间货物消费可通过网络来实现,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服务消费受到的打击则明显更大。而且由于人们无法进行服务消费,一部分消费开支便转移到了货物消费领域,造成了全球的工业生产、货物消费和贸易在2020年下半年时就完全恢复、甚至超过疫情之前的水平。2021年,随着全球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的货物消费和全球工业生产在三季度以后逐渐减速,全球服务消费总体上开始经历一个积压需求的释放。
总的来看,疫情给经济活动造成了非常广泛深刻的影响,一些短期的经济活动扭曲正在恢复正常,但仍有一些相对持续时间更长的影响,比如受疫情期间的恐慌影响,一些行业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破产潮”。在远洋运输行业,2020年上半年集装箱就出现了比较集中的拆解,因为大家对于经济的预期非常悲观。在页岩油领域,由于对能源消费的预期较低,在大规模的违约潮下,页岩油领域的一些现成产能不断关闭、新增产能异常低。其他一些领域也都出现了投资异常下降或是在较长时间之内受抑制的局面,这与2021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也有一定关系。
《北大金融评论》:近期全球范围内抬头的通胀与疫情影响下的短期供应链扰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高善文: 全球范围内供应链的扰动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已经比较明确,供应链恢复正常以后,通胀的压力会有一定的减轻。目前通胀成因很多,但从全球性的因素看,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全球供应链的恢复进度始终比预期的更慢。发达经济体的疫情得到控制了,但东南亚以及新经济体又经历了一轮的暴发,从全球来看始终不尽如人意。另一个是供应链之外的一些压力。比如中国的“能耗双控”政策、全球的去碳努力等,这对商品价格、能源价格以及通货膨胀都有一定的影响。2021年以来,能源价格的高企跟疫情的关系并不那么强,与全球去碳的努力的关系更强一些,由此带来的通胀压力仍处在较高水平。
《北大金融评论》:相比于过去10年,目前市场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高善文: 2018年,财政领域开始去杠杆,2021年,房地产领域也开始比较快去杠杆,这些都体现了政策的着重点跟过去相比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保增长”开始让位于“调结构”。从更深层次来看,在过去“保增长”的背景下,表面上是政府基建和房地产在打头阵,其背后是中国的城市化仍处在一个非常旺盛的浪潮之中。未来10年,中国城市化逐步退潮,城市化本身虽然还在继续,但浪潮的动量(每年进入城市的人数)可能已经开始或者即将开始下降,这对中国整个经济运行的环境会产生非常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北大金融评论》:如何看待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高善文: 人口的问题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人口因素本身是一个慢变量,无论是对于决策者还是金融市场,人口以及人口变化的趋势不会太超预期,可以相对稳定地预测,进而我们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去做一些准备。坏消息是人口的趋势一旦形成便很难逆转。从东亚国家和全球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城市化、工业化完成以后,人口的出生率比较低,妇女的生育意愿比较低,老龄化相对比较严重,人口的增长相对在放慢,这些趋势很难用政策因素去干预和逆转,政策因素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但其效果有多大却是存疑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政策的重点必须越来越多地放到如何为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比较全面的准备。
《北大金融评论》:您预测中国经济总量最晚在2035年会超过美国,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高善文: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劳动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这一增长要么表现为工资的加速上升,要么表现为汇率的升值。如果工资的上升比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更快,名义汇率就会贬值,但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又比大多数其他经济体更快,此时尽管汇率在贬值,但工资增长更快,计算所得的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仍会有极其高速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
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比较接近——劳动生产效率增长非常快,但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仅有一部分表现为工资的增长,即工资的增长比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要更慢。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部分的压力就通过汇率的升值显现出来。日本历史上劳动生产效率增长的50%表现为工资的增长,50%表现为汇率的升值。所以一旦用美元汇率去计算日本的国民收入,它的增长非常快,但若只计算本币的情况,增长相对就没那么快。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历史数据显示,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约80%表现为工资的增长,20%表现为汇率的升值。所以从1997年至今,在长期的趋势上,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剔除通货膨胀等名义因素后,年均升值速率(几何平均)在1.3%左右。这1.3%体现为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之中,没被工资吸收的部分。
结合在微观上看到的数据,我们相信中国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在很长的时间之内,仍然会比发达经济体、贸易伙伴要更快一些。因此,尽管短期之内人民币汇率会有一些波动,但长期之内人民币汇率仍处在一个升值的趋势之中。保守估计,未来实际有效汇率平均每年升值1%是有可能实现的,甚至可以维持在1.3%。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2021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12000美元,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但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美国的1/5左右,只有韩国的一半左右。一个相对更低的人均收入水平,意味着我们的技术发展、资本积累、生活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一空间正是支持经济在一段时间之内继续维持中速增长最重要的基础。
再换一个角度观察金融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水平。大型经济体中,日本、欧洲的长期利率在零甚至是零以下水平,美国的长期利率剔除通货膨胀后也是负值。但中国10年期国债利率在3%左右。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边际回报率比上述国家显著更高。相对更高的资本边际回报率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比它们会明显更快。
基于对历史数据的测算,我们预计2021-2030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将是“保四争五”的水平,经济增速跌破4%不会成为趋势。因此,把经济增长的稳健预测与汇率升值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中国经济总量最晚在2035年会超过美国的预测并不是很激进。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比较容易忽视的是汇率的升值影响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北大金融评论》:我国人均GDP已达12000美元,您认为我们已经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了吗?
高善文: “中等收入陷阱”本身是否存在,学术界仍有争议。仅从学术讨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已经非常接近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但在高收入国家里,我们也仅是刚迈进门槛,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在那时我们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差不多接近于现在韩国的水平。历史成绩巨大,但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采写:钟龙军、本力)
(责任编辑:钟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