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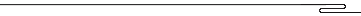
现存有关汉代公文书形态的专门记载,是东汉末年蔡邕的《独断》。从汉代政治体制变迁的角度看,《独断》所记载的公文书反映的主要是蔡邕所处时代的制度,并曲折地反映了此前体制的变迁。
《独断》一书流传不广,常用的有《钦定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三编》据明弘治刊本等,但尚未有很好的整理本。其中有些文句的理解,在已有的相关论著中存在着严重的误读。所以首先必须对《独断》有关公文书的表述进行考证。
今见对《独断》进行全面整理的是日本学者福井重雅的《译注西京杂记·独断》。他对《独断》的全部内容进行了断句,并用日文进行解释及翻译。其中第14~24条为皇帝的命令文书(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敕四类)和群臣上书于天子的奏事文书(分为章、奏、表、驳议)。兹将其断句后的文本移录于下:
14.策书。策者简也。……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
15.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迁书文亦如之。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官、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16.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
17.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
18.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
19.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20.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21.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
22.章曰报闻。公卿使谒者、将、大夫以下至吏民尚书左丞、奏闻、报可。表文报已奏如书。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
23.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意者曰驳议。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赣议异。其非驳议、不言议异。其合于上意者、文报曰某官某甲议可。
24.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王莽盗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顿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尚书衣帛而朝曰朝臣。诸营校尉、将、大夫以下亦为朝臣。

福井重雅的断句和理解存在着不少错误,只要对照一下一些学者对《独断》的引用,就知其绝非善本。文献整理切忌望文生义,而福井重雅的注释和翻译中,有一些讲不通的地方,存在着强作曲解的问题。
本人对《独断》的相关文字有着与所见学者的引用和上引福井重雅的译注不同的理解。兹以《钦定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照《唐六典》所引用的文字,将皇帝的命令文书试释如下:
策书。策者,简也。……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一尺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
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疑作上]迁,书文亦如之。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官,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
 ,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曰
,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曰
 ”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戒[戒,衍]书。
”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戒[戒,衍]书。

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

《独断》对于策书的概括,文义甚明。其主要的应用场合是对于诸侯王、三公的除免和诔谥。
制书则有一些地方需要略加考释。其中“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疑作上]迁,书文亦如之”一句,汪桂海断为“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迁文书,亦如之”,并说此段文义不明
 。福井重雅的断句与汪桂海同,并称“下土”为“下士”的误记,进而将此句理解为:刺史、太守等朝廷任命的地方长官向皇帝上奏弹劾,以及地方僚属(下臣)的申述,这些文书都同样要本官送返
。福井重雅的断句与汪桂海同,并称“下土”为“下士”的误记,进而将此句理解为:刺史、太守等朝廷任命的地方长官向皇帝上奏弹劾,以及地方僚属(下臣)的申述,这些文书都同样要本官送返
 。本人的理解是,刺史、太守和诸侯国相进行劾奏的文书本身并不是制书,而只有对这种文书进行的批复(即所谓申下)才能成为制书。而“土迁”一语殊不可解,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本人疑其为“上迁”,即指刺史、太守和相的升迁。下文“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官”,就是对刺史、太守、相“上迁”的具体表述。若,及也,或也。如此,则制书的应用场合甚明,主要是用于九卿和郡国守相的任免,赦令、赎令是特例。卜宪群则指出,制书还包含着对各种争议、议论的最高裁决之意。
。本人的理解是,刺史、太守和诸侯国相进行劾奏的文书本身并不是制书,而只有对这种文书进行的批复(即所谓申下)才能成为制书。而“土迁”一语殊不可解,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本人疑其为“上迁”,即指刺史、太守和相的升迁。下文“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官”,就是对刺史、太守、相“上迁”的具体表述。若,及也,或也。如此,则制书的应用场合甚明,主要是用于九卿和郡国守相的任免,赦令、赎令是特例。卜宪群则指出,制书还包含着对各种争议、议论的最高裁决之意。
卜宪群前引文中认为,制书的下达并非如《汉制度》《独断》所云“制诏三公”,实际上制度的下达对象包括三公、皇太子、将军、太守、诸侯王等各类人物。制书的内容也不限于“制度之命”,一般非制度性的告白也常用制书下达。这里既有对“制诏三公”一语的误解,也有对“制度之命”的误解。“制诏三公”并非下达给三公,而是文书的用语,是汉代的制书经三公下颁的一种程式。“制度之命”也不是指制定典章制度。汪桂海认为制书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下给三公,令三公向全国颁布赦令和赎令;二是任免九卿或京师近臣
 。恐不确。不确之处有三:一是对“制诏三公”作为文书用语的误读;二是制书不仅用于任免九卿或京师近臣,还应包括郡国守相,如其在后文中所举诸例;三是制书的内容不是向全国颁布赦令和赎令,至于赦令和赎令,是制书应用的特例,对于印封和颁下都有特殊的规定。
。恐不确。不确之处有三:一是对“制诏三公”作为文书用语的误读;二是制书不仅用于任免九卿或京师近臣,还应包括郡国守相,如其在后文中所举诸例;三是制书的内容不是向全国颁布赦令和赎令,至于赦令和赎令,是制书应用的特例,对于印封和颁下都有特殊的规定。
《独断》对于诏书的概括,后人可能存在严重的误读。如诏书的第二种形态,一般理解为: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
 。从《独断》对制敕文书的记载看,蔡邕是根据文书的用语进行划分的。策书、制书、诏书、戒敕的划分非常明确,不至于在讨论诏书的时候又说“下有司曰制”。制书和诏书在这里有着明显的区分。因为诏书有两种形态,是对奏事文书的批复,为了更好地理解诏书的文书特征,有必要与汉代的奏事文书进行对照分析。《独断》将群臣向君主陈事的上行文书分为章、奏、表、议四种:
。从《独断》对制敕文书的记载看,蔡邕是根据文书的用语进行划分的。策书、制书、诏书、戒敕的划分非常明确,不至于在讨论诏书的时候又说“下有司曰制”。制书和诏书在这里有着明显的区分。因为诏书有两种形态,是对奏事文书的批复,为了更好地理解诏书的文书特征,有必要与汉代的奏事文书进行对照分析。《独断》将群臣向君主陈事的上行文书分为章、奏、表、议四种: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
 但[《唐六典》“但”作“上”]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唐六典》“者”作“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
但[《唐六典》“但”作“上”]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唐六典》“者”作“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
 也。
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
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章口(当作曰)报“闻”,公卿使谒者,将大夫以下至吏民,尚书左丞奏闻,报“可”。表文报“已奏如书”
 。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帛[帛,《唐六典》作皂]囊盛。
。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帛[帛,《唐六典》作皂]囊盛。
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赣议异”。其非驳议,不言议异。其合于上意者,文报曰“某官某甲议可”。
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王莽盗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顿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以上关于陈事文书的表述,是按照文书的用语、应用的场合和通奏的途径进行分类的,尤其是文书的用语被特别强调。章称“稽首上书”,用于谢恩陈事,是由陈事者诣阙交由公车通送的。奏则上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应用的场合是有所陈请,以及举劾官员的不法行为,通奏的途径则根据上奏者的身份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是公府上奏,则送御史台,如果是公卿校尉上奏,则送谒者台。表则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通奏的途径是诣尚书通者也。这里的问题是,表的应用场合没有交代,而表恰恰是当时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奏事文书。
其中“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一段,涉及文书的署名、批复用语及封盛问题,乃针对章、奏、表综括而言,而非专指表。不过,批复用语是分别说的。按照《唐六典》所引用的《独断》,报章曰“闻”,报奏曰“可”,其表文尚书报云“已奏如书”。尽管整个两汉时期的陈事文书形态有着不断的变化,但在《独断》里,蔡邕是将章、奏、表三种陈事文书明确区分的,对章的批复用语是“闻”,对奏的批复用语是“可”,表则由负责呈递的尚书进行批复,用语为“已奏如书”。
从奏事文书的批复用语看,用于谢恩陈事的“章”,批复用语是“闻”,其实是不需要批复的,皇帝知道了便可以。而有所陈请以及举劾官员不法行为的“奏”,是需要皇帝批复处理意见的,批复用语为“可”。这正好与诏书的第二种形态相合,即“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广泛应用的奏事文书“表”,由尚书报云“已奏如书”,与诏书的第三种形态相合,即“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曰’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
按:大庭脩对制诏文书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偏差,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未将制诏文书与奏事文书结合起来进行对比。他论述汉代制诏的形态,主要是通过分析制诏的下达程序,分为三类。第一种形式是皇帝凭自己的意志下达命令,其中有关国家大事的宣言占重要的部分,对应的是《独断》中的“诏书者,诏诰也”一语
 。第二种形式是官僚在被委任的权限内为执行自己的职务而提议和献策,皇帝加以认可,作为皇帝的命令而发布。对应的是《独断》诏书条所载“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亦曰诏书”
。第二种形式是官僚在被委任的权限内为执行自己的职务而提议和献策,皇帝加以认可,作为皇帝的命令而发布。对应的是《独断》诏书条所载“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亦曰诏书”
 。第三种形式即指皇帝根据自己的意志下达命令,其对象仅限于一部分特定的官僚,而且需要这些官僚进行答申。或者说是皇帝向一部分官僚指示政策的大纲或自己的意向,委托他们进行详细的立法时使用的,它由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复合而成
。第三种形式即指皇帝根据自己的意志下达命令,其对象仅限于一部分特定的官僚,而且需要这些官僚进行答申。或者说是皇帝向一部分官僚指示政策的大纲或自己的意向,委托他们进行详细的立法时使用的,它由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复合而成
 。这种形式,它并没有与《独断》的记载相对应,事实上也无法对应。大庭脩的论述中只是概括地说“制诏”的形态,虽然没有明确说是制书还是诏书,但显然主要是针对诏书而言的。而卜宪群认为制书和诏书并无严格区分,所以在引用大庭脩的论述时作“日本学者大庭脩考证汉代制书下达有三种形式”
。这种形式,它并没有与《独断》的记载相对应,事实上也无法对应。大庭脩的论述中只是概括地说“制诏”的形态,虽然没有明确说是制书还是诏书,但显然主要是针对诏书而言的。而卜宪群认为制书和诏书并无严格区分,所以在引用大庭脩的论述时作“日本学者大庭脩考证汉代制书下达有三种形式”
 ,是误解之上的又一重误解。
,是误解之上的又一重误解。
综上所述,蔡邕记载的公文形态已经是一套相当发达的文书系统,不同政务文书的申奏与批复,各有固定的书写程式。不过,由于现有记载的简略和出土材料的缺乏,还很难对其应用范围进行严格的区分,尽管有学者(如汪桂海等)在这方面开始努力。其中还透露出京师官、公府、公卿校尉、将大夫以下至吏民等不同的上书者身份,但是否因奏事者身份不同而使用不同的陈事文书,这一点还不是很明确。
蔡邕的记载即使在公文书的名称上可以涵盖整个汉朝,如《文心雕龙·诏策》所说这几种皇帝命令文书是“汉初定仪则”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文书的具体形态上,它一定不包括西汉初年的情形。因为,西汉初年的制度,章奏文书的用语都不会是“稽首上书”或“稽首以闻”,而称“昧死”。既然“稽首”是王莽以后的用法,则《独断》所说只能是新莽和东汉时期的制度。又“群臣有所奏请”的陈事文书本身,在西汉并不出现“尚书令奏”之字,也不可能由尚书令直接下某官。尤其是“表”,据《唐六典》所引《独断》,其表文尚书报云“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是由尚书直接批复上表者的。此外,“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制书由尚书令印封下达外朝的程式,也说明尚书令已经掌握了很大的政务裁决权。从下文的论证和引用的实物史料看,文书上有“尚书令奏”之字以及其表文尚书报云“已奏如书”的情形,出现在尚书台实际上成为内廷辅政机构和决策机构的制度背景下。而所谓“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仲长统说是从东汉初年光武帝时形成的
 。实际上,仲长统所说的局面,是尚书台成为宫中的辅政机构,但没有取代三公府成为执掌朝政的宰相机构
。实际上,仲长统所说的局面,是尚书台成为宫中的辅政机构,但没有取代三公府成为执掌朝政的宰相机构
 。而尚书台从纯粹的呈递上下文书的机构,转变为按照任务的性质分工、参与谋议和谏诤、直接将奏事文书下达给有关官员的机要之司,则是东汉中后期的事情了
。而尚书台从纯粹的呈递上下文书的机构,转变为按照任务的性质分工、参与谋议和谏诤、直接将奏事文书下达给有关官员的机要之司,则是东汉中后期的事情了
 。
。
显然,蔡邕并未将整个汉朝的公文形态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所记主要应为其所处时代的制度。我们用它来概括整个汉朝的文书制度,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导致对一些基本文献和实物史料的误读。
在西汉,丞相、御史大夫和列卿等公卿大臣可以直接上书于皇帝。在公文程式上,“臣昧死以闻”或“臣昧死请”之后,紧接着就是皇帝对这些文书进行批答用的“制曰可”
 ,中间并没有其他的环节。在这种公文形态中,公卿大臣作为皇帝私人助手身份的色彩很重。
,中间并没有其他的环节。在这种公文形态中,公卿大臣作为皇帝私人助手身份的色彩很重。
从何时开始,形成了《独断》所说的那种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呢?文书形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就是汉朝政治体制的变迁历程。此种文书形态的背后,体现的是尚书成为皇帝批办政务文书的私人助手,而作为帝国官僚主体的公卿大臣与皇帝之间多了一道隔阂,皇帝的内朝系统在逐渐扩张。这是专制皇权在制度上发展起来的体现。
西汉前期也有尚书之官在文书传递过程中起作用的记载
 ,还有一些相关的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
,还有一些相关的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
 ,但我们还无法论明“尚书令奏”的用语落实到文书本身,以及尚书令将批复后的陈事文书直接下达有关九卿或郡国长官执行,而不通过丞相御史或三公这种制度出现的具体时间。其间一定有一个相对长期的日积月累的变化过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时期来稍加分析。
,但我们还无法论明“尚书令奏”的用语落实到文书本身,以及尚书令将批复后的陈事文书直接下达有关九卿或郡国长官执行,而不通过丞相御史或三公这种制度出现的具体时间。其间一定有一个相对长期的日积月累的变化过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时期来稍加分析。
第一,汉武帝时期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随着地方政务和边疆形势的变化,帝国事务大量增加,政治体制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丞相人选出身构成的变化及其职权的削弱,中朝官的作用突出,九卿的职权加强。元人朱礼在《汉唐事笺》前集“宰相”条中有一段评论:“自武帝以公孙弘为丞相,而其后儒者始相继秉轴……既任以相,乃使侍中出入禁闼,辩论数诎大臣,以侵外庭之权,九卿更进用事,而天下之务不关决于宰相。”在“三公”条中又称“武帝宠假大司马之权而不任宰相,故终汉之世大司马专秉国柄,而宰相具位,奉行文书而已”。另一方面,原有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格局被打破,中央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加强,遣使巡行之事日渐多了起来。朱礼评论说:“文帝在位最久,未尝遣使。遣使之烦,自武帝始。……故劝农种麦,则遣谒者,存问鳏寡,则遣博士。”

这两方面的变化都会引起文书制度的变化。祝总斌先生强调了随着奏事文书的增加而形成了中朝官领尚书事的制度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新增加的大量文书在运行程式上是否还遵循原有行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新增加的大量文书在运行程式上是否还遵循原有行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呢?
《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汉官仪》称“尚书四员,武帝置”
 。《汉书·成帝纪》“初置尚书员五人”条注引《汉旧仪》曰:“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
。《汉书·成帝纪》“初置尚书员五人”条注引《汉旧仪》曰:“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
 。尽管没有直接材料证明后者所指为武帝时制度,但联系前一条材料看,应是武帝置尚书四员时的分工情况。所谓“主某某事”,即负责某一方面的文书呈递工作,也就是“通章奏”。这是按照上书者的不同身份进行的分工。由于各方面文书的增加,尚书的任务繁重起来,“尚书奏事”因此具有了特定的含义。当所有臣民奏事都要经过尚书奏达之时,汉初那种文书奏行皆由御史的机制便改变了。所以,《宋书·百官志》载,“汉武帝世,使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昭帝即位,霍光领尚书事”
。尽管没有直接材料证明后者所指为武帝时制度,但联系前一条材料看,应是武帝置尚书四员时的分工情况。所谓“主某某事”,即负责某一方面的文书呈递工作,也就是“通章奏”。这是按照上书者的不同身份进行的分工。由于各方面文书的增加,尚书的任务繁重起来,“尚书奏事”因此具有了特定的含义。当所有臣民奏事都要经过尚书奏达之时,汉初那种文书奏行皆由御史的机制便改变了。所以,《宋书·百官志》载,“汉武帝世,使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昭帝即位,霍光领尚书事”
 。《晋书·职官志》则说“案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
。《晋书·职官志》则说“案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
 。这正好说明汉武帝时期尚书在奏事文书传递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汉武帝时期政治体制及文书运作机制的变化,应该是汉朝文书形态变化的一个重要背景,其相互影响的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这正好说明汉武帝时期尚书在奏事文书传递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汉武帝时期政治体制及文书运作机制的变化,应该是汉朝文书形态变化的一个重要背景,其相互影响的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第二,从西汉成帝到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变化。祝总斌先生论证了成帝时期尚书制度变化的意义主要在于分曹办事,有了固定的曹名和职掌;又指出东汉前期尚书的职掌一般还是按照上奏文书者的身份加以分工的
 ,《后汉书·百官志》记“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之说并不可信
,《后汉书·百官志》记“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之说并不可信
 。成帝时尚书有五曹,《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曰:“三公尚书二人,典三公文书”,“(常侍曹尚书)主常侍黄门御史事。世祖改曰吏曹”。这个说法与本注所记其他诸曹职掌相符,即五曹分别负责三公、常侍黄门御史、郡国、凡吏及外国夷狄所上文书。东汉初年大体应延续此种设置与分工。尚书分工负责文书接收保管的制度已经很完善,尚书令掌“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
。成帝时尚书有五曹,《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曰:“三公尚书二人,典三公文书”,“(常侍曹尚书)主常侍黄门御史事。世祖改曰吏曹”。这个说法与本注所记其他诸曹职掌相符,即五曹分别负责三公、常侍黄门御史、郡国、凡吏及外国夷狄所上文书。东汉初年大体应延续此种设置与分工。尚书分工负责文书接收保管的制度已经很完善,尚书令掌“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
 的职掌也更加明确。这是汉武帝以来尚书制度的完备化,但还没有脱离传递文书的范围。
的职掌也更加明确。这是汉武帝以来尚书制度的完备化,但还没有脱离传递文书的范围。
第三,东汉中后期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尚书的职掌逐渐转向按任务的性质进行划分。祝总斌先生已经敏锐地指出,由按上奏者身份分工到按事务性质分工的演变,是尚书权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为魏晋以后代替三公府准备着条件
 。传递文书的尚书取得对某一方面事务相关文书进行谋议参决的职权之后,这种职权一旦落实到制度上,一定要反映到文书本身,成为文书的规程;否则,就没有制度的保证。蔡邕所说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的文书规程,应该就是在这种制度变革的背景下形成的。此种形态的文书,还未见到实物史料,有些转写的史料,如记录灵帝光和四年(181)太常“奏”和批复诏书的《无极山碑》,大抵可以反映此种形态。碑文略曰:
。传递文书的尚书取得对某一方面事务相关文书进行谋议参决的职权之后,这种职权一旦落实到制度上,一定要反映到文书本身,成为文书的规程;否则,就没有制度的保证。蔡邕所说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的文书规程,应该就是在这种制度变革的背景下形成的。此种形态的文书,还未见到实物史料,有些转写的史料,如记录灵帝光和四年(181)太常“奏”和批复诏书的《无极山碑》,大抵可以反映此种形态。碑文略曰:
光和四年【缺】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顿首上尚书:谨按文书云云。请少府给珪璧,本市祠具,如癸酉、戊子诏书故事报。臣耽愚戆,顿首顿首。上尚书,制曰可。大尚承书从事,上【缺】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洛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臣耽、丞敏下常山相【缺】从事下承【缺】用者如诏书。书到言(后略)。

碑文并非照录当时公文的原文,而是记录对祭祀无极山之事进行请示和批复的经过,大致是由常山相上太常、太常上尚书、尚书奏皇帝及皇帝批示后尚书令下太常、太常下常山相的程式。按照《独断》的记载,这份太常上尚书的文书,应是用于“其中有所请”的“奏”,批复用语是“制曰可”,但文书的用语却与“上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不合。这说明实际运作中的文书形态,当比《独断》的记载要复杂,且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其中“上尚书,制曰可。大尚承书从事,上【缺】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洛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一段文字,恐是根据批复奏事文书的诏书进行的转写,“尚书令忠奏洛阳宫”的字样未必不是文书的原文,然后是“制曰可”。
需要强调的是,《独断》中关于汉代文书形态的记载,并不能涵盖整个两汉时期的文书制度,只是两汉文书形态演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尽管不同时期的具体文书形态还不是很清楚,整个汉朝文书形态的变迁轨迹也还无法完整地勾勒出来,但以《独断》有关记载和其他汉代文书的研究成果为前提,结合学界已有的对两汉政治体制变迁的论证,我们还是可以简要条缕出汉朝奏事文书形态的演变与政治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章、表、奏、议四种形态的文书,即使从文书的名称上说是适用于整个两汉时期的文书,但其应用范围、批复程序和奏递途径等,随着两汉时期政治体制的变迁,势必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同样,策书、制书、诏书、戒敕四种皇帝命令文书,其具体形态和运作机制也会随着奏事文书的变化而变化。蔡邕《独断》里记载的情形,只能是其所处时代公文书的形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