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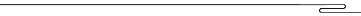
父母大人台鉴:
保定有人下车,移到窗边小桌前坐,可以铺开信纸给您们写几个字了。
华北平原真单调。今天倒是沐浴在一片春阳里。到处种着冬小麦,所以大地还透着青色;树梢也有回春之意。石家庄向西,这条路我从前没走过。比京城暖,柳梢青了。小镇里平顶尖顶的住宅相间。公路在侧,路面挺好,没什么机动车行。多了丘陵,到处修整出梯田;快到永贵大叔的老窝了。
播音器里介绍着名胜娘子关,伴奏以Sweet Home,奏得轻盈感人。娘子关一带,确实美丽,出得隧洞,即临清泉深涧。只是石家庄后,车厢里挤满了人,所以到站停靠时没下车,也看不清“关”在哪里。
这次出游,诸亲人帮忙准备,安排各地的接待,非寸草之心可称报。只盼大家都像我一样高兴就好。尤其小妹[笔者的妹妹]切忌急躁生气,伤害有身之身。
3月17日 娘子关
阳泉之后,颇为荒凉,气温也低,涧里结着冰,冰间赤色的溪水。荒丘落日,淡远迷离。
天暮,灯昏,收了纸笔。一路读了六张报,两页英文,写了两封信,小桌子成了我的办公桌,倒像比在家里还用功些。
车到太原,同座一位席姓小战士留了地址给我。跑出去看。候车室的秩序挺好,也挺干净。站外的样子像北京站,不过不那么挤。
就这样坐车,走走未到过的地方也好。
20:32 出太原
北京的日子还是太安逸了,车厢里的条件让人难以入睡。但总是休息过了。
由于时差,车过孟源天才拂晓,错过了黄河大桥。在朦胧中首先看到的是一树树桃花,开得正盛。一派渭川田家的风光了。
临潼下车后,直奔秦俑坑。天气晴和,郊行自然就愉快。在发掘大厅里,没去看“禁止翻越”的牌子,钻到一排排俑人之间。他们都和我身高仿佛,在其中转来转去,觉得在一群现代人中间似的。
路过始皇墓,一座大土丘,其上栽满桃树。看上去和电视上的一样,就没下汽车去踏勘一番。
人不停蹄,到了华清池一带。都说到了这里就应该洗洗温泉。果然,只见男女老少,马面牛头,团团围着排队,看见就先觉得脏了。要不是池里真有娇无力,断不肯趟这个浑水。九龙池一带,也都是脏水。华清池则是一个又脏又难看的浴缸,围在一座破屋里。到蒋先生住过的“五间房”,就是平平常常五间房子,里面挂了几张照片。又过了“捉蒋亭”。一路小商贩很活跃,不愁买不到东西吃。
原听说登上骊山极顶,便把八百里秦川尽收眼底,所以赶来攀登。但这时天色灰蒙蒙的,看不出五里开外,就算了吧。抬头望山顶,是周幽王的古烽火台,曾点过火逗诸侯乱跑,从此亡了国。听说已了无残迹。看来石台还不如统治者的行为模式耐得起三千年风雨的侵蚀。
骊山是座土山,长些松树、枣刺,夹杂着桃树。渭川的桃花极多,灼灼其华,可能是在纪念古代的美人。如今这一带不像出产漂亮人物的模样。前后正有几百个西安商业系统的青年男女出来春游,没见着哪个女孩子像玉环褒姒似的。
18日12:00 骊山之半
结果还是登上了山顶。海拔1279米,挺吃力。少崖岩,无何奇趣。将及山顶前一大片林子。山顶上秃秃如也,只有一根电线杆子。若非风微日暖,必很扫兴。
重新下山来,见一群人围着一盘残棋,招人赌胜。算棋,觉有必胜的把握,但自知象棋从来走得不太好,只是禁不住旁边的人激。两块钱一赌,偏又有人激我赌十块,不知当时怎么就被激得应了。走了几着就输了。人有赌胜之心,本来算不得德性上的大缺陷,不过,在自己不行的方面争强好胜终是够可笑的,争得过了头,甚至会把性情也扭曲了。欲成大事者,不可争小胜。不努力成事,偏爱在亲近的人中间争胜,那就干脆让人厌恶了。凭白丢了十块钱,闷闷下山,一面反省自己性格里争强好胜的那些因素。底下还要走几十天,把错误犯在前头总比犯在后头好一点,因为可以买个教训。
上了从太原开来的直快,非常拥挤,只好站着。登了骊山,又扛着衣物跑了6里路赶火车,腿都要折了。不过很自豪,在骊山上,小伙子都跑不过我。
西安站还像十五年前一样。一下子十五年了。
西安和北京都是历代皇朝选来建都的北方城市,所以有很多相像之处。不过,此处的人容貌胜于北京人,也许因为风水好(据说此地鲜有大风沙),也许因为文明的时间比北京更长。西安人的口音却难听,似天津又不似天津,似四川又不似四川。然而,一样的市面招贴,一样的漫天要价,一样的老年人统治,青年人不满。
三路汽车上,同一位西安师大的中文教员攀谈。他说西安是座稳健的城市,从不太好,也不太坏。说人们不大关心政治。但他本人不断打听北京的气候,对政治控制教学也大发牢骚。
下了车问路,问到的竟正好是我师妹的哥哥曹君,而且正好是外院的学生。此人举止不俗。他把我带到法语系。几个年轻人都很热情,带我找到张君,一起聊了一阵。
明早就发出此信。拜祝父母大人健康快乐。
20:10 西安外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