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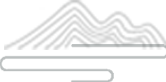
作别了魂牵梦萦的桑梓之地吉安,文天祥不像之前那么孤独了。他知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既然不能死在家乡,那死在其他任何地方也就没了区别。对死志已定的人来说,早一天晚一天死,也不用那么刻意。
日夜奔流的赣江一路喧哗北行,于永修县注入鄱阳湖。文天祥的小船也顺流而北,横渡了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后,来到庐山脚下的湖口,并由湖口进入长江。此时,故乡吉安早已远了,就连江西,也成永别。
六朝古都南京,是文天祥北行途中停留最久的地方。在那里,邓光荐因病躯沉重,被送往天庆观就医。文天祥也因几个月舟车劳顿,加上绝食而元气大伤。这样,文天祥在南京暂住了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后,邓光荐继续留在南京,而文天祥必须北上。当他们执手相看时,他们都知道这既是生离,也是死别。文天祥感叹时运不济,“水天空阔,恨东风,不惜世间英物”,而“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同样是在南京,两个囚徒还干了一桩十分风雅的事:邓光荐编定了他的诗集《东海集》,文天祥为诗集作序。
几年后,被元朝廷释放回乡的邓光荐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此人竟是元军主帅张弘范的儿子张珪。张珪一向敬慕邓光荐的才学,从此师事之。这是题外话。
农历八月底的江南,当富于情趣的江南人忙于登高把酒时,同为江南人的文天祥却不得不再次踏上路途。文天祥知道,今日一别,杏花春雨的江南,从此将恍如遥远的前世。驿站里,他留下了两首泣血之作,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日,化作啼鹃带血归。
文天祥从南京出发,经真州而上扬州。在扬州,他结束了长江上的航行,从长江转入运河北上。此后,他将次第经过高邮、宝应、淮安、邳州、徐州、鱼台、济宁、宁阳、东平、陵县、献县、河间、保定、范阳,进而到达元朝首都大都。
这一路,依赖南北大动脉大运河,文天祥大多时候以舟代步。享国一个半世纪的南宋,拥有的是半壁河山,它先后与北方的金国和蒙古(元朝)对峙,长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作边境。身为南宋人,渡过长江,尤其是进入长年征战的两淮地区后,眼前都是陌生而刺目的异国景象,“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围。隔溪胡骑过,傍草野鸡飞”。至于征雁南飞,寒蛩夜唱,这对一个敏感的囚徒来说,都是无穷无尽的黍离之悲。总之,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江南渐行渐远,如同崖山下沉入大海的故国。
与此同时,随着大都越来越近,文天祥也越加明白,逃脱的奇迹不可能再次发生。他的死志也更加坚定。因而,斯时的文天祥便有一种潜意识行为:他不断寻找精神上的知音与同道。沿途经过的地方,那些历史上涌现出的忠贞者、节烈者,不论男女尊卑,都带给文天祥一种异样的温暖。这种温暖,大抵缘于吾道不孤的欣慰。他不断写诗作文,以抒胸臆,以证大道。
微山湖之南的徐州,大运河横贯境内,自古就是交通要津。九月初九,古人遍插茱萸、登高饮酒的重阳节,风尘仆仆的文天祥解鞍少驻。在徐州,他寻访了城东的一座楼。这座楼叫燕子楼。
很多年后的今天,徐州云龙公园内,一汪湖水包围的知春岛上,也有一座燕子楼。但可以肯定地说,文天祥凭吊过的燕子楼,并非眼前这一座。因为,作为徐州历史上著名建筑的燕子楼遭逢多次毁弃,又多次重建。
最初的燕子楼建于唐朝,是镇守徐州的节度使张愔为爱妾关盼盼所建。白居易和张愔是朋友,曾与关盼盼见过面,他笔下的关盼盼:“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张愔死后,关盼盼拒绝了众多求婚者,在燕子楼上度过了寂寞孤独的后半生。
对这些典故,饱读诗书的文天祥烂熟于胸。他登上燕子楼,凭吊关盼盼。美人芳草,从来都是中国士大夫骨子里最深刻的隐喻,关盼盼为张愔守节不移,很自然地被文天祥用来象征自己对大宋朝的满腔忠贞。他在徐州写下的《燕子楼》,与其说是对关盼盼的褒扬,毋宁说他在借关盼盼之酒杯,浇自家胸中之块垒:
因何张家妾,名与山川存。
自古皆有死,忠义长不没。
但传美人心,不说美人色。
告别燕子楼九天后,文天祥抵达山东陵县,也就是今天的德州市陵城区。唐代时陵县是平原郡郡治所在地,而平原郡,又和另一个如今人所皆知的名人有关,这个人就是书法家颜真卿。关于颜真卿,很多人只知道颜体,却不知道颜真卿也是忠贞之士。安史之乱前,颜真卿被贬平原郡,及至安禄山作乱,以为他乃一介书生,并没把他放在眼里。但颜真卿坚守孤城,有效地牵制了叛军。后来,李希烈作乱,颜真卿奉旨前去切责,被叛军所害。
行经颜真卿曾坚守过的陵县,文天祥必然想起这段尘封的往事。见贤思齐,更何况,在对前贤的缅怀与纪念中,还能获得一种精神力量的加持呢。为此,文天祥写诗感叹:“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还值一提的是,与颜真卿同样忠烈的,是他的堂兄颜杲卿。他在安史之乱中被叛军俘虏后押到洛阳,面见安禄山时,他瞋目大骂,为安所杀。后来,当文天祥被关押在大都狱中,他在他最知名的作品《正气歌》里,历数天地正气,把颜杲卿与博浪沙刺秦的张良、冰雪中持节的苏武和困守孤城的张巡等人相提并论。
1279年,农历十月初一,文天祥终于被押送到了目的地:大都。文天祥是从今天的房山区进入京城的。房山区境内有一条汇入拒马河的小河,名叫琉璃河,又名大石河,古称圣水。如今的琉璃河上,还有一座古朴的大桥。文天祥的《指南后录》里,有一首诗题为《过雪桥琉璃桥》。只不过,他行经的那一座早已荡然无存。我们今天见到的,建于更晚的明代。
那是一个小雪后的早晨,残星在天,寒气逼人,文天祥骑在马上,听着村野小店传来的一声声鸡啼,一大早就上路了。当天,他们进入了自五代十国起就被少数民族占据的大都。这座气势萧森的北方重镇,脱离中原汉族王朝之手,到文天祥时代已有三百余年了。
文天祥在会同馆的一间破屋里被关押了五天后,被移送到兵马司狱中。狱卒对文天祥的态度,随着元朝君臣的想法而不断变化。但无论是“枷项缚手”,还是“供帐饮食如上宾”,都无从改变文天祥的意志。
此后四年间,也就是从四十四岁到四十七岁——文天祥的最后岁月,都是在狱中度过的。接连不断的劝降几乎是家常便饭:从在京的南宋君臣到元朝高官,走马灯似的充当说客。这中间,值得一说的有两次。
其一是此前降元的宋恭宗。宋恭宗来到牢房,还没开口说话,文天祥已经口称陛下哭拜于地,宋恭宗只得尴尬地打道回府。文天祥就义六年后,宋恭宗被打发到西藏学习佛法。此后几十年里,他竟成为一代佛学大师,出任萨迦寺总管。但五十三岁那年,因一首怀念故国的小诗被元朝廷斩首。
其二是平章政事阿合马。平章政事相当于副丞相,是从一品的高官。此人把文天祥招到馆驿中,倨傲上坐;哪知文天祥见到他,“长揖就坐”。然后,两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阿合马:你知道我是谁吗?
文天祥:听人说是宰相来了。
阿合马:既然知道我是宰相,为什么不下跪?
文天祥: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为什么要跪?
阿合马:你为什么到了这里?
文天祥:南朝如果早日起用我为宰相,北朝军队没法打到南方,我这个南朝宰相也不可能到北方。
阿合马回顾左右说:此人生死由我定。
文天祥:亡国之人,要杀便杀,说什么由你不由你。
一番针锋相对后,原本趾高气扬的阿合马只得默然离去。
元朝廷迟迟没杀文天祥,一方面是包括忽必烈在内的元朝君臣,都对文天祥的忠贞抱有程度不一的敬意;另一方面,灭宋的元军统帅张弘范,多次向忽必烈上书,请求善待文天祥。1280年,张弘范以四十三岁的壮年去世,病危之际,犹自关心被押在土牢中的文天祥,并最后一次向忽必烈建议:文天祥忠贞不贰,千万别杀。
世事就是这样难以捉摸:对文天祥来说,张弘范本是他和他的祖国的仇雠,没想到却成了最懂他也最珍惜他的知音。或许,肝胆相照的朋友尚不难得,难的是作为敌人却赤诚以待。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天祥虽然被元朝廷处决,但真正促使元朝廷这样做的,不是元朝君臣,而是文天祥曾经的同僚。从这一角度上说,文天祥不是死于敌人,而是死于同胞。
向元朝廷投降的南宋君臣中,有一个人叫留梦炎。1244年,文天祥九岁时,比他长十七岁的留梦炎金榜题名,高中状元。
状元出身意味着前途无量,留梦炎迅速做到了位极人臣的丞相兼枢密使,相当于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军队统帅。但是,元军南下时,他选择了投降。
文天祥在狱中的最后一年,由于长期关押,屁股上长了一个恶疮,“平生痛苦,未尝有此”。他的几个前同事王积翁等人联名向忽必烈上奏,请求释放文天祥,把他安排到道观做道士。文天祥也表示同意接受这种安排。
忽必烈还在犹豫之际,留梦炎却坚决反对,他说:“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表面看,他怕文天祥以做道士为借口出逃,以后再次兴兵抗元,那样,他和王积翁等人就会受牵连;其实,他更深层的想法在于,文天祥的孤忠耿耿,更加反衬了他的望风而降。有文天祥的名垂千古,也就有他的遗臭万年。因而,这个状元容不得那个状元,这个前丞相容不得那个前丞相。
1282年十二月初八,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他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但是,面对他开出的只要文天祥投降,就任命其为中书宰相或枢密使的条件,文天祥断然拒绝。末了,忽必烈无奈地问:汝何所愿?文天祥对曰:愿与一死,足矣!
次日,文天祥在大都城南柴市引颈就戮。刑前,他面南而拜,大声说:“臣报国至此矣!”
对文天祥之死,元朝人感叹说:“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降,而亡于潮阳之执;不亡于崖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
文天祥求仁得仁,死而无憾。其时,距南宋的灭亡四年有奇。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崖山口外那十万溺水的亡魂,已随着故国的烟消云散而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