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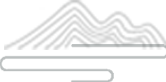
方拱乾这位曾经荣华富贵的老官员,吃惊地发现作为省级行政中心的宁古塔新城竟然还不如南方的一座小镇。一望无垠的荒原上,出现了一座“无疆界,无城郭”的“省城”:这座城枕河而居,一些短木头插在土里为墙,周长约三里,开了四道城门,城门用碎石砌成,高丈余。城里修筑了几间茅草屋,那就是政府机关了。这样的城门和房屋,遇上大雨就会倒塌,倒塌了就不得不重修。很快,方拱乾就对这里酷寒的气候有了切身感受:“四时皆如冬。七月露,露冷而白,如米汁。流露之数日即霜,霜则百卉皆萎。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即冻,至来年三月方释。五六月如中华二三月。”
多年以后,在宁古塔出生并长大的吴兆骞的儿子吴桭臣在回忆录中,也对宁古塔的极端天气记忆犹新:“其地寒苦。自春初至三月终,日夜大风,如雷鸣电激,尘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鹅飞下,便不能复飞起。不数日即有浓霜。八月中,即下大雪。九月中,河尽冻。十月地裂盈尺,雪才到地,即成坚冰,虽白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袭裘,久居即重裘可御寒矣。至三月终,冻始解,草木尚未萌芽。”
今天的海林和宁安一带,虽然冬天依然漫长,但并不像吴桭臣所说的那样极寒多风,这并非吴桭臣夸大其词,而是三百多年前的地球,正好处于远比今天更寒冷的小冰河时期。
对大多数不幸的流人来说,到达流放地,不仅不是苦难的结束,反而是更大苦难的开端。不能生还故乡、埋骨桑梓的不祥命运当然令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深怀恐惧,贫乏的物质供应与谋生的艰难也令这些来自鱼米之乡的南方人不堪其苦;但与完全丧失自由和随时可能死于非命相比,这些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烦恼。
按清朝惯例,流刑其实是一种统称,其下还有诸种区别。最轻的叫迁徙,最重的叫发遣,流放到宁古塔的,几乎都是发遣。被发遣到宁古塔的犯人,去向有二,一是为奴,就是影视里常见的所谓“与披甲人为奴”,披甲人,即守边将士;二是当差。
为奴的命运最为悲惨。一旦为奴,就意味着已经没有丝毫人身自由,这些奴隶的命并不比一匹马一头牛更重要。如果奴主愿意,他们可以将奴隶处死而不须负任何法律责任。那些带着如花美眷一同流放的流人,命运尤其悲惨:奴主为了占有他们的女眷,往往将碍手碍脚的男性杀死。此外,一旦为奴,终生不许赎身,子子孙孙都充当奴主的会说话的工具。这种毫无人性的法律,激起了不少流人绝望的反抗,他们有的逃往深山,有的杀死奴主。但抓获后,他们将被凌迟处死。
与为奴相比,当差相对好得多。当差又分两种。一种是常犯,也就是普通犯人,他们被安排到官庄劳动。清初,政府在宁古塔辽阔的土地上设立了众多官庄,官庄有庄稼要种,有牲畜要牧,需要大量人手,流人正是廉价劳动力。这些官庄每庄十人,一人为庄头,九人为壮丁,“非种田即随打围烧炭”。每个人一年上交粮食十二石,草料三百束,猪肉一百斤,木炭一百斤,石灰三百斤,芦苇一百束。流人们在官庄里起五更睡半夜地终日劳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凡家中所有,悉为官物”,他们仅仅得到一口苟延残喘的粗劣饮食。方拱乾多次看到,冬天里,舂了一夜米的年轻女子,赤脚单衣地到井边挑水,路滑担重,不堪其苦,而这些女子,“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另一种是官犯,也就是曾经做过官或是获得过功名的读书人,他们被安排到驿站、矿山或衙门服各种杂役,这已经是绝大多数流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高规格待遇了。不过,他们仍然是犯人,仍然是戴罪之身,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必须到衙门例行报告,以表示他们一直在朝廷指定的流放地认真改造,绝没有乱说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