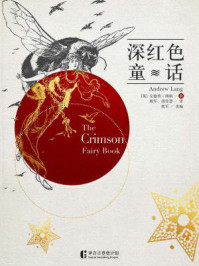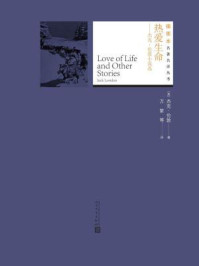我睡醒了才明白,我请两天假时,老板为什么显得不高兴:今天是星期六。当时我却把这茬给忘了,起床才想起来。我的老板自然而然会想到,好嘛,加上星期天,也就有了四天假期。这不可能让他开心的。不过,一方面,妈妈昨天去世,今天下葬,这也不能怪我。而另一方面,不管怎样,星期六和星期天我总归休息。理儿当然是这个理儿,这并不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反应。
昨日累了一整天,起床感到很吃力。我刮脸的时候,心里还琢磨干点儿什么好,最后决定洗海水浴。我上了有轨电车,前往港口海水浴场。到了地方,我便一头扎进泳道里。有许多年轻人来游泳。我在水里碰见玛丽·卡多纳,我办公室从前的打字员,当时她对我还挺有意。现在想来,我也同样。但是,她没干多久就走了,我们也就来不及发展关系。我帮她爬上了一个浮标,趁扶她的时候,摸了一把她的乳房。我还在水里,她已经趴在浮标上了。她朝我转过身来,头发遮住了眼睛,咯咯笑个不停。我也爬上浮标,躺在她身边。天气晴好,我权当开玩笑似的,脑袋往后一仰,就枕在她的肚子上了。她什么也没有说,我也就这样安心躺着。满眼无际的天空,蔚蓝而金光灿烂。我感到玛丽的肚子在我的脖颈儿下面微微跳动。我们半睡半醒,在浮标上待了许久。等太阳烤得太厉害时,她就扎进水里,我紧随其后。我追上去,搂住她的腰,我们便相携共游。她还是一个劲儿地笑。上了码头,我们擦干身子时,玛丽对我说:“我晒得比你黑。”我问她晚上愿不愿意去看电影。她又笑了,对我说她想去看一部费尔南德尔主演的片子。等我们穿好衣服,她看到我扎黑领带,非常惊讶,就问我是否戴孝呢。我对她说妈妈死了。她又想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回答说:“昨天的事儿。”她略微后撤,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我倒是很想对她说,这不能怪我,但是欲言又止,突然想到这话我已经对老板讲过了。这样说毫无意义。归根结底,人总难免有点错。
到了晚上,玛丽已经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影片不时有滑稽可笑的场面,但实在很荒唐。她的腿偎着我的腿。我抚摸着她的乳房。电影快演完时,我亲吻了她,但是很不得劲儿。从电影院出来,我们一起到了我家。我一觉醒来,玛丽已经走了。她早就有话在先,要去她姨妈家。我想到正逢星期天,心里就烦得慌:我不爱过星期天。于是,我在床上翻了个身,在枕头上细闻玛丽的头发留下的咸味,一直睡到十点钟。接着,我就吸烟,在床上一直躺到中午。我不愿意像平时那样,去塞莱斯特饭馆用餐,因为那里的熟人肯定要问这问那,我可不喜欢对付那种局面。我自己煮了几个鸡蛋,直接在托盘上吃了,没吃面包。家里没有了,我又不想下楼去买。
吃完了饭,我有点儿烦闷,就在房间里游荡。妈妈在这儿的时候,这套房子挺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显得太大了,只好把餐厅里的桌子移到卧室里。我只在这间屋子里生活,家具只有几把有点塌陷的草垫椅子、一个镜子发黄的大衣柜、一张梳妆台和一张铜床。余下的房间都废弃不用了。过了一会儿,为了找点儿营生,我就拿起一份旧报读起来。克鲁申盐业公司发了一则广告,我就当作有趣的剪报,剪下来集中贴在一个旧笔记本上。我洗了洗手,最后来到阳台。
我的房间正对着城郊的主要大街。下午天气晴朗。不过,铺石路面腻滑,行人寥寥,而且脚步匆匆。我先是看到上街散步的一家人:两个穿着水手衫的小男孩,短裤长过膝盖,全身笔挺,举止有点儿拘板了;还有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粉红色大蝴蝶结,脚下穿一双锃亮的黑皮鞋;母亲跟在孩子的后面,她躯体肥大,穿着栗色丝绸连衣裙;而父亲身材矮小,又相当瘦弱,看着眼熟。他头戴扁平窄檐草帽,领口扎着蝴蝶结,拿着手杖。看着他同妻子一起散步,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个街区有人说他很有风度。过了半晌,城郊青年陆续走过。他们油头粉面,打着大红领带,上衣紧箍身子,绣了花,脚穿方头大皮鞋。估计他们是去市中心,因此他们早早动身,嘻嘻哈哈笑着,急忙赶有轨电车。
年轻人过去之后,街上行人就眼见稀少了。想必各种演出都已经开始。街面上只剩下店铺老板和猫了。天空无云,但是阳光透过街道两边的榕树,并不那么强烈。街对面一家烟铺老板搬出一把椅子,放在店门前的人行道上,跨坐在上面,两条手臂撑着椅背。刚才有轨电车还人满为患,现在几乎空驶了。挨着烟铺的小咖啡馆“皮埃罗之家”,小伙计正用锯末子擦拭空荡荡的餐厅。好一派星期天的景象。
我调转椅子,像烟铺老板那样骑上,觉得那种坐姿更舒服些。我抽了两支香烟,又进屋拿了一块巧克力,回到窗口吃起来。不久,天空阴沉了,恐怕要来一场夏季暴雨,然而又渐渐放晴了。不过,乌云飘过时,街道更加昏暗,仿佛预示下雨一般。我久久观望风云变幻。
到了五点钟,几辆电车降降驶来,从郊区体育场拉回来大批观众:他们有的站在踏板上,有的扶着栏杆。随后驶来的几辆电车,则运回运动员,从他们的小手提箱我就能看出他们的身份。他们大吼大叫,扯着嗓子唱歌,祝愿他们的俱乐部长盛不衰。好几名运动员向我招手,其中一个甚至冲我嚷了一声:“战胜他们啦!”我应声道:“对。”同时点了点头。从这时候起,小汽车蜂拥驶来。
天色又略微向晚。房顶上的天空转为淡红色,随着渐近黄昏,街道也热闹起来。那些散步者又渐渐回来了。我从人群中认出了那位有风度的先生。孩子们有的哭哭咧咧,有的让大人拖着。本街区的几家电影院,也随即往街上倾泻观众的洪流。观众中间的青年人,比比画画的动作比平时更为坚决,想必他们是看了一部惊险片。从城里电影院回来的人,稍晚一点儿才到达。他们的神态似乎更加凝重。他们还是说笑,但不时显得倦怠,若有所思。他们滞留在街上,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来回踱步。这个街区的姑娘都不戴帽子,彼此挽着手臂。小伙子们故意迎面走去,同她们交错而过,抛出打趣的话,她们就扭过头去咯咯笑。好几位姑娘我都认得,她们跟我打招呼。
这工夫,路灯一下子全亮了。初跃夜空的星星因而黯然失色。总盯着灯光强烈的人行道上的人流,我感到眼睛很累。灯光映得潮湿路面明晃晃的,而间隔时间均匀地驶过的电车,车灯映现出油亮的头发、一张笑脸,或者一只银手镯。过了不久,电车逐渐稀少了,在树木和路灯的上方,夜色弥漫,已经漆黑一片了,不知不觉中,已经人去街空了,直到出现一只慢慢腾腾地穿过空旷街道的猫。于是我想到该吃晚饭了。我俯在椅背上坐了太久,脖子有点儿酸痛。我下楼去,买了面包和果酱,自己做了点儿菜,就站着吃饭了。我想要到窗口抽支香烟,但是夜晚凉了,我感觉有点儿冷。我关上了所有窗户,返身回来,在衣镜里瞧见桌子的一角,桌上并排放着酒精灯和几片面包。我不免想道:又过了一个绷得很紧的星期天,妈妈现已入土为安,我又要去上班,总而言之,生活毫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