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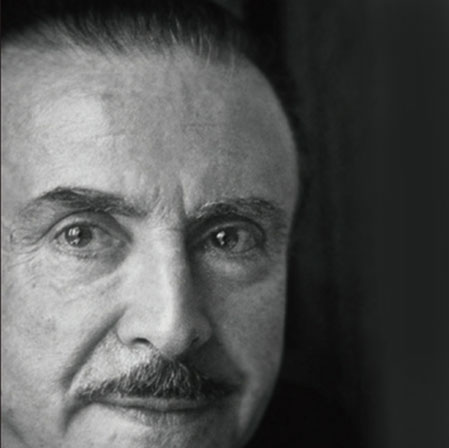


1978年,在伦敦开完演奏会后,阿劳为Vocalion唱片公司录制了一些78转的唱片。我们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终于能听到他的唱片了,这是一个在他刚满18岁时就注定要被写进历史的人;另一方面,之前我也提到过,因为从唱片中我们就可以明确地推断出当时马丁·克劳斯的教诲还是深深地影响着阿劳。比如阿劳演奏的肖邦的《华尔兹》Op.34 no.3,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乐曲以华丽的华尔兹开场,节奏比我们想象中要舒缓一些。但惊喜在第二个章节(第49小节),这时节奏更为缓慢,显得如此婉转曲折、含情脉脉,并伴随着散板,音域极广,让我想起来其实前一辈,出生在1880年左右的钢琴家,如巴克豪斯、安东·鲁宾斯坦、柯查斯基,或者是更老一辈的像戈多夫斯基、霍夫曼,他们都没有弹出过音域如此宽广的散板。从第81小节开始的插曲再次让我们惊喜,阿劳把它演绎得非常生动活泼。这些都是受过马丁·克劳斯的指导的么?可能是。这样的演奏是否有点和时代流行不合?绝对是。但是阿劳的曲风无可挑剔,足够消除我们所有的质疑,因为事实就是他将这个曲子完美地呈现了出来。
如果这是一支更复杂的曲子,如果我把自己变成舒曼,我的心情可能也会和舒曼一样,那时舒曼在拜读了肖邦在17岁创作的《变奏曲》Op.2,对肖邦说:“先生,请允许我脱帽向您致意,您是一个天才。”不过我应该不会对阿劳说这句话,最多可能会耳语一番。但是,当时这个18岁充满着激情的男孩却陷入深深的精神危机中。同样的曲子,从1928年录制的版本中,我们听得出亚伯拉罕森医生的治疗给阿劳的演奏产生了一些影响,促使他对肖邦作品的曲风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21年录制的版本时长3分02秒,1928年的版本长2分14秒:48秒的时差,差不多已经占到整首曲子的近四分之一,这告诉我们相较于第一个版本,第二个版本更集中和紧凑,而且风格也不尽相同,大量减少了散板的运用。所以说阿劳演奏的第二种手法就是2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1979年阿劳录制的版本,运用了第三种手法,从风格上大体说来,不违背第二种手法的特点风格,但是节奏不会那么紧凑了,这个版本时长2分47秒。
1921年录制的唱片中,阿劳演奏了舒伯特的《乐兴之时》no.3,但没有肖邦的《华尔兹》那么完美。1921年的版本时长2分34秒,1956年阿劳也录制了另一个版本时长1分59秒,1990年的版本是2分03秒,这样比较起来,1921年的2分34秒的版本,确实显得过长,更不用提施那贝尔的版本是1分48秒;巴克豪斯的是1分42秒;费舍尔的是1分40秒。1921年,阿劳对音乐的态度是仔细研读作品,保证完整地呈现原作的每一个细节。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手法来表现出他对音乐的理解是深刻的,他的诠释是完满的。不过他把所有的细节放到了同一个层次,未能突出其中的重点,也就是说阿劳运用了一种最唯物、最实际的手法来表现他的音乐,他从原作中能感悟出多少,他就要表现多少。如果用这种手法去诠释大型作品的话,比如奏鸣曲、变奏组曲,可以想象在乐评家的眼里,阿劳就像是一个企图到处讲学说道,思想陈腐的百岁老翁。对此,这里不再赘言。这样,最后剩下的就是阿劳的第一种手法,其实就是他卓越的才华和他对音乐的热情,这在他后来的作品演奏中完全地表现出来,但有时会显得缺乏了一种综合概括音乐的能力。
听阿劳1927—1929年间录制的唱片,我们首先能够感受到的是,无论在风格上还是感情上,阿劳的演绎都有了明显的不同。第二个可以感觉到的是他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1927年,阿劳在赫尔辛基完整地演奏了李斯特的《帕格尼尼练习曲》,但是在给环球唱片录制的时候,他没有录制no.3和no.4,就是《钟》这一章。其实我为阿劳没有录制《钟》这一章感到挺遗憾,因为一战前,这首曲目就是唱片里最重要的曲目之一。如果当时环球能让阿劳录制这一首《钟》,我们就可以展开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比较工作,比如可以把阿劳的版本和帕德雷夫斯基的、霍夫曼的和巴克豪斯的版本作一个比较。不过阿劳的这4首练习曲已经足够让我们把这个音乐家的特点和风格渐渐勾勒出来了。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第二首,因为这首,我们还有霍洛维茨在1930年录制的版本。
霍洛维茨选择的是布索尼的改编版,删掉了一些重复的乐段,修改了管弦乐器部分的一些细节,使演奏更流畅。阿劳采用的是原版。霍洛维茨当时以他的力量、速度和八度音,让练习曲中间部分的节奏几近癫狂,完全震住了当时在场的观众;即使用的是布索尼的版本,霍洛维茨在演奏过程中还是有不少音符弹错,但是却让整首曲子更加澎湃激昂。而阿劳演绎这首曲子时,节奏要合理了许多,从头到尾非常平稳,也没有什么失误,但是无疑这样的风格不能激起观众的热情和尖叫,他们还是偏爱霍洛维茨激情的演奏。在本套书籍的第二册,安东·鲁宾斯坦的自传中,这样写道:鲁宾斯坦在巴黎听了霍洛维茨演奏的《帕格尼尼练习曲》的第二首和第五首,他当时这样评价:“那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天才和智慧,那是一种油然而生的优雅,实在是难以言喻。”
 鲁宾斯坦作出这样的评价,我觉得很奇怪,是否有些过于主观了,因为要谈“油然而生”的优雅,我认为阿劳比霍洛维茨更有资格。阿劳对他的演奏一直都是胸有成竹的,他的诠释也一直都是诚恳的,但是《练习曲》的第一个部分,阿劳可能在技巧运用上有些夸张,使得他的优雅变得太华丽时髦,最终曲子听起来太活泼,但有一丝笑里藏刀的意味。而霍洛维茨更重视曲子带给人的激动和兴奋的感觉,他渴求达到一种像魔鬼一样疯狂的音乐节奏。如果假设这支练习曲分别让李斯特和舒曼来演奏的话,那么霍洛维茨的版本更像是李斯特演绎的,而阿劳的像是舒曼演绎的。可是,阿劳曾经不是李斯特学生的学生吗?可能有些事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如果说到师徒的影响,那阿劳的老师马丁·克劳斯可能受到的影响更多是来自于舒曼的学生卡尔·雷内克(Carl Reinecke),而并非来自李斯特,谁知道呢……
鲁宾斯坦作出这样的评价,我觉得很奇怪,是否有些过于主观了,因为要谈“油然而生”的优雅,我认为阿劳比霍洛维茨更有资格。阿劳对他的演奏一直都是胸有成竹的,他的诠释也一直都是诚恳的,但是《练习曲》的第一个部分,阿劳可能在技巧运用上有些夸张,使得他的优雅变得太华丽时髦,最终曲子听起来太活泼,但有一丝笑里藏刀的意味。而霍洛维茨更重视曲子带给人的激动和兴奋的感觉,他渴求达到一种像魔鬼一样疯狂的音乐节奏。如果假设这支练习曲分别让李斯特和舒曼来演奏的话,那么霍洛维茨的版本更像是李斯特演绎的,而阿劳的像是舒曼演绎的。可是,阿劳曾经不是李斯特学生的学生吗?可能有些事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如果说到师徒的影响,那阿劳的老师马丁·克劳斯可能受到的影响更多是来自于舒曼的学生卡尔·雷内克(Carl Reinecke),而并非来自李斯特,谁知道呢……
练习曲的第二首和第五首一样,霍洛维茨在1930年也录制过,比较的结果告诉我们阿劳可以做到完美无误,而霍洛维茨不行。这里我想起罗伯特·勃朗宁在向安德烈谈起拉斐尔的一幅画时,谈到里面的人物手臂位置是错误时,他说:少即是多。阿劳非常诚恳地和我们谈起了霍洛维茨:在柏林听了他的演奏会后,我被他的才华所倾倒,他的手法非常高超,之前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我记得当时我坐在贝多芬音乐厅的第一排,可以看到霍洛维茨演奏时,手臂非常有力,这也震动了我。我永远记得他演奏的肖邦《葬礼进行曲》的第一部分,还有第二个部分!我妈妈当时已经完全沉浸在其中了,她之前没有欣赏过任何人,但是那天晚上,她完全陶醉了。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她对我说:“你最好坐到钢琴前好好练习,因为他比你弹得好。”阿劳在向约瑟夫·霍洛维茨讲完这句话后,便笑了起来。他当时说得挺有道理。如果说霍洛维茨是一个短跑选手,那阿劳可能是一个马拉松选手,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最后也光荣地到达了终点。
1927—1929年录制的作品中,需要说一下的是肖邦的五首《练习曲》(Op.10 no.3、4和9,Op.25 no.1和2),这个作品完美地体现了新古典主义风格,在风格上和巴克豪斯于1928年录制的那个版本非常相近。1956年,阿劳将肖邦《练习曲》又录制了一遍,和1928年的版本相比,节奏显得稍微舒展了一些,但是风格、思想都没有变化,算是没有太多的创新。不像20世纪50年代末,他录制的《前奏曲》和《奏鸣曲》Op.58获得了很大成功。还有《艾斯特庄园水之嬉戏》也具有巨大的音乐价值,这促使我们想到,阿劳的导师马丁·克劳斯在1883年接触了修道院,并在生命最后三年经常前往,想必克劳斯尤为精通李斯特晚期的作品。但是另一首作品《轻快》却表现得不是那么有力,原因来自阿劳本身,因为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个特点一直到40年代末都有,在下面一段我们会谈到。
1927—1929年阿劳录制的版本,品质非常高,美妙无比、光彩炫目、闪闪发光,但是其他的版本常常会显得晦涩深奥,那时老的乐评家评论说:“有点太灰暗了。”从《轻快》的第3-8小节以及五个降记号的调号中,听众很容易听出曲子要表达的情感:音色不是一直都是洪亮的,只有快接近最后才爆发出来。如果把从第11小节开始的那一拍和第21小节开始有八度音的那一拍做个比较的话,可以听出阿劳那时就像一个歌手,一个可以飙很漂亮高音的歌手,但是发挥不稳定,高音不均匀。这个特点不是每次都那么明显,比如在肖邦的《练习曲》里,就缓和许多。如果这个特点表现出来的话,会弹奏出美妙得令人难忘的作品(比如刚提到过的《艾斯特庄园水之嬉戏》《在喷泉旁》《听!听!云雀!》《帕格尼尼练习曲》第十个变奏曲,即所有以《钟》为基础的片段,或者相反的以低沉的隆隆音为基础,像布索尼的《夜曲》),也会弹奏出晦涩得令人困惑的作品,正如《轻快》。当音调已经拉得非常紧、非常高的时候,这种音色的不均匀是没有办法缓和和纠正过来的,比如在《伊斯拉美》中,技术非常高超,演奏技巧出神入化,时时迸出激烈的火花,但是音色不纯,混杂在了一起。阿劳的这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1933年,阿劳还录制了一些大型的、结构复杂、难度较高的作品,比如李斯特的《西班牙狂想曲》,只可惜因为是78转唱片,所以必须压缩时间,很多片段被剪掉了,这让我们没有办法来评价阿劳的演奏水平。很可惜,因为阿劳演奏的《西班牙狂想曲》,无论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我们都没有其他的版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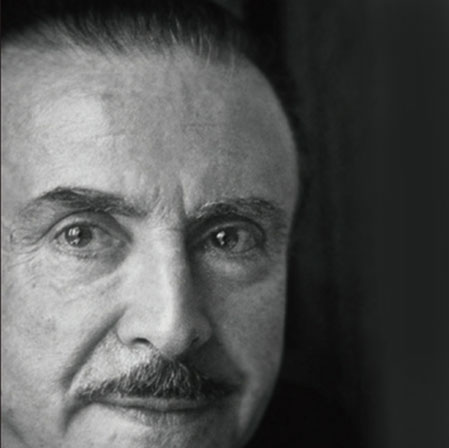


我们之前曾说过,在赢得日内瓦钢琴大赛大奖之后,阿劳开始迈入国际级钢琴家的行列,并一步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的演奏曲目单非常庞大,中小型的作品数量非常多。但这些作品并不总是按时间顺序排下来的。我们来看一下他演奏的最典型的作品:1929年3月13日,他演奏了门德尔松的《庄严变奏曲》;舒曼的《钢琴奏鸣曲》Op.11;李斯特的《彼得拉克十四行诗之123》《葬礼》《B小调叙事曲》;肖邦的10首练习曲。1929年11月16日在罗马,阿劳演奏了贝多芬的《回旋曲》Op.51、《钢琴奏鸣曲》;舒曼的《交响乐练习曲》;肖邦的5首《前奏曲》《谐谑曲》Op.20、一首《夜曲》、两首《练习曲》;德彪西的《阿那卡普里的山丘》《吟游诗人》《烟火》;李斯特的《西班牙狂想曲》。1935年6月18日,在布鲁塞尔,他演奏了贝多芬的《变奏曲》Op.34;勃拉姆斯的《随想曲》Op.76 no.2和《狂想曲》;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阿尔贝尼斯的《纳瓦拉》;法雅的《磨坊之舞》和《恐惧之舞》;李斯特的《艾斯特庄园水之嬉戏》和《超技练习曲》no.10。1937年2月12日为圣·赛西里亚的观众献上了巴赫的《升C小调前奏曲与赋格》(来自《平均律钢琴曲集》,但是属于第一章还是第二章不清楚);勃拉姆斯的《亨德尔主题变奏曲》;肖邦的《叙事曲》Op.52、《夜曲》Op.72,no.1和《谐谑曲》Op.54;拉威尔的《喷泉》;格拉纳多斯的《叹息,玛哈与夜莺》;布索尼的《致意大利》《图兰朵》里的《闺房》;卡赛尔的《托卡塔》。同年的5月25日,在波尔图演出了与上面大致相同的曲目,但是删去了《谐谑曲》Op.54,取而代之的是《谐谑曲》Op.31,还删去了两位意大利作曲家的作品,而那时在意大利举行的所有演奏会都必须要有这两位意大利作曲家的作品;曲目中加入了拉威尔的《水妖》和德彪西的《烟火》。
从阿劳演奏的曲目单可以看出,曲目十分庞大,而且风格偏向于古典,没有受到当时施那贝尔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阿劳倾向于那些文化气息浓厚的曲目,比如那些属于上层人士的音乐。除了录制一些“正常”的曲目外,阿劳在20世纪30年代也录制了一些专题性的乐曲。这些乐曲在观众看来,需要倾入自己超凡的智慧,在音乐家看来,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力。在这些乐曲中,最著名的,也是最有感情的是巴赫的作品:1935—1936年,在柏林,阿劳在十二个晚上弹完了巴赫的整部古钢琴拨弦协奏曲。前六个曲目非常难:第一至第四首来自《平均律钢琴曲集》的12首前奏曲和12首赋格曲,第五首是《法国组曲》,第六首是《英国组曲》,第七和第八首分别包括了15首创意曲和15首交响乐,第九首包括6个组曲,第十首是《法国序曲》《哥德堡变奏曲》,第十一首曲目和第十二首(因为某些情况,这里无从考证),最后是以《半音幻想曲与赋格》结束的。这十二个曲目是在波茨坦广场的音乐厅完成的,这个音乐厅能容纳大约500名观众,观众当时听得精疲力尽,也因为有些曲目是重复的(阿劳说大概两到三个)。
关于音乐作品,在阿劳之前,关于历史性题材的演奏会只有1904年布莱凯·塞尔娃(Blanche Selva)在巴黎举办过,前后一共17场。阿劳随后也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正是一个“严谨的音乐家”。对此,阿劳说:“那个时候,人们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钢琴家,但从不说我是个天才演奏家。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对我能将如此多的乐谱熟记在脑中感到非常钦佩和赞许。”当时阿劳的演奏会轰动一时,足够与当时最流行的乐曲《绝技》所引发的热潮相媲美。而阿劳也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因为十二个晚上的演奏他只在一个乐曲中遗漏了一点。“在那些天,”阿劳说:“我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希望能用现代钢琴重新演绎巴赫的乐曲。这里重新演绎不是说用现代钢琴来模仿古钢琴弹奏出的音乐,而是一种全新的演绎方式。现代钢琴演奏的乐曲其实比巴赫的演绎更有情感,而且没有用踏板,当然排除那些被我认为不能实施踏板的情况。”
阿劳在柏林演奏的巴赫的作品没有留下音响资料。但是我们有1942年录制的《哥德堡变奏曲》,1945年录制的《半音幻想曲与赋格》,三首《交响曲》,三首《创意曲》。阿劳把他的想法实现在他的作品中。从阿劳演奏的这些作品来看,我们可以有个很明确的印象。“严肃而认真的音乐家”,阿劳说。有时候可以说有一些过于严肃和认真,比如演奏舒曼的《童年情景》。在所有巴赫的钢琴演绎版本中,阿劳的版本是我听过的最客观的:非常客观。这些曲子并不是作为教学作品,却像教学作品一样极其谨慎和认真:节拍从来不会慢也不会快,强弱音也控制得很好,振幅不会过大也不会过小,音色纯正,连半个音阶的改变都不会有;除了《半音幻想曲与赋格》的极少数部分里,基本不使用左踏板和共鸣踏板。他的曲子从来不会“加快”也不会“减慢”,除了在乐曲结束时和两个乐章的连接处,会用断音音符营造出一种藕断丝连的感觉,阿劳会完美地表达原作的情感而没有特别内敛也不会特别外放。总之,就是客观。阿劳曾和斯特拉文斯基学习过《小夜曲》,我认为,阿劳正是从这次学习中感悟出了一些重要的理念,进而运用到巴赫作品的演绎中。演奏巴赫作品的钢琴家中,唯一能与阿劳相抗衡的只有谢尔金(《半音幻想曲与赋格》《意大利协奏曲》,1950年在法国普拉德)。
阿劳在20世纪50年代便不再追随巴赫,在我看来,这个决定真的非常难以理解。对于这件事,约瑟夫·霍洛维茨曾问过阿劳,他是这样回答的:“做这个决定部分是因为古钢琴开始风行,尤其是兰多芙斯卡所演奏的,我个人非常欣赏她,我想我作为一个钢琴家,应该用适合这支曲子的方法和工具来演绎这支曲子。”也就是说,阿劳在追随巴赫的过程中,因为极其欣赏兰多芙斯卡,钦佩于她用大键琴激情四射的演奏,而感觉到他用现代钢琴演奏的巴赫离兰多芙斯卡大键琴的版本相去甚远,所以可能会不自觉暗示自己或许不应该用现代钢琴去演奏巴赫的作品。这样的解释,在我看来,有点牵强。关于这一点,当我谈及晚年阿劳回归巴赫的作品时会再做分析。但是在一个艺术家身上,出现这样一种态度的大转变,不管怎么说,是值得深思的。
第二组套曲是莫扎特的作品,演奏了五场。(《奏鸣曲》和《幻想曲》,曲目具体数字不详),还有四个专场演奏了舒伯特和韦伯的作品。“莫扎特的作品不如巴赫的那样轰动,但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阿劳说:“当时有人对我的演奏不满,认为我的表达和原作差距太大,但事实上,我渴望唱这些作品的歌手像我一样倾注情感。”这里需要知道阿劳指的是哪些歌手:弗瑞达·亨佩、玛利亚·伊沃根、伊丽莎白·舒曼、赫尔曼·贾德洛维克、莱奥·斯莱察克。我认为这些歌手正是阿劳的参照点:基本都是那些不专门唱莫扎特作品,但都曾经唱过莫扎特和施特劳斯作品的歌手(莫扎特非常欣赏施特劳斯)。我们手头上有1938年阿劳为德国广播电台录制的《奏鸣曲》K.576和1941年在纽约录制的K.576、K.283:非常细腻的几部作品,慷慨激昂又不失温柔亲切,节奏从减弱音慢慢过渡到一个更令人舒缓放松的节奏上,“女性的温柔”,我觉得应该这样说。这几部作品我觉得并没有过分戏剧化,声音和表达上都很到位,而阿劳在20世纪80年代录制的版本倒是真的有过度这个问题。阿劳和约瑟夫·霍洛维茨的访谈是在1982年出版的。阿劳会下意识地把他现在的版本和过去的做比较吗?我们也不得而知。当然,晚年录制的版本有一种情感的宣泄,灵感的颠覆,不会像三四十年代的版本那样轻柔、透明。
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下重头戏:贝多芬的32首《奏鸣曲》。当时,阿劳的脑子除了已经存储下巴赫和莫扎特所有的作品外,仍然有空间来存储贝多芬的所有作品。贝多芬的这32首《奏鸣曲》很多钢琴家都曾演绎过,从最著名的施那贝尔、巴克豪斯、肯普夫,到不算很有名但广受好评的如伊索·埃里森(Iso Elinson)、哥特弗里德·加尔斯顿(Gottfield Galston)、科里柳斯·科查尼亚维斯基(Cornelius Czarniawski)、保罗·博姆加尔特(Panl Baumgartner),还有当时钢琴界的未来之星费舍尔·迪斯考、罗姆尔德·维察尔斯基。在德国的演奏会上,阿劳全身心地投入到贝多芬的作品中,还没有人是他的对手;1938年在墨西哥城他也演奏了贝多芬的32首奏鸣曲。不过,阿劳演奏的贝多芬的作品,录制下来的版本并不多,1938年在斯图加特的《奏鸣曲》Op.2 no.3和Op.10 no.3及1941年在纽约的《变奏曲》Op.34和Op.35,足以告诉我们在诠释贝多芬作品的钢琴家中,阿劳已经是佼佼者;尤其是《变奏曲》Op.35,更是一支可以载入史册的代表作。不过在《变奏曲》Op.106和Op.111中,阿劳是否也一样艳光四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要提醒读者的是,仅靠三四十年代演奏的这些贝多芬的作品,阿劳就足以在演绎贝多芬的钢琴家中留下自己的大名了。
之前说过,阿劳还演奏了韦伯的《奏鸣曲》和舒伯特的《奏鸣曲》(名称和数目都不详)。我们这里只有阿劳在1941年录制的韦伯的《奏鸣曲》Op.24,这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作品。除此之外,阿劳也是少数几个弹奏过韦伯的《协奏曲》的钢琴家之一。只可惜另外三首《奏鸣曲》他没有录制,因为那时韦伯还刚刚在音乐界崭露头角。至于舒伯特的作品,1956年之前的除了《乐兴之时》no.3和1922年用我们不熟悉的自动钢琴录制的《即兴曲》Op.142,就找不到其他录制的舒伯特的作品了。
其他30年代录制的作品还有:1939年录制的舒曼的《狂欢节》,这是一首斗志昂扬的作品,激情四射,但是几乎所有重奏的部分都被剪去,使结构显得不平衡,所以没办法给这部作品做评价。肖邦的《塔兰泰拉舞》Op.43、《叙事曲》Op.47、《谐谑曲》Op.39,用俚语说就是,作品显得过于灰色,自然也降低了作品的价值。而在演奏德彪西的《舞曲》和《雨中花园》时,音色则更轻快,更透明一些了,因此这两部作品成为他演奏的德彪西的佳作之一。1938年,阿劳为德国广播电台录制的肖邦《叙事曲》Op.23,演奏技术精湛,手法娴熟,作品获得很大成功,20年后,当阿劳再次演奏肖邦的这部作品时,又达到了一个巅峰。
至此,读者可以看出在30年代阿劳的演奏和工作是多么密集,除了录制这些音乐作品外,他还不间断地举办个人独奏会和三重奏的巡回演出,他的教学工作也一直没有间断。就这样,他还能抽出时间来做运动(游泳、划船、标枪),参加探戈、密穴地母祭舞的课程,还有约瑟夫·霍洛维茨所说的“吊马子”,那时,阿劳交了很多女朋友。1937年,他和一位次女高音歌手结婚,妻子名叫露丝·施耐德(Ruth Schneider),那时她的事业才刚刚起步,但在嫁给阿劳后,她便不再唱歌了,而是专注地扮演阿劳生命中最爱的人和最信任的人的角色。阿劳是这样说起爱情的:“和其他二三十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我的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对真爱总是失望的。但当我碰到露丝时,我知道我生命中的那个人终于出现了。你们知道,她那时刚刚开始她的事业,正在学习《卡门》。是她做出了退居幕后的决定,因为她觉得,两个艺术家在一起生活,注定两个人都要四处漂流,两地分居的生活肯定是不行的。”
总之,一个男人在34岁那年娶了个老婆是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了。不过这是一个总是和妈妈、姨妈、侄女们生活在一起的男人,在34岁这一年娶了自己的女人,之前连面包都不曾自己买过,现在却要开始离开家过自己的生活,虽然不能说不正常,但其中的感觉还是非常微妙的。“妈妈会嫉妒吗?”霍洛维茨问。“可能吧,”阿劳说:“但是她什么都没表现出来。她总说我也确实到了结婚的时候了。一开始,离开家的生活是真的有些不习惯。”一年后,1938年,妈妈和他的侄女们就回到了智利,再一年后,姨妈也回去了。1940年,阿劳来到南美洲举行了几场演奏会,他的妻子本来应该呆在柏林待产的,因为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但是她却在1941年也历经周折地去了南美。就这样,阿劳一家在圣地亚哥团聚了,大家还在一起讨论到底哪里适合他们定居。
德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曾青睐阿劳,在20世纪30年代终于完完全全地向阿劳敞开了大门。“能再次被肯定,我真的非常开心。从那时开始,我的演奏生涯真正打牢了根基。但是,还有一座大山等着我去翻越,那就是美国。”阿劳,一个顽强的人,一个勇敢的男人,他并没有忘记16年前在美国不愉快的经历。战争期间,他逃离纳粹统治的德国,因为那时纳粹已经把这个国家的戏剧、文学和音乐文化完全摧毁了。对于美国这座大山,阿劳相信已经到了自己反败为胜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