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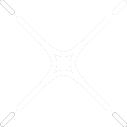
“音乐会非常成功,但此后的事态发展却并不迅速。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也并非一件好事:我更习惯不紧不慢地提升自己。”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年代表,看看世界是如何奖励这位布索尼钢琴大赛四等奖获得者的。如我们所见,在格拉茨,他的维也纳朋友为他准备了两场独奏音乐会。现在,就让我们重新看看第一场独奏会的这张“庞大”曲目表:
巴赫:《半音幻想曲与赋格》
勃拉姆斯:《亨德尔主题变奏曲》
舒曼:《狂欢节》Op.9
舒伯特:《流浪者幻想曲》Op.15
布伦德尔的评论也就是我为这一章节选择的引语:他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生涯,是以一种极为缓慢的速度开始的。李斯特的《圣诞树》是他录制的第一张唱片,之后又相继灌录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协奏曲》和布索尼的《对位幻想曲》。布索尼的这首《对位幻想曲》,他只在1955年的维也纳音乐会上弹奏过,也是唯一的一次。全部由女艺术家组成的维也纳室内交响乐团,偏偏也选择了布伦德尔作为独奏者(演奏巴赫的《D小调协奏曲》和舒伯特的《柔板和回旋复协奏曲》)参加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漫长的巡回演出。之后,布伦德尔又同维也纳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莫扎特的协奏曲K.595)举行了巡回演出,将莫扎特的K.503协奏曲和李斯特的《第二协奏曲》添加到了自己的曲目总表里。他坐火车前往雅典——整整52个小时的旅程——在那里,一位希腊小提琴手正等待他的到来。同他们一起,他又举行了一场独奏音乐会,和两位乐队指挥进行了一次试听,还被聘请弹奏莫扎特的《D小调协奏曲》。他对布索尼的强烈兴趣促使他亲笔抄写后者的《恰空舞曲》乐谱,因为这首作品的印刷版已不再出售。他还在维也纳的国家图书馆里找到了十分罕见的李斯特晚期作品的影印版,并将它们录进唱片。在22岁那年,他研习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Hammerklavier),并很快把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放到了曲目总表里。当声音唱片公司要求他将这些曲目录进唱片的时候,他还用一些俄国作品丰富了唱片,学习演奏了《伊斯拉美》和《彼得鲁什卡》:
……我学习那些作品,在艰难地完成了《彼得鲁什卡》之后,弹奏《伊斯拉美》更像是在休息。在练习《彼得鲁什卡》的时候,为了达到要求,我第一次迫使自己保护好指甲,以免裂开:也因为这样,我发现了橡皮膏药,并从那时起开始使用它们。
橡皮膏药,著名的保护布伦德尔脆弱指甲的橡皮膏药!除了带着望远镜去音乐会现场的听众是无法注意到它们的,只有在录像带,还有在今天的DVD里才能看到。这些橡皮膏药着实打破了一项教学黄金法则。根据这项法则,只有当手指肚敏锐的触觉在琴键下落时对其进行引导,触键技术才会异常精密。善良的玛利亚·舍尔·杜劳特曼(Marie Jaëll-Trautmann)——一位实证主义老师,甚至让她的学生剪下一些纸板,把它们固定在键盘上,并在手指肚上涂上墨水——红色的墨水!——在他们弹完了极为简单的乐段之后,立刻仔细检查墨迹,以确认手指肚的中心是否触碰到了纸板。我记得在一次采访里——我没能找到它的具体信息——布伦德尔曾经对那些反对他使用橡皮膏药的人说过,弹奏钢琴可不是爱抚一个女人的身体。
让我们重新回到《彼得鲁什卡》,布伦德尔曾对这首曲子做过评论:
让我觉得魅力难挡的是乐队的色彩。从本质上说,就是把钢琴转变为一支乐队。我早在李斯特的作品和布索尼的论文里就已经得到了启发,我也竭尽所能将它变为现实。《彼得鲁什卡》最初的版本是为乐队而作,因此即便是在钢琴演奏的部分,仍然保留了乐队的音色。于是,我还对总谱进行过研究。……我当时唯一能找到的是安塞美(Ansermet)指挥的版本。我仔细聆听了这个版本,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我自己的理解,试图在音色和节奏这两方面最大限度地以乐队的方式进行演奏。
有意思的是他的结语:
我并不想像舒拉·切尔卡斯基(Shura Cherkassky)那样,通过一些乐队根本无法实现的自由发挥,无耻地将它变成一首钢琴作品。
“把钢琴转变为一支乐队”对布伦德尔来说,是“最为关键的”。这也就导致了——定理的必然结果——他拒绝采用“乐队根本无法实现的自由发挥”。早在1980年发表于《伟大钢琴家的自辩》
 的一篇论文里,布伦德尔就已经阐述过这一概念:“我对指挥乐队怀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因为它告诉我哪些速度调整是钢琴师应该避免的:那些不能成为指挥对象的。”要对这则定理和结论作出分析,对我们来说恐怕太难。还是让我们把范围限制在引文里,它能够帮助我们确定布伦德尔式风格的各项标准。
的一篇论文里,布伦德尔就已经阐述过这一概念:“我对指挥乐队怀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因为它告诉我哪些速度调整是钢琴师应该避免的:那些不能成为指挥对象的。”要对这则定理和结论作出分析,对我们来说恐怕太难。还是让我们把范围限制在引文里,它能够帮助我们确定布伦德尔式风格的各项标准。
布伦德尔在声音唱片公司揽下的差事使他呈现出一张全部由贝多芬作品组成的曲目表。1958年,他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表演了贝多芬的第二、第三号作品、《热情》和《钢琴奏鸣曲》;1961年,他第一次在伦敦进行演奏,在8场晚会里弹奏了贝多芬所有的奏鸣曲和其他一些作品,“几乎按照年代顺序”对节目表中的曲目进行了排列。
在60年代,布伦德尔的音乐会工作不再如此繁重,但也绝不轻松。他的足迹遍布奥地利、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英格兰、意大利、南美、美利坚、澳大利亚、新西兰……如此度过十年,他的事业也得到了巩固。1968年,他离开声音唱片公司,并在1970年加入飞利浦公司。说到这里,我想斗胆插入一段我个人的回忆。在1969年时,我还在担任罗马的大学音乐会机构艺术总监一职。这所机构在1959年和1967年推出了一组32首贝多芬奏鸣曲的曲目表,而演奏者是威廉·肯普夫。学校的大教室在这两次演出期间都座无虚席,那无疑是一鸣惊人的成就。1970年恰逢贝多芬诞辰200周年,机构主席福尔图纳(Fortuna)认为有必要重新推出这组奏鸣曲,而这也是广大学生的愿望。这样的需求显而易见,因为3年来,学生中的人员结构发生了不小变化。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想要满足这一需求却显得十分困难。
在1969年巴克豪斯去世之后,肯普夫已然成为贝多芬的化身。同各大知名机构的合作,使他无法再为罗马的大学抽出两周时间来完成这组奏鸣曲。此外,1968年的工人学生运动浪潮使得机构不得不将演出场地转移到一个小厅里,也就是圣雷欧·马涅学院(Istituto S.Leone Magno)的小厅。如果说大教室的宽敞还配得上肯普夫所拿到的酬金,那么这个小厅就显得太不相称了。形势所迫,而最终拍板的权利又落在了我的手上。坦白地说,大学音乐会机构和肯普夫的交情不浅,所以不管怎样,他还是在10月17日和19日包办了1970—1971年度音乐季的头两场音乐会(他在第一场独奏会上演奏了贝多芬的奏鸣曲Op.10 no.3,Op.31 no.2和Op.110,以及小品曲集Op.126,在第二场则演奏了舒曼的幻想曲与《蝴蝶》,狂想曲Op.76 no.4和Op.116 no.3,间奏曲Op.76 no.4和奏鸣曲Op.5)。在场的观众无不心醉神迷。
形势所迫,我之前说过,最终拍板的权利落在我的手上。我心目中理想的人选有年逾花甲的保罗·包姆加特纳和埃德瓦多·德勒·普尤,28 岁的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和39岁的布伦德尔。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在我看来都不那么可靠。布伦德尔曾经在1953年和维也纳交响乐团一起为机构演奏过。还有一次是在1969年12月15日的单独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Op.10 no.2,舒伯特的奏鸣曲D.960,巴托克的摇篮曲以及舒曼的《克莱斯勒偶记》)。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基于何种考虑而最终选择了布伦德尔(坦白地说,他的独奏会并不让我感到完全满意,因此将七场演奏会完全交托于他,着实是一场不小的冒险),然而事实证明,选择了他,我并未遇上什么麻烦。布伦德尔在妻子的陪伴下来到罗马,完美无缺地演奏了七个夜晚,但没有受到追捧。
这并非一次失败,而是一次不温不火的成功,在第一场处女秀之后,圣雷欧·马涅学院的音乐厅里空出了一些位子。有些奇怪的是,人们对他的异议不是其他,而是他演奏各首奏鸣曲时散乱的顺序——他并没有按照肯普夫采用的年代顺序。只要想到肯普夫在最后一场晚会上演奏的第106、109、110和111号作品,我就不寒而栗,不仅为他,也为我自己。在1970年,听众对苦行主义的推崇要远远大于新世纪的今天,而布伦德尔对曲目随意地编排,对那些渴望重新登上巅峰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冒犯。此外,布伦德尔还因其七场独奏会的长时间跨度而受到指责(时间分别为1970年11月11日、17日、21日、28日,12月1日、9日、12日,整整一个多月),要知道,肯普夫曾经把它们浓缩在了短短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就此事而言,公众的指责其实有一定道理。不仅时间跨度增加了一倍,我们还不得不在布伦德尔的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独奏会之间精心安排其他五场音乐会的时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听众在沉浸于贝多芬的作品之余,已无法像先前那样得到意外的惊喜。
在这里回顾一下七场独奏会的演出曲目,我想读者朋友应该也会对此抱有兴趣:第一场:Op.2 no.2,Op.13,Op.31 no.1;第二场:Op.109,Op.26,Op.57,Op.14 no.2,Op.90:第三场:Op.2 no.3,Op.7,Op.27 no.2,Op.78,Op.101 no.1;第四场:Op.53,Op.79,Op.14 no.1,Op.10 no.3,Op.2 no.1;第五场:Op.101,Op.28,Op.49 no.1,Op.31 no.3,Op.54;第六场:Op.110,Op.10 no.2,Op.31 no.2;第七场:Op.106,Op.22,Op.49 no.2,Op.81a,Op.27 no.1和Op.111。无论从表达特点、钢琴乐谱、创作年代、调性还是形式来看,在这些作品之间,都毫无规律可循:从音乐会演奏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精明的混搭”,但对于当时的听众而言,它所制造出的只有混乱。在以后的日子里,布伦德尔对这32首奏鸣曲的位置进行了重新部署:
在最近几年里,我重新安排了曲目表中作品的位置,找到了更令我满意的解决方案:保留下完整的各组“三首奏鸣曲”,由于各组之间已经存在非常巨大的差异,也就没有必要再在它们中间进行划分。按照这个想法,在最后一场音乐会里,我把最后的三首奏鸣曲也连在一起进行了演奏。Op.26,Op.27,Op.28也一样,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这三首作品非常接近。
布伦德尔的演奏姿势不受人喜欢。肯普夫所代表的是白发先知的形象,他的目光总是射向高处,从视觉的角度来看,也更富有灵感和诗意,体现出高贵的简洁和平静的雄伟。布伦德尔,高大、懒散,总是以别扭的小步走上舞台,快速地鞠躬,坐下,然后看着乐器开始演奏。有时,他做出的手势会让人觉得键盘热得烫手。他握紧拳头,抬高手臂,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可怕的表情(在第一场独奏会,当他弹到奏鸣曲Op.31 no.1的第二乐章时,手指的长颤音在颌骨颤抖的伴随下,显得有两倍之多,而他的下颌骨——我发誓是真的——甚至脱了臼,布伦德尔猛地用手打了一下,才又恢复过来)。这一有关演奏姿势的话题,在《秩序的面纱》里曾被提到过。采访者说:“……公众注意到,您年轻的时候,在60年代甚至是70年代初,弹奏时总有很多手势,可能连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之后,您却表现得非常节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布伦德尔这样回答道:
在我身边,总有朋友对我说:“听着,你演奏得非常出色,但你应该明白,很多次,你的矫情、你挥舞的双臂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那时的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只知道自己专注于音乐,他们却来跟我谈外表!然而有一天,我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我自己。……我只能用震惊来形容,尤其是当我注意到我的动作和我表达的音乐有多么格格不入。……我看到在我表现的和我弹奏的内容之间,存在着多么强烈的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稍有改观。我开始意识到,究竟哪些动作才是与音乐相一致的——这也多亏了观众的帮忙。很遗憾,人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
1970年,布伦德尔弹奏《钢琴奏鸣曲》和小品曲集Op.126 no.2,no.3的一段视频录像,使我们得以证实39岁布伦德尔的演奏姿势。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那些手势并非慌乱不安,也绝非毫无缘由。只是,1970年在圣雷欧·马涅学院音乐厅里的观众却一点都不欣赏布伦德尔的脸部表情和身体动作:在他们看来,这位来自奥地利的瘦高个儿,实在缺乏高贵。
同样,他也缺乏对贝多芬高贵精神的尊敬。当约瑟夫·霍洛维茨问及克劳迪·阿劳是否发现过什么滑稽的器乐时,后者——在《与阿劳的对话》(Conversation with Arrau),[科林斯出版社(Collins),伦敦,1982年]一书中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并且还补充说,不明白为什么艾德温·费舍尔会将Op.10 no.3终曲的第一个主题定义为“幽默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一主题想要表达的是“一种迫切的需求”。布伦德尔曾经写过一篇相当精彩的两段式论文,题为“古典音乐必须通篇严肃吗?”(Must Classical Music Be entirely Serious?)。他的论点是,喜剧即为“高尚的背面”。在第一段的结尾处,他引用了康德《判断力批判》(Critica delgiudizio)一书中有关喜剧性的论述:“较之高尚的艺术,这种方法更适合于快乐的艺术,因为后者的主题,其自身必须显示出某种高贵。”布伦德尔评论道:“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追随海顿和贝多芬,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高尚的背面’占据了主导,失礼的言行取笑高贵的姿态。”布伦德尔早在1970年时就承认了贝多芬在奏鸣曲共和国里的合法地位。那是一个谱写《为黑白混血儿布里奇托尔——伟大的黑白混血疯子和作曲家所作的黑白混血奏鸣曲》(即日后的《克鲁采奏鸣曲》)《没有华彩的华彩段》以及《克莱门特为克莱门特所写的协奏曲》的贝多芬,亦是一个向“最高统帅”——奥地利出版商托比斯·海斯林格(Tobias Haslinger)发去嘲讽信息的贝多芬。然而,1970年的听众一点都不喜欢这些。综上所述,布伦德尔在圣雷欧·马涅学院音乐厅里的一系列独奏会,一半是败笔:对他如此,对我亦然。
在布伦德尔的职业生涯里,要说质的飞跃,应该出现在1973年起他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一系列独奏音乐会。不妨让我们来看看1973年时的演奏曲目表:
1月21日
贝多芬:《奏鸣曲》Op.27 no.2
舒伯特:《奏鸣曲》D959
李斯特:《意大利》,选自《旅行岁月》
2月18日
贝多芬:《奏鸣曲》Op.31 no.2,《奏鸣曲》Op.53
舒伯特:《奏鸣曲》D945
李斯特:《梅菲斯托圆舞曲》第一首
3月18日
贝多芬:《奏鸣曲》Op.13
舒伯特:《奏鸣曲》D894
李斯特:四首晚期作品,《B小调奏鸣曲》
1974年的演奏曲目都是海顿、贝多芬和舒曼的作品:
3月17日
海顿:《奏鸣曲》(第四十九号)
贝多芬:《小品曲集》Op.126,《奏鸣曲》Op.101
舒曼:《幻想曲》Op.17
4月7日
海顿:《奏鸣曲》(第二十号)
舒曼:《交响练习曲》Op.13
贝多芬:《奏鸣曲》Op.109,《奏鸣曲》Op.110
4月21日
海顿:《奏鸣曲》(第五十号)
舒曼:《克莱斯勒偶记》Op.16
贝多芬:《奏鸣曲》Op.90,《奏鸣曲》Op.111
1975年演奏曲目的作者是舒伯特、贝多芬和莫扎特:
3月9日
舒伯特:《音乐瞬间》Op.94,《幻想曲》Op.15
贝多芬:《奏鸣曲》Op.31 no.3
莫扎特:《柔板》K.540,《奏鸣曲》K.331
3月23日
莫扎特:《奏鸣曲》K.333
贝多芬:《奏鸣曲》Op.57
舒伯特:《奏鸣曲》D850
4月4日
莫扎特:《回旋曲》K.511
舒伯特:《三首钢琴曲》D946
贝多芬:《奏鸣曲》Op.106
1976年时的作曲者则变成了巴赫、李斯特和贝多芬:
4月11日
巴赫:《A小调幻想曲与赋格》BWV 904
李斯特:第十三、第十七和第十一匈牙利狂想曲
贝多芬:33首迪亚贝利圆舞曲变奏Op.120
4月25日
巴赫:《半音幻想曲与赋格》
贝多芬:《变奏曲》Op.35
李斯特:三首曲子,选自《诗歌与宗教的和谐》。
5月9日
巴赫:《A小调幻想曲》(前奏曲)BWV922,《意大利协奏曲》
李斯特:《痛哭、抱怨、担忧、忧郁主题变奏曲》《巴赫主题前奏曲与赋格》
贝多芬:《变奏曲》Op.34,32首《C小调变奏曲》《温特主题变奏曲》
1977年,布伦德尔举行了一组三场献给贝多芬的独奏音乐会(在三场音乐会中他分别演奏了大师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作品)。有那么整整5年,卡内基音乐大厅的观众都被他的演奏吸引得目瞪口呆,甚至还表现出意犹未尽的征兆。虽然施纳贝尔、卡佩尔(Kapell)、科尔托、费舍尔、莫伊塞维奇(Moiseiwitsch)、卡琴(Katchen)、卡萨德修(Casadesus)相继去世,所罗门(Solomon)的隐退,弗莱舍的生理疾病、凡·克莱本的心理问题,以及1969年巴克豪斯永远离开了人世,但他们所留下的某些空缺正慢慢得到填补。当时步入不惑之年的布伦德尔受到了飞利浦公司的重用,还拥有一位力捧他的美国经纪人,而他所获得的成功,如同他自己向我们讲述的那样,更多来自于听众,而非媒体的喜爱:
卡内基音乐大厅的组织工作和我在纽约的经纪人给予了我强有力的支持,那还是在没有《纽约时报》拥护的情况下。即使一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试图阻碍你,在纽约,你还是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这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
如果说70年代以前,布伦德尔所扮演的还只是一名候补队员的角色,那么从70年代开始,他已跃然成为音乐会演奏界的一颗耀眼明星。自那以后的种种,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作详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