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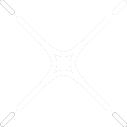
“如果我说自己是有一些达达主义的,那么我是在暗示我同时也是另一个人。”
1949年,18岁的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出现在博尔扎诺的首届布索尼钢琴大赛(il Concorso Busoni)上,并最终获得四等奖。四等奖是一个还算体面的奖项,当然,若是他的竞争对手中多了当时在各项大赛里抢尽风头的俄国人和美国人,这一奖项的分量或许还会重些。但事实上,在那次的比赛里,既没有俄国人和美国人的加入,也缺少了法国人、英国人、南美人和日本人的参与。这些骁勇战士的缺席,加之空缺的一等奖位置,使得第四名的意义对于一位日后国际演奏界舞台上的主角而言,实在微乎其微。在世界重大比赛中斩获头名的有为青年并非凤毛麟角——19岁在日内瓦赢得冠军的贝内代托·米凯兰杰利(Benedetto Michelangeli),16岁同样在日内瓦摘得桂冠的古尔达(Gulda),18岁时在华沙获得肖邦奖的波利尼(Pollini),还有16岁在莫斯科获得柴科夫斯基大奖的索科洛夫(Sokolov)皆是如此。如果引用一则冒昧却写实的俗语,即把二流选手比作“小国之君”的话,那么布伦德尔在博尔扎诺所获得的四等奖甚至堪比三等奖的分量。他意欲在巴黎的隆-蒂博大赛(il Long-Thibaud)和日内瓦钢琴大赛(il Concorso di Ginevra)上一雪前耻。然而,由于这些大赛的评委并非总是那么一丝不苟——我们就假设如此吧——他在初试时就惨遭淘汰。不过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酬金虽然不多,但至少能保证他在维持生计的同时,还能继续完成学业,直到1955年。
对于布伦德尔而言,他的比赛历程等同于三次参与和收入囊中的一个孤零零的四等奖。换言之,我们的主人公如此异乎寻常,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在他身上看到任何一点伟大钢琴家的影子。要知道,从上世纪大约30年代起,参加音乐大赛就几乎成为了开启职业生涯大门的必经之路。在1930年以前,国际性大赛极为罕见,尽管也成就了一些星光夺目的主角,比如列维涅(Lhevinne)、巴克豪斯(Backhaus)和阿劳(Arrau),但也不曾妨碍另一些从未参加钢琴比赛的演奏家取得同样的成功,比如霍夫曼(Hofmann)、施纳贝尔(Schnabel)、吉泽金(Gieseking)和霍洛维茨(Horowitz)。与此同时,这些比赛也并未给那些曾经名落孙山的选手带来任何障碍,比如费舍尔(Fischer)和阿图尔·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然而在布伦德尔的那个时代,无论是吉列尔斯(Gilels)、里赫特(Richter)、贝内代托·米凯兰杰利、弗莱舍(Fleisher)、古尔达,还是比布伦德尔年轻的凡·克莱本(Van Cliburn)、阿什肯纳齐(Ashkenazy)、奥格登(Ogdon)、波利尼、女钢琴师阿格里奇(Argerich)、鲁普(Lupu),以及许多其他的钢琴家,却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竞赛从而强势地进入了演奏界。只有古尔德和巴伦博伊姆(Barenboim)凭借着他们轰动一时的处女秀赢得了人们关注的目光。反观布伦德尔,既没有一场重大比赛的胜利让他春风得意,也没有任何一次取得国际性反响的登台使他扬眉吐气。事实上,他属于“新人类”,而他成名的方式则是普及音乐最为现代的工具——唱片。
他的认真——要知道他是极其严谨的——和他的同龄人(姑且就算同龄人吧,毕竟只相差一岁)弗里德里希·古尔达的疯狂有着云泥之别——在我看来,正是他的一丝不苟,使他进入了旋转之声唱片公司(Vox-Turnabout)的视线范围。随着LP密纹唱片(Long Playing)的问世,旋转之声唱片公司很快从市场上捕获了唱片革新和流行趋势的信号,意图进入与各大老牌唱片企业竞争媲美的行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策划出一张精彩纷呈的曲目表,与此同时,还不能招募那些已和竞争对手扯上干系的著名演奏者。公司签下了一位技艺纯熟的奥地利演奏者弗里德里希·乌赫勒(Friedrich Wührer),相比他二战前在戈培尔唱片行受到的青睐,战后的他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此外,公司还聘请了布伦德尔、克林(Klien)、弗兰克(Frankl)和女钢琴师海布勒(Haebler)前往录制唱片。在这四位年轻人中,布伦德尔所录制的唱片数量最多,最好的证据就是辉煌唱片公司(Brilliant)在2009年收集的35张唱片,几乎包括了所有他曾经为声音唱片公司(Vox)、旋转唱片公司(Turnabout)和先锋唱片公司(Vanguard)灌录的作品。自相矛盾的,或者说令人惊讶的是,在13年里犹如工作狂一般录制唱片的时候,布伦德尔却没有在其唱片雷声初动之时重复其他同行在漫长路途中所选择的常规路线。
在布伦德尔一步步用心经营其演奏生涯的同时,他浩大的唱片录制工作也在1955年到1968年间(也就是大师24岁到37岁的年华里)稳步前行(事实上,唱片所收获的好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演奏生涯的发展)。布伦德尔曾多次强调,他既没有精妙绝伦的技术,也没有过目不忘的记忆。然而,他曾经录下的那些唱片却告诉我们,尽管布伦德尔在演奏技法上不比霍洛维茨、吉列尔斯、里赫特,甚至也不比他同一时代的钢琴家——如卡钦、弗莱舍或古尔达,但他却在体裁甚广的曲目总表中从容跨越了一个又一个荆棘密布的技术障碍。他的手指轻巧敏捷,在演奏八度音与和弦时,手臂摆动自如,气定神闲。他所缺少的是日后逐渐形成的舍我其谁的气势,尽管这种气势和已经登峰造极的鲁宾斯坦、霍洛维茨还有吉列尔斯相比,依然相去甚远。
作为一名演奏者,当时23岁的布伦德尔可以说是一位双面神。当然,扮演同一角色的还有古尔达。他在演奏奥地利曲目的时候,以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方式对传统进行了颠覆,却在演奏法国作品时中规中矩。布伦德尔在诠释他对古尔达的观察之后,也在无意中描述了他自己:
……一位极具天赋并且在技术上无懈可击的钢琴家,像古尔达那样,如果要和费舍尔或是肯普夫相比,他的冷漠和在弹奏古典作品时缺乏的情感是我所无法接受的。相反,在他演绎拉威尔、德彪西或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时候,我却甚为欣赏,音乐仿佛瞬间被赋予了色彩和活力。直到今天,我们都能从他最初录制的那批唱片中感受到这一点。
“令人无法接受的冷漠和缺乏情感”,这些在年轻的布伦德尔身上倒是毫无踪影,因为那时的他似乎被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紧紧捆住,而他对这些曲子的演奏,除了太过缺少他本人的诠释,实在无可非议。当然,我们还是能够或多或少地看到他自己的一些东西,比如,在莫扎特的协奏曲K.459中,在贝多芬《第三协奏曲》的终曲部分中,还有在一些奏鸣曲的乐章中,尤其是在那些能够充分显示他极具绅士风度的幽默感的时候。只是,与他录制作品的总数相比,这样的时刻实在寥寥无几,在变奏作品和音乐小品中就更是屈指可数。按理说,在诠释像变奏曲和音乐小品这样的作品中,是最容易发挥个人想象力和独创性的了。
几乎很少有人问津贝多芬一些作品编号不详的变奏曲,除了C小调那部。由于缺少可以参照的资料,布伦德尔大失水准。他接受了声音唱片公司的要求,破坏了作品原有的结构,删除了大部分重奏。在音乐会上,他也没能够像大师当年初到维也纳时那样踌躇满志,没能那样优雅地走进音乐厅,将自己复杂矛盾的性格融入音乐审美和对观众心思的揣摩之中,进而赢得他们慷慨的掌声。遗憾的是,尽管布伦德尔在日后的职业生涯里曾多次重新演绎贝多芬的协奏曲、奏鸣曲及其大部分变奏曲,但他再也没有拾起年轻时弹奏过的那些变奏曲,也因此没能在历史的舞台上为我们重塑一个“平凡的”贝多芬。直到普雷特涅夫(Pletnev)和奥利·穆斯托宁(Olli Mustonen)的出现,才让世人看到了这样一位不同于人们印象之中的创作者,他虽举世闻名,受人敬仰,却并不因此而少了异想天开和妙趣横生。
令人称奇的是,布伦德尔的双面神角色也出现在对舒伯特作品的演奏里。艾德温·费舍尔(Edwin Fischer)的训练对布伦德尔演奏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表现在他对《流浪者》、一些即兴曲和《音乐瞬间》的演奏中。这些演奏充分展现了作品的表达,捍卫了作品的结构,但同时也缺少灵感和个性(除了他在即兴曲Op.142 no.4中的表现)。在《C小调奏鸣曲》、未完成的《C大调奏鸣曲》以及《德国舞曲》Op.33的演奏中,布伦德尔没有先例可循,因为费舍尔把探究和发现舒伯特这样一位伟大的奏鸣曲作者的难题留给了施纳贝尔。此外,在当时有名的演奏家里,也没人致力于舞曲的研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布伦德尔遵从了肖邦的朋友、伟大的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的名言:“请仔细聆听你的心声。”在仔细聆听了自己的心声之后,30岁的布伦德尔变得犹如50岁般成熟。我们很少能够听到那样紧张激烈的《C小调奏鸣曲》,也很少能够听到那样优雅并且完美周旋于风趣和亲切之间的德国舞曲。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双面神”好战的个性绝不弱于他平和的一面。更多强有力的证据将会随着之后的叙述慢慢浮出水面。
舒曼却不同。德国和奥地利文化对舒曼产生了非凡的影响,这是人们无法否认也无法忽视的。面对舒曼的作品,布伦德尔徜徉在传统的世界里,效仿前辈。但要说到肖邦、李斯特和俄国作曲家,情况却又不尽相同。在那些作品里,布伦德尔的创造力得到了完全的激发。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演奏都如此波澜壮阔,我只想表达:他总能以一种方式——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即一种英雄主义的方式将自己与作品融为一体,在与声音中尽情地展现自己,并始终冷静地掩饰自己过分的激情。他对李斯特作品的演绎方式最令人叫绝。在20世纪50年代,李斯特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人们对于他的评价还相当苛刻,直至《B小调奏鸣曲》——即勋伯格具有革命性的作品《第一室内交响曲》在形式上的原形之作——才因为它别具匠心的结构特点为知识分子阶层所接受。布伦德尔不仅大量演奏了李斯特职业生涯中的中期作品,还先驱性地探索了他的晚期作品,包括大师在前魏玛时代的作品,要知道,那于50年代早已是明日黄花了。
毋庸置疑,在《拉美莫尔的露琪亚》中的六重奏里,我们能够发现意大利的美声唱法并非布伦德尔的兴趣所在。然而,他对这首由李斯特在1836年改编的六重奏的选择,却是意义非凡的:正是在这首改编曲里,李斯特通过运用手臂的力量发现了能够在宽敞的剧院里余音绕梁的如歌琴音。相同的美学极限也在《“诺尔玛”的回忆》里得到了强烈对比。对这首曲子的选择同样表现出演奏者敏锐的观察力:在还没有《奏鸣曲》之前,《“诺尔玛”的回忆》的结构远比李斯特想象中要大胆新颖。
至于李斯特的早期作品,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布伦德尔逆流而上的勇气,因为他重新提出的这张曲目总表,无论从历史、技术还是结构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同凡响的。在50年代,这些作品不仅早已被废弃,并且对它们的演奏还遭人鄙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美学极限恰好体现在他对意大利美声唱法的陌生,显然,这样的极限在《汤豪塞》的“朝圣者之歌”和《奥伯龙》的序曲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演奏的《奥伯龙》堪称楷模,如果说我们想要了解缘何那些从交响曲目改编而来的李斯特作品能够在40年代里征服公众,那么布伦德尔对这首作品的演绎就要成为我们的必修课了。
布伦德尔所演奏的李斯特作品主要集中于大师在魏玛时期的作品。布伦德尔的技术虽然优秀,却并非超凡,这一点在《帕格尼尼练习曲》《威尼斯与拿波里》中的《塔兰泰拉舞曲》以及在一些《匈牙利舞曲》里就可见一斑。在这些作品里,精湛技巧是当仁不让的主角。然而在一些需要用思维去征服在场芸芸大众的作品里,布伦德尔却完全掌控了局势,若是再考虑到他的小小年纪,就更加令人目瞪口呆了。当然,他对《B小调奏鸣曲》的演奏还是略显青涩的:布伦德尔在他的曲目总表中长期保留了这首作品,并在日后为我们呈现了两次更为成熟的演奏。而他在1958年演奏的另一首幻想奏鸣曲《但丁读后感》,却毫不逊色于1986年的版本,甚至从某种角度看,前者的技术处理方式要更为清新自信,与此同时,也将他在演奏贝多芬式作品时采取的极为激烈的“柔弱”和“强硬”对比运用得恰到好处。
同样,在对《诗意与宗教的和谐》五首曲子的诠释中,年轻的布伦德尔也至少四次正中靶心。让他有失水准的是第四首《死之冥想》。这首高深莫测的曲子将分别在1834年和1852年写下的片段组合在了一起,或许也因为如此而无法得到统一。总之在我看来,布伦德尔没能成功地将这两部分融为一体。相反的倒是他演奏的《葬礼》,直到高潮点之前的极为简洁的和声进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让霍洛维茨在1932年的那场著名演奏都有些相形见绌,后者在结构上更加自由随性,或许更加自我陶醉于显示左手炫技的八度音之中。当然,我不得不说——身处21世纪的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坦白的呢——在演奏中,结构并不能代表全部,比起布伦德尔黑白分明的表达方式,霍洛维茨万花筒般的音色和声响造诣最终使得他的演奏更为引人入胜。
在协奏曲和《死之舞》中,让我们甚为欣赏的是他与迈克尔·吉伦(MichaelGielen)合作的默契,同样令人称道的是,在李斯特那些于当时被认为俗不可耐的作品里,两位对先锋音乐已驾轻就熟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一丝不苟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看到了过多将李斯特“贵族化”的痕迹。然而,布伦德尔对大师作品所表现出的尊敬和投入是令人感动的,这也足以使他能够和活跃在五、六十年代里的两位最为伟大的李斯特协奏曲演奏者——阿劳和里赫特平起平坐。最后,我们看到了他演奏的大师的晚期作品,那些作品在日后70年代里被用来探索李斯特作为先锋音乐家的一面,或者引用人们的话,即他“20世纪音乐之父”的一面。
李斯特的晚期作品常被表现得好像先知紧锁的眉头那样刻板拘泥,这种现象直到今天还屡见不鲜。布伦德尔却把它们看做是马戏团的小丑,为了向他的同代人讲述那些让人无法理解的真相,他滔滔不绝,天马行空,当然也会不时冒出一些令人发笑的双关妙语,有点类似奥斯卡·王尔德。总之,他的演奏使人吃惊,也让人兴奋,而如果我们可以想到布伦德尔是在1951年到1952年间录下最早一批的李斯特晚期作品,比如《圣诞树》,这样的感觉便会愈加强烈。在这部神秘莫测的曲集里,十二首作品中至少有五首(《谐谑曲》《排钟》《催眠歌》《普罗旺斯的圣诞老歌》和《晚钟》)的演奏被发挥到了极致,而另外的第六首(《老时光》)的演奏,也只是仅次于经验老到的魔术师霍洛维茨,因为后者对曲子略微进行了修饰,为其注入了苦甜交融的思念。不管怎样,在这以前,仅仅只有一位伟大的李斯特作品演奏家推荐了《圣诞树》这部曲集——费鲁乔·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他在1918年将曲集纳入了自己的曲目总表。布伦德尔是在当时继布索尼之后,唯一一位成功征服这部曲集的演奏者,而那时的他,年仅20岁。
对布伦德尔的职业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的20世纪奥地利文化几乎去除了所有有关李斯特的残痕,这一点是以音乐评论家爱德华·汉斯力克(Eduard Hanslick)——交响诗的死敌——为主导的19世纪晚期奥地利文化所不曾做到的。如同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布伦德尔并没有在奥地利传统中寻找演奏李斯特作品的先例。同样,他也没有在以李斯特的学生安索格(Ansorge)、达尔伯特(d'Albert)和绍尔(Sauer)为代表的德国传统里汲取灵感。绍尔曾长期在维也纳教学,并于1938年录制了李斯特的两首协奏曲。事实上,正是在协奏曲中,我们可以看到布伦德尔效仿绍尔的一些痕迹,当然,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罢了。我倒认为,布伦德尔是通过费鲁乔·布索尼和布索尼学派的演奏家爱德华·斯托尔曼(Eduard Steuermann)一步步走近李斯特的。布伦德尔曾经公开演奏过布索尼的《对位幻想曲》,并为“艺术家同盟会”(Society of Partecipating Artists)录制了这首曲子。他曾写下四篇关于布索尼的文章,并在曲目总表中保留了布索尼直到20世纪末的一些创作。他在青年时代就已熟读布索尼《音乐的本质》中有关李斯特的文章。我相信,正是在这些文章和布索尼的音乐里,布伦德尔寻找到了接近李斯特的重要途径。总之,我们能够肯定的是,作为李斯特作品的演绎者,他在30岁时的地位就已非同小可,但要说到演奏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曲子,却还略欠火候。
我不知道这样的评论是否也适用于他对肖邦作品的演奏。声音唱片公司将《波兰舞曲》指派给了他(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公司居然把《夜曲》交给了海布勒进行演奏)。我却认为,日后让布伦德尔大有作为的是肖邦的《前奏曲》。诚然,他演奏的《波兰舞曲》Op.44和Op.53充满骑士般的激情,英勇无畏,朝气蓬勃。但是,在50年过后仍然能够激发起我们极大兴趣的却只有他对《幻想波兰舞曲》的演奏。2007年,当布伦德尔为一部选集思量一些他之前从未在唱片中发表的乐曲时,他把目光投向了《平稳的行板与辉煌的大波兰舞曲》,1968年的钢琴独奏版本。我似乎在这样的选择里看到了一种媚态。在《平稳的行板》这部作品的演奏中,他对细微结构的处理和对分句的诠释极尽精雕细琢,延音踏板的使用被减到最小,如歌的声音则好似钟琴。一位钢琴家,在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为一部精选集挑选了这样一首他最为得意的演奏作品,似乎让我们嗅到了那么一丝报仇雪恨的味道。向谁复仇?我想此人应该是霍洛维茨吧。他在《平稳的行板与辉煌的大波兰舞曲》的演奏里几乎呈现了所有的钢琴演奏技巧,不得不让人想到地中海沿岸的那些商人蜂拥而至,挥舞着让人眼花缭乱的精美地毯的画面。有关布伦德尔和霍洛维茨之间的千丝万缕,我在之后的章节里还会详细叙述,但在这里,我并不想错过这样一个令人有些费解的片段。
布伦德尔第一次弹奏的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就如同他演奏李斯特的《奏鸣曲》一样,不如之后的表演那么成熟老练。在布伦德尔的国际演奏生涯取得一定成功后(也就是在70年代以后)认识他的人,也绝对无法想象他会以一种近乎自负的态度弹奏巴拉基耶夫的《伊斯拉美》。灌录在磁带上的现代录音可以纠正一些胆大冒失的错误,而那是78转老式唱片所无法掩盖的。当然,即便再强大的录音支撑也不能将这些因莽撞而遗留下的痕迹消灭得一干二净。我之前曾提到,布伦德尔并非霍洛维茨那一类的演奏能手,但他指下的《伊斯拉美》可绝非“动听”二字可以形容,相同的还有《彼得鲁什卡》。布伦德尔睿智的演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个深受新古典主义文化熏陶的斯特拉文斯基,而不是那位10年前创作芭蕾舞曲的俄国式作曲者。另外,如果说在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协奏曲》里,布伦德尔必须恭敬地在里赫特面前退避三舍,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少数人能够在年仅25岁之时(布伦德尔在1955年弹奏了这首曲子)就达到像他那样的高度。最后,一个像布伦德尔这样的李斯特作品演奏者,是注定能够与理夏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以及勋伯格志同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