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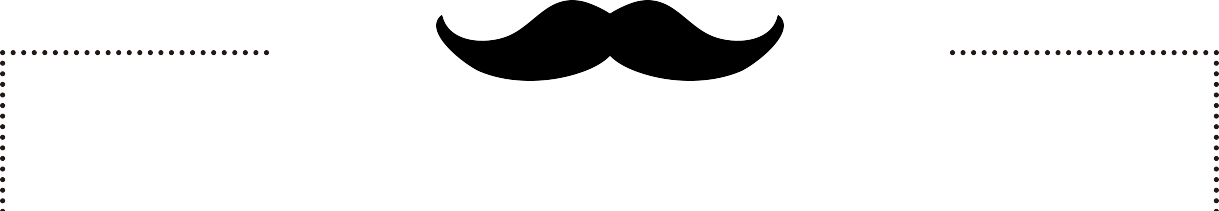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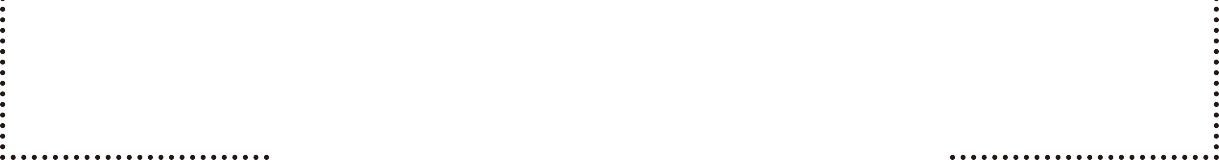
在对肖邦的各种评价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评价:教育者肖邦。一开始科托对这样的评价几乎感到抱歉,也为肖邦感到抱歉:
把教育者肖邦这两个词用在我研究的对象身上时,事实上我对它有着一种本能的拒绝。
教育者肖邦?钢琴老师肖邦?肖邦教的是什么?这全然是一幅不现实的画面,几代人众星捧月般建立起肖邦的诗人音乐家形象,将肖邦定义为教师,那神一般的形象也会随着教育者肖邦这一评价的出现而消失不见。
无论怎样,事实是存在的,是不可争辩的。
从以上我们可以知道,科托并不觉得肖邦会成为教师那么沉闷的人,他把这种现象定义为“肖邦,以做音乐教师来缓解他的压力,因为像肖邦这一类人,平时的社会活动完全是单调的,长时间地缺少欢乐的元素”。尽管这样,我们不能对等地觉得科托也是一个沉闷的人。他是活跃的演奏家、评论家、手写论文方面的收藏家,除撰写过肖邦回忆录,还是各种活动的组织者,会不定期地做乐团指挥。尽管生活如此紧张,科托还是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工作,其中不仅有各种音乐课,还对韦伯、弗兰克、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肖邦、舒曼、李斯特、舒伯特的众多音乐作品进行修订和评注。关于这个方面,我们有简妮·蒂埃弗里从科托课堂上整理的演奏课程资料的笔记。除此之外,还有三张CD,是在1954—1960年高级音乐大师课程中所录制的。通过这些庞大的真实案例,我们可以充分了解科托当时的活动。
以蒂埃弗里整理的笔记为例,引号之间的内容是她记录下来的科托在上课时的评论(“[……]禁止作任何添加”,修订者就是这么写的),科托也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到了当时的意图。科托对于演奏的构思,基于他的信念,音乐没有办法非常准确地将其表达出来,但它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感染力。让人感到惊奇的还有下面的文字:
基于听众的不同意向和喜好以及个人最本质的思想,应该允许每一个人活在那些不同的、由短暂情感影响下的梦中。
这种说法,可能会被认为是音乐的新教(信徒依照自己的想法来阅读圣经),但是从天主教的角度,很快又会被纠正过来(注解揭示了圣经真正的意义):
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得到更多的磨练,聪明才智得到更大的发展,我们的情感有更大的可能趋于完美。作曲家通过他们的作品所传达给我们的思考,正是为了唤起听众和他们一样的那份激动感觉。
然后科托说:
有几次,他试图寻找出两种音乐的差别,一种是表现情感的音乐,另外一种则只是单纯的表达声音的音乐。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在那些理论家定义的纯音乐范畴之内,作曲家灵感创作中一定包含着一种情感,需要演奏家在演奏时将这种情感传达给听众。
最后:
毋庸置疑,音乐语言是非常高级的,也是非常奥妙的,但对于那些新手来说,音乐语言还仍旧保留着那种单纯情感。因此只有通过一种无限细致的智慧演绎,演奏者才能够或者应该,通过声音的象征语言,清晰地表达出作曲的意义。
感觉、感情、感想、情感,四个看似可以互相替代的词,但我们不能说科托的演说是一种严密的科学理论。科托也并不在撰写一篇科技论文,而是为了吸引那些坐在大厅里的青年男女的兴趣,他们需要努力抛掉坏习惯、懒惰和过于注重技术性的观念。事实上,科托有了这个坚定的想法之后,他这样说:
我认为,为了改善乐器的演奏技巧,曾经最快且保险的方法就是用诗情画意的方式演奏。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如何变得与众不同,如何为演奏增添不同的色彩,让大家透彻地理解音乐作品,同时也可以丰富演奏的流派。
这种看待演奏技巧的方式,并不是勇敢地面对面地看待它,而是需要通过一张滤网去看待它。这引起了年轻人文琴佐·维塔内的极大反对,因为他之前觉得无瑕的音乐演奏才是最重要的,这些是他在那些演奏技巧论文中明白的道理,尤其是马太和布鲁尼奥利的演奏技巧。科托的演奏技巧还属于这样的时代:就像阿劳所说(《与阿劳的谈话》,约瑟夫·霍洛维兹,伦敦,1982),他认为出现很多错误音符或许就是天才的权利。关于科托的音乐大师班的作用,维塔内回答得很辛辣:
很早之前人们说过:每个人可以通过说法国方言变得优雅。举个例子,对于我来说,本应引起共鸣的《鬼火》我却无动于衷。然后根据科托的建议,我弹奏了贝多芬的《谐谑曲》Op.106,它的作用也就是让我们了解到眼镜和望远镜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来形容它们。(钢琴,鼓槌和制音器,那不勒斯,1975)
稍后我们再来深入科托给我们的建议。现在我们研究一下由蒂埃弗里从科托课堂上整理出来的文件,一些内容指出科托在上课之前,就要求接见那些登记的新生。在考试中,除了要问音乐家的生平以及作品的题目、确定的年代、献词之外,科托还会提问:a)形势环境对于音乐作品的贡献,指出在相同时代的此类作者;b)作曲的规则(结构、节奏、调性);c)重要的细节(共鸣的分析,直接的感受、类比、衍生);d)特点和作品意义;e)美学和技巧评论,以及对于自身学习和演奏的思考。
最后一条,“对于自身学习和演奏的思考”,是和能否成为大师有着最紧密联系的一项。因为通常科托和学生都是第一次见面,正是为了“鉴定”学生的一些音乐素养,他才使用这个特别的方法。上述所列举的几条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科托和学生在一起时是怎样工作的,而且可以了解科托自己工作时的状态,这样的一个列表,可以算是作者演绎方法的一个简表。
蒂埃弗里整理过后的笔记,被放在“演绎”这一章中也显得有趣。我再补充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在科托的演奏中被多次表现出来:
对于一部作品来说,如果有历史文献会严格规定作品的情感特点,如果作品的演绎者不分享他的情感,在类似这种情况下,我承认你们要做的就是跟随自己的感觉。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出发点,关于自由考试的新派理论。
从“作品演绎”再说到“作品形式”时,我们的兴趣骤然下降,因为缺乏音调的文字是苍白的、无力的,也是晦涩的。再来看看剩下的,在“固定形式作品”这章之后,是被删去的“自由形式演奏的作品”一章。这一章从未在科托的《演奏课程》这本书中出现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市场没有给予《演奏课程》很大的热情。
“固定形式”这章包括肖邦和德彪西的序曲,但这个决定只是用来掩饰科托的真实想法。我们不要刻意地揭开这个谜团,可以先来看一下科托在《序曲》Op.28 No.4中所说的:
演奏这一部分时,要表现出来将眼泪藏在心里面的淡淡的悲伤。旋律一开始一定要非常的缓慢,低声弹奏,让听众知道乐曲已经开始,却又没有察觉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左手只用手指弹奏和弦,呈现出一种极为轻盈的演奏。右手诠释满是悲伤的情感,那种哀鸣就好像没有一丝力气去提高声调一样。
接下来,科托又将“我们的感情由伤心带到了害怕”,接着又加入了“一点疯狂的成分”。科托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关于那种好似雪地上的足迹一般轻盈的感觉,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伤口的印记是怎样在一瞬间被掩盖住的呢?”作品《枯叶》让我们想到“某片树叶脱离枝干,自己旋转着落下”?天啦,科托到底是怎样做到的?这是怎样的技巧?
现如今我们只有短短的一小部分珍贵的影像资料(《钢琴的艺术》DVD)能让我们看到科托是如何演奏的:在发表讲话后,他坐到了钢琴旁开始给大家表演,他在弹奏时嘴里还在说着话。我想维泰内收到这个充满文学性的影像礼物时,应该非常恼火吧。影像中,技术的问题依旧存在,但是在这片纱的后面充满着演绎者的智慧和感性,科托弹奏时候说的那些话正是之前维泰内不屑的那些大道理。在这部DVD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女学生让科托听她演奏完《诗人诉说的童年》之后,科托在钢琴的左侧倚靠站立着,面朝大厅,也就是面朝听众,用平静的声音点评着,边思考边对学生做出总结:“真正的演奏是需要你去幻想着那一部分乐章,而不仅仅只是弹奏。”
接着,他走向了那个女学生,像一位年长的绅士一样询问道:“你们允许我坐到你们的位子上吗?”女学生站起来,他坐下开始弹奏,嘴里随意地说出几个词,脸上一副梦幻的表情。但是他的演奏却不是虚有其表。相反的是:他的演奏是如此的透彻,这时摄影师又将镜头移到了科托弹奏的双手上,这样,我们可以看清楚科托的每一个指法都非常坚定而严谨。这就好比演员在扮演某个“角色”:观众应该明白,舞台上的有些对白并不只是说给舞台上的对话者听的,与此同时这个对话者要清楚地明白对白的含义。事实上,科托在给观众解释的时候,弹奏的并不是他幻想中的声音,而是呈现给听众的音乐:他的听众并不只是离他三米远的那些人,而是遍布一个能容纳1500人大厅的所有人。在科托弹奏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魔幻的词汇:“温柔的……质疑未来。”然后这个梦消散……伴随着那减弱的和弦而结束。
科托的这次示范不足两分钟,但毋庸置疑的是,对于那些能够懂得它的人,这几乎就像一篇短篇论文,完美地示范了演奏的情感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那么在科托之前演奏的那个瘦高的褐色头发的女生收获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大胆的猜想立刻浮现在我脑中,或许五十年后那个女学生留下的更多感受是如何做一名情感投入的听众,而不是怎样成为一名成功的演奏者。
学生在听完科托的演奏后,希望知道这位神一般的老师是怎么用这种奇妙的方式来呈现音乐的。答案就在他的《钢琴技术的合理原则》中,在书中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柔和的水平手腕姿势”的练习,还有“手指柔韧性”的练习。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音乐大师作为教师的成就是伟大的,他教授的方法对于学生来说极为有用。此外,在书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大量的练习和详细的解释,以及为了锻炼以下五个方面的技能而设计的小提示。对科托来说,他解决了所有指法上的技术性难题:1.手指的对等、独立和柔韧性;2.手指的跨度(音阶和琶音);3.双音和复调;4.音域的延伸;5.手腕技巧与和弦演奏。
学生们或许已经找了理论的部分,但还是没能找到任何关于指法的解释,即声音是怎么产生的解释。现在对于“好声音”的概念是在1903年由托比亚斯·毛掏伊写的《触摸的艺术》中被重新定义的。书中分析了42种指法,也就是声音产生的方法。而鲁道尔夫·玛丽亚·布赖特豪普特随后的著作方向也和托比亚斯是一样的。1910年费鲁齐·布索尼在他的短文《钢琴家需要什么》(现在这篇文章被放到《喜悦的眼光》中,米兰,1977)中,说了几句话,这些话如今成为不争的事实:“指法的运用,而且包括踏板的运用都应该属于技术的一部分。”对比马太、布莱特豪普特以及布索尼的想法,科托在1928年写出了《钢琴技术的合理原则》一书,却感觉像是五十年之前就写好的。所以卢卡·齐亚多内(《钢琴技术历史》,马德里,2001)在《原则》中有以下言论并非巧合:“在讲解卡克布雷勒、赫兹、齐默曼和斯塔马特的时候,他用惊人的方式展示了他的方法和技巧。”
科托并没有忽视指法问题和多变性。这里我们说的是科托写的一篇关于拉威尔的评论文章《绞刑架》。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话:
吉尔-马尔凯斯曾经统计过,这首只有几小节12个音符的曲子中,要使用27种不同的指法:我相信这是有事实根据的,相较于书写文字中的那种纯粹和简单,拉威尔为我们的手指安排的这套令人害怕的键盘指法,却并不会限制他创造美妙声音的可能性。
吉尔-马尔凯斯提供了这个绝好的机会让我们分析这27种不同的指法,也给大家增加了了解科托想法的机会!但对于科托来说,指法的技巧不能被列入弹奏技巧里面,并且也不是演奏的一部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它甚至不存在。技巧和现场演奏在19世纪是如何发展的,《原则》这本书将它们分开考虑。科托这样总结道:
当提及指法技巧效果时,我们需要极大的耐心来等待,有一些话可以来形容这件事,这些话正是加西亚将青少年玛丽布朗从严酷的学习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说的:“就是现在,冲吧——随着你的心自由歌唱吧!你知道你的使命!”
相信我们内心真实的声音……难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吗?或许是太过于简单了吗?科托说钢琴家在演奏时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方面”,一个是“生理方面”。第二个迹象是可以预见的。当谈到第一个方面时,科托这样说:
关于提高心理素质,尤其是人的性格和品位,在教育学中找到的相应论点只有丰富总体文化水平;发展想象和分析能力,从而让自己的情感和感情可以通过音乐表现出来,不存在好或坏的体制,也不存在好老师或者坏老师。
古典音乐的一些改编版本我们稍后再谈论。研究了上面的两个因素,却还没有研究指法,是因为指法是两个因素间的桥梁。除了蒂埃弗里的那些资料,还有三张高级音乐讲习班的唱片,我明确说过,阿尔弗雷德公开的那些课程里只顾到了心理因素——我希望送给你们的并不是课程,而是对艺术的热爱。对这个言论,科托也给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并和他的演绎联系起来,不可否认的是第一个因素在他的乐曲演绎中表现得很明显。但是关于指法、音色这些可以让他创造出极优美的音乐画面的技巧,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原则》中建议“在键盘上的食指以自然的姿势来演奏”,这样食指就可以“照顾到其他指头”,因为科托通常弹琴的时候手指跨度都很大。
在1828年的时候,科托还没有找到一个成功的方法来演绎肖邦的曲目。而在1849年的《教育者肖邦》中,他让全世界了解到一些令人震惊的肖邦轶事:“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反大自然的规律,试图将每个手指练习成有相同的力量”,而且“最弱的四指和三指是连体双胞胎,通过同样的点连接到身体上,但是四指却试图努力与三指拉开距离,这是不可能的,是无用的,感谢上帝。”在《教育者肖邦》中科托没有以自我批评的方法重新考量《原则》当中的第一章,也没有提到在1849年这种独立性可能已经存在了,虽然是部分的。也就是说在慢节奏下,这种同等力量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所要求的乐曲结构也极为严格。科托对于钢琴技巧的想法是遵从于法国传统的,他既不以最近的研究为基础,也不以自我分析为基础,最终无法将他演奏技巧的奥秘传授给他的学生,即使是最有才华的哈斯基尔、里帕蒂、弗朗索瓦耶也没有成功。当时那位冲动的文琴佐·维塔内,也只能争辩说,在科托的课程里,他学到的只有单柄眼镜和独柄眼镜的区别,便携式望远镜和长柄单片式眼镜的区别。
科托在教育学领域最后的著作的贡献可以说也是最小的:1960年出版的《钢琴课的基本原则》。这本书给出了练习时的实用意见,有的确实是好的建议,有的却只会引发一些困惑。第一页可以说是最珍贵、贡献最大的:“应该一直从原则出发,因为学生需要领会到音乐的缘由。”说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