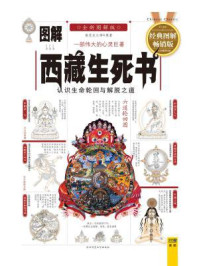众所周知,古希腊埃利亚派是对古希腊早期感性的自然哲学的一个反动,这些哲学家不再从感性的自然界中另找一个元素(水、火、气、无定形者)或一种规定性(数、逻各斯)作为万物的始基,也不再用这寻找出来的始基对感性的自然物加以解释,而是力求凭借理性的力量超越整个感性自然,并寻求对宇宙整体的抽象的普遍规定。这就达到了巴门尼德的“存在”和“一”的原则。当然,这种规定仍是针对整个自然界的,但哲学家们关注的已不是为这个那个感性事物找到它们共同的“始基”,并不认为只要找到这个始基就为整个宇宙定了性(从感觉或数量关系上定了性);恰恰相反,它们关注的首先倒是给宇宙整体定性(从理性、概念上定性),至于这个整体定性是否能作为感性事物的始基来解释万物的产生,这倒在其次。他们通常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可能的,因而感性事物是不值得重视的。希腊哲学在埃利亚派这里首次跃升到了一个思辨的反思层次,一个单凭理性进行抽象概念的论证推理的层次,对希腊自然哲学观的整体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就遇到了如何能用宇宙整体的这些最抽象的规定来解释万物的现象(如运动变化)的难题。巴门尼德用唯一的不可分的“存在”来否定“非存在”的实在性,芝诺对运动的诡辩性的取消,都使这一难题更加尖锐化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在存在的“不可分”的基础上把非存在也容纳下来,使存在和非存在能够在一个共同的结构体系中并行不悖。这就是从恩培多克勒到阿那克萨哥拉和德谟克利特的一条思路,它从埃利亚派已达到的纯粹哲学高度高屋建瓴地下降到自然万物,建立了古代科学而又实证的自然结构理论。这就体现为这样一股强大的思潮,它致力于“打碎”埃利亚派那不可分的“一”,而返回到早期自然哲学用自然本身的各种要素来解释感性的自然现象这一传统;但这一返回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立足于埃利亚派已经达到的哲学层次上,也就是:唯一的存在虽然被打碎成了“多”,但每一个“碎片”却仍然被看作是不可分的、有定形的“一”,它具有这个“一”的一切特性;不同的是,在它的外部还有别的“一”存在,而在这些“一”之间,则最终插入和承认了“非存在”(德谟克利特)。这就是他们所找到的一和多、存在和非存在和平共处、不相矛盾的结合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宇宙的某种既有感性内容又有抽象形式的结构。
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 495—约公元前 435)据说做过巴门尼德的学生,他是从埃利亚派的理性主义转向感觉经验的。他虽然也看到人的感官有其局限性,但仍然主张通过各种感官来补正每一种感官的不足,“你要用各种官能去观察,看看每一件事物用什么方式才是明白的”
 。他通过对感性世界的广泛的、不带偏见的考察,认为必须把日常经验所公认的自然界四大元素即水、火、土、气全部看作构成自然界的基本要素,他称之为“四根”。在他这里,“始基”概念已经过时了,由这概念而来的对自然的一元的解释也被放弃了,他的原则虽然说的是“多”;但他同时也没有完全否定“一”。只是他不是把“一”用来包容一切元素(大一),而是将它赋予构成世界的每一种元素(小一),使之成为有永恒的规定性的东西。在他看来,世上万物都是由这四种元素不同比例的混合而构成的,并随着这种结合方式的变化(比例的改变或完全解体)而变化或消灭;但严格说来,这四种根自身是不会变化和消失而只会转移的,它们每一种都是绝对的“存在”,没有产生和消灭、增加和减少,永远保持自己确定的性质,永远为“一”。当然,他也没有否定作为“多”的统一体的“一”,但他把这种“一”理解为由“多”聚集在一起形成的暂时现象,而不再具有超越一切多之上的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每一个“一”的生成都意味着另一个“一”的破坏,而这个“一”本身迟早也要被破坏。所以“任何变灭的东西的基质,都没有真正地产生,在毁灭性的死亡中也没有终结,有的只是混合物和混合物的交换,产生只是人们给这些现象所起的一般名称”。
。他通过对感性世界的广泛的、不带偏见的考察,认为必须把日常经验所公认的自然界四大元素即水、火、土、气全部看作构成自然界的基本要素,他称之为“四根”。在他这里,“始基”概念已经过时了,由这概念而来的对自然的一元的解释也被放弃了,他的原则虽然说的是“多”;但他同时也没有完全否定“一”。只是他不是把“一”用来包容一切元素(大一),而是将它赋予构成世界的每一种元素(小一),使之成为有永恒的规定性的东西。在他看来,世上万物都是由这四种元素不同比例的混合而构成的,并随着这种结合方式的变化(比例的改变或完全解体)而变化或消灭;但严格说来,这四种根自身是不会变化和消失而只会转移的,它们每一种都是绝对的“存在”,没有产生和消灭、增加和减少,永远保持自己确定的性质,永远为“一”。当然,他也没有否定作为“多”的统一体的“一”,但他把这种“一”理解为由“多”聚集在一起形成的暂时现象,而不再具有超越一切多之上的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每一个“一”的生成都意味着另一个“一”的破坏,而这个“一”本身迟早也要被破坏。所以“任何变灭的东西的基质,都没有真正地产生,在毁灭性的死亡中也没有终结,有的只是混合物和混合物的交换,产生只是人们给这些现象所起的一般名称”。
 只有那个作为自然整体的“一”,他称作“全体”的,才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但那原因不是因为它是“一”,而是因为它的每一个构成元素都是不可毁灭的。
只有那个作为自然整体的“一”,他称作“全体”的,才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但那原因不是因为它是“一”,而是因为它的每一个构成元素都是不可毁灭的。
这样,整个自然界在他眼里就成了一个由不变的“四根”相互结合与分离的各种感性事物的总和,在每个感性事物中都以不同的比例包含有这四种元素的微小粒子,在粒子与粒子之间有流通的孔道供别种的粒子通过,一个物体就是凭借这种方式和另一个物体交换物质粒子的。例如人的感觉就是通过感官(如眼睛)中的物质粒子和对象中的同类粒子互相“流射”而形成的,因此能够反映出对象的真实情况,这也是他为什么相信感觉到的东西不是不可靠的“意见”,而是唯一的认识途径的原因。不过,“孔道说”和“流射说”并没有使他想到元素粒子之间存在着“虚空”(非存在),相反,他仍然坚持说:“全体中没有任何部分是虚空,也没有过剩的。”
 他的想法似乎是,尽管同一种粒子之间存在着“孔道”,但孔道里却时时流着别种粒子,永远是充满的。在这里,他仍然坚持着埃利亚派的充满性(没有多余的空间),但却是各种元素紧紧黏合在一起的充满性,这些元素在黏连纠结中不断地在作相对运动。
他的想法似乎是,尽管同一种粒子之间存在着“孔道”,但孔道里却时时流着别种粒子,永远是充满的。在这里,他仍然坚持着埃利亚派的充满性(没有多余的空间),但却是各种元素紧紧黏合在一起的充满性,这些元素在黏连纠结中不断地在作相对运动。
上述解释虽然较好地解决了“一”和“多”的关系问题,但在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非常棘手的运动问题上却陷入了更大的困境。运动的来源问题在埃利亚派那里是通过根本否定运动来逃避掉的,恩培多克勒要返回感性世界,这个问题却是逃不开的。在感性世界中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唯有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也曾一度想用“火”来作为运动的根源。 但“四根”的假定严重地妨碍了他,他不能像赫拉克利特那样,认为火在燃烧之后自身变成了土、水和气,而只能认定火像其他元素一样是自身不变的物质粒子。自身不变而能变化万物,这在物质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只有精神的东西,如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才能如此)。所以恩培多克勒需要引入另一种性质的动力来解释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这就是“爱”和“恨”(“争”)。他认为爱使各种物质结合,恨使各种物质分离,遂造成万物的变化。但爱和恨本身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呢?对此他说得非常含糊,因而引起后来的研究者众说纷纭。
 的确,如果它们是物质的,那么它们或者是另外两种元素,宇宙的基本元素就不是四个而是六个了;或者是元素的属性,这时每种元素就不再是不变的,而是一会儿“爱”一会儿“恨”的了。如果是精神的,那么它们或者作为元素本身的精神力量(物活论),也会使元素改变其性质而不再是有定形的“一”;或者作为全体之外的推动力,那么它们的主体又是谁呢?(“爱”“恨”推动万物,谁又来推动“爱”“恨”?)看来,一切可能的解释都在违背恩培多克勒的自然结构设想,而只有最后一种解释似乎还留有一条出路,这就是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推动万物的想法。更有甚者,除了运动的来源问题之外,运动本身如何可能的问题现在就以尖锐化的形式突出出来了。因为恩培多克勒虽然把“多”纳入了“一”,但却没有把非存在(虚空)纳入存在。这样,“全体”虽然是由多个元素所结合而成的,但这些元素仍然像巴门尼德的“一”那样充满、结实,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空隙(“孔道”不是真正的空隙),因此这些元素相互纠结在一起,实际上一动也动不了。不引入虚空(非存在),恩培多克勒就还没有真正“打碎”巴门尼德的“一”,事物的运动也就根本不可能。对此迈出关键性的一步的,是德谟克利特。所以,从恩培多克勒引出来的两种思维方向就是阿那克萨哥拉的方向和德谟克利特的方向,我们先来看看与恩培多克勒同时代的阿那克萨哥拉。
的确,如果它们是物质的,那么它们或者是另外两种元素,宇宙的基本元素就不是四个而是六个了;或者是元素的属性,这时每种元素就不再是不变的,而是一会儿“爱”一会儿“恨”的了。如果是精神的,那么它们或者作为元素本身的精神力量(物活论),也会使元素改变其性质而不再是有定形的“一”;或者作为全体之外的推动力,那么它们的主体又是谁呢?(“爱”“恨”推动万物,谁又来推动“爱”“恨”?)看来,一切可能的解释都在违背恩培多克勒的自然结构设想,而只有最后一种解释似乎还留有一条出路,这就是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推动万物的想法。更有甚者,除了运动的来源问题之外,运动本身如何可能的问题现在就以尖锐化的形式突出出来了。因为恩培多克勒虽然把“多”纳入了“一”,但却没有把非存在(虚空)纳入存在。这样,“全体”虽然是由多个元素所结合而成的,但这些元素仍然像巴门尼德的“一”那样充满、结实,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空隙(“孔道”不是真正的空隙),因此这些元素相互纠结在一起,实际上一动也动不了。不引入虚空(非存在),恩培多克勒就还没有真正“打碎”巴门尼德的“一”,事物的运动也就根本不可能。对此迈出关键性的一步的,是德谟克利特。所以,从恩培多克勒引出来的两种思维方向就是阿那克萨哥拉的方向和德谟克利特的方向,我们先来看看与恩培多克勒同时代的阿那克萨哥拉。
阿那克萨哥拉(约公元前 500—约公元前 428)在认识论上主张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不可偏废的。他一方面强调感性的基础作用。与恩培多克勒不同,他认为感觉不是感官和对象中的相同元素的沟通,而是由双方的差异所导致的,如我们只能用热认知冷,“如果一个事物和我们一样热或冷,和它接触时我们是不会感到热或冷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感官的这种分辨力是有限的,“由于我们的感官的无力,我们不断判断真理”,因此需要理性的帮助。这两方面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可见的东西使我们的眼睛对不可见的东西睁开了。”
 阿那克萨哥拉就是用这种眼光来看宇宙的结构的。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宇宙是由无限多种多样的“种子”混合而成的,每一样种子原则上都是可感的,但由于体积无限小而看不见,所以“这些部分是只有理性才能认知的”
阿那克萨哥拉就是用这种眼光来看宇宙的结构的。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宇宙是由无限多种多样的“种子”混合而成的,每一样种子原则上都是可感的,但由于体积无限小而看不见,所以“这些部分是只有理性才能认知的”
 。例如在面包中就包含有血、肉、骨头的微粒即“种子”,人吃了面包就能长出血肉骨头来。同时,任何一种物质中都包含着所有的种子,只是其中某一种物质的种子占优势,所以才表现出是这种物质。于是,“一切中包含着一切”,“一切中分有着一切”
。例如在面包中就包含有血、肉、骨头的微粒即“种子”,人吃了面包就能长出血肉骨头来。同时,任何一种物质中都包含着所有的种子,只是其中某一种物质的种子占优势,所以才表现出是这种物质。于是,“一切中包含着一切”,“一切中分有着一切”
 。宇宙的这种“种子”结构与恩培多克勒的“四根”结构有很多相同之处:每个“种子”都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的“一”;它们充分混合并致密地构成“全体”,不留“虚空”;每个感性事物都是由同类的“种子”构成的,但都不是绝对纯粹的,只是这一类种子占优势或较大的比例而已;因此感性物质是构成世界的基础,但都是肉眼看不见的细小的微粒,因而还需要理性的帮助才能认识到。但与恩培多克勒不同的是,“种子”不限于四种,而是无限的,每种感性事物都有其种子(如骨头是小骨片构成的,金子是小金粒构成的,等等);四种“元素”(水火土气)本身在现实中也不是纯粹的,而是混有一切其他成分(骨、血、金,等等);所以种子的现实形态永远是无限可分的、复合的,只有在理论上才是真正的“一”。尽管如此,“种子说”与“四根说”一样,也没有能解决宇宙中的运动的可能性问题即“虚空”(非存在)问题。阿那克萨哥拉这时所关心的是运动的来源问题,在这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努斯”。
。宇宙的这种“种子”结构与恩培多克勒的“四根”结构有很多相同之处:每个“种子”都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的“一”;它们充分混合并致密地构成“全体”,不留“虚空”;每个感性事物都是由同类的“种子”构成的,但都不是绝对纯粹的,只是这一类种子占优势或较大的比例而已;因此感性物质是构成世界的基础,但都是肉眼看不见的细小的微粒,因而还需要理性的帮助才能认识到。但与恩培多克勒不同的是,“种子”不限于四种,而是无限的,每种感性事物都有其种子(如骨头是小骨片构成的,金子是小金粒构成的,等等);四种“元素”(水火土气)本身在现实中也不是纯粹的,而是混有一切其他成分(骨、血、金,等等);所以种子的现实形态永远是无限可分的、复合的,只有在理论上才是真正的“一”。尽管如此,“种子说”与“四根说”一样,也没有能解决宇宙中的运动的可能性问题即“虚空”(非存在)问题。阿那克萨哥拉这时所关心的是运动的来源问题,在这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努斯”。
努斯(
 ),本是“心灵”的意思,阿那克萨哥拉用来指一种超越于动物性和感性的心灵之上的理性心灵(这一用法也被后世所沿用,因此该词也直接被理解和翻译为“理性”)。这种理性心灵置身于整个感性自然的宇宙之外,不和任何事物相混合,它是独立存在的,无限
),本是“心灵”的意思,阿那克萨哥拉用来指一种超越于动物性和感性的心灵之上的理性心灵(这一用法也被后世所沿用,因此该词也直接被理解和翻译为“理性”)。这种理性心灵置身于整个感性自然的宇宙之外,不和任何事物相混合,它是独立存在的,无限
 的;“它是万物中最精最纯的,它有关于一切事物的所有知识,具有最大的能力。努斯能支配一切有灵魂的事物,不论大的或小的。努斯也支配整个漩涡运动,使它在最初开始旋转……所有一切过去存在的东西,一切过去存在而现在已不存在的东西,以及一切现在存在和将来要存在的东西,都由努斯安排有序。”
的;“它是万物中最精最纯的,它有关于一切事物的所有知识,具有最大的能力。努斯能支配一切有灵魂的事物,不论大的或小的。努斯也支配整个漩涡运动,使它在最初开始旋转……所有一切过去存在的东西,一切过去存在而现在已不存在的东西,以及一切现在存在和将来要存在的东西,都由努斯安排有序。”
 显然,这种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恩培多克勒有“爱”“恨”支配万物的观点,塞诺芬尼也提出过神“以他的心灵(努斯)的思想力左右一切”。但前者没有为爱恨找到一种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精神主体,后者的“神”虽然是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的,但并不用来解释万物的运动变化,而是架空的。阿那克萨哥拉则是第一次明确把精神性的努斯与物质性的世界作了区分(虽然还带有某些用语上的不精确),古希腊哲学自产生以来在运动问题上总是未能摆脱的“物活论”倾向在他这里也就在理论上有了一个了结;而后世凡是在涉及运动的最终根源时总是诉之于一个能动的精神实体这样一种思维定式(这成为西方哲学的一大传统模式)也就从这里开端了。
显然,这种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恩培多克勒有“爱”“恨”支配万物的观点,塞诺芬尼也提出过神“以他的心灵(努斯)的思想力左右一切”。但前者没有为爱恨找到一种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精神主体,后者的“神”虽然是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的,但并不用来解释万物的运动变化,而是架空的。阿那克萨哥拉则是第一次明确把精神性的努斯与物质性的世界作了区分(虽然还带有某些用语上的不精确),古希腊哲学自产生以来在运动问题上总是未能摆脱的“物活论”倾向在他这里也就在理论上有了一个了结;而后世凡是在涉及运动的最终根源时总是诉之于一个能动的精神实体这样一种思维定式(这成为西方哲学的一大传统模式)也就从这里开端了。
根据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努斯”在他那里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它和一切物质的东西不相干,是“最精最纯”的精神事物;二是它具有无所不知的认识能力,是最普遍的理性;三是它具有支配一切的最大的能力,相当于某种最高的意志;四是它由此成为万物的第一推动者;五是它之所以推动万物是有目的的,这就是使万物“安排有序”。最后,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还可以分出“大小”:“努斯不论大小,都是一样的”
 ,似乎暗示了最高的努斯和人心中的努斯是相通的、同一的。总之,努斯在他这里已经十分类似于后来基督教中的神或上帝,更有一些人将它等同于近代欧洲的“自然神论”思想。
,似乎暗示了最高的努斯和人心中的努斯是相通的、同一的。总之,努斯在他这里已经十分类似于后来基督教中的神或上帝,更有一些人将它等同于近代欧洲的“自然神论”思想。
 但其实努斯虽然是精神性的,但作为人格神来看还是不成熟的。阿那克萨哥拉只是用努斯来说明万物的最初动因,努斯的目的也只是“安排有序”,而并没有进一步的意思(如“善”“美”等),在实际解释整个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时,他就完全抛开努斯的作用,而用物质本身的相互关系来说明物质世界的各种现象了。
但其实努斯虽然是精神性的,但作为人格神来看还是不成熟的。阿那克萨哥拉只是用努斯来说明万物的最初动因,努斯的目的也只是“安排有序”,而并没有进一步的意思(如“善”“美”等),在实际解释整个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时,他就完全抛开努斯的作用,而用物质本身的相互关系来说明物质世界的各种现象了。
所以后来苏格拉底责备他没有把自己的原则贯彻到底,其实是对他的一种误解。不过,毕竟他的这种目的论的确启发了后来的哲学家们,为希腊哲学中的一次最大的转折,即从自然哲学转向精神哲学,提供了最重要的契机。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 460—公元前 370)对自然结构的看法,是把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哥拉的“化一为多、寓一于多”的方向再向前推进了一步,把非存在也纳入了存在着的世界。他认为,世界是由无数的原子和虚空(非存在)共同构成的,所谓“原子”(
 ),即“不可分”之意,它从巴门尼德的不可分的存在而来,但却不再是唯一的,也不再是与虚空完全不相容的,而是体积最小、小到不能再分而数量却无限多的物质微粒,它们的内部虽然是充实的,但却在周围的虚空中运动。所以,对于存在的世界来说,“‘存在’并不比‘非存在’更为实在,因为充实并不比虚空更为实在”,
),即“不可分”之意,它从巴门尼德的不可分的存在而来,但却不再是唯一的,也不再是与虚空完全不相容的,而是体积最小、小到不能再分而数量却无限多的物质微粒,它们的内部虽然是充实的,但却在周围的虚空中运动。所以,对于存在的世界来说,“‘存在’并不比‘非存在’更为实在,因为充实并不比虚空更为实在”,
 也就是说,非存在同样也是存在着的。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大胆的思想,由于它真正把巴门尼德的铁板一块的不动的存在“打碎”了,通过虚空给原子的运动留下了余地,于是就把自赫拉克利特以后、毕达哥拉斯以来困扰着希腊哲学的“运动如何可能”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但原子仍然保持了埃利亚派的“存在”的各种特性:它是不可分的、内部充实的,永恒不变的,抽象的(超越于感性性质之上的)。这样,一切自然界的变化都只发生在原子的互相结合的方式中,即由于原子的排列、位置和组合的不同而造成了千差万别的感性事物,原子本身相互之间则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只有大小、形状和运动方向的不同。例如他认为黑色是粗糙的原子,白色是光滑的原子,其他颜色则取决于原子运动方向的变化,但原子本身并没有所谓颜色。事物的产生是由于原子的聚合,事物的消灭则是由于原子的分离,而原子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原子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后单位,它们在虚空中按照直线作永恒的运动,由于方向不同而相互碰撞,逐渐形成漩涡运动并产生宇宙万物。在这样一个宇宙中,除了运动着的原子和虚空之外,什么也没有,人的灵魂是一种精微的原子,甚至就连神也是原子构成的,最终也要解体即死亡的。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纯粹唯物主义的哲学。但这种唯物主义也是非常机械的。德谟克利特相信原子的运动具有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所谓必然性,他理解为外在的强制性:“一切都由必然性而产生,漩涡运动既然是一切事物形成的原因,这在他就被称为必然性。”
也就是说,非存在同样也是存在着的。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大胆的思想,由于它真正把巴门尼德的铁板一块的不动的存在“打碎”了,通过虚空给原子的运动留下了余地,于是就把自赫拉克利特以后、毕达哥拉斯以来困扰着希腊哲学的“运动如何可能”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但原子仍然保持了埃利亚派的“存在”的各种特性:它是不可分的、内部充实的,永恒不变的,抽象的(超越于感性性质之上的)。这样,一切自然界的变化都只发生在原子的互相结合的方式中,即由于原子的排列、位置和组合的不同而造成了千差万别的感性事物,原子本身相互之间则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只有大小、形状和运动方向的不同。例如他认为黑色是粗糙的原子,白色是光滑的原子,其他颜色则取决于原子运动方向的变化,但原子本身并没有所谓颜色。事物的产生是由于原子的聚合,事物的消灭则是由于原子的分离,而原子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原子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后单位,它们在虚空中按照直线作永恒的运动,由于方向不同而相互碰撞,逐渐形成漩涡运动并产生宇宙万物。在这样一个宇宙中,除了运动着的原子和虚空之外,什么也没有,人的灵魂是一种精微的原子,甚至就连神也是原子构成的,最终也要解体即死亡的。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纯粹唯物主义的哲学。但这种唯物主义也是非常机械的。德谟克利特相信原子的运动具有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所谓必然性,他理解为外在的强制性:“一切都由必然性而产生,漩涡运动既然是一切事物形成的原因,这在他就被称为必然性。”
 所以他在对事物的研究中致力于寻求事物的原因,认为“只找到一个原因的解释,也比成为波斯人的王还好”。
所以他在对事物的研究中致力于寻求事物的原因,认为“只找到一个原因的解释,也比成为波斯人的王还好”。
 但由于原因后面还有原因,因果的链条是无穷尽的,所以实际上这种必然性在每个具体场合就都成了偶然性。
但由于原因后面还有原因,因果的链条是无穷尽的,所以实际上这种必然性在每个具体场合就都成了偶然性。
 所以许多人都认为德谟克利特是在用原子偶然的相互碰撞来解释事物的产生,
所以许多人都认为德谟克利特是在用原子偶然的相互碰撞来解释事物的产生,
 亚里士多德也说:“有些人把偶然性看成是天空和一切世界的原因。因为产生分离并建立世界上的秩序的这种漩涡运动,似乎是出于偶然的。这是很奇怪的。”
亚里士多德也说:“有些人把偶然性看成是天空和一切世界的原因。因为产生分离并建立世界上的秩序的这种漩涡运动,似乎是出于偶然的。这是很奇怪的。”
 他把这归结为德谟克利特没有为原子的运动指出最终的来源,这是切中要害的。这正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哲学的致命缺陷,即他虽然通过虚空的建立解决了运动如何可能的问题,但却回避了运动的根源的问题。因为在他那里,原子内部是充实的,运动不可能从内部产生,只能从外部接受,只能在原子之间传递,这种接受和传递对每个原子来说自然就是偶然的了,而那能够被原子传来传去的运动到底从何而来就永远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德谟克利特甚至没有看出自己的这个问题,他简单地认为原子“本来”就在运动中,运动为原子所“固有”。但原子的概念中并没有包含运动的概念,原子的性质和规定也不能说明运动如何由原子内部产生,这正是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不能不陷入机械论并且无法抵御唯心主义的攻击的原因。在他之后,希腊哲学就进入了一个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哲学”的时代。
他把这归结为德谟克利特没有为原子的运动指出最终的来源,这是切中要害的。这正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哲学的致命缺陷,即他虽然通过虚空的建立解决了运动如何可能的问题,但却回避了运动的根源的问题。因为在他那里,原子内部是充实的,运动不可能从内部产生,只能从外部接受,只能在原子之间传递,这种接受和传递对每个原子来说自然就是偶然的了,而那能够被原子传来传去的运动到底从何而来就永远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德谟克利特甚至没有看出自己的这个问题,他简单地认为原子“本来”就在运动中,运动为原子所“固有”。但原子的概念中并没有包含运动的概念,原子的性质和规定也不能说明运动如何由原子内部产生,这正是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不能不陷入机械论并且无法抵御唯心主义的攻击的原因。在他之后,希腊哲学就进入了一个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哲学”的时代。
然而,唯心主义的产生,精神哲学对唯物主义的超越,单凭对世界的动因作外在的反思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思维主体对自身(思维本身)的内在反思,人们很可能永远停留于运动的来源问题这一悬案而不觉痛苦,如原子必然是“自动”
的或“本来”就在运动中这种说法就类似于一种自我安慰。
 第欧根尼·拉尔修指出:
第欧根尼·拉尔修指出:
一切事物都是根据必然性发生的,漩涡运动是产生一切事物的原因,他(德谟克利特)称之为必然性;这种活动是为了得到平静,……不受恐惧、迷信以及其他情绪的困扰。

这种解释很可能是以后来伊壁鸠鲁的生活态度来附会德谟克利特,但并不能否认德谟克利特潜意识中也有这种“中止判断”的渴望。其实,德谟克利特的内在反思是极其痛苦不堪的,体现为他在认识论上的剧烈的矛盾性。他力图用他的原子论来解释人的认识过程,特别是人的感觉,但这种解释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使人的感觉变得可以信赖了,不再是虚幻不实的“意见”;另一方面却又恰好使感觉依赖于理性的解释,感觉本身就成了对理性的遮蔽。这就是他的“影象说”。
德谟克利特认为,灵魂是由构成火的同样的原子构成的,是一些最精细、最圆滑的原子,它们渗透于人的身体的原子之中,所以人的身体会有感觉。感觉是通过“影象”发生的,即每一个事物总是在产生一种“流射”(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因而会压缩周围的空气而放出自己的“影象”;影象触及人的感官如眼睛上,眼睛就把这种影象保留在瞳孔里,并通过眼睛里面的脉络传递到脑子里,这就产生了与外界对象相符合的形象。其他各种感官也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接受外部的影象的,这些接受既取决于对象的形象,也取决于感官的接受方式。当然,这一切都是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结果,而这一点并未反映在感官中,人们只看到影象而看不到是什么造成了影象。所以德谟克利特说:“甜是习惯俗成的,苦是习惯俗成的,热是习惯俗成的,冷是习惯俗成的,颜色是习惯俗成的。真实存在的是原子和虚空。”
 这样,他虽然承认感觉能够产生认识,但又把这种认识称之为“暗昧的认识”,认为理性(努斯)才能产生“真理的认识”。理性(努斯)当然也是一种原子,它作为人形成概念和推理的思维器官,居于人的灵魂和脑的中心,必须接受由感官传达来的资料才能起作用,“感觉和思想都由外界影象的作用而发生,它们在任何人中都不会没有影象的作用而发生的”;但理性和真理的认识“具有一种更精致的工具”。
这样,他虽然承认感觉能够产生认识,但又把这种认识称之为“暗昧的认识”,认为理性(努斯)才能产生“真理的认识”。理性(努斯)当然也是一种原子,它作为人形成概念和推理的思维器官,居于人的灵魂和脑的中心,必须接受由感官传达来的资料才能起作用,“感觉和思想都由外界影象的作用而发生,它们在任何人中都不会没有影象的作用而发生的”;但理性和真理的认识“具有一种更精致的工具”。
 所以,只有理性才能告诉我们事物的背后实际上只有原子和虚空。然而,德谟克利特并不想走向唯理主义,他希望兼顾双方。当他用理性的“真理的认识”来“抑低了现象的地位以后,又让感官以下面的语言来反对理性:‘可怜的理性,你从我们这里取得证据又要推翻我们?你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你的失败!’”。
所以,只有理性才能告诉我们事物的背后实际上只有原子和虚空。然而,德谟克利特并不想走向唯理主义,他希望兼顾双方。当他用理性的“真理的认识”来“抑低了现象的地位以后,又让感官以下面的语言来反对理性:‘可怜的理性,你从我们这里取得证据又要推翻我们?你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你的失败!’”。
 于是他提出了真理有三种标准:现象是了解可见事物的标准;概念是研究的标准;情感是取舍事物的标准,“凡是合乎我们本性的是应当寻求的,凡是违反我们本性的是应当避免的”。
于是他提出了真理有三种标准:现象是了解可见事物的标准;概念是研究的标准;情感是取舍事物的标准,“凡是合乎我们本性的是应当寻求的,凡是违反我们本性的是应当避免的”。
 显然,他试图以“情感”来作为感性现象和理性概念之间的仲裁。但情感在这时是多么脆弱啊!我们不是先得认识到什么是“我们的本性”,才能决定情感的取舍吗?如果使我们感到痛苦的恰好是符合我们的概念的,或使我们感到快乐的正是违背我们的概念的,我们又将如何取舍呢?他自己也说过:“愚蠢的人是按照命运提供给他们的好处来安排生活,但认识这些好处的人们则是按照哲学所提供的好处来安排生活。”
显然,他试图以“情感”来作为感性现象和理性概念之间的仲裁。但情感在这时是多么脆弱啊!我们不是先得认识到什么是“我们的本性”,才能决定情感的取舍吗?如果使我们感到痛苦的恰好是符合我们的概念的,或使我们感到快乐的正是违背我们的概念的,我们又将如何取舍呢?他自己也说过:“愚蠢的人是按照命运提供给他们的好处来安排生活,但认识这些好处的人们则是按照哲学所提供的好处来安排生活。”
 其实,当他一旦要为真理寻求一种“标准”时,感性就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了,因为所谓标准就是一种普遍规范,而感性的性质恰好就在于没有普遍性,它是相对于每个人和每次具体场合而不同的。所以德谟克利特在很多情况下都倾向于否认感觉的真理性,要“摒弃一切现象”,“摒弃显现在感官中的事物,断言它们都不是真理的表现,只是意见的表现”,甚至因此而主张“要认识每一事物的实在本性是不可能的”,“关于真理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真理隐藏在深渊中”。
其实,当他一旦要为真理寻求一种“标准”时,感性就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了,因为所谓标准就是一种普遍规范,而感性的性质恰好就在于没有普遍性,它是相对于每个人和每次具体场合而不同的。所以德谟克利特在很多情况下都倾向于否认感觉的真理性,要“摒弃一切现象”,“摒弃显现在感官中的事物,断言它们都不是真理的表现,只是意见的表现”,甚至因此而主张“要认识每一事物的实在本性是不可能的”,“关于真理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真理隐藏在深渊中”。
 但完全相反的话也被认为是他说的:“德谟克利特明白地说真理和现象是同一的,真理和显现于感觉中的东西毫无区别,凡是对每一个人显现,并且对他显得存在的,就是真的。”
但完全相反的话也被认为是他说的:“德谟克利特明白地说真理和现象是同一的,真理和显现于感觉中的东西毫无区别,凡是对每一个人显现,并且对他显得存在的,就是真的。”
 其实,否认我们知道任何真理正是把感觉现象当成真理的必然结果,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当德谟克利特“假定知识就是感觉”时,由于感觉的相对性,所以他就必然会认为“或者真理是没有的,或者至少我们于真理还没有明白”。
其实,否认我们知道任何真理正是把感觉现象当成真理的必然结果,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当德谟克利特“假定知识就是感觉”时,由于感觉的相对性,所以他就必然会认为“或者真理是没有的,或者至少我们于真理还没有明白”。
 这种内心矛盾是极其痛苦的:究竟相信感觉,还是相信理性?要不要完全放弃感官的见证?“和自己的心进行斗争是很难堪的,但这种胜利则标志着这是深思熟虑的人”,
这种内心矛盾是极其痛苦的:究竟相信感觉,还是相信理性?要不要完全放弃感官的见证?“和自己的心进行斗争是很难堪的,但这种胜利则标志着这是深思熟虑的人”,
 但要战胜这种矛盾对他来说还太遥远。马克思说这是“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以至于他虽然走遍了半个世界去增进经验、知识和观察,但据说最终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
但要战胜这种矛盾对他来说还太遥远。马克思说这是“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以至于他虽然走遍了半个世界去增进经验、知识和观察,但据说最终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
 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的这一矛盾只有在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的哲学”那里才得以解决。而自我意识的形成和独立,则是需要一系列中间环节的,因为在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之间,横亘着整个“精神哲学”。但德谟克利特虽然还未进入这个更高的层次,却也以自己深刻的内心矛盾和惨烈的自我否定行动,预示了一个努斯精神奋力超越感性现实世界向上飞腾的时代的到来。
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的这一矛盾只有在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的哲学”那里才得以解决。而自我意识的形成和独立,则是需要一系列中间环节的,因为在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之间,横亘着整个“精神哲学”。但德谟克利特虽然还未进入这个更高的层次,却也以自己深刻的内心矛盾和惨烈的自我否定行动,预示了一个努斯精神奋力超越感性现实世界向上飞腾的时代的到来。
原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