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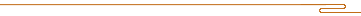
在十年前翻译《日本书法史》之时,即对嵯峨天皇《李峤诗残简》的文字内容极感兴趣。李峤在中国唐代诗上并没有什么显眼的地位,嵯峨天皇选取他的作品作书,其中似乎包含了一些什么内容。随即在三年以后我著《东瀛书论》时又对这一问题产生探讨的兴趣。我当时把它归结为两国文学交流史上常见的一种现象:因为日本当时仰慕中国文学的先进,而日本本国文学又都处在筚路蓝缕的初步阶段,因此选取中国文学对象作引进时,当然是选取最精致的、最能见出中国文学如诗的形式美体现得最充分的特征所在的对象。这样一来,被中国推为诗圣、诗仙的李白、杜甫未必能获宠,而像李峤那种咏物、应制诗却最有可能被日本人所激赏。因为这种精巧玲珑的咏物诗,无论在遣词造句,还是排比对偶方面,常常是最精到的——有如汉赋与元曲相比,在一个外国人看来,汉赋更具有典型性一样。贵族上层是以精巧为尚,而民间则以通达易学为准。老妪能解的白居易诗,和排比精巧的李峤诗,正构成了这样的对应。
但这是我几年前的结论。来日本以后,对于《李峤诗残简》的注意须臾未曾放过。而在翻阅了一些参考资料,又对李峤作了充分了解之后,我对过去的结论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是李峤本人的身份,对其诗传入日本可能有相当的影响。李峤字巨山,武后之世即起家,于中宗时为中书令,并被封为赵国公。这一时期是他仕途最得意之际。唐睿宗即位,李峤被黜,外放怀州刺史,历任外郡官至唐玄宗开元三年卒,时年七十。《新唐书》《旧唐书》本传皆指出他有两个方面的形象:一是地位绝高的政治家,另一是“文章之宿老”,是当时有地位的文学家。我想李白、杜甫等人无其地位之高,因此不太会被日本来朝的遣唐使所注目,最多只能限于民间个人交流而已;而当时宰执大臣亦有不少,却缺乏文誉诗名,因此对怀抱文学目的的遣唐使团中人也缺少吸引力。李峤兼有二者,宜其捷足先登也。
《李峤杂咏》又名《李峤百廿咏》,是五言律诗的咏物诗集,《新唐书·艺文志》录载。这是以十二部诗题,每部含诗十首的大型系列诗作。据说列十二目是对应于十二个月,每目十篇则是对应于每一旬日,取其数字整饬之意。因为都是咏物,故称百廿咏,亦有取其多而称“百咏”者,均属同义。
《李峤百廿咏》早在唐代即受到时人重视。李峤死后不数年的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张庭芳已对百咏诗进行注释,注释中包含了许多用典的说明;而在宋初,李昉奉宋太宗敕所编《文苑英华》,亦采录李峤百廿咏中的四十首入典。这可以说是《李峤百廿咏》在当时受欢迎的主要佐证。而唐代流行的百廿咏之传入日本,除遣唐使本人的努力之外,当然也与日本国内的文学态势有关。当时日本上层贵族对六朝咏物诗如“咏……”的诗风诗式已有了解,只是大都限于单题,未如李峤那样成系列而已。而且学者也已指出,嵯峨天皇所书的《李峤百廿咏》,无论如何说也是对日本平安文学予以重大影响的事实。这种影响,并不是《文选》文风和白居易诗风的影响所能取代的。它们是三个不同的影响进程。
《李峤百咏诗》传入日本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但藤原佐世撰《日本国在见书目录》中已有“李乔百廿咏一卷”,可见至少在宽平以前(889—898)即已有此诗流行。而嵯峨天皇既有《李峤诗残简》墨迹传世,当然更足证它在平安初已被传入日本。现代学者神田喜一郎《李峤百咏杂考》(1949)则指出在宽治八年(1094)古籍《中右记》中已见到关于李峤《杂咏诗》张庭芳注的记载。以《张庭芳百咏注》的序是写于天宝六年(日本天平十九年,747),当时日本停止遣唐使派遣,那么早期流行的应该是《李峤杂咏》本文。而《张庭芳百咏注》的传入日本,恐怕应该迟至唐末宋初。但在平安末期,日本汉籍中仿张庭芳注百咏之例,成《和汉朗咏集私注》《白氏新乐府略意》以及类书《幼学指南抄》等,其中有的直引《张庭芳百咏注》的典故出处。这样看来,《张庭芳百咏注》的传入时间,似乎又不止限于唐末宋初了,此中差距,恐怕至今尚未有一个很好的解说。
盛唐正处在五言律诗向七言律诗的转变期。受其影响,日本平安初期的文学风气也一如唐朝,平安初有《敕撰三汉诗集》,即已是七言律诗为主的格局。因此《李峤百咏诗》这样的五言律,显然已是过时了,作为作诗楷范,恐怕于理未通。我想它应该是以精巧玲珑、密丽秀媚的风格,在修辞上、用典上成为日本诗人向往的境界。即如《张庭芳百咏注》传入日本,应该也是作为诗学用典、学习修辞的某种依据或参照。很显然,对日本文化人来说,学习复杂的中国古诗用典并非唾手可得,是需要一些工具书或有针对性的参考书作为支持的。
《李峤百咏诗》与《张庭芳百咏注》固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刺激了日本汉文学的自我完善,但它毕竟是过去了的文学形式(又是异国形式),对偶工整、刻画精细的汉诗,首先取决于汉文字的单音节特点,而这种优势,与日本的表音假名相比显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因此,汉文、汉字的应用相对于日本文化生活而言,总也难以贴切与圆融。除非单学汉诗,倘以汉诗而与日本假名配合,显然有无法逾越的障碍,关于这一点,过去曾在《空间诗学导论》中作过细致的语言、文字等文学物质媒介方面的比较。我以为日本文学对李峤诗的引进与吸收,也不出这个限定。因此,《李峤百咏诗》在日本文学中必然是个“匆匆过客”。室町时期,日本已有《百咏和歌》出现,《李峤百咏诗》则逐渐消失,正是由于这种限定的作用。但到了这时,百咏诗被取代,作为一个具体代价,反而换来李峤作为诗人象征的新的比较文化含义,这又是始料未及的。古活字本《太平记》卷十二“大内里造营事附圣庙御事”条即有一段叙说,把菅原道真指为“风月之主”“文章之祖”。其中有一段话:
同年三月二十六日,延喜帝尚在春宫御座,召菅少将(即菅原道真)。曰:“汉朝李峤一夜能作诗百首,汝盍如其才,一时作诗十首,以备天览。”菅少将得赐十题,半时即作诗十首以呈。
文中的汉即是唐,非如我们中国史概念中的汉唐之分。对日本这样的外国而言,汉人即唐人。而“一时”之说,亦是指一小时或一个时辰,是个具体的时间界定。这样,李峤一夜成诗百首,而菅原道真则半时成诗十首,似乎是菅原道真诗才更胜于李峤,这当然只是《太平记》的记载,且以数量定优劣,本也是比较幼稚的说法。但我想,以李峤作为一个参照对象,作为日本当时朝野的文化意识,恐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近世以来,消失已久的《李峤百咏诗》由于舶来的《全唐诗》所载而再次引起文人们的兴趣。正德三年(1713),《和李峤百二十咏》《李峤咏物诗解》均纷纷登场,据说野村篁园还专有细密注释之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