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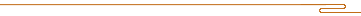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文学当然也属于外国文学的范畴。按理讲,中国文学、英美文学都在外国文学之列,当然都存在着一个接受、输出与输入的关系。即如明治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进日本,英、法、德、意等各国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样,从理论上说,中国文学应该也不外乎此一范围。
但事实上,作为外国文学的中国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却有着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绝非英、美、法、德诸西方文学所能取代。也就是说,中国文学不但作为客体文化与日本文学产生交流与影响,而且在古代还为日本文学的发生、形成立下汗马功劳。一个最有趣的事例是,我在日本大学里讲授中国文化史常常习惯以“汉文”指中文,于是顺理成章地认为汉文学当然也即指中国文学,但不久即发现这是一个极荒谬的错误。日本的“汉文学”是归于日本国文学科,而“中国文学”却归于外国文学学科。所谓的“汉文”,是指日本文学史中的汉诗文部分,它仍是日本文学而绝不是中国文学,只不过它常常与中国文学发生联系罢了。
当然,既是汉诗文,必然会用汉字。虽然作者是日本文学家,但对汉诗文的语言应用、解读方法以及汇注集释的一套,也全然不同于中国。因此在日本,一个汉诗文研究家可以完全不会讲汉语,他所擅长的是用日本方法去解读,当然无须先成为汉语专家了。
这就是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特殊亲缘关系。汉诗文(汉字)缔造了日本最初的文化;其后又时时作为推动力,催促日本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英、美、法、德文学与日本文学构成纯粹的对等关系,而中国文学则不;早期它是根基,后来又成为对等的一方,同日本文学互相影响,而这种影响仍以中国向日本的单向输送为多,日本文学反过来影响中国文学的事例极少,显然不具有典型性。因此,对日本文学史来说,中国文学既是一个客体,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说又曾经是个主体。中近世以来,同一时代的中、日文学构成互相影响关系,但由于有上古时代汉诗文对日本文学的缔造之功,又在日本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汉文学”现象并自成脉络,故它实际上无法拒绝中国文学“曾经”作为主体的价值——事实上,这种价值渗透到文学最基本的元素文字语言中去,无论何时何地都会体现出来。
作为外国文学的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横向影响,是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毋庸置疑,它必然会随着日本与中国之间政治关系与交通方式等等的盛衰而有浮沉起伏。一般而言,这种影响与交流大致可分为三期。
(一)以遣隋使、遣唐使为媒介的奈良、平安前期,即从延历、弘仁直到宇多天皇的宽平时期,约二百数十年。这是一个完全以吸收中国大陆文化而不存在自我本位意识的时期。中国文学最发达阶段——六朝至隋唐时期的赋与诗,对日本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影响,白居易、李峤即是此中的典型。而日本方面接受这种影响的,则大都是以王伯、廷臣、僧侣为中心的上层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中国的诗赋如醉如痴,但对中国的儒学却充耳不闻。
(二)以镰仓五山丛林名刹中的禅僧等进入宋元之时为标志,也构成一个有二三百年历史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唱主角的全是五山禅僧特别是曹洞宗的僧人。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也仍是诗赋,与第一期相近。至于哲学方面,对儒学也仍然不甚关心,充其量只是限于对宋学的一部分进行简略介绍而已。
(三)以长崎为贸易港口,通过它取得对中国文学的新认识,但在整体上,则是闭关锁国达三百年得德川幕府时代。这是第三期。长崎是日本全国唯一对外交通窗口。马上打天下的德川家康试图以文治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对文治上伦理依据的需求,使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儒学。于是刀入鞘、弓入藏,专攻儒学的文士奔走各地。儒学一旦昌盛,当然诗文大兴,但相比之下,与前两期已有明显的不同:①学习中国诗文,以儒学为中心,这是一种哲学先行的、非纯文学的交流。②诗赋仍是重点,但它显然已不是唯一的。小说、戏曲、戏文、笑话等庶民文学即俗文学,因为能迎合一般市民的需要而骤然兴盛。③就是单攻诗赋,也已脱离第一、第二期的那种生硬与做作的态势(日本称此为“和臭”),而具有更纯正的、足可与中国同行相对垒的高水准。经过几百年的孕育与淘洗,日本的汉诗文在江户时代形成了空前绝后的高潮。
江户时代是个很奇怪的时代。一方面,它锁国,限制与海外的来往,显得出奇的狭隘与保守;另一方面,它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范围,又比不锁国的平安、镰仓时期要大得多,从诗词歌赋到小说戏曲,应有尽有。一方面,它是以服从幕府的政治需要为中心,显示出上层统治阶级的意向;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对中国文学的欢迎,上至官府,下至里闾庶民,或是学者名士,无不翕然相从,具有最大的范围和最全面的影响力。一方面,在第一、第二期传统的映照下,江户时代学习中国古典诗赋的大家辈出,有像斋藤拙堂这样不让明清诗文的艺坛巨子;另一方面,在新兴的小说、戏曲文学中,我们又看到了像都贺庭钟、泷泽马亭这样优秀的俗文学专家,他们对中国小说戏曲的学习与借鉴,具有空前的水平。正是基于此,日本学者才认为,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说是空前,我想是指其范围之广、种类之富,比奈良、平安、镰仓时代不可以道里计。说是绝后,我想则应该是指江户的锁国造成了中国文学独尊,明治以后,与西洋的交流日渐发达,自然对中国文学不再有如此单纯的关注;来源既广,于某一专项的用功自然也就少。故而我们可以说,在江户时代,中国文学仍然是日本文学的唯一支柱,但到明治时代,则这“唯一”二字就用不得了。
毋庸赘辞,诗赋文学是正宗,是雅训,而小说、戏曲是俗事。但正是这个“俗”,在两国文化交流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因为俗故可推广迅速,能风行千里,万民同乐。具有精湛古典功夫的斋藤拙堂们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对嬉笑怒骂的小说、戏曲还是更乐于接受的,这就是“寓教于乐”的出奇功效。又比如,因为俗,故而可以为最基本的语言教材,在长崎成为“唐通事”们的教科书。诗赋艰涩,规范闳深,非久于此道者不易得。不比小说,平白如话,能想就能说能写,中国小说能成为日本“唐通事”们学习语言的教科书,此中的道理值得深思。虽然据说在日本也有接受圣训而视小说、戏曲为邪道的道学家,但从学习语言角度上取其利,却又无关乎文学载道的流派之争。从文学到语言学,横跨其间,左右逢源,此即中国小说以及衍生的日本小说之所以兴隆昌盛之故也。
奈良、平安时代的诗赋缔造了早期的日本文学,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轮廓的日本汉诗高峰,毋宁说是和歌成为上古至中世日本文学的标志。江户时代的中国小说继承热,却形成了一个从评介到翻案到创作的清晰的文字脉络,我想它之所以能成功,正在于其庶民性——它具有最广泛的社会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