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成长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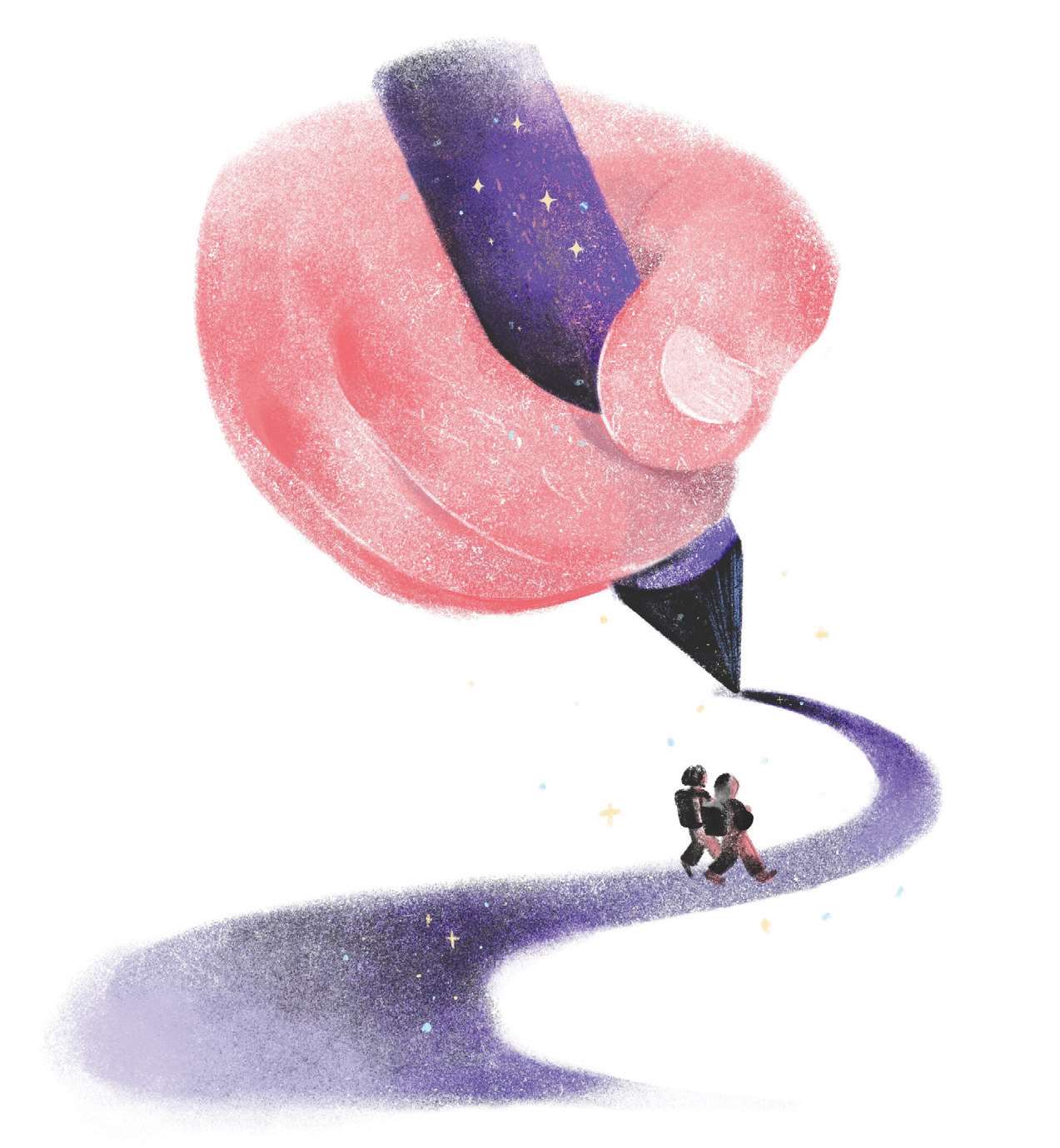
深夜失眠,我离开睡床,不知从何处翻出一幅陈旧的素描画。
画纸微微泛黄,浅灰色的铅墨勾勒出女孩青春的侧脸,线条利落,阴影恰好,女孩的鼻尖似有微光浮动——我知道画中人是我。
距离画作里的盛夏已有几年之远,我不再梳着“高入天际”的马尾,脸颊也不再有恼人的青春痘,但我仍无比怀念当时少不更事的自己。在那样的如花年华,所有缺点都会无限模糊,只留下正当最好年龄的美丽。
我摩挲着画纸,看到右下角用铅字写着“曾菀绘”,时间是2015年6月。
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那个漫长得不能再漫长的夏天。
高中时,我是老师口中常常表扬的对象,曾菀则是被批评的“常客”。当其他人都伏在课桌上埋头苦读时,只有她拿着一支笔,画教室里那些静止不动的物体,比如讲台上的地球仪,角落里的立式空调。除了绘画,她对法语小说亦情有独钟。素描本被老师没收了,她便偷偷在课桌下翻看16开本的法语小说。若素描本和小说都被“无情”地收缴,她只能悻悻地蒙头大睡。
曾菀的成绩差,这是公认的事实。无论老师如何费尽心力地干预,给她“开小灶”,频繁让她请家长,她都无动于衷。无奈之下,老师找到了我:“你成绩好,带一下她,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实在无法理解,那些一看就能落笔洋洋洒洒解答的题目,曾菀是如何“厚着脸皮”做到弃答的。我面红耳赤地为她讲题,她却笑得没心没肺,毫不上心。我时常学着老师的口吻,大声斥责她:“你知道吗曾菀,你差不多要‘废’了。”
“废”这个字似乎刺痛了她的神经,她瞬间收起玩世不恭的笑脸,显露出伤感的样子。
“你认为什么是‘废’?考不上大学吗?还是永远考不出高分?”她纤长的睫毛卷起几分忧思。
“当然啊!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考高分,上大学,不是吗?”我义正词严地看着她说。
“你知道我的梦想吗?我想做个画家、翻译家,去世界各地写生,把所有动人的法语小说翻译成中文译本……你觉得这是‘废’吗?”
“当然。”
我不假思索的回答成功把她还想说的话堵在了喉咙里。她垂着头,扯扯我的袖子:“你继续给我讲题吧。”
我大获全胜般“不可一世”地俯视曾菀。给她讲题的过程,是一遍遍增强自信的过程,是不断积累优越感的过程。她的目光越迷茫,我的内心便越不屑:怎么这么简单都听不懂?事实上,我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清晰的规划,也没有特别想上的大学,只是人人都在往前冲,我自然不能落在后头。
“不能落在后头”,这6个字像是促我奋进的“鸡血”。那么多个星光熠熠的夜晚,我都把自己牢牢“锁”在课桌前,于题海中翻腾。眼睛干涩至极,我忽地想看看窗外的宁静夜色,或许此时耀眼绚烂的星辉,这辈子只能遇见一次。
算了,我还是不想像曾菀那样,沉溺于虚浮的烂漫。
“你有没有喜欢的东西?”课后,曾菀突然问我。
我想了想:“学习算吗?”
她扑哧一笑,两颊漾起浅浅的酒窝:“当然不算。我说的是爱好——喜欢做的事,喜欢的东西。”
这是什么问题?眼看就要期末考试,她还在想一些有的没的,真是浪费时间。
“我喜欢写生,我想给所有我认为特别的人画画,我想画出他们的忧伤和快乐。”曾菀见我不作声,右手撑起下巴,自顾自地说话。我斜眼看她,发现她长长的秀发如瀑布般倾泻,阳光照进来,为她的发梢点缀了几缕金色。她的嘴一张一合,那些带着对未来美好憧憬的话语像是颜料,为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不少色彩。
“小时候,我挺喜欢吉他的。”我开了口。
她眼睛一亮,兴奋地抓着我的手,说:“其实我也喜欢吉他!我觉得弹着吉他唱着歌真的好酷,可我偏偏是个‘音盲’,怎么学也学不好,就放弃了。”
“我一直很想问你,你为什么爱看法语小说?”我问她。
“哈哈……你终于问我这个问题了!”曾菀笑盈盈地说,“我爸爸年轻时在法国工作,精通法语,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觉得法语是一门很美的语言,就让爸爸教我。现在,我基本能独立阅读较为浅显的法语小说了。”
我很少见她侃侃而谈的样子,提及爱好,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从眉眼到头发丝都透着喜悦。我忽然意识到这个世界除了学习还有别的一些东西,一些只要说起就“甜得像吃了蜜”一样的东西。那天,我和曾菀推心置腹地聊了许多,她为我描绘了一片我从未见过的景色,天地宽广如斯,我就像匍匐于井底的青蛙,蠢笨地把一小片空间放大为一个宇宙。
期末考试的卷子发下来,果不其然,曾菀的成绩排名还是垫底。我愠怒地指着错题问她:“考试前,同样的题,我是不是教过你?”
曾菀朝我抱歉地笑笑,又埋下头,继续涂涂画画。我好似一拳打在棉花上,看着她无所谓的模样,怒火噌地一下燃上心头。
“都什么时候了,还画画?你不知道离高考只有一年了吗?”
“画好了!”她欢快地放下画笔,用手指轻抹画作上的铅墨,“送给你。”
曾菀的画中不再是抬眼可见的静物,而是我——我从未被任何人画过,恍然见到自己的面容被高度还原在纸上,竟有种奇妙的感觉,像在照镜子,也像与双胞胎妹妹会面。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紧握画纸的手也在发抖。
“是不是画得很好?”她在我面前骄傲地仰起头。
“是……你画得确实很好。只是,为什么要画我?”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离高考只有一年了。”她随意地翻着自己的素描本,“我想送你一件礼物,好让你记得我,记得这个可能会‘废’掉的‘学渣’。”
我突然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她的面色昏沉沉的,眉毛耷拉下来,显得没精打采。
我第一次那么讨厌“废”这个字。但我不知如何安慰她,也许收回我对“废”的看法也有点傻气。我只好一言不发,细赏着她送我的礼物,任时间在耳边呼啸而过。
高考的脚步近了。
曾菀的成绩仍如一潭死水,激不起浪花。纵使我的成绩排名长期高居榜首,也没令我拥有太长久的快乐——只要想到我和曾菀如同分隔在地球两个不同的半球,我尽享春光,她寒冷如冰,春光也变得萧索无味。
但看曾菀,还是不以为意的样子,素描本越画越多,抽屉里的法语小说比一摞卷子还厚了。看到“三模”试卷被法语小说重重地压在下面,我怒气冲冲地把几本法语小说都扔在地上,抽出那张触目惊心的、被红色的大叉填满的试卷。
“曾菀,你要‘废’了知道吗?你要‘废’了!”我“挥舞”着象征耻辱的试卷,声嘶力竭地吼出这句话。所幸是在放学后,教室里的同学不多,但在场的人还是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
她吃惊地看着我,眼神里写满惊恐。我是如此讨厌说“废”这个字,却还在用这个字伤害她。也许我已经猜到一个月后她会考出怎样的高考成绩,也许我想将她心中对学习的热情点燃,也许我不愿她跌入漆黑莫测的深渊……也许,我只是在用不成熟的方式关心身边的人。
曾菀定定地看着我,涨红了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有掉落。她俯下身捡起她视若珍宝的法语小说,将它们悉数装入书包,而后头也不回地离开教室。
她的背影渐渐消失,与漫天铺染的夕阳融为一体,我想追上去,双脚却像被灌满了铅,重得拔不起来。我懊悔地挠着头,方才发生的一切有如断了片,徒留挥之不散的空虚和怅惘。
直至高考结束,曾菀都没有再和我说一句话。后来,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内一所一流的大学,老师和同学都纷纷向我表示祝贺。我惦记着曾菀,小心翼翼地问老师:“曾菀考得好不好?”
老师叹了口气,说:“好像考进了一所很一般的美术学院。”不知为何,我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她终于能够光明正大地追逐理想,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了。我仿佛看见她在郊外写生,在法国的街头为游客作画,仿若看到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在她因梦想实现而发光的脸上显得更加可爱。
没想到,当面跟她说一句再见,都成为一件极其奢侈的事了。自高考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在大学忙得晕头转向,争取奖学金,担任学生会主席,筹划大型活动。某次迎新晚会上,我看到学弟学妹沉醉地弹吉他,突然羡慕得眼眶通红。我好似瞬间回到几年前,一个长发如瀑布一般的女生正兴奋地抓着我的手,说弹吉他很酷。
是啊,弹吉他很酷,有梦想也很酷,只是我再也看不到很酷的那个她了。

(依依摘自《特区教育·中学生》2022年第7—8期,习K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