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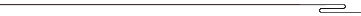
任何一个文化客体从一个背景进入到另一个背景,必然导致其意义的转变,以及产生一种语义再化(résémantisation)的动力。而这一切,我们只有通过考虑其转移的历史载体才能充分认识到。因此,尽管文化迁变的研究发展自某些特定的领域,我们仍然可以说,该研究与绝大多数的人文研究相关。抛开这个极简主义式的定义,便可以规避掉由术语本身暗含的一些错误线索。迁变,并不是输送(transporter)。迁变,更多地意味着变形(métamorphoser)。“迁变”这一术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简化为那个没有很好界定且极为平常的文化交流(échanges culturelles)问题。“迁变”,它不是指文化产物(biens culturels)的流通,而更多的指对文化产物的重新诠释。
文化迁变的概念是从十九世纪德国的德法关系的研究背景中发展而来
 。所以,在人文科学的发展中,德国作为参照,有着结构性的地位。从不断地通过阐明法国哲学与黑格尔及谢林的关系来构建法国哲学框架的维克托·考辛(Victor Cousin)开始,到奏响了第二帝国的盛会的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德国成为了法国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实证主义与圣西门主义也未能免于一场带有罗曼语研究特点或者古代科学研究特点的渗透。
。所以,在人文科学的发展中,德国作为参照,有着结构性的地位。从不断地通过阐明法国哲学与黑格尔及谢林的关系来构建法国哲学框架的维克托·考辛(Victor Cousin)开始,到奏响了第二帝国的盛会的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德国成为了法国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实证主义与圣西门主义也未能免于一场带有罗曼语研究特点或者古代科学研究特点的渗透。

要进入这个参照,一方面需要意识到,德国文化区域所发生的改组要比对这个文化区域的客观认知更为重要,另一方面需要探索迁移(translation)的载体。当专注于定义新生意义的阐释型的研究与关于两国之间转移的所有载体的历史社会学调查相遇时,文化迁变便开始存在。我们可以在圣西门主义那里找到对黑格尔的一种认知迹象的同时,也能观察到这些迹象所产生的全然独特的重构,以及密切关注到那些频繁出现的普鲁士的大学,正是通过它们知识元素得以传播。关于文化迁变的研究必须假设我们可以将一个文化对象归为己有,并且能使它从其构成的原型中解放出来,也即是说一种搬移(transposition),即便它与文化对象的原型相去甚远,也与其原型具有同等的正当性。因此,在人文社科领域,“比较”作为向不同区域开放的附加原则失去了它的意义,而应当由对杂交(métissage)与混合(hybridité)形式
 的观察所代替。从文化迁变的范畴来思考,也导致“比较”的恰当性变得相对化。实际上,后者为了记录他们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趋向于一种整体的对立化,但却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作比较的观察者,为了让二者对立而进行的收集,实际上投射了其自己的范畴体系,也制造了一些由他简化的对立,而通常他自己就属于对立二者当中的一方。建立于印欧语系的比较语法之上的比较主义尤其具有局限性。通过比较历史着手研究欧洲以外的疆土似乎尤为棘手,一般而言就是通过疆土、文化或者文学发生关系来进行研究,但这种情况下它们之间一种根本的质的不同已被悄然地预设。
的观察所代替。从文化迁变的范畴来思考,也导致“比较”的恰当性变得相对化。实际上,后者为了记录他们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趋向于一种整体的对立化,但却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作比较的观察者,为了让二者对立而进行的收集,实际上投射了其自己的范畴体系,也制造了一些由他简化的对立,而通常他自己就属于对立二者当中的一方。建立于印欧语系的比较语法之上的比较主义尤其具有局限性。通过比较历史着手研究欧洲以外的疆土似乎尤为棘手,一般而言就是通过疆土、文化或者文学发生关系来进行研究,但这种情况下它们之间一种根本的质的不同已被悄然地预设。
同样,影响范畴,词源学足以呈现它的不可思议的维度,它必须被一种可从历史上确认的接触以及由这些接触所引起的适应与再诠释的批评方法所替代。同样应该的做的,是避免传播中真实性的概念,或者避免传播中原初概念对复制概念的优越性。我们知道,谢林(Schelling)的一位次要弟子,克劳泽(Krause),引致了西班牙社会一个思想流派的产生——克莱泽主义,这个被弃置在德国哲学以外的主义,实际建立在对(谢林的)文本的粗略认知之上。现实仍然是,这个附带地标志着谢林的形而上学向政治思想的纪律性的转变的自由思想形式,与促使它生成的动因(谢林的思想)是同样正当的。我们不考量克劳泽主义对谢林的忠诚程度,我们也不评判荷尔德林(Hölderlin)对索福克勒斯(Sophocle)所作的那些颠倒文本段落的翻译的精确程度。至少,在一个传统被引入与重建之前,对它的认知可以是非常简短的。
所有可能从一个国家、民族、语言或者宗教的空间到另一个空间去的社会群体都能够成为文化迁变的载体。运输商品的商人同样也传递了象征或者知识。翻译者、一个外国文化区域的专家教师、因政治或者经济或者宗教原因流亡并移居他国的人、回复订单的艺术家以及外国雇佣兵,都构成了文化迁变的载体,也很应该考虑到他们作为不同的媒介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我们同样可以很好地回想起那些建立在诸如书籍或艺术品等物品流通之上的迁变。图书馆史、外国收藏品创建史、出版品传播史、翻译史,与收藏史及艺术品跨民族国家市场史
 一样,都属于文化迁变研究的一部分。当我们从人媒介进入到书籍或者档案媒介,文化迁变的问题便会遇到“记忆”的问题。事实上,图书馆或者档案馆趋向于固化同一性(identité),因为它们的管理模式常常需要我们为之建立历史。它们通常遵循一种合理的原则被组建。这一原则与群体(大多数时候是国家或者民族)的同一性表现相一致。对文化迁变变得谨慎,就意味着至少以一种可能的方式去审查,通过研究那些常常被边缘化的引入元素,去审查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集体记忆结构。毕竟,一个外来记忆元素的流动绝不会是偶然。当我们要在输入方(contexte d’accueil)的记忆层里寻找外来元素时,通常会遇到这个背景下千头万绪的记忆信息。这就应该区分尚且无用的累加记忆(mémoire accumulé)与有效记忆(mémoire effective)。
一样,都属于文化迁变研究的一部分。当我们从人媒介进入到书籍或者档案媒介,文化迁变的问题便会遇到“记忆”的问题。事实上,图书馆或者档案馆趋向于固化同一性(identité),因为它们的管理模式常常需要我们为之建立历史。它们通常遵循一种合理的原则被组建。这一原则与群体(大多数时候是国家或者民族)的同一性表现相一致。对文化迁变变得谨慎,就意味着至少以一种可能的方式去审查,通过研究那些常常被边缘化的引入元素,去审查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集体记忆结构。毕竟,一个外来记忆元素的流动绝不会是偶然。当我们要在输入方(contexte d’accueil)的记忆层里寻找外来元素时,通常会遇到这个背景下千头万绪的记忆信息。这就应该区分尚且无用的累加记忆(mémoire accumulé)与有效记忆(mémoire effective)。
一个文化的迁变从来不是只发生在两个语言、两个国家或者两种文化区域之间的,这里几乎总会涉及到第三者。所以,我们必须把文化迁变更多地当作是多极的、多个语言区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忽略掉启蒙运动的英国根源与以及它在俄国的延伸部分,就会使法国启蒙运动进入德国变成一个狭窄的现象。着手凯特琳二世时期的俄国文化,就要理解沙皇俄国、德国女皇时期的文化、她对法国的兴趣,以及她透过法国文学的滤镜所看到的一个意大利,这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过,如果说确认那些众多文化空间的相遇地点是很容易的话,这些地点我们可以用一种新逻辑主义的观点去把它们看作“全球化的门户”(portail de globalisation),我们也仅仅能对那些数量有限的术语的相遇进行描述。而要呈现一种交汇的全貌仍然是不可行的。
即使当我们着手于两个文化区域之间的迁变时,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把其中任何一个视作是同质的和原初的—因为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之前“迁移”(déplacement)的结果,都有一段持续的混合的(hybridation)历史。当我们试图描述德法之间的文化迁变时,很应该记住,无论法国还是德国,都不是实体(essence)。它们作为整体(entité)还是具有争议的,一种描述的必要性迫使我们假设一个短暂时间内存在着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将会对德国或者法国,古希腊文化或者拉丁文化进行洗礼。但我们立刻就会努力证明这些整体是铸就在“引入”(importation)之上的,对于法国而言是德国,对于拉丁文化而言是希腊文化,或者对于经院哲学而言是阿拉伯国家,对于中国佛家而言是印度,等等。文化迁变研究揭示出文化区域的层叠交错(imbrication)。所以说,文化区域只是一种临时样态(configuration provisoire),但对于理解文化流通现象还是有必要的。
人文科学通常与受限于特定语言空间的民族叙事相一致。它们在引入与引入所伴随的重组的基础上制造同一性。有系统地重审这些同一性的构建,为文化迁变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调查田野,其范围将可能是人文科学的跨民族国家史。
即使是哲学,和数学一样,也追求一种原则的普世性。在面对承载概念的语言时,哲学也追求一种概念的独立性。哲学在十九世纪期间的发展显然是带有德国的印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世俗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也是有赖于一种革新的康德主义。无论夏威容(Ravaisson)的谢林(Schelling)还是科耶夫(Kojève)的黑格尔(Hegel),自然都与他们所依靠诠释的本源不一致。更有意义的是确定他们的诠释中添加了什么,但尤其要观察的是意欲创建一种民族国家公民道德的知识传统建立于引入的参照的基础上。如果对胡塞尔(Husserl)的引入不是先于那些在其基础上所转化的其它形式的流传,现象学将可能变得难以理解。此外,在这一点上,法国哲学并不是唯一的。马提亚斯·格鲁特(Martial Guéroult)早已致力于揭示费希特(Fichte)对法国革命的主张以及对他那个时代在法国所谈论的政治立场的选取都有所汲取。当代法国哲学有重要意义的边缘部分,用英文讲就是“一种心灵哲学”,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奥地利哲学的英文翻译。毫无疑问,这一边缘部分的倾向与构建一种同一性符合一样的纲要。这种同一性,想要通过一个以引进文化为参照的系统来实现它的普世化。此外,这个系统的核心概念里有很大一部分被忽视了的语言学上的锚固(ancrage linguistique)。
在艺术史上,一种迁变模式由德国阐释学在意大利的应用,以及前期年代层在后期年代层当中的组成部分的研究(历时性的迁变,比如文艺复兴里的中世纪)产生的。当海因里希·沃尔夫(Heinrich Wölfflin)林将其艺术史的基本概念应用于意大利时,他仅仅只是将德国心理学范畴搬到了另一个地方
 。当卡尔·贾斯蒂(CarlJusti)把类似于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诠释学的范畴应用到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的艺术上,或者他那个时代的委拉斯开兹现象上时,也没有太大的不同。
。当卡尔·贾斯蒂(CarlJusti)把类似于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诠释学的范畴应用到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的艺术上,或者他那个时代的委拉斯开兹现象上时,也没有太大的不同。
 当安东·斯普林格(Anton Springer)在德国中世纪艺术当中,观察到根据新背景的需要而被重新诠释的古代的痕迹时,他仅仅分析了文化的迁变,而他的这些观察被在佛罗伦萨旅居期间的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读到后当作范例。
当安东·斯普林格(Anton Springer)在德国中世纪艺术当中,观察到根据新背景的需要而被重新诠释的古代的痕迹时,他仅仅分析了文化的迁变,而他的这些观察被在佛罗伦萨旅居期间的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读到后当作范例。

作为科学的人类学非常注重文化之间的关系,注重它们之间的接触以及赋予文化活力的相互渗透的形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的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就是从明登(Minden)移居到美国的德国人。在美国,他将格林兄弟(Frères Grimm)民间童话收集的考察模式应用到西海岸的印第安人研究,特别是对夸夸嘉夸族(Kwakiutl)
 的研究当中。重要的是收集印第安语的故事,并且,在进行分析确认它们所揭示的印第安社会之前,便将其记录下来。这尚属首次。当博厄斯研究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contamination)时,他力求观察那些可认出的历史性接触以证实那些系统的复现(récurrence systémique),与那些结构上的同源。他并不试图作比较,但是力求观察层叠交错的发生,并且追踪那些相互影响。不仅仅博厄斯的生平与学术历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迁变的案例,他所发展出来的方法也尤为适用于此种现象。博厄斯以一种清晰的方式,让人类学文化迁变的观念变得更为具体。他的作品在这一视角下的细致分析之所以让人信服,那是因为他的众多亲近弟子都是来自欧洲日耳曼地区的移民,并且他们都参与了一个大规模的外来知识向美国的转移。总体而言,根据博厄斯所传递的观念,语言是一个文化的主要标签。这一观念承自于洪堡(Humboldt)。并且通过海曼·施泰因塔尔(Heymann Steinthal)和某些斯拉夫学生所起的媒介作用,我们可以在整个欧洲尤其是俄国追踪到它的踪迹。在那里,这一观念成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形式主义基石的一部分。当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尤其是雅各布森(Jakobson)将他与博厄斯联系在一起)来到美洲,遇见博厄斯,人类学上基本迁变的两种形式交汇了。
的研究当中。重要的是收集印第安语的故事,并且,在进行分析确认它们所揭示的印第安社会之前,便将其记录下来。这尚属首次。当博厄斯研究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contamination)时,他力求观察那些可认出的历史性接触以证实那些系统的复现(récurrence systémique),与那些结构上的同源。他并不试图作比较,但是力求观察层叠交错的发生,并且追踪那些相互影响。不仅仅博厄斯的生平与学术历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迁变的案例,他所发展出来的方法也尤为适用于此种现象。博厄斯以一种清晰的方式,让人类学文化迁变的观念变得更为具体。他的作品在这一视角下的细致分析之所以让人信服,那是因为他的众多亲近弟子都是来自欧洲日耳曼地区的移民,并且他们都参与了一个大规模的外来知识向美国的转移。总体而言,根据博厄斯所传递的观念,语言是一个文化的主要标签。这一观念承自于洪堡(Humboldt)。并且通过海曼·施泰因塔尔(Heymann Steinthal)和某些斯拉夫学生所起的媒介作用,我们可以在整个欧洲尤其是俄国追踪到它的踪迹。在那里,这一观念成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形式主义基石的一部分。当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尤其是雅各布森(Jakobson)将他与博厄斯联系在一起)来到美洲,遇见博厄斯,人类学上基本迁变的两种形式交汇了。
文学上,强调翻译(尽管在书店里大量存在,也总是被认为是一个外来的,有些周边的元素);强调文学传统之间的衔接手法;强调每个文化所构建的外来圣殿(尤金·梅尔基奥尔·德·沃格于埃(Eugène-Melchior de Vogüé)认为,托尔斯泰(Tolstï)即使没有成为法国作家,至少成为了法国外国文学圣殿里的核心作家。);强调那些用非母语写作的作家(从用德语写作的土耳其裔作家费希顿·赞莫格路(FeridunZaimoglou),到用法语写作的俄裔作家安德烈·马金尼(Andrei Makine),再到用英语写作的索马里作家努鲁丁·法拉赫(Nuruddin Farah))。从这一角度看,文学史可以通过不局限于民族国家元素的交替连续性的视角被重新审视。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rge)深受其所翻译的马拉美(Mallarmé)的启发,荷尔德林深受卢梭(Rousseau)的启发,所以在德国的抒情诗史当中,我们不应该试图重构那些不将这些外来传入考虑在内的演变关系。安德烈·舍尼埃(André Chénier)与席勒(Schiller)对于同一时期的俄国文学也是一个道理。这样一来,整个文学史须得重新写过。
关于民族国家的(或者范围更大一点的)文学文化的认知,一般被邻近的文化区域的科学所限定,比如德国的罗曼语语文学或者法国的斯拉夫语文语文学。这些科学产生于被研究的文学的空间与观察者自己的视野二者之间的折衷。除此以外,这些科学还可以成为引入的对象。如果我们认为,比如说德国的罗曼语语文学(就像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迭斯(Friedrich Christian Diez)所体现的那样)的方法是将罗曼文化视为整体,其标志性的语文学对象的理解方式明显借自德国传统,那么,加斯东·帕里(Gaston Paris)将其引入法国,且优先应用于法国中世纪研究,这样一来就与研究对象本身——罗马尼亚(romania)的重新诠释相呼应了。
因为文学史见证了文化的迁变,所以从文化迁变的视角审查文学史是极具意义的。同样重要的是,在所有的欧洲国家,文学史都成为了民族国家的构成中不可或缺一的部分。从《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一直到《伊戈尔远征记》(Dit du prince Igor),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民族可以离开奠基文本而存在,这个奠基文本我们同样可以在那些遥远的空间当中找到(例如《金云翘》(Histoire de Kieu)之于越南文学,《豹皮骑士》(Le Chevalier à la peau de panthère)之于格鲁吉亚,吉尔伽美什史诗(épopée de Gilgamesh)之于古代)。不过,很明显的是,这些部分常常与外来的引入有关。爱沙尼亚史诗,克列茨瓦尔德(Kreutzvald)所作的《卡列维波埃格》(Kalevipoeg),便是后赫尔德时代(post-herdérienne)的德国传统下培养出来的语文学家之手笔。这些,我们同样可以在芬兰大型史诗,隆洛特(Lönnrot)的《卡勒瓦拉》(Kalevala)当中感受到。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对荷马史诗的解读当中存有的莪相(Ossian)诗歌的残篇,其实是一个民族的成果。从莪相和赫尔德(Herder)开始,缔造民族的作品模式被整个欧洲所接受。从文化迁变的角度对文学史的回顾,便能让那些被认为是奠定了国家民族文学的原型的流传更为突显。
其实,某些人文科学一上来就会超出国家民族的界限。东方学(orientalisme)就是例子,能够从十九世纪初发展起来:就像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这本期刊能够被看成是德法对于近东尤其是阿拉伯、土耳其与波斯的文化文学的探索的核心刊物。这个新学科的中心人物,西尔维斯特· 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在亚洲研究方面算是“德国的大师”(《praeceptorGermaniae》),因为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大多数东方研究教席的主持者都是他的学生。在法国与德国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再加上英国,意大利和俄国。这些国家不再试图创建隔离东方的科学,他们试图拥有一个共同的认知,这一共同认知建立在对两方面的妥协之上,一方面是他们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是他们自身的概念框架。
关于文化迁变的研究是跨国家民族文化史学史的一部分。但它不能仅仅局限在就现代欧洲国家民族空间之间层叠交错形势的分析。它能够很好地找到其他的应用的场地。为了成为远东权力的标志,中国的皇廷使用了基督教传教士所传入的欧洲数学,这完全符合一个文化迁变的现象,正如普鲁士人在明治时期日本的社会改革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样。我们习惯于将罗马帝国或者古希腊世界看作是同质的整体,古代如此,到现代仍然如此。但是,考古学很早以前便已经观察到了混杂的现象,它所寻找的是埃及与希腊之间,米索不达米亚数学与希腊数学之间,诸多难以勾勒的转移。视野的转化,会引导我们将古代看作是适应于环地中海文化的元素的一连串的重新占有的背景。在现今土耳其的海岸上,那些曾经古希腊城市住满了卡利亚人(Cariens)、吕基亚人(Lyciens)以及适应了当地文化的吕底亚人(Lydiens)。而安纳托利亚(Anatolie)的赫梯古国城市(Villes hittites)的那些考古遗迹,足以证明外来的米索不达米亚殖民的存在。不过,层叠交错并不是只有唯一的意义。古代文化与其周边居民的相遇也会使新的文化实体得以出现,从希腊伊朗佛教文化的巴克特里亚或者索格底亚那(la Bactriane ou la Sogdiane gréco-irano-bouddhiques)
 ,到罗曼高卢文化皆是如此。
,到罗曼高卢文化皆是如此。
现代欧洲的自我认知所基于的社会的早期历史是迁变的结果,这让重新审问欧洲的统治地位变得合理。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的《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的假说使谢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关于黑色埃及的作品(《黑人民族与文化》(Nations nègres et culture),1954)更为可信,后者旨在指出,在非殖民化的早期,古代非洲的文化遗产就存在于欧洲文明的中心。所以,文化迁变的问题可以包含一部分后殖民的研究方式。但它并不仅仅停留于此。当一位中世纪文化研究者阐明由大师埃克哈特(maître Eckhart)所代表的德国神话,其智力理论实际上是借自阿威罗伊
 (Averroès),以及阐明了希腊哲学绕道伊斯兰思想成为了希腊研究的经典课题的时候
(Averroès),以及阐明了希腊哲学绕道伊斯兰思想成为了希腊研究的经典课题的时候
 ,这些都不是后殖民的问题,而是概念体系的流传问题。这些概念根据输入方的背景而改变了它们的意义
,这些都不是后殖民的问题,而是概念体系的流传问题。这些概念根据输入方的背景而改变了它们的意义
 。
。
文化迁变的史学研究使中心的观念变得尤为相对化。非常清楚的是,历史一旦超越了国家民族或者文化区域的界限(为了融入那些更大的同心圆,历史是发散的),它就会将它所属的文化区域自身作为参照的中心。十八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 [1] ,当全球通史开始在哥廷根大学被撰写时,当阿拉伯半岛、印度或者中国都被这场人类历史的总体扫测纳入其中时,我们认为欧洲是中心,并且认为周边文化以进入历史的方式融入进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中心有着清楚的界定——欧洲的。我们不禁要想,所谓“《通史》”(《global history》),其自身就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为中心而构建的。在历史进程里,其他的中心也可能存在。我们想到了中华帝国,想到了中国皇帝们在地图绘制上的苛求——中国必须呈现在已知世界的正中。我们想到了凯末尔主义(kémaliste)的土耳其,它习惯于将安那托利亚(Anatolie)绘制在世界地图的中心,它自身便在土耳其世界的正中,它与阿尔及利亚一侧的距离与它到到中亚一侧的距离相等。 [2] 对中心的重新审视,是关于文化迁变的研究的一个基础部分。
视野中心的根本的相对性,导致了总体(global)与个别(particulier)的相遇。每一个特殊个体必须有一个通向总体的路径。下面是这种相遇容易发生的地方:城市中心、大学、图书馆,这些我们认为是“总体性门户”(《portails sur la globalité 》)。研究这些地方(关于这些地点,我们避免给出一份限定的名单),显然构成了文化迁变研究中的重要目标。我们可以想一个地方,比如哥廷根图书馆,这是日耳曼国家的主要图书馆,也是十八世纪以来第一个收集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科学文献用来培养一种人类的普世科学的教学的中心。而用另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想起那些汇聚了众多民族的城市,比如维尔纽斯/维尔纳/维尔诺(Vilnius/Wilna/Wilno),一座同时拥有犹太、德国、波兰、立陶宛、卡拉派(karaïte)和俄罗斯等众多文化的城市,它是犹太文化的传播地,也是波兰以及立陶宛的民族文学的发生地。这些“总体性门户”,将文化迁变与地点的范畴结合了起来。
一次文化的迁变有时就是一次翻译。只需要看看任意一个语言里的一本小说的版本与它在另一个语言里的翻译,观察一下占有封面四分之一的附带介绍、插画、尺寸、那些系列的背景效果甚至排版,便知道一个翻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一个对等物。当它只是简单地从原型里获取灵感而不去说明的时候,就如同某些拉丁作家从希腊原型里获取灵感那样,它更不是对等的。卢克莱修(Lucrèce)绝不是德谟克利特(Démocrite)的对等物。翻译让一个事实更为显然,概念根植于语义的背景当中,与翻译有关的语义背景的转移体现了意义的一次新的构建。但翻译同样也属于历史社会学或者书籍史的研究范畴,这些领域的研究明显依赖于与文化迁变有关的研究。就翻译者们的群体传记学(étude prosopographique)的研究将我们引向对语言获取模式的探问,以及对选择搬移(transposer)书籍的标准的探问。重要的是分析出版社的策略,分析它们的运作模式以及翻译作品所遇到的反响。从七十士译本(traduction des Septante)到十九世纪康德(Kant)的早期翻译,费尽周折才有了德文文本,以及弗里德里希·戈特洛布·伯恩(Friedrich Gottlieb Born)晦涩的拉丁文版本与温琴佐·曼托瓦尼(Vincenzo Mantovani)意大利语版本。就翻译现象的非语言学的分析是文化迁变研究的主轴之一。
通过连结对个别(particulier)以及对普遍(universel)的描述,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解全球史或者说至少大的跨国家民族的大体轮廓的途径。对于整体的观察应该从具体情况甚至是独特性出发。观察两个文本层与两个变体的更替的语文学家或者遗传学家所做的细致严谨的工作,往往伴随着与修正着关于概念的“环球航行”(circumnavigation)的思考。任何一个地球平面球形图都不可以简略地绘制江河与海岸。正是语言的多样性能够推断出翻译的语义转移。文化迁变研究更多的是一个进展中的理论,而不是学说的一次尝试,它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新视点。
[1] Luigi Marino, PraeceptoresGermaniae: Göttingen 1770-1820, Göttingen, Vandenhoeck&Ruprecht, 1995; Hans-Erich Bödeker, Philippe Büttgen et Michel Espagne (éd.), Göttingenvers 1800. L”Europe des sciences de l’homme, Paris, Le Cerf, 2010.
[2] Étienne Copeaux, Une vision turque du monde à travers les cartes de 1931 à nosjours , Paris, CNRS Édition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