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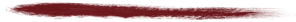
玉峰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后,便留在南京大学任教,留校20年来,兢兢业业,专心教学和科研,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科研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作为昔日的导师和同事,至今仍为之哀恸不已;凡与玉峰熟悉的亲友和同行学者,闻此噩耗,也无不扼腕悲叹。玉峰虽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本书便是其中的一部。元代《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认为,鬼有“已死之鬼”,也有“未死之鬼”,衡量是否是“鬼”,不是以生或死来确定,有的人虽活着,但已是鬼;有的人虽已死去,但是“未死之鬼”。如有的人虽有学问,但不事著述,“于学问之道,甘于暴弃”,因无著作留存,“临终之后,漠然无闻”,不为后人所纪念,这样的人无论其生或死,皆为“已死之鬼”;而那些既有“高才博识”,又有著述留存后世的人,如当时的曲家,虽然“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但他们创作杂剧,“俱有可录”,能留存后世,故这样的人即为“未死之鬼”。按钟嗣成的这一标准来衡量,玉峰即为“未死之鬼”,他既有“高才博识”,又有著述留存后世,为后人所纪念,虽死犹生。
玉峰的这部著作,收录的多是曾刊发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故最能代表他的学术水平和治学风格。在短暂的学术生涯中,玉峰已形成了他独特的治学风格。他思维敏捷,不从众,也不盲从前人的结论,敢于标新立异。不仅对前人尚未研究的课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且对于一些为学术界多有论及且已有结论的课题也加以探讨和研究,提出新的见解。本书收录的文章,便充分显示了他的这一治学风格。如他在《“曲”变为“词”:长短句韵文之演进》一文中,对明清以来诗词曲的沿革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自明清以来,诗演变为词,词又演变为曲,这已成为学界的通识。玉峰对几百年来文学史上这一成见提出了质疑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学艺术的历史演进虽受其所处历史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亦有其自身特有的演进逻辑。如“词”与“曲”的沿革关系,从时代的角度来看,“词”产生在前、“曲”产生在后,但不能仅从时代的角度来探讨两者的沿革关系,如从文体的本质特征来看,即从文体的规范性和稳定性来看,无论是唐代的曲子,还是宋元时期的南北曲,最初都产生于民间,其文体无规范;而“词”则是文人对产生于民间文体无规范的“曲”进行规范化后产生的,据此,长短句韵文的演进不应是“词”变为“曲”,实即是“曲”变为“词”的过程。同时,他认为,“诗变为词”、“词变为曲”这一观念的产生,并成为数百年来文学史上的主流观念,其根本原因,是出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即习惯于把一个王朝与一种文体对应起来,所谓“唐诗”“宋词”“元曲”,从而将王朝的更替与文体的沿革联系起来,唐诗演变为宋词,宋词又演变为元曲。
自明清以来的曲调格律谱所罗列的曲调,直至近代学术界论及戏曲和散曲的曲调,都将曲调分为南曲与北曲两大类。玉峰在《“曲牌”本不分“南”“北”》一文,也对此提出了颠覆性的见解。他认为,“曲牌”的“乐体”是不稳定的,同一个曲牌,在传唱过程中,其旋律必然会有差异,甚至完全不同,而其文体则相对稳定,每一个曲牌有相应的句数、每句有字数、平仄的特定要求以及用韵等方面的规定。而从曲牌的文体来看,也就无所谓有“南”“北”之分。
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曲坛上的“汤沈之争”是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玉峰的《也谈曲学史上的“汤沈之争”》一文,也对这一“旧题”,提出了新见,认为汤显祖虽然主张“以意、趣、神、色为主”,但不能据此将其归为“文辞”派并认为其不守格律。其实其剧作的曲文不但优美动人,且多为律句,据记载其“四梦”在当时即可演唱。相反,自魏良辅将昆山腔的演唱形式改为“依字声行腔”后,改变了曲牌的原腔古调,同一曲牌有不同的腔格,而沈璟“斤斤于返古”,要保存曲牌的原腔古调。这与当时因魏良辅改革昆山腔后“依字声行腔”的创作方式不符。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汤显祖归为文辞派,将沈璟归为格律派。
玉峰的标新立异、提出新的见解,是建立在拥有翔实的资料基础上的。如《论元曲调牌及其宫调的标示》一文,分别对未见宫调标示的元曲文献和有宫调标示的元曲文献作了梳理和考察,并追溯了《中原音韵》“北九宫”体系的文献依据,通过对大量的元曲文献的梳理和考察,揭示了元曲调牌宫调标示的来源及其实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所谓的“宫调”,其实是“人为”创造的,并非本已有之。“北九宫”体系最初是由元代周德清正式确立的,到了明代中叶蒋孝、沈璟又仿效“北九宫”,进一步建构了“南九宫”。
又如《元剧“楔子”推考》一文中,他通过对《元刊杂剧三十种》《元曲选》《元曲选外编》《改定元贤传奇》《古名家杂剧》《古杂剧》《杂剧选》等所收杂剧楔子使用情况的考察,对前辈学者有关楔子包括曲与科白、是“折”之外的叙事结构单位的论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楔子”的指义仅就曲而言,不包括科白,“楔子”不是由科白构成的叙事单元,而是构成元剧的核心结构即曲体结构的一部分。早期元剧作家制作楔子是偶然为之,后起作家效仿前辈作家所作,楔子使用渐多,乃渐成为元剧结构成分之一。
同时,玉峰的标新立异,也是建立在严谨缜密的考辨的基础上的。如长期以来,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乐府诗”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一类,而玉峰在《汉唐“乐府诗”辨证》一文中,对学术界的这一“通识”提出了质疑,而其考辨严谨缜密,首先对唐以前历朝音乐官署的设置和功能作了考察;其次,考证了最早提出“乐府诗”一词的文献为刘宋著名文人鲍照《松柏篇》之 《序》;第三,梳理了《文心雕龙》《文选》《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论》等文献中有关乐府的论述;第四,对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录的“乐府诗”的体裁作了分析,指出郭茂倩是以是否“入乐”来区分“乐府诗”与“非乐府诗”,故其所谓的“乐府诗”在文体上没有统一的标准。通过层层严密的考证和辨析,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如果不是以“文(体)”为标准,而是以“乐”为标准来区分具体的诗作,那么“乐府诗”的概念便十分广泛,无所不包。故不宜把“乐府诗”作为一类“诗体”的专称。
重视文与乐的关系的研究,将文本研究和度曲实践相结合,这也是玉峰治学的一大特色。南京大学自吴梅先生将戏曲研究搬上大学讲台始,就十分重视文本研究和度曲实践紧密结合,后经钱南扬先生、吴新雷先生等前辈学者传承,薪火相传,一直保持着南大治曲的这一学术传统。而玉峰也很好地传承了南大的这一传统,他熟谙曲律,能擫笛,会拍曲,不仅开设了度曲课,组织曲社,指导学生度曲,而且注重度曲理论的研究。如本书收录的《曲唱“字腔”“过腔”辨证》一文,对曲唱中的“字腔”“过腔”做了研究和论述,“字腔”“过腔”的概念虽是洛地先生提出来的,但洛地先生对此尚未加以深入的研究和充分论述,玉峰则对此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如果没有丰富的度曲实践,是不可能对“字腔”“过腔”做出如此专业和细致的论述的。
总之,本书所收录的文章,都显示了玉峰的学术水准和治学风格,相信出版后,一定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为今天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借鉴,而玉峰也随着本书的出版和传存,得以为后人所纪念,成为“未死之鬼”。
最后,以当时得悉玉峰去世时所作的一首小诗作结,一是表彰其学术成就,二是寄予对他的哀思:
笛奏大雅绕梁声,
良辅玉茗遇知音。
笔撰论曲惊世文,
宁庵笠翁叹高深。
英年摇落伤人心,
遥想当年悲难禁。
南雍自此铁笛沉,
瑶池迎来长短吟。
2020年9月8日于温州大罗山麓五卯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