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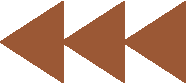
日本中国学家吉川幸次郎说过:“重视非虚构素材和特别重视语言表现技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的两大特长。”他还指出中国哲学“抑制对神、对超自然的关心,而只把目光集中在地上的人。这种精神同样地也支配着文学”
 。这当然主要是针对古代正统文学创作而言的。吉川提出的“特长”,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优点,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局限。而就吉川所提出的两个方面论佛教、佛典及佛典翻译文学的输入,仅就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而言,贡献就是不可估量的。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推进了中土固有传统的扩展和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对它的丰富和补充。所以正如刘熙载所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
。这当然主要是针对古代正统文学创作而言的。吉川提出的“特长”,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优点,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局限。而就吉川所提出的两个方面论佛教、佛典及佛典翻译文学的输入,仅就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而言,贡献就是不可估量的。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推进了中土固有传统的扩展和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对它的丰富和补充。所以正如刘熙载所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
 下面仅就几个最为显著的方面概略地加以说明。先讨论语言和表现形式方面。
下面仅就几个最为显著的方面概略地加以说明。先讨论语言和表现形式方面。
文学语言:
语言乃是文学的表现工具。佛典传译大量输入外语的词汇、语法和修辞方法、表达方式。从词汇看,翻译佛书输入大量外来语新词和新的构词法。外来词语翻译为汉语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利用汉语固有词语赋予新概念,如“空”、“真”、“观”、“法”之类,是赋予原有词语以特殊宗教含义,实际等于创造新词;另一种是利用汉语词素的本义组合成新词语,如“四谛”、“五蕴”、“因缘”、“法界”之类;再一种则是另造新词语,如实际、境界、法门、意识、大千世界、不可思议、万劫难复、头头是道等等。特殊的一种是音译词,即玄奘所谓“五种不翻”
 的词,如般若、菩提、陀罗尼、阎浮提等。这一种里应包括音、义合译的,如禅定、偈颂、六波罗密、阿赖耶识等。随佛典翻译传入汉语的词语数量难以统计,有许多已经成为现代汉语常用词语。词汇本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如此众多的新词语输入汉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材料。从语法看,梁启超曾指出:
的词,如般若、菩提、陀罗尼、阎浮提等。这一种里应包括音、义合译的,如禅定、偈颂、六波罗密、阿赖耶识等。随佛典翻译传入汉语的词语数量难以统计,有许多已经成为现代汉语常用词语。词汇本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如此众多的新词语输入汉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材料。从语法看,梁启超曾指出:
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它书迥然殊异。其最显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二)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丽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格调;(三)倒装句法极多;(四)提挈句法极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六)多复牒前文语;(七)有连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之名词——一名词中,含形容格的名词无数;(八)同格的词语,铺排叙列,动至数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十)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凡此皆文章构造形式上,画然辟一新国土。直言之,则外来语调之色彩甚浓厚,若与吾辈本来之“文学眼”不相习,而寻玩稍近,自感一种调和之美。

这里(一)(三)(四)(五)(六)(七)项都是属于语法的。其他还有:叙述文中多插入呼语,如“时我,世尊!闻说是语,得未曾有”之类句法;多用复句,等等。前述梁启超所举第(二)(八)两项是属于修辞的。佛典中特别多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方法,展卷即是,毋庸赘述。至于音韵方面,由于转读佛经,启发了汉语反切、四声的发明;而声韵学的进步,直接影响到各种韵文文体的演进。总之,佛典翻译的过程实际也是汉语和多种外语的长期、广泛交流的过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汉语文学语言及其表现手段。
行文体制:
长期的译经实践,形成了“译经体”。这是一种华、梵结合,韵、散间行,雅俗共赏的文体。前引梁启超列举的第(二)(九)两点,指的就是这种文体特征。魏晋以来,文坛上文章“骈俪化”倾向日渐严重。行文讲究对偶声韵、使典用事,大量使用华词丽藻,刻意追求形式美,创作上弥漫着绮靡、唯美之风。中土大德如慧远、僧肇写作时用的也是十分精致的骈体文(他们的骈体文相对来说比较质朴),但译师们使用的却是完全不同于骈体文的“译经体”。胡适谈到翻译文体说:
这样伟大的翻译工作自然不是少数滥调文人所能包办的,也不是那含糊不正确的骈偶文体所能对付的。结果便是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新材料和新意境是不用说明的,何以有新文体的必要呢?第一因为外国来的新材料装不到那对仗骈偶的滥调里去。第二因为主译的都是外国人,不曾中那骈偶滥调的毒。第三因为最初助译的很多是民间的信徒;后来虽有文人学士奉敕润文,他们的能力有限,故他们的恶影响也有限。第四因为宗教的经典重在传真,重在正确,而不重在辞藻文采;重在读者易解,而不重在古雅。故译经大师多以“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义”相勉。到了鸠摩罗什以后,译经的文体大定,风气已大开,那般滥调的文人学士更无可如何了。

另一方面,则是行文中韵、散间行。胡适又说:
印度的文学有一种特别体裁: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韵文(韵文是有节奏之文,不必一定有韵脚)重说一遍。这韵文的部分叫做“偈”。印度文学自古以来多靠口说相传,这种体裁可以帮助记忆力。但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便是从这种印度文学形式得来的。

“译经体”里的偈颂是一种不规则的韵文,使用五、四、七言或六言句,基本不用韵,节奏和句式则根据文义安排。这种“偈颂体”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自由体”诗。后来颇有些中土文人加以模仿。此外什译《法华》被称赞“可谓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乃是既合乎汉语规范、又保持外语风格、成功译经的典型例子。这种具有异域情调的译文对中土文人产生相当的吸引力,对文风的演变也起了一定作用。就文章结构而言,如陶渊明写了韵文《桃花源诗》,又写散文《桃花源记》,唐人写传奇小说也常常与诗歌相配合,都是借鉴佛典韵、散结合写法的新创造。至于民间说唱体裁的变文、宝卷等,则更直接地取法佛典的行文体例。甚至唐宋人创作新“古文”,也从译经得到一定的启发。
,乃是既合乎汉语规范、又保持外语风格、成功译经的典型例子。这种具有异域情调的译文对中土文人产生相当的吸引力,对文风的演变也起了一定作用。就文章结构而言,如陶渊明写了韵文《桃花源诗》,又写散文《桃花源记》,唐人写传奇小说也常常与诗歌相配合,都是借鉴佛典韵、散结合写法的新创造。至于民间说唱体裁的变文、宝卷等,则更直接地取法佛典的行文体例。甚至唐宋人创作新“古文”,也从译经得到一定的启发。
文学体裁:
佛典的经藏和律藏主要是叙事,论藏主要是议论。其实论藏的议论也很有特点,值得注意。部派佛教的“阿毗达摩”作为议论文字很有特点:注重名相、事数的辨析、由因及果的论证、条分缕析的行文结构和举事为譬的说明方式。把它们译成汉语之后,首先影响到僧俗的义学著述,进而对中土的议论文字产生重大影响。僧人文字如僧肇《肇论》、文人文字如刘勰《文心雕龙》,就是受其影响的典型例子。唐宋人的议论文字也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滋养。更重要的是佛典对中土叙事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隋唐以前中土叙事文学主要是史传和志怪、志人小说。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志人小说如《世说新语》,或者记录奇闻异事,或者传述名士逸闻,还没有脱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
 的“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
的“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
 的规模。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
的规模。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
 ,就是说,前此还没有自觉地通过“幻设”创作小说的观念和实践。而佛典特别是大部佛传和一些大乘经,却是充满玄想的具有复杂情节的叙事文字。陈寅恪论及《顶生王经》、《维摩诘经》等与《说唐》、《重梦》等的关系说:“虽一为方等之圣典,一为世俗之小说,而以文学流别言之,则为同类之著作。然此只可为通识者道,而不能喻于拘方之士也。”
,就是说,前此还没有自觉地通过“幻设”创作小说的观念和实践。而佛典特别是大部佛传和一些大乘经,却是充满玄想的具有复杂情节的叙事文字。陈寅恪论及《顶生王经》、《维摩诘经》等与《说唐》、《重梦》等的关系说:“虽一为方等之圣典,一为世俗之小说,而以文学流别言之,则为同类之著作。然此只可为通识者道,而不能喻于拘方之士也。”
 正因为如此,后来中国小说的发展,包括长篇小说的兴盛,有形无形间与佛典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服务于佛教宣传还形成一批新文体。陈寅恪在论及当时被称为“佛曲”的《维摩诘讲经文》时说:“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
正因为如此,后来中国小说的发展,包括长篇小说的兴盛,有形无形间与佛典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服务于佛教宣传还形成一批新文体。陈寅恪在论及当时被称为“佛曲”的《维摩诘讲经文》时说:“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
 陈寅恪当年说的“佛曲”实际是讲经文,同样的情况还可以补充变文、押座文、缘起等一系列讲唱文体和明、清的宝卷、弹词等。
陈寅恪当年说的“佛曲”实际是讲经文,同样的情况还可以补充变文、押座文、缘起等一系列讲唱文体和明、清的宝卷、弹词等。
以上属于文学表现的纯技术方面。在观念层面上,即艺术思维、构思方面影响就更为深远。佛典,包括佛典翻译文学所表现的正属于“子不语”的“怪、力、乱、神”之列,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方式,都是中土传统思维所缺乏的。牟子《理惑论》里说:
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辱,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

后来范晔也说:
……然(佛典)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这类记述清楚表明当初佛陀形象和佛典文字给人多么新奇的印象。它们在艺术上和美学上代表的是与中土不同的另一种传统,体现着特殊的思维方式,使用特殊的构思和表现技巧。中土文人在震惊、赞赏之余,必然要加以模仿和借鉴。吉川幸次郎又曾指出过:“小说和戏曲使文学从以真实的经历为素材的习惯限制戒律中解放出来……戏曲和小说都是虚构的文学。”
 佛教和佛典中大量玄想的内容、虚构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小说、戏曲创作想象力的解放,对其艺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佛教和佛典中大量玄想的内容、虚构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小说、戏曲创作想象力的解放,对其艺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这首先表现在佛典里运用想象手法之普遍,表达方式的大胆、奇妙,是中土文学所不可比拟的。自部派佛教时期发展出独特的宇宙观、佛陀观,从而想象的世界变得无限的恢宏和神异。由于内容出自玄想和虚构,思维方式也就与中土重“实录”的原则根本不同。在佛教宇宙观里,有情世界有过、现、未三世和六道;诸佛及其佛国土更超越三世、遍在十方。佛典里表现的“人物”不只有三世轮回中的人,还有罗汉、天神、“天龙八部”以及恶魔、饿鬼等等。在俗的佛陀自不必说,就是罗汉、菩萨以至佛陀的敌人、恶魔等都有无数神通。由这些出于想象的“人物”、事件构想出千奇百怪、五彩缤纷的故事。如前述《维摩经》里维摩居士示疾说法,示现无数神通,典型地显示了大乘佛典富于玄想的性格。《法华经》里的“火宅”、“化城”等喻同样是出于大胆夸张和想象的成果。又例如《杂宝藏经》卷一《莲花夫人缘》,描述莲花夫人“脚蹈地处,皆莲花出”,她被立为夫人,生五百卵,王大夫人嫉妒,掷恒河中,成长为敌国的五百力士,两军对垒时“夫人按乳,一乳作二百五十岐,皆入诸子口中,即向父母忏悔”
 ;而《贤愚经》著名的须达起精舍故事里的舍利弗与劳度差变化斗法情节,更被《西游记》等众多中土作品借鉴和发挥。佛典里的奇思异想不仅超凡绝伦,往往又充满幽默感,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后来的小说、戏曲从中取得借鉴,开拓出创作的新生面。
;而《贤愚经》著名的须达起精舍故事里的舍利弗与劳度差变化斗法情节,更被《西游记》等众多中土作品借鉴和发挥。佛典里的奇思异想不仅超凡绝伦,往往又充满幽默感,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后来的小说、戏曲从中取得借鉴,开拓出创作的新生面。
富于玄想的佛教故事,结构上更是恢宏自由。如上所述,一些佛典如本生、譬喻故事具有教条化、程式化倾向。这在宗教作品里也是普遍的弊病。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佛典大量输入的晋宋时期,中土叙事文字结构还比较单纯,一般篇幅也相当简短,而佛典里却包含有篇幅较长、情节更为复杂的作品。它们作为外来文化产物,反映着与中土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构思与结构也具有不同于中土传统的特色。例如有些篇幅较长的佛典在佛陀说法的大的框架之下,组织进另外的故事,从而形成双重或多重结构。像《佛本行集经》里就组织进不少本生或本事故事;《贤愚经》里的故事不少是多重结构的;而如《维摩经》,从佛陀在庵罗树园说法开始,到文殊师利率领众弟子、菩萨等来维摩方丈问疾,再回到庵罗树园听佛陀说法,像是三幕戏剧,其中每一部分又插入另外的故事,构成极其复杂但又统一的结构。佛典里有些常见的观念,除前面提到的神变、拟人外,还有变形、分身、幻化(化人、化物、化现境界)、魔法、异变(地动、地裂、大火等)、离魂、梦游、入冥(地狱)、升天、游历它界(龙宫、大海等)等等,都是超出常识的构想,也成为构造故事情节的重要方式。它们直接给六朝传奇小说创作以启发,对后代更造成巨大影响。
在具体写作技巧方面,佛典又具有许多突出特长。如大量使用比喻、夸张和排比。佛典多用譬喻和譬喻故事前面已经说明。佛典的比喻修辞手法更是多种多样。《大涅槃经》里提出“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三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七者先后喻,八者遍喻”
 。该经同卷还举出所谓“分喻”,即喻体只比喻被喻者一部分。《大智度论》又指出“譬喻有两种:一者假以为喻,二者实事为喻”
。该经同卷还举出所谓“分喻”,即喻体只比喻被喻者一部分。《大智度论》又指出“譬喻有两种:一者假以为喻,二者实事为喻”
 。这即是所谓“假喻”和“实喻”。给人印象更深刻的还有所谓“博喻”,即连用多种比喻。至于佛典的所谓“好大不经”,即多用极度夸张,更是超越时空界限,超越常识度量。这本是印度人富于玄想性格的体现。如数量单位有俱胝(十万)、亿、那由他(兆)、阿僧祇(无限大);时间单位从刹那(一瞬间)到劫(世界生灭一次,无限长的时间),都是极度夸张的。又如《华严经》里描写诸佛世界,以极度夸张的笔法描绘出无限奇妙、不可思议的佛土庄严。具体夸说一些事相,如写施舍,就不但施舍钱财,而且施舍家人妻子,舍身跳崖、割肉、剜眼等等,行为极其极端、不可思议;又如讲恶人,不但毁佛、骂僧、悭吝、骄恣,而且弑父、杀母,恶贯满盈,等等。这类极度夸张往往会有损作品整体的美感,情理上往往也难以让人信服,当然是缺陷。但也有些夸张虽然有悖情理,如鹦鹉用羽毛沾水灭火,有人用龟甲舀干大海水,等等,在艺术表现上却又是相当动人的。还有些夸张,如说恶人一旦反悔立即成为罗汉,平常人一旦皈依佛陀就剔除须发、袈裟在身,都意在表现佛法的无限威力,则是出于宣教的需要。比喻和夸张相结合则能造成更强烈的表达效果。佛典又常使用复叠和排比,胡适说:
。这即是所谓“假喻”和“实喻”。给人印象更深刻的还有所谓“博喻”,即连用多种比喻。至于佛典的所谓“好大不经”,即多用极度夸张,更是超越时空界限,超越常识度量。这本是印度人富于玄想性格的体现。如数量单位有俱胝(十万)、亿、那由他(兆)、阿僧祇(无限大);时间单位从刹那(一瞬间)到劫(世界生灭一次,无限长的时间),都是极度夸张的。又如《华严经》里描写诸佛世界,以极度夸张的笔法描绘出无限奇妙、不可思议的佛土庄严。具体夸说一些事相,如写施舍,就不但施舍钱财,而且施舍家人妻子,舍身跳崖、割肉、剜眼等等,行为极其极端、不可思议;又如讲恶人,不但毁佛、骂僧、悭吝、骄恣,而且弑父、杀母,恶贯满盈,等等。这类极度夸张往往会有损作品整体的美感,情理上往往也难以让人信服,当然是缺陷。但也有些夸张虽然有悖情理,如鹦鹉用羽毛沾水灭火,有人用龟甲舀干大海水,等等,在艺术表现上却又是相当动人的。还有些夸张,如说恶人一旦反悔立即成为罗汉,平常人一旦皈依佛陀就剔除须发、袈裟在身,都意在表现佛法的无限威力,则是出于宣教的需要。比喻和夸张相结合则能造成更强烈的表达效果。佛典又常使用复叠和排比,胡适说:
《华严经》末篇《入法界品》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写善财童子求法事,过了一城又一城,见了一大师又一大师,遂敷演成一部长篇小说……这种无边无际的幻想,这种“瞎嚼蛆”的滥调,便是《封神传》“三十六路伐西岐”,《西游记》“八十一难”的教师了。

反复地使用复叠和排比,有时也会使行文显得烦琐、枯燥;但运用得当,则确实能加强艺术效果。
佛典翻译文学是古代的外国和外民族文学,带有外来文学的特征;作为翻译作品,它们又有外国、外民族文学的特色;而它们作为宗教圣典,还具有宗教文献的特征。这就形成这些作品的极其复杂、丰富的面貌。历代中国文人吸收、借鉴佛典翻译文学的成果,不断开拓出创作的新生面;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学的交流和结合从而成为文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结成众多丰硕而精美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