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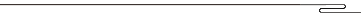
草原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类型,要明确草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便不能不涉及中国古代文化的类型划分,以及与草原文化同时生存的其他文化类型。
文化类型的划分是以经济类型为基础的。关于经济类型的划分,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在《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一书中,将人类的经济类型划分为如下四大类型:猎人和采集者、园艺种植者、犁耕农业、畜牧业。
猎人和采集者
直到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年之前,搜寻地里的野生植物、鱼类和动物还是人类生活的普遍方式。我们不可能重建遥远先民的文化,但当代猎人和采集者的文化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具有的某些局限性。如上所述,这类人可在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和美国西经 100°——它横贯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广大地区上发现。亚马(孙。编者注)森林中也有小块猎人和采集者的专有地域、南美(洲。编者注)南部的三分之一是他们的独占领地。澳洲土著也全是猎人和采集者,非洲和东南亚很少有这样的地区。
园艺种植者
显而易见,发明培植庄稼至少独立出现于三个地区:近东、东南亚和中美及南美的山区。它扩展到了除澳洲以及那些气候和地域均不允许的地方之外的每一个大陆。早期园艺种植者的技术非常简单,只有些用于翻地的掘棍和锄头以及用于其他目的的一些器具,这还不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园艺是以更加基本的方式来革新人类社会的:群体结束了他们流徙的方式、定居于固定的家园。
犁耕农业
美洲大陆家养的唯一可套轭的动物是美洲驼,它只能用于驮货和作为驼毛的来源。在亚洲、欧洲和撒哈拉以北的非洲,犁的使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犁耕农业把我们带进了复杂社会、都市和国家的成长、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之中,这一切将在第七章里论述。现在只需注意到至此单系血统和血统群消失了,而且随着犁耕农业的兴起,妇女的社会地位普遍变低。在园艺种植者中,妇女包揽了大部分栽培工作,因为男人经常从事捕鱼打猎以便供应食物中的蛋白质部分。妇女因艰辛劳动而受到尊重,有时享有和男人同等的声望。然而,犁耕一般是男性的工作,牲畜也归男人占有。妇女变成了经济生产的配角并且被降到家务劳动中去了。
畜牧业
主要经济来源是放养家驯动物,大概出现于犁耕农业时期或略早一些。东半球当代畜牧者大部分分布在西起撒哈拉、东到中亚的干旱地区。这些地区的主要牲畜是骆驼、牛、绵羊和山羊。芬兰北部和瑞典北部的拉普人(Lapps)以及西伯利亚东部的一些群体,也放牧驯鹿。美洲大陆仅有的畜牧者就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纳瓦霍人,哥伦比亚北部的瓜希罗人(Goajiro),他们分别放牧绵羊和牛,这两种牲畜都是西班牙人带来的,故这种畜牧经济是后起的(postcontact)。
虽然上述四种经济类型的出现有时间上的先后,但不是后一种经济类型出现后,前一种经济类型就消失了,而是呈现一种共存状态。因此,这种经济类型的划分便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1885—1952)所著的《草原帝国》,虽没有对世界经济类型进行划分,但书中明确说明该书“记述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三千年碰撞史”,可见他是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作为主要对峙互动对象。
中国民族大学张海洋教授在《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一书中,将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类型分为三大类: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和农耕经济文化类型。如下表所示。
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体系(简表)

简要说明:此方案虽然列出体系、类型组、类型、亚型和地方变体等五个层次,但第四和第五个层次只是日后的研究空间。本书暂时综合基本材料描述类型组和类型这两个层次。方案中的类型分布,按生计方式和生计类型的集约化程度排列。类型组和类型之间的各种连续和过渡形式被忽略。文化分类中的这种缺憾,只能靠人类认知上的完成(closure)能力来弥补。
我们必须注意,张海洋先生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的“渔猎”区域是指“分布在东北极边的大兴安岭北端、小兴安岭以及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主要居民是讲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赫哲、鄂伦春、部分鄂温克和少量达翰尔等民族。这一组内包含着以赫哲族为典型的采集渔捞和以鄂伦春族为典型的采集狩猎两个类型”。
因此,这里的“采集渔猎”与海洋以及海洋经济文化并没有关系。
笔者主张将中国古代的主要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为三大类:农耕(农业)文化类型、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和海洋经济文化类型。
人类的采集和渔猎显然是较之农业与畜牧更早、更普遍的经济文化类型,这种经济类型既有内陆的,也包括海洋采集、渔猎。而且这种经济文化类型迄今仍然存在,无论是内陆,还是海洋,无不如此。海洋的采集渔猎,就放在海洋经济文化类型之中,而内陆的采集渔猎,如大小兴安岭、三江草原东北角,即赫哲、鄂伦春、部分鄂温克和少量达翰尔等民族的采集渔猎就归类于畜牧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文化类型或草原文化类型)之内。
经济文化类型与自然地理环境关系密切,经济文化类型具有明显的区域文化的特点,因此,这种经济文化类型的划分研究,与区域文化研究通常是结合起来进行的。关于经济文化类型和中国区域文化类型,也包括所谓“文化传统”研究,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等都曾有过论述。
将地下出土文物、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即依据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于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进行了空前深入的研究。比如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将传说中的古史分为西方之夏、东方之夷及南方之苗。蒙文通先生的《古史甄微》也将其分为三大系统:一是西部的河洛民族(黄族),二是南部的江汉民族(炎族),三是东方的海岱民族(泰族)。杨宽先生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将其分为两大系统:即东系民族(殷、东夷、淮夷等)、西系民族(周、羌、戎、蜀)。认为神话传说也属于这两系。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我国人民有一部分从古代起,就自称诸夏,又自称华夏,又单称夏或华。到春秋战国以后,华夏就成了我们种族的名字……把我国较古的传说总括来看,华夏、夷、蛮三族实为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从较古的春秋时期或战国前期传说仔细耙梳,还不难看出在此之前的部落的确分为三个不同的集团的痕迹。”
丁山先生在《古代神话与民族》一书中是按照神话的演变和各个种姓的活动区域分析古代种族,认为我国在先秦时陶唐氏偏向汾水流域发展,有可能是北狄。夏侯氏偏向伊、洛、嵩区域发展,可能是中原旧族。殷商初期沿着漳水流域向海滨发展,后来又迁到河内,大概是东胡族。
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认为夏商时中国民族的两大主干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的分布地区和发展线素基本相近。他在《简明中国通史》一书中提出中国人种源于蒙古人种和马来人种,其中商族的一支沿海往南迁徙,到山东半岛后沿河西进。另外一支迁徙到陕甘的夏族,向东到晋南、豫西。
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一书中提到“未经记载的历史”,指的就是传说时期。其第四章中说:“历史愈往后延,诸部族逐渐合并……这只要看黄帝及夏禹时之万国,商汤时之三千国,周武时之八百国云云,便可断定。”他又在《中国政治史》一书指出:“自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以至商汤及周文王、武王,其间的经过都可以说是氏族联合之过程。黄帝当神农之衰世,曾以武力使诸侯或同时并立的许多氏族首长皆来服从。……诸侯在古代等于氏族首长,黄帝以武力克服诸侯,或容纳被侵凌的诸侯,或联合诸侯以共同攻击暴虐之人,其实都是联合氏族首长,而进行氏族的联合。”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说:“远古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居住在东方的人统统被称为‘夷族’……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统统被称为‘狄族’‘戎族’……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炎帝族居住在中部地区,炎帝姓姜……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
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一书中说:“古代黄河流域分布着不少的部落。在陕西一带有姬姓黄帝部落和姜姓炎帝部落,他们之间世代通婚。在冀、鲁、豫交界的地方有九黎部落,他们的酋长名蚩尤……黄河下游一带有太灏氏和少昊氏,太昊氏活动中心陈(今河南淮阳),少昊氏在奄(今山东曲阜)。”
刘起釪先生广泛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把对中国上古时期传说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将史前原始文化划分为四个阶段:有巢氏(蒙昧时代低级阶段,生活在森林中,巢居在树上)、燧人氏(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已发明用火)、庖牺氏(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猎物成了日常食物,用火烧熟再吃)、神农氏(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开始种植作物)。
黄河上游出自氐羌奉龙图腾创造了早期青铜器文化的黄帝族——夏族。
我们的祖先在黄河流域创造了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等文化和仰韶文化及其在仰韶文化基础上出现的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再到齐家文化(出现了青铜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发展成山东龙山文化(出现冶铜术),再发展成岳石文化。其中黄河上游的部族在中原建立了夏代,黄河下游的部族则在中原建立了商代。夏商周在整理和记载远古传说资料时,便以夏代和始祖黄帝为中国传说时期古史的开始。同时由于民族融合则形成了中国传说时期的历史系统的主干,再加上其他民族的融合,最终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族。
从渭水地区到湟水地区有黄帝族及炎帝族。
黄河下游奉鸟图腾创造了成熟的青铜器文化的东夷——鸟夷诸族。
北方、西北、东北的戎、狄、氐羌、肃慎等。
东南的吴越族。
源于氐羌的巴、蜀、发羌等西南夷诸族。
新时期以来,由于考古学方面的成果日渐增多,因此关于经济文化类型及区域文化、文化传统的研究,也有了更为明确的论述,张光直、苏秉琦、严文明、佟柱臣、石兴邦等先生都曾发表过很精到的见解。
张海洋先生在《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一书中,依据“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体性及共生关系”“参照前人成果并综合语言、民俗等资料,向上归纳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就是建立在中国自然地理板块基础上的两大文化板块以及生成于其间(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大传统。
具体说来,这两大文化板块为:
一、西北畜牧文化板块
这一板块作为宏观文化带,由兼通考古、历史和人类学的童恩正教授提出并证成。他 1987 年发表的《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以“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为称谓,从范围、地理、气候、生态、文化要素的相似性等方面,对这一地带的存在及其成因,都作了有力论证。其用“传播带”一词,强烈暗示这一从东北到西南绵延万里的地带之间,存在着远古人类的文化交流。当然,这也不排除在主客观条件相类似的前提下各地独立发明某种文化要素的可能性。本文认同童教授观点,认为它是中国的农耕文化板块的对映体。
根据童教授观点,这一文化带大致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其南、东界线约为从北、西两个方面环绕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理上,以青藏高原为集结点,其东翼有青海祁连山脉、宁夏贺兰山脉、内蒙古阴山山脉直至辽宁、吉林境内的大兴安岭;其南翼是由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气候上,这一地带以现在的年均降水 400 毫米线为重心,主体落在年均 600 毫米降水线与年均 8 摄氏度线以西及以北。比较而言,这相当于前述苏秉琦、陈连开两教授所指的是背靠欧亚大陆的内陆部分,也平行于人口学家胡焕庸教授 1935 年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中提出的,以黑龙江瑷珲与云南腾冲为连线的西北部气候干燥和人口稀疏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带之内的河西走廊与新疆部分地区,兼有绿洲农耕生计。
以河西走廊和黄河为界,这一地带可分北、南两片。但在从东北的吉林西团山到西南的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之间,存在乌鞘岭等联系桥梁,因而也存在如下的共同文化因素: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石头建筑遗迹和以石球、穿孔石器、单孔或双孔的半月形石刀、条形石斧或石锛、铸造青铜工具或武器的石范、诸多青铜器的器形、风格及器物上的动物纹饰等。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这一地带便一直是畜牧或半农半牧族群的生息之地。从古代东北的肃慎、东胡到川、滇、黔的西南夷,从风俗上的编发(辫首)、左衽到生计特点上的善骑射、逐水草、随畜迁徙等方面,都表现出相当高度的文化一致性。
二、东南农耕文化板块
这一板块内存在粟作和稻作两个文化地带的事实已经昭然。本书从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性出发,要证成它是一个在东北与西南两端与畜牧带相接甚至交叉,以面向大海的中国东部为重心,以河流与海洋的联系为纽带结成的一个宏大文化板块。本书论证的步骤是:先识别出一个连贯的沿海(或海洋)文化带,然后借助于东西走向的各大江河使它与川陕盆地乃至滇南连成一体,构成农耕文化板块。沿海文化带对我们考察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认同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在西北畜牧文化板块贯穿中国西部的基础上,再为中国巨大幅员内部密不可分的地理和文化联系提供一个新维度。笔者以为,只要从东北到西南的沿海文化带得以证成,其与内陆通过江河而存在的联系自会顺理成章。因此,本书对于农耕板块内陆文化与沿海文化的连续性将不做过多描述。
这其实很好理解,既然张海洋先生将中国文化归结为“西北畜牧文化板块”与“东南农耕文化板块”,那么后者之地域在前者地域弄清楚的基础上,就很明确了,即除了上述的“西北畜牧文化板块”之外,余下的部分就是中国的农耕文化板块,因其与西北相对而地处中国的东南,故称为“东南农耕文化板块”。
如上所述,笔者主张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为畜牧文化、农耕文化、海洋文化三大类型;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而言,就是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文化板块:西北畜牧文化板块、中原农耕文化板块、东南沿海海洋文化板块(从辽东半岛经渤海、黄海、东海,一直到南海的广东与海南岛)。其中西北畜牧文化板块与张海洋先生的“西北畜牧文化板块”一致,而将张海洋先生的“东南农耕文化板块”一分为二,其内陆为“中原农耕文化板块”,沿海为“海洋文化板块”。海洋文化类型是指以海洋为资源,主要从事海洋捕捞(采集)、海洋养殖、制盐、航海(贸易)为生计方式的沿海居民,它不仅包括通常人们所说的“渔民”,还包括以航海(贸易)“为生计方式”的居民。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学者为了对世界民族进行语言谱系以外的分类而提出的一个分类体系概念。在应用中,这个概念又衍生出一套分类方法(有时与历史民族区配合使用)。用这套方法取得的分类成果,可以用于解释民族学人类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社会经济技术形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不同民族在文化上表现出相似性或差异性的原因。例如,语言谱系不同的民族其文化或有相似,语系相近的民族其文化或有差别。由于这些差别不能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明,所以学者们要到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生计方式和生计类型中去找原因。
这一理论在中国取得的学术成果,就是当年同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林耀华与切博克萨罗夫教授合写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
张海洋先生对于用实证方法揭示出中国文化基础结构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拓展人们视野的潜力和特点的评价(五条),及其对整个“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和方法”本身固有的局限性的评价(三个方面),都是很有见地的。但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张海洋先生对于“经济文化的类型定义的修正”:
总之,经济文化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生态和生计基础既有重要价值又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本文对之提出如下修正:
第一,在定义中去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代以“生计方式”,去掉“自然地理环境”而代之以“生态环境”。这样它的定义就是: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对比原定义及其用例,这一定义并无乖悖之处。
第二,根据中国历史文化特点对经济文化类型、历史民族区和居民语言谱系三者实行通约,即试将中国历史民族区和语言(及方言)谱系分类的成果,整合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分类体系内加以描述。这样做的理由是:有史以来的中国民族(例如华夷)分类,主要都是按外在的文化(礼教加言语)和地域(水土加距离)而不是按其他(如血统和内在信仰)标准。这种文化遗产,使得历史民族区与语言谱系与经济文化类型可以在较高的可行性基础上得到整合。这种整合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划分既重视基础结构也涉及结构和上层建筑,以此体现这一理论的经济文化分类而非纯经济分类的原意。
第三,为反映中国经济文化多元一体的现实,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基础建立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分类体系。这个体系分成三个层次:最高一层是体系本身。体系之下主要按生计方式分出三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类型组之下,按具体生态环境和生计技术分出若干经济文化类型(简称生计类型)。由于各个类型在规模和分布范围上大小不一,所以对于大的类型还有分出亚型的必要。亚型之下,又应留出地方变体的空间。这样修正的结果,能保证在深化认识研究对象的同时不破坏其完整性。
张海洋先生的这种修正显然是将“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充实到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之中了。
对于“生态人类学”,张海洋先生在叙述“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时,曾作过介绍:
早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怀特(L White,1900—1975)为首的美国密执安大学的人类学家们已在提倡新进化论和文化科学,旨在强调生产技术、物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密切关系。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教授(Julian H. Steward,1902—1972)也已开始为当代文化生态学奠基。这是一个“主要研究文化制度适应环境的过程和由这种适应性所导致的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的学科(吴文藻,1984)。斯图尔德在他 1955 年发表的《文化变异论》中,也提出过文化类型说,其定义为“文化类型是不同的民族文化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各种文化特质的相互整合的核心特征丛”(李宗桂,1988)。这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定义异曲同工。本书指出这些,并不否认苏联学者所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原创性。它能说明的是:当时世界上的民族学人类学主流,受到科学经验主义(scientific empiricism)的影响,正把研究重点转向人类物质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上。苏联学者不失时机地提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正说明他们的研究与世界学术潮流息息相关并站在前沿。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前述的种种概念(包括经济文化类型概念),都可归入文化生态学门下,只有“埃及中心说”意义上的“文化圈”和心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模式”或可除外。
以苏联列文·切博克萨罗夫为代表的“经济文化类型”概念是一个民族学理论,而以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教授为代表的文化生态学属于人类学方面的范畴。张海洋先生是将民族学与人类学合在一起,所以他使用了“民族学人类学”这样的术语。
尽管如此,张海洋先生关于“经济文化类型”的新定义,仍然属于民族学理论,因为他所聚焦的,或者说他的定义的落脚点,仍然是“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的综合体”,“综合体”乃是其核心。
而“草原文化”所聚焦的不是“文化的草原”,而是“草原的文化”,因此“海洋文化类型”的确定更接近于生态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定义。
著名生态人类学学者罗康隆先生在《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一书中对于人类文化类型的划分,作过如下叙述:
人类学研究开始认真地对待文化所处的生态系统开创于斯图尔德。在他的划分指标中,明确地纳入了生态环境的因素。他根据人类谋生的主要手段,把人类分为狩猎民、采集民、畜牧民、农民等。其后,众多的研究者基本接受了他的划分办法,同时作了相应的修订。如将狩猎、采集和捕捞水产合为一种生计方式,统称为狩猎采集阶段。在游牧阶段之前,沿袭哈恩的研究成果,区分出一个游耕阶段。学术界对这一阶段的名称至今尚存在一些分歧,有人称为“刀耕火种阶段”或者“斯威顿耕作阶段”,为了行文的统一,我们采用了“斯威顿耕作”这一名称。再如,在农业阶段之后,人们公认还有一个工业阶段。
人类文明演进的架构与怀特所规定的用能量控驭水平标示文化发展的程度基本吻合。这些阶段的名称尽管与怀特的提法不同,但它反映的实质基本符合怀特的进化思想,或者说,与萨林斯所主张的一般进化为同一内容。顺着这个文化演进的阶段顺序,我们可以将世界上已有的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并进而发现不同的文化在资源利用上也会表现出系统性的差异。
罗康隆将文化类型划分为五大类:狩猎——采集文化类型、斯威顿耕作文化类型、畜牧文化类型、农耕文化类型和工业文化类型。
与民族学“经济文化类型”划分相比,我们不难看出他们虽然类型不同,但大致还是相似的。以列文·切博克萨罗夫的民族学“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以及林耀华、切博克萨罗夫合著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的经济文化类型划分,是以工业文化类型存在之前的“经济文化类型”划分,因此,在其“经济文化分类”中,也就有“工业文化类型”。
由此,民族学“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与人类学的文化类型划分,无论是理论依据,还是所划分的类型,是大致相似的。其目的都是建立在研究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来探讨文化的差异性。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民族学“经济文化类型”划分,还是人类学的文化类型划分,都没有将海洋文化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而是将其放在采集——渔猎类型之中了。
这里之所以将中国的主要文化类型或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为三大类,即不仅将“海洋文化”单独分类,而且使之与“畜牧文化”“农耕(农业文化)”鼎立,是因为中国海岸线漫长,海洋资源丰富,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历史文献记载,以及现实生活中,都存在着一个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连续不断的海洋文化的事实,从鱼盐,特别是盐以及海运(包括海上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出发,从海洋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通道等事实出发。除了事实之外,当然也有理论上的依据:
第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区域文化、风俗与商业经济有内在的关系,已经意识到海洋经济对于区域文化与风俗的重大影响。其海洋经济区为燕、西楚、东楚、齐。这一点将在第六章中加以叙述。
第二,中国自古以来就将居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以为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对人的个性乃至品行都有重大影响,所谓“术不可不慎”,而商则与海洋文化关系特别密切,即海洋文化实质上乃是一种商业文化。
第三,更为直接的理论依据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论述。钱先生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此三种文化,可分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
关于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海洋文化的事实等有关问题,将在第五章中加以叙述,这里不再赘言。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张海洋先生在《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一书中,虽然将中国的文化形貌概括为“太极”图形,其内部有西部的畜牧业与东部的农耕业两大生计板块,但他对于中国的海洋文化,还是相当重视的,而且也使用过“海洋文化”这一术语:
(一)自然联系。就像西北畜牧文化板块有从东北到西南的文化交往通道一样,东南农耕文化板块形成的关键也是文化通道的存在。本文认为中国文化大传统形成之前,横亘在中国东面的大海,以及与大海相通的辽河、黄河、长江、珠江几大水系,曾是中国东部广大地区的文化交往通衢。江、河作为文化通道不难为人接受。辽阔的大海能否或是否曾经作为远古居民交往的主要通道?这是一个与文化价值取向有关的问题。以大陆文化眼光度之,此说不免唐突;但以海洋文化眼光度之,则大海可作通途乃是自然之理。欧洲与北非上古技术基础与中国上古相酹,但环地中海的航运与贸易,却构成其文明的重要基础。中国史前的海洋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对中国文明产生过什么影响,何以在文化大传统中的地位总不如畜牧文化显赫,考古发现中哪些透露着海洋文化的信息,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性具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不仅饶有兴味,而且与中国的未来命运攸关。对照前述各家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的划分,我们能看到一点共同之处,就是除张光直外,其余各说均对远古沿海居民利用近海作为南北通道的可能性着意不深。以陆界作为划分文化区、带依据,不仅反映出大陆文化视野,而且在强调山河分界作用的同时忽略了海洋的整合作用。结果,学界对中国文化区、系、类型的划分基本顺山河走势以东西连横为主导,未能留意中国文化同样具有的南北合纵性质。
…………
考古学资料(物质文化):
贝丘遗址:贝丘(shell mound)日本称贝冢,是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以包含大量古代人类食余抛弃的贝壳为特征,在世界各地有广泛分布,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坐落则多在海、湖、河沿岸(安志敏,1986)。严文明教授指出:“贝丘遗址广泛分布于广东、广西沿海和西江两岸,主要有广东潮安石尾山,广西防城杯较山、马兰嘴山,南宁豹子头,扶绥江西岸和敢造,邕宁长塘和横县西津等处。遗址面积小者仅数百平方米,最大者 1 万—2 万平方米不等。这些遗址的共同特点就是有大量的贝壳堆积。厚 1 米—3 米,布满整个遗址。说明这些遗址的居民是以贝类为食物的主要来源。”(严文明,1989)这些遗址中还发现过一些以蹲葬为特点的墓葬,是一种很特殊的埋葬习俗。“在中国,除了黑龙江的依兰倭肯哈达发现过类似的葬式外,其他地点均不曾见。”(同上)还应指出,严教授例数的贝丘反映的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南的情况。实则“中国沿海发现贝丘遗址最多的,当推辽东半岛、长山半岛、山东半岛及庙岛群岛,此外在河北、江苏、福建、台湾、广东和广西的沿海地带也有分布。在内陆的河流和湖泊沿岸还发现有淡水性贝丘遗址,前者以广西南宁邕江沿岸的贝丘遗址为代表,后者则以云南滇池东岸的贝丘遗址为代表”(安志敏,1986)。这就把从云南到辽东串连成一条文化分布带。
…………
第四,海岸线长海域辽阔。中国的海岸线长达 18000 多公里,而且大陆架宽广,滩涂较多。这种地形不利于商用港湾,却有利于海产的开发养殖和农业围垦。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人口多半近海而居,不能不向海洋讨生计。因此整体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忽视中国面对海洋的地理现实。其中南北贯通的海洋通道对文化交往的影响已如前述。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升华,一方面它对于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谓具有前瞻性,但理论同样具有滞后性的特点。民族学关于“经济文化类型”的划分理论,人类学关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文化类型划分理论,也是如此,它们都对研究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但也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加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