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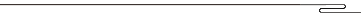
突厥的最初活动地在准噶尔盆地之北,约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来迁移到高昌的山北。
公元 552 年(西魏废帝元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大败柔然,自称伊利可汗,建突厥汗国于漠北地带。土门死,子科罗(乙息记可汗)、俟斤(木杆可汗)先后继立。木杆可汗在位时(553—572 年),灭柔然,破厌哒,走契丹,并契骨,威震塞外,“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
公元 583 年(隋文帝开皇三年),突厥一分为二,西突厥占有今新疆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
公元 599 年(隋开皇十九年)前后,突厥自漠北“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今呼和浩特西北)”,接踵降隋者数十万众。
隋炀帝大业初年,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即达头曾孙阿史那达漫)因“抚御无道”,致“其国多叛”,又“大为铁勒所败”。朝廷因处罗生母向氏(汉人)居留京师,遂以向氏之命招降处罗。
公元 609 年(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处罗辞以他故不至。隋炀帝大怒,从裴矩之策,鼓动处罗叔父阿史那射匮攻之。处罗大败后率数千骑东走高昌,并于公元 611 年(大业七年)降隋。隋炀帝对内徙处罗部众分三处安置:使处罗弟阙度设统羸弱万余口,居于会宁(今甘肃靖远);特勒(即王子)阿史那大奈将余众居于楼烦(今山西静乐);命处罗将 500 骑扈从天子巡幸,并赐号“曷萨那可汗”。
公元 619 年(唐武德二年),东突厥始毕可汗卒,其弟俟利弗设继立,是为处罗可汗。次年,处罗卒,更立其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颉利自恃强大,几乎年年南侵唐土。
公元 629 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乘其内外交困和连年灾荒,派兵一举灭亡其国,生擒颉利,俘突厥人十余万口。“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
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公开叛唐,拥强兵数十万,不断侵扰唐王朝的西境。唐高宗从公元 652 年(永徽三年)起,多次派兵征讨,最终于公元 657 年(显庆二年)彻底平定了叛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贺鲁已灭,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
西起里海,逾咸海,溯锡尔河,涉楚河,东至新疆北部地区,为西突厥十姓部落及其部游牧栖息地带。后来西突厥衰亡。在西突厥衰亡过程中,曾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内徙。一为公元 690 年(武周天授元年)10 月的阿史那斛瑟罗的率众内迁。斛瑟罗为步真之子,原为在朝供职的右玉钤卫将军。公元 686 年(垂拱二年),册为可汗。在其还蕃治理五弩失毕期间,屡遭后突厥侵掠,致部众“散亡略尽”。为回避寇扰,斛瑟罗于公元 690 年(天授元年)10 月“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另一次大的内徙发生于公元 714 年(玄宗开元二年)9 月至次年 4 月。这次内徙是因突骑施汗国可汗娑葛为后突厥可汗默啜擒杀,致十姓及别部某些首领率众内附以求庇护。据《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载,先后有葛逻禄三姓部落、五咄陆胡禄屋阙等部、五弩失毕诸部 2 万余帐(户),分别诣凉州、北庭内属。唐玄宗为安抚来归者,敕令北庭都护汤嘉惠等接援,下制“皆以河南处之”。又“寄在凉州界内”有“兴昔部落”,且置有隶于凉州都督府的“兴昔都督府”,当为斛瑟罗前次或此次五咄陆内徙者。此外,居于“金娑山(今新疆尼金山)之阳,蒲类之东”的西突厥沙陀部,于公元 808年(宪宗元和三年)因不堪吐蕃压迫,亦悉众内迁。其部先被置于盐州,后移众于定襄川至神武川一带。
公元 682 年(高宗永淳元年)至 744 年(玄宗天宝三年),颉利族人阿史那骨咄禄等尽复东突厥汗国故地,建立了强大的后突厥汗国。公元 745 年,后突厥破亡。其部众或依附回纥并最终为回纥所同化,或南徙降唐,或西迁中亚。
后突厥附唐者不少于万余帐。公元 742 年(天宝元年),后突厥贵族“西杀”妻子、默啜之孙勃德支特勤、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烛公主、宰相康阿义屈达干以及阿布恩、阿史德等部落 5000 余帐,驱驼马牛羊 20 余万,款塞归朝。
《周书·突厥传》云:“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贱老贵壮,寡廉耻,无礼义,犹古之匈奴也。”由此可见,突厥主要是一个以游牧业为主的民族。突厥也是中国北方各族中第一个创造了自己文字的民族。突厥文创作于 5世纪,近似于古代日耳曼人使用的卢尼文,其字母来源于阿拉米文的草体字母。如今保留下来的突厥文,主要是碑文,最著名的突厥文碑有三块: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暾欲谷碑。这三块文碑记录了毗伽可汗及其两位重要官员的功绩,是研究突厥历史的珍贵文物。
铁勒于战国、秦汉时称“丁零”,因民俗喜乘高轮车,所以北魏时亦号“高车”,“或曰敕勒,讹为铁勒”。铁勒部族种类繁多,活动区域相当广大。西海(今咸海)、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汉一带)、得嶷海(今里海)、拂林(即东罗马帝国)以东,以及北海(今贝加尔湖)均为其活动区域。唐贞观年间铁勒诸部百余万户,曾并为唐的州郡。公元 647 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及其部落设置了 13 个羁縻州。随后内属的铁勒其他部落,也都先后设置了羁縻府州。这些羁縻府州较远者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以骨利干部置玄阙州(在今贝加尔湖一带),以结骨部置坚昆府(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带),以俱罗部置烛龙州(在今西伯利亚赤塔东)。
铁勒部之一的回纥部属在唐玄宗时期曾建立起强大的回纥汗国并统一了漠北。公元 839 年(唐文宗开成四年),由于上层内讧和自然灾害,回纥急剧衰亡,其民族分为五支,两支南下,三支西迁。南下两支十余万众,多数降唐,并被配隶诸道。西迁三支,一支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
吐蕃的活动区域大致在今西藏、青海西南以及川西一带,曾建立过强大的吐蕃王国。公元 634 年(贞观八年),吐蕃曾派遣使者,与唐通好。公元 641 年(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西嫁吐蕃王赞普。从此大唐与吐蕃结甥舅之好,“和同为一家”。但其间战争亦不断发生。
吐谷浑原为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西晋初年游牧于今辽宁锦西北一带。后西迁至青海、甘南一带,公元 4 世纪初“兼并羌狄,号为强国”,公元 5 世纪时已经“地兼鄯善、且末”。隋炀帝因吐谷浑阻遏西域通道,于公元 609 年(大业五年),一举击破吐谷浑,其部落降隋者 10 余万人。公元 639 年(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派李靖等大破吐谷浑,并以宗女弘化公主嫁其可汗。唐高宗时吐谷浑为吐蕃所灭,其部族内徙者更多,唐高宗置安乐等州,武则天以归德等州予以安置。
党项为“三苗之裔”“西羌别种”,隋代时处地“东接临洮、西平,西距叶护,南北数千里”,唐代其东辽阔至松州。自公元 627 年(唐太宗贞观元年)开始,党项诸部相继内属,唐王朝就其部落设置了很多羁縻州。党项内属者人数极多,公元 692 年(武周天授三年)内附户凡 20 万,公元 760 年(唐肃宗上元元年)内徙者 10 万众。北宋时强大的西夏即其所建。
契丹属东胡族,初居漠北,唐时东与高丽接,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北至室韦,地方 2000 里。公元 648 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契丹君长“举部内属”。
奚族亦属东胡族,唐时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距白狼河(今大凌河),北至霫国(今内蒙古乌兰浩特至巴林左旗一带),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今西拉伦河)以至其国。公元 648 年,其酋长可度率部内属。
靺鞨,即先秦时的“肃慎”,部族种类繁多,其中一支曾于唐时建立过强大的渤海国。当其盛时,“南与新罗、与唐为界,东际海,西界契丹,东北至黑水靺鞨,西北至室韦,地方五千里”。公元 713 年(唐先天二年),曾封其王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部为忽汗州。室韦,为契丹别种,唐时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海。室韦诸部曾隶属于唐,唐王朝置室韦都督府以统辖之。室韦乌罗护部落有内徙者,如以讨安史之乱闻名的乌承恩、乌承泚兄弟,即出此族。
如上所述,隋唐时期的胡汉大交流大融合是在一个空前广大的区域中进行的,而且胡人内附内迁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这种大融合是在国家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的,而且在安史之乱之前,唐王朝国势强盛,这就为这种大融合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胡人进入内地,或分属各地,或侨置单立,大多都已编入户籍,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生产和生活。“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加速了改变其原本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进程。将内附内迁的胡人采用侨置州县的方式进行安置是唐人的一种创造,这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汉人相差极大的胡人自然是有益的,但这种做法也留下了不小的隐患。胡人与汉人杂居一处,和汉人通婚,使得这些胡人很快汉化了。
在唐代的胡汉大融合过程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长安、洛阳两大文化中心不仅有大批胡人居住,而且有大量的外国人居住。这在中国民族融合史与文化发展史上是有着特殊的贡献与意义的:
唐朝初年,“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公元 662 年(龙朔二年),洛阳置国子监,学生中也有不少胡人和外国人。日本先后 10 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也有自费入唐学习的。至公元 837 年(开成二年),新罗在长安诸学中学习的学生已达 216 人,为诸国遣唐留学生之最。周边诸族中入学的学生,唐初以吐蕃最多,后以渤海人为多,其他如粟特九姓、南诏,契丹、突厥等民族,都有子弟入国学学习。
如果说从汉代开始,代表中原文化的汉民族文化已经基本定型,那么在唐代,汉民族文化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汉文化吸收了大量异域文化,从而使汉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由于吸纳融入了大量异质文化,从而使汉文化本身的特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自然包括物质生产方面的内涵,但更突出地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比如佛教的传入,不仅直接影响了玄学,而且在唐代儒、释、道三教并举鼎立。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以及文学领域,亦是如此,隋唐燕乐正是吸收了大量异域音乐的产物。
总之,在这种胡汉民族大融合过程中,不仅使胡人汉化,也使得汉文化本身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