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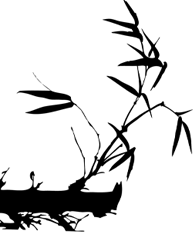
那是1955年春天,母亲挺着个大肚子,边晒太阳边替别人做着针线活,做新的补旧的,纳鞋底做袜底(那时买双新袜子都要缝上袜底,这样经得穿)。吃过午饭不久,母亲开始肚子痛,在太阳下山的时候生下了你。你是母亲生下的第六个孩子,也是我最小的弟弟,父亲给你起名杨锐。
母亲生产时根本不要人帮忙,只让我烧了一壶开水,将剪刀在火上消毒。我就站在母亲旁边,将烧好一阵子的开水倒进脸盆里。听到你的第一声啼哭,我很惊喜,可是母亲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如一个大病初愈才缓过气来的人。母亲接过我递给她的热毛巾,一次又一次地仔细给你擦洗身子,此刻起,你就是母亲疼爱的小家伙。我听到她轻轻地说了一句:“儿啊,你来得不是时候啊!”声音凄恻。我的心忽然抽紧了一下,不敢去看母亲的脸。
1955年,农村靠工分吃饭。劳动力多的家庭分到的粮食吃不完,而我们家人口多但没一个正劳力。母亲裹过的小脚只能做点旱地的活计,我还只十四岁多,一个半大妹子拼着小命做一天工,评给的工分也少得可怜,我们一家早早地进入了饥荒,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幸亏大哥尽可能节省钱和粮票帮衬家里。可是你和大哥一面之缘都没有,因为大哥在外地教书没有回来,没遇上你生也没看到你逝。
锐弟,你生下来好小好小,但母亲奶水好,哪怕喝口白开水的营养都要过给你,因此,你长得很快,一出月子就成了个小胖子。漆黑的头发长齐后脖子,黑珍珠般的眼睛,洁白的皮肤,胖手胖脚如藕节一般,又特别爱笑,你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小东西。上屋二菊见到你就要带你做崽,但有了田四送人的结局,母亲再也不敢把孩子送人,说死也死在一起。
真的是大人过一天小孩过一天,自然而然你就跟着我们长大了。你那么小,哪知父母是在怎样艰难的日子里度过一天又一天的呢?但你从来没有缺少爱,每个人都爱着你。父亲身体不好不能抱你,总是拿着你的小脚丫子亲。我做个鬼脸,学声牛叫、狗吠、猫叫都能逗得你咯咯地笑。我们朝夕相处,把彼此的命紧紧地捆在一起。你的笑给一家人带走了许多愁苦。
母亲裹过的小脚不能下水田,出着有限的工,生计全靠没日没夜地帮别人做针线活。我晚上也要跟着做到好晩,那瞌睡不请自来,脑壳栽下去,一激灵抬起头又接着做。母亲接针线活从不跟人讨价还价,用稻米、红薯、菜、柴火当工钱都要。日子仍吃了上餐愁着下顿,没米下锅是常事。
一日,一户人家要嫁女,要母亲帮做套新衣。吃过早饭,母亲对我说,今天你带弟弟们到远的地方玩,我这套嫁衣要做得更细致,让别人满意。母亲把你喂得饱饱的,乳白色的奶从嘴角都流出来了,用一根宽宽的布带把你绑在我背上。六岁多的赔三牵着三岁多的田四走在前面,就这样我们出发了。
这是一个阳光温煦、微风徐徐的上午。我们决定去桥墩底下玩。桥墩下是我们那里通往平江最近的一条河,是湖南四大河流之一湘江的支流,离家有两里多路。
我们沿着傍山小路走走停停,你在我背上,为了逗你,我时不时捏下你的小屁股,你在我背上咯咯地笑,我们几个都非常快乐。
河上用四根木头并拢架起一座木桥,只有四十多厘米宽,走在上面胆战心惊,稍不留神都有掉到河里的危险。这地方就叫桥墩,是通往平江的必经之路。我们沿着河堤下到桥墩下,河边的沙子冲洗得干干净净,太阳一照闪着光辉。沙滩柔软,河水清亮,波光粼粼。沙滩上长着大丛大丛碧色的芦苇,迎风摇曳。河滩上有蚌壳可捡来玩,岸边浅水处有小鱼一群一群地游来游去,我们捡石头打它们,看着小鱼慌忙乱窜好不开心。等一会儿它们又凑拢来了,甩着小小的尾巴游着,无比优雅,我们又用石头扔它们,乐此不疲地玩着。
我忽然抬头朝桥上看去,恰好见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掮根扁担,扁担一头缠着一大把棕绳,他从桥上飞跑过来,脚步踩得那桥直晃悠。我一下想起近些时间大人在传说来了几个捉细伢子的,捉到的细伢子捆紧挑到深山老林去卖。这人的样子像个捉细伢子的,吓得我魂飞魄散。我连忙要赔三、田四闭上眼睛,以防芦苇刺着,把他们塞进一堆芦围丛里,我紧紧抱着你也钻进芦苇里,大气都不敢出。似乎过了好一阵子,我从芦苇里轻轻地爬出来朝桥上一看,刚才那个男人牵着一头大黄牛,空扁担掮在肩上从容地从桥上走过去,我才恍然大悟,他的牛跑了,他是去牵牛的。
我抱着你从芦苇丛里爬出来,拉着赔三、田四的手让他们爬出来。我们几个的头上沾了好多草叶,我忍不住笑,把你放在地上坐着,帮赔三、田四捏掉头上的草叶,告诉他们那个人不是捉细伢子的,是去牵牛的,大概是他的牛挣脱绳子跑了,他带着绳子急忙去找他的牛。
只是这一惊,几乎吓得魂不附体,再无心思玩了,我说回家去。我紧紧抱着你,沿路走小腿还在轻轻地发抖,踩在地上似乎不瓷实,坐在路边休息了几次才回到家。
又一个春天来了,初春还有些冷,吹在脸上手上的风冰凉冰凉。一日,母亲要去福婶家做衣,你还没断奶,我驮着你跟母亲一起去。不要工钱,只管我们三人的一日三餐。
做衣服的门板就用两条长板凳搁在堂屋里,母亲不让我带你去堂屋玩,怕吵着她做衣服。我带着你在禾坪上玩,你刚开始学走路,两手分开,一边笑着,一边像鸭子样蹒跚走着。有时我在前面迎你,有时我在旁边牵你,有时我又在后面轻轻抓着你背带裤的背带。走了一阵,累了,你抓住我的衣,耍着赖,双脚勾起,怎么也不肯下地了,非要我抱不可。
一天过去了,吃过晩饭,母亲收拾好剪刀和针针线线,我仍驮着你,三人打道回府。回家的路上,你在我背上打了个战,我说:“冷吧,杨锐。”可是你还没学会说话。
回到家,你没有发烧,直接咳嗽起来。咳得小脸通红,咳得透不过气来。母亲到处打听土方子,每打听到一个土方子就是一个希望,一个又一个地尝试也毫不见效,咳嗽有增无减。没钱请医生没钱买药,抱着你看着你咳嗽的痛苦样子,我手足无措,一会儿给你拍拍背,一会儿给你摸摸胸,想减少你的一点痛苦。晩上,你咳得不能入睡,我和母亲通宵轮流抱你坐在怀里,被子上放着一个抽屉,抽屉里装着你的玩具——别人送的一个会跳的青蛙,母亲做的三个布娃娃,布娃娃有漆黑的头发,笑眯眯的眼睛,脸上打着腮红,还有几个小盒子,这些算你的全部玩具。实际上你哪里有心思玩呢,一会儿又咳,一会儿又咳。看着你的痛苦,我心里有着无尽的悲哀,但又无可奈何。
这是开始咳嗽的第十九个夜晚了,我照例和母亲在床上轮流抱你,你咳得似乎要柔和一点点,我想我的锐弟咳嗽快好了。内心一阵轻松,揽住你柔软的腰,你紧紧靠在我怀里,忽然睁开眼睛看我,又往我怀里拱了拱。我又把你抱紧一点,你居然不咳嗽了,我一阵惊喜,告诉母亲:“妈妈,杨锐不咳嗽了,好像好了。”母亲露出怔忡不安的眼神,伸手过来欲试探你的鼻息。母亲伸出的手似有千斤重,抖抖索索伸到你的鼻子前,随之轻轻地说,轻得似乎让人听不见:“我儿到底还是死了,我晓得早晩会有这一天。”
母亲把你从我怀里接过,紧紧抱住,脸贴着你的脸。
我似乎麻木了,心中似乎连悲伤都没有,甚至没为你小小生命的早逝而伤心哭泣。相反,我想着你总算解脱了,以后不用饿饭,无须体会饥饿等于活埋的滋味了。
天亮了,新的一天开始了,你全然不知。没有你的咳嗽声,家里显得格外安静,又觉得没有你的咳嗽声家里越发空荡荡的。父亲取下一片门板,把你放在门板上,你安静地躺着,如睡着一般没有一丝痛苦。我坐在你的侧边,手里纳着鞋底,不伤心,一点也不伤心,又在开始为活着努力。
爸爸终于钉成了个木匣子,爸爸似乎怕弄醒你,把你轻轻地从门板上抱起放进木匣子里,盖好板子钉好,然后抱着木匣子往旁边的山上走去。我拿着锄头低着头跟在后面。一滴眼泪也没流。
爸爸坐在一堆草上,木匣子还抱在怀里,凄败的脸色不忍看。我挖好了坑,爸爸把木匣子放进坑里,当第一锄泥巴撒向你的小屋(现在把它权当你的小屋,因为以后你每天都住在这里),我的心碎了,如那纷纷落下的泥土。但我始终没流眼泪。而心碎比号哭要痛苦得多,那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吞噬着我的心,一口一口。
一家人都没吃早饭,如被寒霜冻坏了的植物,低垂着沉重的头颅。
1958年,我家被迫搬迁到鱼家冲大屋场住。搬家前,我去看你,你的小小的坟茔变得更矮更小了。我回家拿了锄头给你培了些土,算是最后为你做的一件事情。
搬到鱼家冲,晩上有很多人坐在禾坪里乘凉。几个三四岁的细伢子在那里疯玩,母亲指着其中一个对我说:“要是杨锐在,也像他们那么大了。”猛然间我泪眼模糊。锐弟,其实我们都没忘记你啊!
锐弟,黄泉路上无老少,只是你来这阳世间也太过匆忙,匆忙得没能和姐姐说上一句话。我写这些,似乎在写一个长久的梦,恍惚中,我想我们还能见面,我们相拥在一起,天长地久,永不分开。这日子应该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