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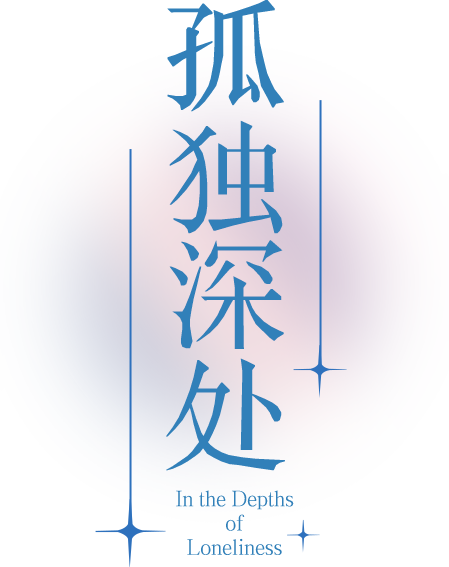
广场,黄昏。疲惫中的演奏。
天空沉寂而壮阔,金色的云碎成一丝一丝,铺陈在天边。夕阳的余晖照在鸟巢的边角,巨大的钢筋铁架明暗分明,西侧明亮反光,东侧在暗处,强烈的对比让锈迹斑斑的庞然大物显得苍老,就如同用真的树木枯枝在悬崖上铸就的荒废的巢。在庞大的避难人群的簇拥中,老旧的体育场似乎也带上了悲哀的气息,与第一乐章的葬礼进行曲的哀悼配合得天衣无缝,相得益彰。
演奏会在平淡无奇中进行。这已经是我们第一百二十一场演奏会了,乐手们演奏得缺乏激情,听众们也心不在焉。每个人都心事重重。尽管是新曲目,尽管是马勒第二这样激情的曲子,但大部分人还是不能保持精神清醒。重复让人麻木。第一声炮响传来的时候,一些人已经在台下睡着了。
对攻击到来,大多数人都毫无准备。当时我从台上望着台下的听众,这是我每天的习惯。一些小孩不断想挣脱母亲的怀抱去玩,母亲不许,双臂环抱住他们,手紧紧扣住他们的肩膀。母亲们总是面对台上的,只是她们也并没有在听,目光游移不定,头巾锁住额头疲倦的皱纹。这很正常。在这种时候演奏《复活》并不是个好主意,原本太艰难晦涩,庞大深沉,放在这种时候演,就更不能抓住人的注意。除了指挥,每个人都有些心不在焉,甚至包括我自己。在第五乐章一少半的地方,远方响起隆隆的炮声,与乐曲混在一起。有那么一瞬间,大家都还以为那只是音乐的效果。
轰隆。轰隆。那效果出奇地好,和低沉的音乐配在一起,震撼人心。台上台下一起呆呆地欣赏了片刻,片刻之后,才有人突然明白听到的是什么。
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声指着远方。人们吓了一跳,起身向后观望,森林公园方向有若隐若现的火光传来。一时间大家还在迟疑,没有人说话,除了面面相觑,就只有手指抠住手臂。远处能看到火光,但看不到人的奔逃。空气仍是静的。演奏仍在继续,女高音是唯一的声音,让四周显得愈发寂静。
片刻之后,声浪传来。爆炸燃烧的激波推动热浪,带着热气的空气经过压缩、膨胀、再压缩,穿过黄昏的冷气一路呼啸,从远方传到身边,成为衰弱却混杂着暴力和躁动的湍流。远处闷声的爆破压抑着痛苦,越模糊越让人恐惧。身边的人开始奔逃。喊叫、慌张、混乱。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攻击正在向身边转移,但人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向南拥挤,前推后搡,汇成洪流,跨过摔倒和尚未起步的人。刚刚那些搂着孩子的母亲此时像母鸡用翅膀护住小鸡一样将孩子护在身侧,左手拖着,右手挡在他身旁,孩子跟不上,跑得跌跌撞撞,母亲为了将周围人的挤撞挡开,爆发出了惊人的母牛般的力气。尖叫声不时撞击着耳膜。
我们仍然想演奏,可是不管怎么尽力,曲子还是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小提琴听不到黑管,定音鼓进错了位置,舞台外有人跌向贝斯,琴身发出碎裂的闷响。乐手们也开始恐惧,弦音不用揉就发出颤音。只有指挥在台上尽最大努力维持着乐队的平稳,可是不管他多么努力,我们也没能到达复活的天堂。
火光的橙红中,我们放弃了演奏。天边的颜色伴着夕阳,由橙变金,融入深蓝。我们坐在台上,没有和大家一起逃离。我们需要等待最后乐器的撤离。没有人说话。寂静充满天地,听不见喊叫和身边的哭闹。
人流漫过身旁,舞台像失事的船只。我们坐在乐器中间,看逃亡中的人,他们不看我们。按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不是一次激烈的攻击。天边的色调渐渐变浅,说明燃烧正在减弱熄灭。攻击很可能已经结束了,只是人们的逃离并没有暂缓,广场四面八方的难民源源不断地奔逃,挤进鸟巢,似乎是想为被惊吓勾起的恐惧记忆寻求一个庇护的窝。事后我们知道,这是海军一个隐藏的指挥控制据点被炸毁,像以往一样精确,没有多余的攻击和死亡,战火没有弥漫到森林公园之外。当天的我们是安全的。可是在那时那刻,看着那些因惊恐而僵硬的面容,绝对没有人能说大家的逃离是过度夸张。
曲终人散,凌乱的舞台只留声音的碎片。
攻击者始终没有出现。直到暮色越来越浓,我才看到飞机的一影。四架扁平的三角机在幽蓝黯淡的天空滑过,一闪而逝,机翼留下闪光,消失在平流层看不见的高度。
从战斗第三年开始,我们的演出就成了义务。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人们发现钢铁人不破坏古老的城市和与艺术相关的场所,这起初只是个猜想,经过小心翼翼的尝试,逐渐得到证实。乡村和小镇的人们开始疯狂地涌向古老的文明之都,寻求庇护,艺术演出团体也莫名地担上了防卫的责任,每天在各处演出,演出的方圆境内不受攻击。这就是我们的演出。
没人知道钢铁人的母星在哪里,它们懂地球人的语言,但不让地球人了解它们的。没人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入侵才只有三年,战斗却如摧枯拉朽,地球人败得毫无机会,抵抗一直进行,人们却越来越绝望。逃跑的士兵如同瘟疫,逃得越多,继续逃跑的就越多。从电视里偶尔能看见现身的外星人的样貌,比地球人略高,两米到三米之间,流线型的钢铁外表,永远看不见表情的冷酷和精确。
恐惧。悲愤。猜疑。人心惶惶中,流言不绝于耳,传着钢铁人的各种举动。它们捕获了一名音乐家。它们劫掠了历史博物馆的资料。它们对古迹和美术殿堂加以拍摄、研究和保护。它们对抵抗的军队杀戮铁血,不留情面,但拣出科学艺术和历史的相关群体,加以宽容。这是一幅既统一又分裂的肖像,一方面很残酷,一方面又很宽容,让人不知道它们是暴力主义还是贵族主义。它们住在月亮上,像月之暗面一样,永远不正面面对人类。人们只好猜测,在猜测中演艺术,让艺术家成为莫名的超人。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保卫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被动,却责任重大,严肃却失去艺术原本的意义。
三年中,人们从热血变得现实。从鼓舞的战斗变成求存的妥协,为了生存,努力学习。如果学习科学和艺术,它们说不准会格外网开一面。如果顺从地活在它们笼罩的天空之下,说不准还能活得很好。只要屈服。只要放弃。只要在它们的天空下歌舞升平。
总有人会不甘心,心怀不切实际的最后幻想。
林老师想要炸毁月球。
“老师。老师!”忽然有声音将我从沉思中拉回现实,我回过神。
是娜娜。她刚拉完一段协奏曲。
“这段拉得行吗?”娜娜问我,声音有点急躁。
“哦,还行。”我有点不好意思,几乎没有听清她的演奏。兵荒马乱中,很难让一个人心无旁骛地教授提琴。我知道老师有这个能力,可是我没有。我在浅层记忆记录的临时录音中搜寻了一下,似乎搜寻到刚刚听到的片段拉奏,不完整,而且缺乏鲜明对照。我只好说,“还不错,比你上周进步了,只是……还是能听出有一点急躁。”
“那是因为我不想拉了。”娜娜说,“您能不能告诉我妈妈,我不想学了。”
“为什么?”
“Alexon要走了。下个星期就走。”娜娜脱口而出。
“去哪儿?”
“不是告诉过您吗?”她说,“他要和爸爸妈妈去香格里拉。”
“哦。是的。我一时忘了。”
娜娜确实跟我说过。她今年十七岁,Alexon是她喜欢的男孩。他们曾经是同学,这两年停学,他们的感情却越发笃近。Alexon家里有显赫的势力,钢铁人在地球上圈出几块它们的控制中心,作为对地球的势力入侵,只有少数有金钱和权势的人被它们选中做傀儡控制者。Alexon一家被选中了,他们借助人间天堂的古老神话和从天而降的征服者,移居人间仙境,成为人间国王。娜娜不能同去,伤心欲绝。
“老师,您也有爱的女孩不是吗?”她说,“您一定明白,如果他走了,我再学什么都没意义了。”娜娜望着窗外,神情忧郁而悲伤。世间纷乱对她来说是无所谓的,两个人相爱是重要的。她早不想学琴了,只是妈妈逼她。她想和Alexon一起去钢铁人的管辖区。她爱他。“您能不能告诉我妈妈,我不学了。我要走。他会带我走的。”
我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回应。她信任我,不告诉妈妈的事情却告诉我,可是我不能回应这种信任。我可以信守承诺替她向母亲求情,可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不认为她和Alexon能幸福地生活在香格里拉。可我没法劝她,劝她她也不会信。
自从钢铁人的偏好被曝光,学琴的人数就呈几何级数增长,每个家长倾尽所有让孩子学防身的艺术,让每个能做家教的乐手应接不暇。不能再单独授课,小班上总要挤进四五个人,不宽敞的小屋显得越发拥挤。
越是这样,我越觉得没办法面对我的学生。在这样的时候,为了这样的生存需要而教琴,让我有一种无法承担的奇异的责任感。红木家具在身后压迫,谱架上写着令人慌张的速度,窗口透入的月光洒下人人皆知的威胁味道。
娜娜和雯雯是最近找我学琴的两个女孩子。娜娜不想学,可是雯雯比谁都想学好。她的母亲在逃难中伤了腿,只是为了她才坚持,拿出一切家当供她学琴,似乎未来的家的期望就托在她细细的琴弓之上。雯雯比谁都努力,拉琴的时候也有其他孩子没有的顽固的僵硬。
“雯雯,你放松一点。手指太僵了。”
雯雯涨红了脸,更加努力地拉,但这样一来,手指就更僵也更紧了,声音束缚而浮动,换弦的时候相当刺耳。看得出来,她是太认真,认真得过分了,过分得反应迟缓。
“等一下,”我试图调整,微微笑了笑,“雯雯,你怎么每次都这么紧张呢?出什么事了?没什么好紧张的。咱们这样,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再非常非常安静地试一次,心平气和,准备好了再开始。来,不着急,深呼吸。”
雯雯听我的话,深呼吸,闭上眼睛再睁开。可是一开头就错了。她停下来,不等我说就重新来,可是又错了,再重新来,连第一个音都找不准了。她又闭上眼睛,深呼吸,再睁开,睁开的时候满眼泪水。她还想拉,可是弓子仿佛太重了,她一提起来手臂就坠了下去,身子弓起来,像受惊的小猫一样哭了。她害怕了。
我的心随着她的眼泪沉下去。她在哭声中嗫嚅着说她必须拉好,拉不好可怎么办。月光透过窗子,洒在她弓起的背上,一片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