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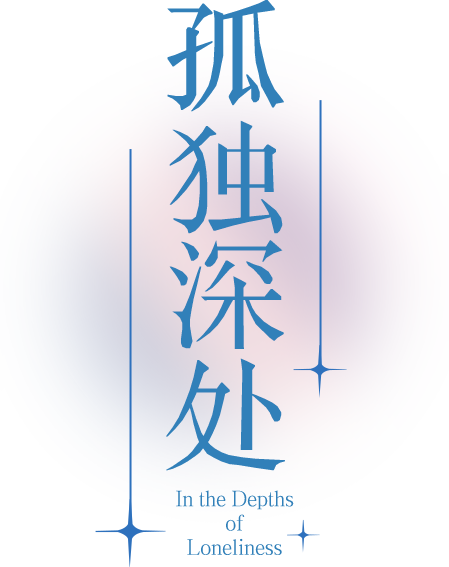
清晨4:50,老刀穿过熙熙攘攘的步行街,去找彭蠡。
从垃圾站下班之后,老刀回家洗了个澡,换了衣服。白色衬衫和褐色裤子,这是他唯一一套体面衣服,衬衫袖口磨了边,他把袖子卷到胳膊肘。老刀四十八岁,没结婚,已经过了注意外表的年龄,又没人照顾起居,这一套衣服留着穿了很多年,每次穿一天,回家就脱了叠上。他在垃圾站上班,没必要穿得体面,偶尔参加谁家小孩的婚礼,才拿出来穿在身上。这一次他不想脏兮兮地见陌生人。他在垃圾站连续工作了五小时,很担心身上会有味道。
步行街上挤满了刚刚下班的人。拥挤的男人女人围着小摊子挑土特产,大声讨价还价。食客围着塑料桌子,埋头在酸辣粉的热气腾腾中,饿虎扑食一般,白色蒸汽遮住了脸。油炸的香味弥漫。货摊上的酸枣和核桃堆成山,腊肉在头顶摇摆。这个点是全天最热闹的时间,基本都收工了,忙碌了几个小时的人们都赶过来吃一顿饱饭,人声鼎沸。
老刀艰难地穿过人群。端盘子的伙计一边喊着让让一边推开挡道的人,开出一条路来,老刀跟在后面。
彭蠡家在小街深处。老刀上楼,彭蠡不在家。问邻居,邻居说他每天快到关门才回来,具体几点不清楚。
老刀有点担忧,看了看手表,清晨5:00。
他回到楼门口等着。两旁狼吞虎咽的饥饿少年围绕着他。他认识其中两个,原来在彭蠡家见过一两次。每个少年面前都摆着一盘炒面或炒粉,几个人分吃两个菜,盘子里一片狼藉,筷子仍在无望而锲而不舍地拨动,寻找辣椒丛中的肉星。老刀又下意识闻了闻小臂,不知道身上还有没有垃圾的腥味。周围的一切嘈杂而庸常,和每个清晨一样。
“哎,你们知道那儿一盘回锅肉多少钱吗?”那个叫小李的少年说。
“靠,菜里有沙子。”另外一个叫小丁的胖少年突然捂住嘴说,他的指甲里还带着黑泥,“坑人啊。得找老板退钱!”
“人家那儿一盘回锅肉,就三百四。”小李说,“三百四!一盘水煮牛肉四百二呢。”
“什么玩意儿?这么贵。”小丁捂着腮帮子咕哝道。
另外两个少年对谈话没兴趣,还在埋头吃面,小李低头看着他们,眼睛似乎穿过他们,看到了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目光里有热切。
老刀的肚子也感觉到饥饿。他迅速转开眼睛,可是来不及了,那种感觉迅速席卷了他,胃的空虚像是一个深渊,让他身体微微发颤。他有一个月不吃清晨这顿饭了。一顿饭差不多一百块,一个月三千块,攒上一年就够糖糖两个月的幼儿园开销了。
他向远处看,城市清理队的车辆已经缓缓开过来了。
他开始做准备,若彭蠡再不回来,他就要考虑自己行动了。虽然会带来不少困难,但时间不等人,总得走才行。身边卖大枣的女人高声叫卖,不时打断他的思绪,声音洪亮刺得他头疼。步行街一端的小摊子开始收拾,人群像用棍子搅动的池塘里的鱼,倏一下散去。没人会在这时候和清理队较劲。小摊子收拾得比较慢,清理队的车耐心地移动。步行街通常只是步行街,但对清理队的车除外。谁若走得慢了,就会被强行收拢起来。
这时彭蠡出现了。他剔着牙,敞着衬衫的扣子,不紧不慢地踱回来,不时打个饱嗝。彭蠡六十多了,变得懒散不修边幅,两颊像沙皮狗一样耷拉着,让嘴角显得总是不满意地撇着。如果只看这副模样,不知道他年轻时的样子,会以为他只是个胸无大志只知道吃喝的㞞包。但在老刀很小的时候,他就听父亲讲过彭蠡的事。
老刀迎上前去。彭蠡看到他要打招呼,老刀却打断他:“我没时间和你解释。我需要去第一空间,你告诉我怎么走。”
彭蠡愣住了,已经有十年没人跟他提过第一空间的事,他的牙签捏在手里,不知不觉掰断了。他有片刻没回答,见老刀实在有点急了,才拽着他向楼里走。“回我家说,”彭蠡说,“要走也从那儿走。”
在他们身后,清理队已经缓缓开了过来,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将人们扫回家。“回家啦,回家啦。转换马上开始了。”车上有人吆喝着。
彭蠡带老刀上楼,进屋。他的单人小房子和一般公租房无异,六平方米房间,一个厕所,一个能做菜的角落,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胶囊床铺,胶囊下是抽拉式箱柜,可以放衣服物品。墙面上有水渍和鞋印,没做任何修饰,只是歪斜着贴了几个挂钩,挂着夹克和裤子。进屋后,彭蠡把墙上的衣服毛巾都取下来,塞到最靠边的抽屉里。转换的时候,什么都不能挂出来。老刀以前也住这样的单人公租房。一进屋,他就感到一股旧日的气息。
彭蠡直截了当地瞪着老刀:“你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就不告诉你怎么走。”
已经5:30了,还有半个小时。
老刀简单讲了事情的始末。从他捡到纸条瓶子,到他偷偷躲入垃圾道,到他在第二空间接到的委托,再到他的行动。他没有时间描述太多,最好马上就走。
“你昨天躲在垃圾道里?去第二空间?”彭蠡皱着眉,“那你得等二十四小时啊。”
“二十万块。”老刀说,“等一礼拜也值啊。”
“你就这么缺钱花?”
老刀沉默了一下。“糖糖还有一年多该去幼儿园了。”他说,“我来不及了。”
老刀去幼儿园咨询的时候,着实被吓到了。稍微好一点的幼儿园招生前两天,就有家长带着铺盖卷在幼儿园门口排队,两个家长轮着,一个吃喝拉撒,另一个坐在幼儿园门口等,还不一定能排进去。前面的名额早用钱买断了,只有最后剩下的寥寥几个名额分给苦熬排队的爹妈。这只是一般不错的幼儿园,更好一点的连排队都不行,从一开始就是花钱买机会。老刀本来没什么奢望,可是自从糖糖一岁半之后,就特别喜欢音乐,每次在外面听见音乐,她就小脸放光,跟着扭动身子手舞足蹈。那个时候她特别好看。老刀对此毫无抵抗力,他就像被舞台上的灯光层层围绕着,只看到一片耀眼。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想送糖糖去一个能教音乐和跳舞的幼儿园。
彭蠡脱下外衣,一边洗脸,一边和老刀说话。说是洗脸,不过只是用水随便抹一抹。水马上就要停了,水流已经变得很小。彭蠡从墙上拽下一条脏兮兮的毛巾,随意蹭了蹭,又将毛巾塞进抽屉。他湿漉漉的头发显出油腻的光泽。
“你真是作死,”彭蠡说,“她又不是你闺女,犯得着吗?”
“别说这些了。快告诉我怎么走。”老刀说。
彭蠡叹了口气:“你可得知道,万一被抓着,可不只是罚款,得关上好几个月。”
“你不是去过好多次吗?”
“只有四次。第五次就被抓了。”
“那也够了。我要是能去四次,抓一次也无所谓。”
老刀要去第一空间送一样东西,送到了挣十万块,带来回信挣二十万。这不过是冒违规的风险,只要路径和方法对,被抓住的概率并不大,挣的却是实实在在的钞票。他不知道有什么理由拒绝。他知道彭蠡年轻的时候为了几笔风险钱,曾经偷偷进入第一空间好几次,贩卖私酒和烟。他知道这条路能走。
5:45。他必须马上走了。
彭蠡又叹口气,知道劝也没用。他已经上了年纪,对事懒散倦怠了,但他明白,自己在五十岁前也会和老刀一样。那时他不在乎坐牢之类的事。不过是熬几个月出来,挨两顿打,但挣的钱是实实在在的。只要抵死不说钱的下落,最后总能过去。秩序局的条子也不过就是例行公事。他把老刀带到窗口,向下指向一条被阴影覆盖的小路。
“从我房子底下爬下去,顺着排水管,毡布底下有我原来安上去的脚蹬,身子贴得足够紧了就能避开摄像头。从那儿过去,沿着阴影爬到边上。你能摸着也能看见那道缝。沿着缝往北走。一定得往北。千万别错了。”
彭蠡接着解释了爬过土地的诀窍。要借着升起的势头,从升高的一侧沿截面爬过五十米,到另一侧地面,爬上去,然后向东,那里会有一丛灌木,在土地合拢的时候可以抓住并隐藏自己。老刀没有听完,就已经将身子探出窗口,准备向下爬了。
彭蠡帮老刀爬出窗子,扶着他踩稳了窗下的踏脚。彭蠡突然停下来。“说句不好听的,”他说,“我还是劝你最好别去。那边可不是什么好地儿,去了之后没别的,只能感觉自己的日子有多操蛋。没劲。”
老刀的脚正在向下试探,身子还扒着窗台。“没事。”他说得有点费劲,“我不去也知道自己的日子有多操蛋。”
“好自为之吧。”彭蠡最后说。
老刀顺着彭蠡指出的路径快速向下爬。脚蹬的位置非常舒服。他看到彭蠡在窗口的身影,点了根烟,非常大口地快速抽了几口,又掐了。彭蠡一度从窗口探出身子,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缩了回去。窗子关上了,发着幽幽的光。老刀知道,彭蠡会在转换前最后一分钟钻进胶囊,和整个城市数千万人一样,受胶囊定时释放出的气体催眠,陷入深深睡眠,身子随着世界颠来倒去,头脑却一无所知,一睡就是整整四十个小时,到次日晚上再睁开眼睛。彭蠡已经老了,他终于和这个世界其他五千万人一样了。
老刀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向下,一蹦一跳,在离地足够近的时候纵身一跃,匍匐在地上。彭蠡的房子在四层,离地不远。爬起身,沿高楼在湖边投下的阴影奔跑。他能看到草地上的裂隙,那是翻转的地方。还没跑到,就听到身后在压抑中轰鸣的隆隆声和偶尔清脆的嘎啦声。老刀转过头,高楼拦腰截断,上半截正从天上倒下,缓慢却不容置疑地压迫过来。
老刀被震住了,怔怔看了好一会儿。他跑到缝隙处,伏在地上。
转换开始了。这是24小时周期的分隔时刻。整个世界开始翻转。钢筋砖块合拢的声音连成一片,像出了故障的流水线。高楼收拢合并,折叠成立方体。霓虹灯、店铺招牌、阳台和附加结构都被吸收入墙体,贴成楼的肌肤。结构见缝插针,每一寸空间都被占满。
大地在升起。老刀观察着地面的走势,来到缝的边缘,又随着缝隙的升起不断向上爬。他手脚并用,从大理石铺就的地面边缘起始,沿着泥土的截面,抓住土里埋藏的金属断茬,最初是向下,用脚试探着退行,很快,随着整块土地的翻转,他被带到空中。
老刀想到前一天晚上城市的样子。
当时他从垃圾堆中抬起眼睛,警觉地听着门外的声音。周围发酵腐烂的垃圾散发出刺鼻的气息,带一股发腥的甜腻味。他倚在门前。铁门外的世界在苏醒。
当铁门掀开的缝隙透入第一道街灯的黄色光芒,他俯下身去,从缓缓扩大的缝隙中钻出。街上空无一人,高楼灯光逐层亮起,附加结构从楼两侧探出,向两旁一节一节伸展,门廊从楼体内延伸,房檐沿轴旋转,缓缓落下,楼梯降落延伸到马路上。步行街的两侧,一个又一个黑色立方体从中间断裂,向两侧打开,露出其中货架的结构。立方体顶端伸出招牌,连成商铺的走廊,两侧的塑料棚向头顶延伸闭合。街道空旷得如同梦境。
霓虹灯亮了,商铺顶端闪烁的小灯打出新疆大枣、东北拉皮、上海烤麸和湖南腊肉的字样。
整整一天,老刀头脑中都忘不了这一幕。他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八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一切。他的日子总是从胶囊起,至胶囊终,在脏兮兮的餐桌和被争吵萦绕的货摊之间穿行。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世界纯粹的模样。
每个清晨,如果有人从远处观望——就像大货车司机在高速北京入口处等待时那样——他会看到整座城市的伸展与折叠。
清晨六点,司机们总会走下车,站在高速边上,揉着经过一夜潦草睡眠而昏沉的眼睛,打着哈欠,相互指点着望向远处的城市中央。高速截断在七环之外,所有的翻转都在六环内发生。不远不近的距离,就像遥望西山或是海上的一座孤岛。
晨光熹微中,一座城市折叠自身,向地面收拢。高楼像最卑微的仆人,弯下腰,让自己低声下气切断身体,头碰着脚,紧紧贴在一起,然后再次断裂弯腰,将头顶手臂扭曲弯折,插入空隙。高楼弯折之后重新组合,蜷缩成致密的巨大魔方,密密匝匝地聚合到一起,陷入沉睡。然后地面翻转,小块小块土地围绕其轴,一百八十度翻转到另一面,将另一面的建筑楼宇露出地表。楼宇由折叠中站立起身,在灰蓝色的天空下像苏醒的兽类。城市孤岛在橘黄色晨光中落位,展开,站定,腾起弥漫的灰色苍云。
司机们就在困倦与饥饿中欣赏这一幕无穷循环的城市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