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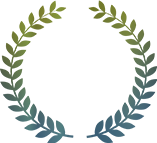
爸爸妈妈和娜佳姨妈不在家。他们到那个总是骑着一匹小灰马的老军官家参加洗礼去了。在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格利沙、安妮娅、阿辽沙、索尼娅和厨娘的儿子安德烈坐在客厅的餐桌旁玩“罗托”
 。凭良心说,他们该去睡觉了,但还没有从妈妈那儿打听出受洗礼的小娃娃长什么样,以及晚宴上都有什么吃的,难道能睡得着吗?
。凭良心说,他们该去睡觉了,但还没有从妈妈那儿打听出受洗礼的小娃娃长什么样,以及晚宴上都有什么吃的,难道能睡得着吗?
此时桌子的上面吊着一盏灯,照着桌子上乱七八糟的数字板、果壳、纸片和带有数字的小玻璃片。每个参加游戏的孩子面前都放着两张数字板和一小堆玻璃片。桌子当中有个白白的小碟子,里面放着五枚一戈比的硬币;在盘子周围,有一只吃了一半的苹果,一把剪刀,一个应该用来放果壳的盘子。孩子们在赌钱,赌注是一戈比,大家定了一条规矩:谁作弊就马上开除谁。除了这几个玩游戏的孩子,桌旁再没有别人了。保姆阿加菲娅·伊万诺夫娜正在厨房教厨娘裁衣服;他们的大哥,五年级的瓦夏,正无聊地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
他们玩得很起劲。格利沙的表情最紧张。这是个九岁的男孩,矮个子,胖脸蛋,剃着光头,嘴唇厚厚的,像黑人一样。他已经在上学校的预备班了,因此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他是为了赢钱才玩的。如果不是为了碟子里的那些戈比,他早去睡觉了。格利沙褐色的眼睛不安而嫉妒地扫视着同伴们的纸板,他的光头里塞满了赢不了钱的恐惧、妒忌,以及钱财方面的考虑,这使得他集中不了精神,没法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总是如坐针毡地扭动着身体。他一赢就急忙把钱抓过来,立刻藏在口袋里。
他的妹妹,八岁的安妮娅,长着一个尖下巴,一双聪颖、明亮的眼睛,她也生怕别人赢:她的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其他的赌徒。她对钱并不感兴趣,对她来说,赌运是关乎自尊心的问题。
另外一个妹妹索尼娅,是个六岁的小姑娘,长着一头鬈发,脸蛋白里透红。只有非常健康的孩子,价钱昂贵的娃娃,以及糖果盒上画的小孩才有这样的脸蛋。她是因为喜欢游戏本身才玩的。她满脸痴迷,无论谁赢了,她都一样开心,拍手大笑。
阿辽沙是个小胖子,像个圆球,他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也瞪大眼睛盯着牌。他既不爱钱,也不争面子,只要不把他从桌子旁赶走,不打发他去睡觉,他就谢天谢地了。别看他表面上挺超脱的,骨子里可是个十足的小坏蛋。他坐在这儿与其说是为了玩“罗托”,不如说是为了等着看赌钱时在所难免的纠纷,要是谁打了人或是骂了人,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本来他早就想去趟厕所了,但他却一分钟也不离开桌子,生怕不在时别人会拿走他的玻璃片和戈比。因为他只认得一位数和以零结尾的数,所以就由安妮娅替他算数目。
第五个玩伴是厨娘的儿子安德烈。这是一个皮肤发暗、病恹恹的男孩,他穿一件印花衬衫,胸口戴着一个铜十字架,正带着一种痴迷的表情凝神望着数字。他对赢钱和别人的斩获都无动于衷,因为他完全沉浸于数学的游戏及其简单的哲理中:世界上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数字啊!而它们竟然不会互相混淆!
除了索尼娅和阿辽沙,所有的人依次喊出数字。由于数字太单调,玩着玩着,孩子们就为它们发明了许多的术语和可笑的外号。比方说,赌徒们把七叫作拨火棍,把十一叫作两根小棍,把七十七叫作谢苗·谢苗内奇,把九十叫作老爷爷,等等。此时孩子们玩得正起劲。
“三十二!”格利沙喊道,一边从父亲的帽子里掏出一些黄色的圆纸筒,“二十七!拨火棍!二十八—割干草!”
安妮娅看见安德烈错过了二十八。要放在其他时候,她一定会向他指出来,但现在她的自尊心跟硬币一起放在那个小碟子里,所以她暗自高兴。
“二十三!”格利沙继续喊,“谢苗·谢苗内奇!九!”
“红蟑螂,红蟑螂,”索尼娅指着一只跑过桌子的红蟑螂喊着,“哎呀!”
“别打,”阿辽沙用他的男低音说,“它可能有孩子……”
索尼娅目送着红蟑螂,想着它的孩子:“它们该是些多小的红蟑螂啊!”
“四十三!一!”格利沙继续喊道,他因为安妮娅快赢了而感到痛苦,“六!”
“赢了!我赢了!”索尼娅叫起来,她娇憨地转动着眼珠,大笑起来。
其他的玩伴脸都拉长了。
“得检查一下!”格利沙恨恨地看着索尼娅,说道。
格利沙仗着自己年龄最大、最聪明,在牌桌上发号施令,别人都得听他的。他们把索尼娅的纸板仔仔细细地检查了很久,使她的玩伴们大失所望的是,她并没有作弊。下一盘又开始了。
“昨天我看见了什么呀!”安妮娅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菲里普·菲里普维奇不知怎么弄的,把眼皮翻了起来,他的眼睛变成了红的,可吓人了,像魔鬼一样。”
“我也看见了。”格利沙说,“八!我有个同学会动耳朵。”
安德烈抬眼看看格利沙,想了想,说:
“我也会动耳朵……”
“你动动看!”
安德烈动他的眼睛、嘴唇、手指,他以为他的耳朵也动起来了。大家一起笑他。
“这个菲里普·菲里普维奇是个坏人,”索尼娅叹了口气,说,“昨天他到我们儿童室来,可那时我只穿着一件衬衣……我觉得这样很没礼貌!”
“赢了!”格利沙忽然大叫起来,同时把钱从碟子里抓过来,“我赢了!你们检查吧,要是愿意的话!”
厨娘的儿子抬起眼睛,脸变白了。
“我,那个,不能再玩了。”他喃喃地说。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没钱了。”
“没钱不能玩!”格利沙说。
安德烈抱着一线希望又把衣兜翻了一通,可是除了一些面包皮和一截带着牙印的铅笔,什么也没有。他撇撇嘴,开始难过地眨眼睛,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我替你下注!”索尼娅说,她受不了他那痛苦的眼神。“可是你以后得还我。”
钱凑齐了,赌局接着进行。
“好像什么地方在敲钟。”安妮娅瞪大眼睛说。
所有的孩子都停下游戏,张开嘴,望着黑乎乎的窗户,却只看到了室内的灯投射在黑暗中的影像。
“你听错了。”
“夜里只有墓地才敲钟。”安德烈说。
“墓地为什么要敲钟?”
“为了不叫强盗进教堂。他们怕敲钟。”
“强盗进教堂去干什么?”索尼娅问道。
“这还不明白:为了把看门人打死呗!”
有一会儿谁都不说话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战战兢兢地继续玩。这一次安德烈赢了。
“他作弊。”阿辽沙无缘无故地用男低音说。
“你胡说,我没作弊!”
安德烈气得脸都白了,嘴也歪了,照着阿辽沙的脑袋打了一下子!阿辽沙凶狠地瞪着眼睛,蹿起来,一只膝盖跪在桌子上,也照着安德烈的脸打了一个耳光!接着两个人又互相打了一个耳光,都大哭起来。索尼娅受不了这么可怕的场面,也哭了,于是餐厅里不同调门的哭声响成一片。但不要以为赌局就此结束了。过了还不到五分钟,孩子们开始大笑,又和和气气地说话了。他们脸上还带着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笑。阿辽沙甚至感到满足:总算打了一架!
五年级的学生瓦夏走进餐厅。他一副困倦颓唐的样子:
“真岂有此理!”他看见格利沙正摸索着他那装着硬币、叮当作响的口袋,“难道能给小孩子钱吗?难道能允许他们赌博吗?这种教育真够好的,没说的。岂有此理!”
但小孩子们玩得那么来劲,他自己也不禁想要参加进来,试试运气。
“等一下,我也玩。”他说。
“拿出一个戈比!”
“马上。”他掏着兜说,“我没有一戈比,但这儿有一卢布。我出一卢布。”
“不行,不行,不行……放一个戈比!”
“你们这些傻瓜,不管怎么说,卢布要比戈比值钱。”中学生解释道,“谁赢了,就找给我钱。”
“不行,对不住,你走吧!”
五年级学生耸耸肩膀,去厨房找女仆要零钱。但厨房里一个戈比都没有。
“那你换给我零钱。”他从厨房回来后,又来缠格利沙,“我付给你利息。你不愿意?那卖给我十个戈比,我给你一卢布。”
格利沙怀疑地斜眼看着瓦夏:他是不是在耍什么圈套?这是不是一个骗局?
“我不。”他说,紧紧攥住口袋。
瓦夏开始发脾气、骂人,管这些赌徒叫蠢货、死脑筋。
“瓦夏,我替你出钱!”索尼娅说,“坐下吧!”
中学生坐下来,在自己面前放了两张纸板。安妮娅开始喊数。
“我掉了一个戈比!”格利沙忽然焦急地说,“等会儿!”
孩子们取下灯,爬到桌子底下去找那一个戈比。他们的手抓到痰和果核,头碰在一起,但没有找到戈比。他们又重新开始找,直到瓦夏把灯从格利沙手里夺下,放回原处。格利沙还是摸着黑接着找。
但现在终于找到了那个戈比。赌徒们在桌旁坐下,想继续玩。
“索尼娅睡着了!”阿辽沙报告。
索尼娅把长着鬈发的脑袋放在胳膊上,睡得十分香甜,就像她已经睡了一个钟头似的。她是在别人找戈比时不知不觉睡着的。
“去,到妈妈的床上睡去!”安妮娅说,领着她离开餐厅,“走吧。”
孩子们一起送她。而过了大约五分钟,妈妈的床上呈现出一个有趣的场面:索尼娅在睡觉,阿辽沙在她的旁边打着鼾,格利沙和安妮娅把头枕在他们的腿上睡着,厨娘的儿子安德烈也挤着躺在那儿。在他们身边散落着许多的戈比,它们已经失去了作用,直到下次赌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