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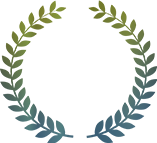
夜里一点多。我在公寓里赶一篇诗体小品文的约稿。忽然门开了,跟我同住的前音乐学院的学生彼得·鲁波廖夫完全出人意料地走进屋来。他头戴大礼帽,大衣敞着怀,乍一看,我觉得他活像列别基洛夫
 ;随后,当我定睛看清他那苍白的脸庞和异常尖锐的目光,以及那好像发炎的眼睛,就不觉得他像列别基洛夫了。
;随后,当我定睛看清他那苍白的脸庞和异常尖锐的目光,以及那好像发炎的眼睛,就不觉得他像列别基洛夫了。
“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早?”我问道,“才刚两点钟,难道婚礼已经结束了?”
我那同屋并不回答。他一言不发地走到屏风后面,脱了衣服,喘着粗气躺到床上。
“睡吧!你这蠢猪!”过了十分钟,我听见他嘟囔,“既然躺下了,那就睡!要是不想睡,那就……见你的鬼去!”
“你睡不着吗,别佳
 ?”我问道。
?”我问道。
“鬼才知道……不知怎么睡不着……总是想笑……笑得睡不着!哈!哈!”
“你有什么可笑的?”
“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竟出了这种该死的事!”
鲁波廖夫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笑着坐到我身旁。
“可笑,又……丢脸……”他一边用手把头发拨乱,一边说,“打从出生,我的老弟,我还没经历过那样的怪事!……哈!哈!一场混乱,头号闹剧!上流社会的一出闹剧。”
鲁波廖夫用拳头敲着膝盖,又一下子站起来,光着脚在凉地板上走来走去。
“我挨了个巴掌!”他说,“因此我提前回来了。”
“得了,干吗说谎?”
“上帝保佑……一个巴掌……一点儿不错!”
我打量着鲁波廖夫。他面色疲惫,可是整个外表依然是那么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以至于“一个巴掌”这个粗鲁的词和他的书生气质完全扯不到一块儿。
“那是一场头号闹剧……我一路回家一路大笑,噢,你快别写你那破玩意儿了!我跟你说说,把一切说出来,也许,就不那么想笑了!……快停下!很有趣的事!……喏,你听我说……在阿尔巴特街住着某位普里斯维斯多夫,一个退伍中校,娶了冯·克拉克伯爵的私生女……也算作贵族……他把女儿嫁给了商人的儿子叶斯基莫索夫,这位叶斯基莫索夫是个paevenu
 、mauvaisgenre
、mauvaisgenre
 和戴小圆帽的猪猡
和戴小圆帽的猪猡
 ,mauvaiston
,mauvaiston
 ,可那父女二人,一心想着manger
,可那父女二人,一心想着manger
 、boire
、boire
 ,也就顾不了什么mauvais genre了,今晚八点多钟我去普里斯维斯多夫家弹钢琴。道路泥泞,雾雨迷蒙……我心里像平日一样忧郁。”
,也就顾不了什么mauvais genre了,今晚八点多钟我去普里斯维斯多夫家弹钢琴。道路泥泞,雾雨迷蒙……我心里像平日一样忧郁。”
“你说简短点儿,”我对鲁波廖夫说,“别搞心理描写……”
“好吧……我来到普里斯维斯多夫家……婚礼过后,年轻人和客人们正在大嚼水果,我等着舞会开始,走到我的工位—钢琴旁边坐下来。
“‘啊,啊……你来了!’主人看见我,说,‘那么你,伙计,要当心,好好弹,主要是—别喝醉了……’
“我,老弟,已经习惯人家这样迎接我,也没生气……哈!哈!……既是个蘑菇,就不能不让人采啊!……不是这样吗?我算个什么呢?钢琴师,仆人……一个会弹琴的侍者……在商人家还被人用‘你’呼来唤去,还赏我茶钱—而我一点儿也不生气!于是,由于无事可做,我就在舞会开始前稍稍试练一下,你知道,好活动活动手指。我弹了一会儿,听见,我的老弟,身后有人在随着琴声哼唱。我回头一看,是位小姐!这小妖精站在我的身后,亲切地看着琴键。我说‘mademoiselle
 ,我不知道有人在听我弹琴!’而她叹息道:‘多好的曲子!’‘是啊,’我说,‘是支好曲子,……那么您喜爱音乐喽?’就这么攀谈起来,那小姐很健谈。我又没逗她说,是她自己侃起来的。‘多遗憾,’她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学习严肃音乐了。’我这傻瓜,糊涂虫,很高兴有人能注意到我……还是那讨厌的自尊!……我,你知道,就拿开了架势,向她解释年轻一代的冷漠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缺少美的需求,我竟讲起大道理来了!”
,我不知道有人在听我弹琴!’而她叹息道:‘多好的曲子!’‘是啊,’我说,‘是支好曲子,……那么您喜爱音乐喽?’就这么攀谈起来,那小姐很健谈。我又没逗她说,是她自己侃起来的。‘多遗憾,’她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学习严肃音乐了。’我这傻瓜,糊涂虫,很高兴有人能注意到我……还是那讨厌的自尊!……我,你知道,就拿开了架势,向她解释年轻一代的冷漠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缺少美的需求,我竟讲起大道理来了!”
“那闹剧呢?”我问鲁波廖夫,“你爱上她了,还是怎么的?”
“亏你想得出!恋爱……这是私人的闹剧,而发生的却是差不多全体卷入的、上流社会的闹剧……是的!我跟那小姐谈着谈着,忽然觉得有点儿不对劲:我身后坐着的几个人在叽叽喳喳……我听见‘钢琴师’这个词,有人‘嘿嘿’地笑……就是说,在议论我……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我的领结松了?我摸摸领结—好好的……当然,我就没有在意,继续谈话……而那小姐情绪激动,和我争论,脸涨得红红的。她是那么激烈,猛烈抨击作曲家们,可真够冲的!照她的意见,《恶魔》中管弦乐的编排是好的,可是没有旋律,李姆斯基─克尔萨柯夫只是个鼓手,瓦尔拉莫夫创作不出任何完整的东西……如今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们花二十五戈比上一节音乐课,刚能凑合弹几个音阶,就以为能写音乐评论了……我这位小姐就是这样的……
“我听着,但并不争辩……我喜欢那青春的气息,喜欢看到他们思考问题,但我的身后一直在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到底怎么回事呢?忽然一个胖胖的雌孔雀摇摇摆摆地向我这位小姐踱过来,大概是妈妈姨姨之流,神情庄重,面色紫红,足有五抱粗……她看也不看我,在她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什么……你注意听……那小姐跳起来,捧住双颊,就像给蜇了一下似的,一下子从钢琴旁边跳开了……
“到底怎么回事?聪明的俄底浦斯,请解释一下吧!喏,大概,或是我的礼服从后面开裂了,或是那小姐在衣装打扮上出了什么问题,否则很难理解这件怪事。为了稳妥起见,过了十分钟,我到前厅去检查自己的形象……我检查了领结、礼服、裤扣……全都安然无恙,什么也没破。算我走运,老弟,前厅里有个拿着包的老妈子,她把一切解释给我听了……要不是她,我会被一直幸福地蒙在鼓里。‘我家小姐总是改不了脾气,’她跟一个仆人说,‘她看到钢琴旁边有个年轻人,就跟他扯起闲篇儿来了,就像和一个真正的上流人谈话似的……又是叫又是笑,可这个年轻人原来不是客人,是钢琴师……是个弹琴的。你可聊得真来劲!多亏玛尔法·斯捷潘诺夫娜悄悄告诉了她,要不她没准儿还会跟他挽手呢……现在害臊了,可是晚了,说出的话也收不回来了……’你觉得如何,啊?”
“小姑娘也蠢,老妈子也蠢,”我对鲁波廖夫说,“不值得介意。”
“我也没介意……只是感到可笑,再就没什么了……我对这种事习以为常了……当初,的确曾经难受过,而如今……去他的吧!小姑娘傻乎乎的,年纪轻轻……她也怪可怜的!我坐下,开始弹舞曲……那里不需要任何严肃的作品……我只管弹那些华尔兹、卡特里尔舞曲、轰鸣的进行曲……要是你那颗音乐家的心感到难耐,就去喝上一杯,于是你自己也就会随着《薄伽丘》
 的乐曲兴奋起来了。”
的乐曲兴奋起来了。”
“那闹剧又是怎么回事?”
“我按着琴键……并没想那姑娘……只是一笑了之而已,可是……我的心底有某种东西在翻腾,就好像有个老鼠正在那里偷啃不花钱的面包干……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何那样郁郁不乐……我说服自己,骂自己,嘲笑自己……我随着自己的琴声哼唱,可是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刺痛……不知怎的刺得难受……先是胸口有什么东西在翻腾、啃咬,突然冲向喉咙,那感觉……就像堵着一团东西……你咬紧牙关,忍一会儿,它就退下去了,然后又来一次……这是什么事儿啊!就这样,好像成心似的,脑子里尽是各种各样倒霉的想法……
“我想到,我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废物……跑了两千里地来到莫斯科,指望当个作曲家或钢琴演奏家,却成了个钢琴师……实际上,这是很自然的……简直可笑,可我心里还是翻江倒海的……我也想起了你……我想,我那同屋此刻正在那儿爬格子呢……这可怜的家伙描写昏睡的议员、面包里的蟑螂、秋天的坏天气……写的都是早就被描写过的东西,陈词滥调……我这样想着,不知为什么可怜起你来了……怜惜得快掉泪了!……你是个圣洁的小人物,有灵魂,可是你知道,你没有那种如火的东西,没有胆子,没有力量……没有狂热的激情。为什么你不是个药剂师,不是个鞋匠,而是个作家,基督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我想起我所有那些不走运的朋友,所有这些歌手、画家、业余爱好者,曾经,所有这些幻想是那么令人心潮起伏、朝思暮想,他们豪气冲天,而如今……鬼才知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脑子里净钻进一些这样的念头。把自己的事赶出去,就想起朋友们,把朋友赶出去,又想起那姑娘……我嘲笑那姑娘,断定她一钱不值,可是她总不让我安生……我想,俄国人是什么鬼东西啊!当你自由自在,正在念书或者无事游荡,你可以跟他一起喝茶,拍他的肚皮,跟他女儿谈情说爱,可只要你成了地位稍微比他低一点儿的人,你可就得有自知之明了……你知道,我竭力扼制这些想法,但它们还是直往嗓子眼里撞……一个劲儿往上撞,揪心、憋闷……最后我觉得我的眼眶湿了,我的《薄伽丘》中断了,于是……一切都见鬼去了,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一阵鬼哭狼嚎……我歇斯底里大发作……”
“你胡说!”
“上帝保佑!”鲁波廖夫红着脸强笑着说,“那真是一场大乱啊!后来我觉得有人把我拽到前厅……给我穿上大衣……我还听见主人的声音‘谁把钢琴师灌醉了?是谁竟敢给他喝伏特加?’末了,我挨了一巴掌……真是奇事!哈!哈!……当时顾不得笑,可现在觉得可笑极了……可笑至极……一个身强力壮的大高个子!像个消防瞭望塔似的,没想到……却忽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哈!哈!哈!”
“有什么可笑的?”我问道,他的肩膀和脑袋都笑得直抖,“别佳,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这有什么可笑的?别佳!亲爱的!”
但别佳还在哈哈大笑,从他的笑声中我不难看出歇斯底里的发作,于是我一边骂着公寓里夜间不送热水,一边张罗着照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