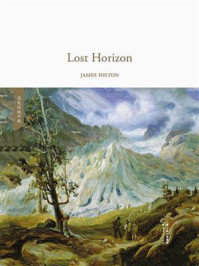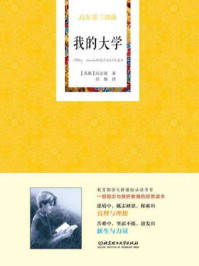“今天,那边,听不到昨天那样的嚎叫了,先生;你说呢?”
“我没有听到什么。”
“那你就可以肯定, 的确 没有什么声音了。这些人要么不叫,叫就是要让人听见。”
“人们大抵是这样,我想。”
“啊!不过这些人老是喊个不停。不大喊大叫心里便不高兴。”
“你是指马赛人吗?”
“我指的是法国人。他们老是没有停息的时候。至于马赛嘛,我们谁都知道马赛是个什么地方。马赛把前所未闻的最具有造反精神的曲子传到了世界上
 。它要是不朝着这个或那个目标allons,marchons
。它要是不朝着这个或那个目标allons,marchons
 ,就存在不下去——不胜利,毋宁死,毋宁进地狱,如此等等。”
,就存在不下去——不胜利,毋宁死,毋宁进地狱,如此等等。”
说话的人身上一直有一种异样的快活的情绪,他站在护墙前瞭望,对马赛极端地藐视。他摆出坚定的姿势,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不屑一顾地把口袋里的钱币抓得哗啦啦地响,还发出一阵短促的笑。
“Allons,marchons,一点不错。我看,要是能让别人也都allons,marchons,去干他们的合法的事情,而不是把他们在隔离检疫站里关着,那末你们就更加光彩了!”
“叫人够烦心的了,”另一个人说。“不过我们今天可以出去了。”
“今天出去!”第一个人重复了一句。“那几乎是罪上加罪,说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出去。出去!那么把我们关进来,又是什么道理?”
“我说也没有什么很充分的道理。不过,由于我们是从东方过来的,东方那个地方又老发瘟疫——”
“瘟疫!”另一个人又重复了一句。“我就是受够了这种苦。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就一天天地受这瘟疫的苦。我好像自己是一个神志清楚的人被关进了疯人院;怀疑我们得了瘟疫,那我可受不了。我一生当中都是好好儿的,到这儿时也是好好儿的;可是,要是怀疑我得了瘟疫,那等于是把瘟疫传给我。我已经给染上瘟疫了——我已经得了瘟疫了。”
“您过得很好,弥格尔斯先生,”另一个人笑着说。
“不。要是您了解事情的真相,就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了。这些日子我总是一夜夜地惊醒,总是对自己说, 现在 我已经得了瘟疫了, 现在 瘟疫已经恶化了, 现在 我要倒大霉了, 现在 这些家伙要大做文章,提醒大家小心了。唉,我宁愿让人用烤肉叉戳在身上,并且钉在甲虫标本卡上,也不愿意过这些天来在这里过的这种生活。”
“行了,弥格尔斯先生,这事儿就不要再去说它了,现在事情就要过去了,”一个活泼的女人声音这样劝道。
“过去了!”弥格尔斯先生重复道。他似乎(尽管没有什么恶意)处于一种特殊的心境,这种时候不管哪个人说的话,最后几个字便是对他的又一次伤害。“过去了!为什么事情过去了我便不可以再说话了!”
劝弥格尔斯先生不要再说的人是弥格尔斯太太;弥格尔斯太太与弥格尔斯先生一样,漂亮而健康,一张漂亮的英国人的脸庞,五十五年还多一些的日子里,这张脸一直是注意那些平平常常的事情,眉宇间流露出这些事情给她带来的欢乐的神情。
“好了!别管它,爸爸,别管它!”弥格尔斯太太说道。“看在上帝分上,你要心满意足了,有宝宝在。”
“有宝宝在?”弥格尔斯先生用受到伤害的语气重复道。然而,宝宝就站在他的身后,她在他肩膀上推了一下,于是,弥格尔斯先生顷刻之间便从心底里宽恕了马赛。
宝宝约摸二十岁。她是一个容貌美丽的姑娘,披着一头浓密的天然卷曲的棕色长发。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有一张坦诚的脸,一双妙不可言的眼睛;那眼睛如此大,如此温柔,如此明亮,长在她那善良的脑袋上是如此地完美。她长得十分丰润,精神饱满,有一对笑窝,受到父母的宠爱。宝宝身上有一种羞怯和柔顺的神情,这是天下最可爱的弱点,使她具有魅力;一个如此可爱、美丽的姑娘是大可不必再具备的,不过,有了这种魅力,她的美貌便登峰造极了。
“唔,我问你,”弥格尔斯先生表现出非常和蔼的信任问道,他退后一步,把女儿向前推上一步,以此来说明他问的话;“你知道,我只是就我们个人之间请教你一句,把宝宝也关到隔离检疫站里来,这种可恶的荒唐事情你 可曾 听说过没有?”
“这么一来就连隔离检疫站也有意思了。”
“嗨!”弥格尔斯先生道,“的确,那倒是真的。我非常感谢你,说了这么一句话。走,宝宝,我的宝贝,你还是跟着妈妈,准备上船吧。卫生官员,还有一群戴三角帽的骗子,他们总算就要出来,把我们放出去了。我们这些囚犯又可以聚在一起,吃一顿多少有一点基督教风味的早餐,然后张开翅膀,大家各奔前程。泰蒂柯伦,你要好好跟着小姐。”
他是在吩咐一个有光泽的黑发、乌溜溜的眼睛,穿着整洁的漂亮姑娘。那姑娘略微屈膝行了礼,答应了一声,便跟在弥格尔斯太太与宝宝的后面走了。她们三个人一齐穿过在日光下烤晒的光秃秃的露台,走进耀眼的白色拱廊消失了。弥格尔斯先生的同伴,一个心情抑郁、皮肤黝黑的四十岁的男人,在她们三人消失之后,依然站在那里凝视着拱廊;弥格尔斯先生在那人的胳臂上拍了一下。
“对不起,”他吃了一惊,说道。
“不要紧,”弥格尔斯先生答道。
他们在护墙的阴凉儿里又来回默默地走了一阵,在这隔离检疫站简陋房屋坐落的高地上,尽量享受早晨七点钟习习吹拂的海风带给人的一丝儿凉意。弥格尔斯先生的同伴又与他交谈起来。
“不知能否请问您一声,”他说道,“名字叫什么,那个——”
“泰蒂柯伦吗?”弥格尔斯先生插嘴道。“我一点儿也不清楚。”
“我觉得,”另一个说道,“觉得——”
“泰蒂柯伦吗?”弥格尔斯先生又提示道。
“谢谢——我想泰蒂柯伦是个名字,我有好多次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奇怪。”
“噢,事情是这样的,”弥格尔斯先生道,“弥格尔斯太太和我自己,你知道,都是讲究实际的人嘛。”
“这一点,我们一起在这些石子上来回散步时进行的愉快而有意思的谈话当中,您已经屡次提到过了,”另一个人说道,他那张黑黝黝的、表情严肃的脸上透出了一丝微笑。
“我们是讲究实际的人。所以,五六年前的一天,我们带着宝宝去做礼拜,在那育婴——你听说过伦敦的育婴堂没有?是同巴黎的孤儿院差不多的,听说过没有?”
“我到过那里。”
“噢!有一天,我们带宝宝去做礼拜,到那里听音乐——因为,我们是讲求实际的人,带她去见识见识我们觉得能让她高兴的所有东西,那是我们生活中应该关心的事——妈妈(我通常就这么叫弥格尔斯太太的)就开始呜呜地哭起来,我只好带她出来。‘你怎么啦,妈妈?’等我们让她稍稍平静了一点后,我问她;‘亲爱的,你把宝宝可吓坏了。’‘就是,爸爸,我心里明白,’妈妈说,‘可是,我看就因为我这么喜欢她,我想着想着就伤心起来了。’‘是什么事情让你想着想着伤起心来,妈妈?’‘啊,天哪,天哪!’妈妈说着又哭起来了,‘我见到所有那些孩子一排排地坐在那里,呼天叫地的,喊他们谁也没有见过一面的人间的父亲,喊天上我们大家的父亲,这时我心里就想,有没有哪个可怜的母亲到这里来过,在那些小脸蛋当中寻找,不知道哪一个是她带到这个悲惨世界里来的可怜孩子,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得到过她的爱,从来没有得到过她的吻,从来没有听见过她说话的声音,就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便是妈妈的讲究实际的性格,我对她这么说了。我说:‘妈妈,那一点便是我说的你讲究实际的性格,亲爱的。’”
另一个人,这时也受了感染,表示赞同。
“所以第二天我就说:哎,妈妈,你听我说,我有一个想法,我想你是会同意的。我们就在那些孩子当中挑一个出来,做宝宝的小丫头。我们是讲究实际的人,所以,要是我们发现她的性格有一点缺陷的话,或者她的习惯同我们的习惯有一点儿差距,我们会知道,哪些事情是我们该考虑的。我们会知道,同造就我们自己的所有那些影响和经历相比,那是要打多么大的折扣——她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自己的家,没有水晶鞋
 ,没有仙子恩人
,没有仙子恩人
 。就这样,我们领来了泰蒂柯伦。”
。就这样,我们领来了泰蒂柯伦。”
“那么这名字——”
“上帝!”弥格尔斯先生说道,“说着说着,我把这名字忘记了。那名字嘛,她在育婴堂里的时候名字叫哈莲特·比得尔——当然,那是个随便起的名字。喏,我们把哈莲特改成了哈蒂,后来又改成了泰蒂,因为,我们是讲究实际的人,我们心里觉得,就连一个好玩的名字,对她来说也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也会产生一种温暖、亲切的效果的,你说是不是这样?至于说比得尔这个姓嘛,我就用不着说它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了。假如有什么在任何条件下都无法容忍的东西,假如有什么被称为某种自命不凡的小官吏的傲慢和荒唐的东西,假如有什么穿着外套、背心,拿着大棒,用愚蠢的举动来体现我们英国人的坚持精神的东西,在人人都发觉之后,原来那便是一个‘比得尔’
 。你近来碰见过一个‘比得尔’没有?”
。你近来碰见过一个‘比得尔’没有?”
“作为一个在中国呆了二十几年的英国人,最近我没有碰见过。”
“那么,”弥格尔斯先生说道,一面兴奋异常地用食指戳着同伴的胸口,“假如你有法子躲避,那你千万别碰上一个‘比得尔’。每当星期天我在一所慈善学校门前沿街走的时候,只要看见一个神气活现的‘比得尔’,我必定转身就跑,否则我一定会揍他一顿。既然‘比得尔’这个名字已不值得一提,而收容这些可怜的弃儿的那个机构的创办人,又是一个天国享福的人,名叫柯伦
 ,我们便把那个名字给了宝宝的小丫头了。有一段时间我们管她叫泰蒂,有一段时间我们又管她叫柯伦,后来我们习惯将她两个名字合在一块儿叫,现在我们就一直叫她泰蒂柯伦了。”
,我们便把那个名字给了宝宝的小丫头了。有一段时间我们管她叫泰蒂,有一段时间我们又管她叫柯伦,后来我们习惯将她两个名字合在一块儿叫,现在我们就一直叫她泰蒂柯伦了。”
他们又默默地来回走了一圈,在护墙前站着,注视了一会儿底下的大海,然后,两人又散起步来,这时候,另一个人说道:“你们的女儿,是你们的独生女,我知道,弥格尔斯先生。我能否问您一下——这并非出于唐突的好奇,而是因为这些日子同您在一起,我觉得非常愉快,也许在这个迷宫似的世界上,我再也不可能与您静静地交谈了,而且我希望对您以及您的一家能留下一个确切的回忆——我能否问您一下,从您的尊贵的夫人那里我并没有看出来,你们是否还有其他子女?”
“不对,不对,”弥格尔斯先生说道。“确切地说不是其他子女,是还有一个孩子罢了。”
“恐怕我无意中触及了一个敏感的问题。”
“没关系,”弥格尔斯先生说道。“即便我对于这个问题心情很沉重,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伤心。提起这件事会叫我一时间说不出话,可是并不会使我不高兴。宝宝曾经有过一个孪生姐妹,当她长到踮起脚来抓住桌子,我们正好能看见她的眼睛——同宝宝的眼睛一模一样——的时候,她就离开人世间了。”
“啊!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是的,同时,由于我们是讲究实际的人,由此而造成的一个结果,便渐渐地在我和弥格尔斯太太的心目中产生了,你也许会——也许你不会——理解的。宝宝同她的孪生姐妹长得如此相像,完完全全是一个人,在我的脑海中,从那以后,我们怎么也不能把姐妹俩分开。要劝说我们相信那个死去的孩子是个抱在怀里的婴孩,那是白费力气的。留在我们身边、永远与我们在一起的孩子的模样变了,我们脑海里那个孩子的模样也跟着变了。宝宝长大了,那个孩子也长大了;宝宝变得越发聪明,越发像个大姑娘,她的姐妹也变得越发聪明,越发像个大姑娘,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要是有人告诉我说,假如我明天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不可能得到上帝的仁慈,与我那个同宝宝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儿相会,那就跟劝我相信宝宝本人并非我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一样,都是很难让我相信的。”
“我理解您,”另一个轻声道。
“至于她嘛,”她的父亲接着说道,“那件神秘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同样关心,但是它又不可能那样经常明显地呈现在一个孩子的面前。她的孪生小姐妹和玩耍的伴儿突然失去,以及她对那件神秘的事情的最初联想,必然对她的性格有一些影响的。其次,我和她妈妈结婚的时候年纪都不小了,宝宝又经常同我们在一起,过着一种成年人的生活,虽然我们努力让我们自己适应她的爱好,每当她稍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人们不止一次劝告我们,为了她起见,应该尽量经常地换换气候,换换空气——尤其是在她现在这个年龄——要让她快快活活的。因此,由于我现在没有必要在银行里干坐着(尽管我在一生当中穷得可以,这话你可以相信,否则我早就与弥格尔斯太太结婚了),我们就到世界各个地方到处跑去了。就这样,你看到我们睁大眼睛,观赏尼罗河,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大沙漠,以及其他许多风光;而泰蒂柯伦,她终会在将来成为一个胜过科克船长
 的大旅行家的。”
的大旅行家的。”
“我感谢您,”另一个说道,“衷心感谢您说了这一番心里话。”
“不必客气,”弥格尔斯先生答道,“那是肯定的,你不必客气。现在嘛,克莱南先生,也许我可以请问你,你有没有作出决定,下一站要到哪里去呢?”
“说真的,还没有定呢。我是这么一个四海飘零的流浪汉,我是随波逐流,漂到哪里便到那里。”
“我觉得奇怪——要是你恕我直言——你怎么不直接回伦敦去,”弥格尔斯先生用一个真心诚意为人出主意的人的那种口吻说道。
“也许我要去的。”
“当然!可是我是说要坚决。”
“坚决的意志倒没有。那就是说,”他脸有一点红,“现在就可以化为行动的意志几乎还没有。全靠强迫训练出来的;折断了,不是压弯了;戴上重重的镣铐,拴在一个目标上,从来没有同我商量过,也从来不是我的目标;我还没有成年就被送到了世界的另一端,被放逐到那里,直到一年前我父亲在那里去世为止;没完没了地做着我一直讨厌的工作。如今,人已经到中年了,我还有什么可期望的?意志,目的,希望?我还来不及说出这些字眼来,所有那些灯光都已熄灭了。”
“把它们再燃起来!”弥格尔斯先生道。
“啊!说是容易的。弥格尔斯先生,我是严厉的父亲和严厉的母亲的儿子。我是个独生子,父母亲对于任何事情都要称一称,量一量,然后定出价格来的;对他们来说凡是不能称,不能量,也定不出价格来的东西,那就不能有。正如那句格言所说,他们是刻板的人,是严厉的宗教信仰的宣扬者,他们的宗教信仰本身就意味着令人沮丧地牺牲与自己不合的爱好与同情,这种牺牲是同换取他们的财产安全的交易相关联的。冷酷的面孔,无情的清规戒律,今世是苦行,来世是恐怖——无论哪里都没有什么温柔、优美的东西,每到一处我的沮丧的心都是一片空虚——这便是我的童年,假如我还可以滥用这个字眼来描述这样一种人生的开端的话。”
“果真是这样?”弥格尔斯先生说道,展现在他脑海中的那幅图画使他感到非常不舒服。“那真是痛苦的开端。不过,鼓起劲来!你现在必须学习,像一个讲究实际的人那样,通过学习开拓眼界,从中受益。”
“假如通常认为是讲究实际的那些人,是照您所说的那种讲究实际——”
“怎么,他们是这样的!”弥格尔斯先生说道。
“真是这样吗?”
“这个,我看是的,”弥格尔斯先生答道,心里琢磨起来。“呃?一个人也只能是讲究实际的,我和弥格尔斯太太也是这样。”
“那么,我今后陌生的道路将会比我所预料的要容易了,也更加充满希望了,”克莱南说道。他露出严肃的微笑,晃了一下脑袋。“我的事就不谈了。船来了!”
船上坐满了三角帽,见了他们,弥格尔斯先生就对他们整个国家的人都不满;那些戴三角帽的人上了岸,从台阶走上来。全部被扣押的旅客都集合在一起。于是,三角帽那方面先是取出了一叠叠的文件,开始点名,接下来便是繁琐的手续:签字、按印、盖图章、用墨水书写、用砂子擦干,结果弄得一团糟,到处是砂子,模糊潦草,难以辨认。终于,一切手续都按照规定办完了,旅客们都获得了自由,动身前往他们各自要去的地方,一切听便。
在重新获得了自由的新的喜悦中,他们丝毫也没有在乎那刺眼的强光,只管自己乘上轻快的小船,掠过码头,重新集合在一家大旅馆里。旅馆紧闭的格子窗挡住了阳光,不铺地毯的砖石地板,高高的天花板,响着回声的走廊,把酷热大大地缓解了。旅馆一间大房间里,摆了一张大桌子,桌子上立刻就摆满了美味佳肴;隔离检疫站的宿舍其实已经是空无一人,成了餐桌上回忆的往事,而面前是珍馐美味,南方的水果,冰凉的酒,热那亚采来的鲜花,高山顶上弄来的雪,仿佛镜子里闪烁着彩虹般的五颜六色。
“不过,对那些千篇一律的房屋,我现在倒也没有什么恶意了,”弥格尔斯先生说道。“一旦把一个地方抛在身后,你就会开始宽恕它的;我敢说,一个囚犯释放之后,也会对他蹲过的监狱宽厚心软起来的。”
聚在一起的大约有三十个人,都在交谈;不过,当然是三五成群地谈着。弥格尔斯爸爸与弥格尔斯妈妈,中间是他们的女儿,三个人坐在桌子一端的最旁边。坐在他们对面的是克莱南先生;一个高个子法国人,乌黑的头发和络腮胡子,相貌虽不能说是假作斯文的凶暴,也是黝黑而可怕的,然而,他却是表现得最温和的人;还有一个是漂亮的年轻英国女人,她总是单独行动,一张傲慢而善于观察的脸,可能是她有意躲避别人,也可能是别人对她敬而远之——也许除了她自己,谁也说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余的人便是平常遇见的那些了。有出国办公事的,有旅游观光的;从印度回国度假的军官;在希腊和土耳其经商的商人;一个办事员模样的英国丈夫,穿一件服帖的紧身衣,带着年轻的妻子作蜜月旅行;一个庄重的英国妈妈和一个庄重的英国爸爸,出身高贵,带着三个长大成人的女儿,她们都在记日记账,弄得她们的旅伴们迷惑不解;一个聋子英国老母亲,很吃得起旅途的苦,带着一个完完全全已成人的女儿,这个女儿周游世界画速写,等待着最终定下心来结婚过日子。
沉默寡言的英国女人接过弥格尔斯先生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开了口。
“你的意思是说,囚犯宽恕他蹲的监狱吗?”她问道。她一字一板,语气强调。
“那是我的推测,韦德小姐。我并没有说,我对一个囚犯心里是什么滋味也一清二楚。我过去从未进过监狱。”
“小姐是怀疑,”那个法国人用自己的语言说道,“不会那么轻易宽恕,是吗?”
“是的。”
宝宝只好把这段话翻译给弥格尔斯先生听,因为他从来没有偶然地学到过一点他到过的哪一个国家的哪一种语言。“噢!”他说道。“我的上帝啊!可是,那真太遗憾了,你们说是不是?”
“是我不轻易相信人太遗憾吗?”韦德小姐问道。
“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话应该这么说:你认为轻易宽恕不容易,那太遗憾了。”
“我的经验,”她平心静气地接着说道,“几年来一直在许多方面纠正我的信念。我听说,这便是我们的自然而然的进步。”
“唔,唔!可是,我希望,抱有敌意总不是自然而然的吧?”弥格尔斯先生爽朗地说道。
“假如我被囚禁在哪个地方,受煎熬、受折磨,那我会始终憎恨那个地方,要放火烧了它,或把它夷为平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做法。”
“坚强,对吗,先生?”弥格尔斯先生问那个法国人道。这又是他的一个习惯,用纯正的英语与各个不同国家的人说话,他坚信,他们一定会或多或少听懂他的意思的。“我们这位女性朋友相当地强有力,我看,您会同意我这个说法的吧?”
那法国人彬彬有礼地答道:“Plait-il?”
 听到这句话,弥格尔斯先生洋洋得意地说道:“您说得对。这是我的意见。”
听到这句话,弥格尔斯先生洋洋得意地说道:“您说得对。这是我的意见。”
由于早餐不多时便接近尾声,弥格尔斯向在座的人发表了演说。演说很短,考虑到这毕竟也是一个演说,因此,也是很明智的,而且是由衷之言。他的演说大意不过是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们带到一起来了,大家在一起保持了很好的谅解关系,现在大家都要分手了,不大有可能再会聚到一起来,因此,除了一桌子的人同时举起一杯冰凉的香槟,相互祝愿旅途愉快、一路顺风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方式吗?于是,大家碰了杯,一桌子的人一一握手之后,这一批人便永远分散了。
整个这段时间,孤独的年轻小姐一直没有再说什么话。她随着其余的人站起身来,悄悄地躲到了这个大房间的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她在那角落窗口边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来,似乎是在注视水的反照,因为水的反照在窗格上发出银光似的闪烁。她坐在沙发上,转过脸去,目光避开了整个房间,仿佛她对于自己傲慢的选择也感到孤独了。然而,此刻与过去一样,也很难肯定地说,是她回避其余的人,还是其余的人回避了她。
她此刻坐着的那个地方的阴影,仿佛一片阴郁的面纱,落在她的额头上,与她那种美貌非常地协调。她那张脸,那般安详,含有嘲弄,衬托它的是一对弯弯的黑眉毛和一头黑发,你一看见这张脸就会嘀咕,这张脸倘若发生什么变化,那该是什么样的表情。这张脸会变得柔顺或宽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它会深化为愤怒或无比的蔑视;倘若它会发生什么变化,那必定朝着那个方面发展的,这就是大多数的观察者都获得的奇特的印象。这张脸的打扮、修饰也并不讲究表现。尽管这不是一张坦诚的脸,但也没有什么做作的地方。我沉默寡言,无求于人;你们的看法我并不在乎;对你们我毫无兴趣,你们怎么样我不管,看见你们、听到你们,我都装作没事儿似的——这个意思可以从这张脸上看得分明。这个意思还表现在她那傲慢的眼睛上、微翘的鼻子上、漂亮却是紧闭甚至是冷酷的嘴上。倘若这三个表情的渠道遮去两个,第三个渠道仍然能表现这样的意思。倘若将三个渠道全部蒙住,只要她的头一转,便会显示出不可征服的本性来。
宝宝朝她走过去(她是宝宝一家和克莱南先生谈论的主题;房间里现在除她以外,只剩他们了),在她身旁站定了。
“你是不是”——她转过眼来,宝宝踌躇了——“在等什么人到这里来接你,韦德小姐?”
“我?不是。”
“爸爸要派人到自取信件邮局去。是不是可以让他叫那人在邮局里问一下,有没有你的信?”
“我谢谢他,不过,我知道不会有我的信。”
“我们担心,”宝宝在她身边坐下来,羞怯地、有几分柔声地说道,“我们都走了以后,你会觉得十分孤单的。”
“是啊!”
“不是说,”宝宝表示歉意地说道,她的目光使宝宝感到窘迫,“当然,不是说我们能给你做什么伴,不是说我们给你做过什么伴儿,也不是说我们觉得你希望我们来与你做伴。”
“我并没有要让人家领会我有过这种愿望。”
“是的。当然。不过——总之,”宝宝说道,同时羞怯地触了一下沙发上她那只一动不动地搁在她们中间的手,“你不愿让爸爸为你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或者为你效力吗?他会很高兴帮助的。”
“非常乐意,”弥格尔斯先生说道,这时他正与他的夫人和克莱南走过来。“只要不是说外国话的事,我都乐意效劳,那是一定的。”
“我感谢你,”她答道,“不过我已经安排妥当了,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
“ 是吗 ?”弥格尔斯先生以困惑的神情打量着她,心里说道。“唔!这句话里面也有个性。”
“同青年女子的交往我并不很习惯,而且我恐怕不会像别人那样赞赏这样的交往。祝你旅途愉快。再见!”
似乎她原是不会伸出手来的,然而,弥格尔斯先生把他的手一直伸到了她的面前,使她无法躲避。她将手放到了他的手中,就如同刚才放在沙发上一样。
“再见!”弥格尔斯先生说道。“这是最后一次说再见了,因为我和弥格尔斯妈妈在这里刚同克莱南先生说过再见,他只等着同宝宝说再见呢。再见!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将会见到前来见 我们 的人,他们来自许多陌生的地方,通过许多陌生的道路,”这是她镇定自若的回答;“应该由我们来对他们完成的事,应该由他们来对我们完成的事,都将要去完成。”
从这些话的说法上,宝宝听出了一种不顺耳的味道。那意思是说,将要完成的事必定是不吉祥的,她听了这话之后低声对弥格尔斯先生说:“噢,爸爸!”并孩子似的,带着她那娇生惯养的态度,向他退缩,朝他靠得更近了。说那句话的人对于这一举动,并非视而不见。
“你那漂亮的女儿,”她说道,“想到这种事情就感到吃惊。可是,”她两眼正视着宝宝,“你可以肯定,一些男女已经上了路,他们都有与 你 有关的事要干,他们也一定要干的。他们肯定是要去干的。他们或许要从海上走几百英里,几千英里的路前来;他们或许现在便近在眼前;他们或许——不管你了解什么情况,也不管你能作什么努力来阻止——正是从这座城市的最污秽的垃圾堆中出发的。”
说完最冷淡的告别话,带着她美丽容貌上流露出的某种疲惫的表情(这疲惫的表情,使她那尽管尚未达到全盛时期的美貌,蒙上了一种倦怠的神色),她离开了房间。
再说在那旅馆里,要从那间宽敞的房间所在的那一头到她个人留宿的卧室,她必须经过许多楼梯和通道。当她即将走完这一段路,正沿着她的房间所在的那条走廊走去的时候,她听见一阵怒气冲冲的嘟哝声和哭泣声。一间卧室的门开着,里面她看见了刚刚分手的那个姑娘的侍女,即起了怪名字的那个女仆。
她站定了,望着这位女仆。一个满腹怨气、性情暴躁的姑娘!她那浓密的黑发,披了一脸,她脸涨得通红,十分激动,她一面哭泣,发脾气,一面用她那只毫不留情的手拼命抓着嘴唇。
“自私的家伙!”姑娘在说着,不时地哭泣和抽搐。“我是死是活,一点都不放在心上!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没吃,没喝,浑身没力气,叫我饿死,安的什么心!畜生!魔鬼!没心肝的!”
“可怜的姑娘,你怎么啦?”
她蓦地抬起头来,眼圈通红,正准备去拧自己脖子的手停在空中,脖子是刚变了模样,有一大块一大块的红肿。“什么怎么啦,跟你有什么关系。谁也管不着。”
“噢,哪能呢;看你这个样,怪可怜的。”
“你可怜什么,”姑娘说道。“你开心了。你知道你开心了。我呆在那边隔离检疫站的时候,像这个样子我只不过有两回。那两回你都碰上了。我真怕你。”
“怕我?”
“是的。瞧你那模样,说来就来,就跟我的怒气一样,就跟我的怨恨一样,跟我的——什么都一样——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可是他们虐待人,他们虐待人,他们虐待人!”刚才吃了一惊之后,哭泣,眼泪,拧脖子的手,都一齐停住了,现在又重新活动起来。
不速之客站在那里,眼睛看着她,露出了奇怪、逼人的笑。真有意思,看着这个姑娘大哭大闹,舞动手脚,仿佛古时候的群魔在纠缠她。

显微镜下
“我比她小二三岁,可是倒是我在服侍她,好像我比她大,她倒老那么让人宠着,还叫她宝宝!听了这名字我就恶心。我恨她。他们把她当个傻瓜,把她宠坏了。她心目中只有她自己,她一点也不替我想想,好像我是一根木桩,一块石头!”姑娘就这样说了一连串的话。
“你得忍着点儿。”
“我 绝不 忍着!”
“要是他们老想着他们自己,不大关心或者一点也不关心你,你也不该放在心上。”
“我 一定 记在心上!”
“别说!你得多注意点儿。你忘了你自己下人的地位了。”
“我不管那么多。我要逃出去。我要闹一闹。我不会忍着;我受不了;要是还忍着,我会憋死的!”
这个旁观者站着,一手抚着自己的胸口,眼睛注视着那姑娘,如同一个因身体某个器官得了病而痛苦的人,好奇地注视类似病例的解剖和展览一样。
姑娘大发雷霆,使出她青春年少和生气勃勃时的全部力气,闹呀闹的,直到渐渐地她那暴躁的叫喊越来越微弱,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呻吟,仿佛她浑身疼痛。又那样渐渐地,她坐到一把椅子上,先是跪下来,接着倒在床边的地板上,身上裹着抓过来的床罩,一半是要遮盖那受辱的头和湿漉漉的头发,一半似乎是抱着它,不过并不是她缺少什么东西来捂住她那悔恨的胸口。
“你走开,你走开!我要是发起脾气来,我就会疯的。我知道,只要拼命克制一下,我就可以压下去的。有时候我是拼命地克制,可有时候我没有克制,不愿意克制。我说过什么了!我说那些话的时候,我知道那都是撒谎。他们觉得是够关心我的,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对我是够好的了。我非常热爱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有谁能像他们那样总是待我那么好的。走吧,你走开,我害怕你。我觉得我火冒上来的时候,我连自己也害怕,我也很害怕你。你走开,让我祈祷,让我哭,哭了就好了!”
白天过去了;刺眼的强光又消逝了。炎热的夜在马赛城降临;早晨那一队人,各自分散,穿过这城,走上他们各自预定的路。日夜兼程,冒着烈日,顶着星星,爬过尘土飞扬的山,越过令人困乏的平原,穿过陆地,渡过大海,如此奇怪地来来往往,走到一起去,彼此之间结下纷繁的关系,我们所有忙碌的旅行者们,就是这样走过人生的旅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