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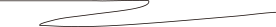
滇言之蟋蟀唤“蛐蛐儿”,此音似“七圈儿”,其实这虫虽在缸里转来转去,却不止于七圈八圈。戏谑更作“嘚嘞”,仿其鸣也!“嘚嘞”斗战,赢者至无对手,座次已然分明,便可“封缸”。因之中小学班上男生明争暗斗,终要“封缸”。最凶狠的,便“封头缸”。此后,班级中一套班子是“班长、学习委员、劳动委员、体育委员……”一群大员,另有“黑社会”的“头缸、二缸、三缸……”一群虫豸。当然,老师懂整合,叫“头缸”当个体育委员之类,也是有的。滇言有关斗蟋蟀的专词有若干,说法有若干。蟋蟀不欲斗则喂辣椒,想是因看到四川哥们多食辣椒而后脾气火暴得到启发;再不斗,以头发掭子撩拨,想是因看到绕眼虫久在鼻前人会大怒而得到启发;若还不斗,则以马尾头发吊颈而甩,这是否警示将行军令?这启发就不清楚了。

滇言之“逢”,可不单纯说的是“相逢”,只说“逢”字时更是如此。如:我不相信逢不下他来!一听便知是挑战,惹事来了。“逢”也就从喜相逢、逢迎变成“不信来战”。而“逢得下、逢不下”也就是说着输赢,甚至生死了。
滇言有将游泳写作“洑水”者(别处也有方言如此写),但应为“凫水”才对。“洑”是水名,也作水回旋讲,而“凫”才是漂在水上。但言“洑上水”就完全别是一义了,那是说一个人逢迎献媚,拍马屁求好处的意思。想想也是,人生艰难,不进则退,抢抢上水也是常情!
滇言之“干”,非但有水分缺少之意,更有蔑视贬义。如“干皮料燥”的主要含义不是“干”,而是“没意思、没搞头、没油水”之类。“干瘪瘪”则不止没水色,更是没精神,而“干叫湿叫”就是好也叫坏也叫的意思了。如果无理吵三分,是“干挣”;吵得厉害,是“干挣命”。
遇有令人厌恶的(重复)动作,以“干……干……”的形式表达:我不理他,他还在干讲干讲的!若是行为无聊或无用,亦以此表述。因此,无用无益也用一个“干”字形容,如干艐(ke,船搁浅,滇音kuò)着儿。
滇言口渴叫“赶水”,但是“赶饭”不是肚饥,因为可以说“赶嘴”。汉语可“赶”之事物甚多,“赶水、赶嘴”算滇中特产。“赶”字本义有“追达、从速”等,滇言之用法也不出此,但“赶”的内容却有些独特了。
滇言触到凸起的东西觉得不舒服或受到损伤叫作“杠”(ɡàn),但除“杠脚”“杠肋巴”外,还可以“杠脖子”“杠耳朵”“杠眼睛”。“杠脖子”就是梗脖子,有气难舒,令人气愤;“杠耳朵”即言语刺耳难听;“杠眼睛”即行为举止使人感到不舒服,看不下去。
滇言称押解、缴收为“械”,是典型的名词作动作动词用,以工具指代行为。因为“械”,是将人身体加以桎梏,也就是制服了对方的意思。小时玩“杀战”,有战胜者“械”着俘虏的情节,十分得意。而叫对方缴枪或拿出输掉的东西,也都叫“械”,例如:叫他械三个烟壳出来!一个“械”字描画了身不自由被迫而行的窘相。
滇言不乏恶谑,被捆绑称为“穿索子领褂”,“索子”是滇言绳子,“领褂”是背心,“穿索子领褂”就是五花大绑。或说“盖草索被”,更加不堪,因为这是被捆得像麻花一般了!这两者都是被人“械”着,有人指滇地多反背双手走路人为“充军”人或其后裔,意谓其是长时间“穿索子领褂”被“械”来滇黔之地之人,此是笑谈,更是毁我彩云之南良民也!
滇言勾结叫作“搞打”,勾搭也叫“搞打”,成功了叫“搞拢”,失败则是“搞拐”。这“搞”字虽是后起,但在汉语中却又十分得势,滇言之中也众多用法,中国人言语中可“搞”之事物众多,但滇人口中之“搞”大概基本无甚好事!就不一一说明了。
滇言之刺耳、啰嗦叫“嗝尖(ɡé jiān),也说“聒尖”。《水浒传》中常用“聒噪”,后来“聒”字使用日稀,然滇地之“嗝尖”“聒尖”却时时嘹亮也!另山西人也还说此字。
声音尖利刺耳是“聒尖”,人语絮叨不已也是“聒尖”。“尖”之古语,意谓巧言又轻薄,比“聒噪”又多一层贬意。
滇言之囫囵、完整称为“亘”(gěn),“亘”之意谓延绵不断者也,因之引为“整”。“亘鸡蛋”,就是原颗煮鸡蛋;“亘票”就是未破零之大额钞票;而“亘数”,即是整数或趸数。
滇言之称“哥”,有一种用法必得一说。汉语“哥”之本义原是兄弟之长,但后则往往指的并非年纪,如梁山土匪之“大哥”便是“头子”同义词。今东北等地为典型的呼“哥”,便是“I服了YOU”的意思。滇言更有意思,不光以“哥”表达兄弟淘的亲切,更可以自称:我哥(家)也不是吃素的,当时就给他个下马威!“我哥”是自称,不是说“我的哥”;也可以说“你哥”或“你哥家”,就是你,不是你大哥。
滇言“锅巴”读为“ɡū bā”,应是吴音,亦是古读。但表字则似不应写作“箍巴”之类,这只是代字,并非正确表字。明清以远,滇地汉族聚居区多为少数民族包围的移民“飞地”,移民来自各方,语音则多保留晋吴川鄂等地语也。本书争取正确表字,因此仍写“锅巴”而说明读音。
方言之保存古音多,如入声字滇言保存甚多,以读古诗,顿觉顺溜。
锅巴用于说事,则有一条揭人目的:“不想吃锅巴么在锅边转哪样?”用于贬损,则呼“锅(ɡū)巴脸”,表面是说肮脏糙皴之谓,暗里却是指人脸厚不知耻罢!
脸若脏皴,唤“锅(ɡū)巴脸”,生动诙谐。忽思锅巴,可充点心,可做大菜,也是小时一大思物!
滇言说缠杂不清叫“裹绞”,应源自丝麻紊乱之形象。“二五裹绞”更是常用口语,“一五一十”是顺理实说,二五正是一十却成了“裹绞”。显见有十(实)而不言非扯“二五”,就真是在“裹绞”。又有人说“二五二五”乃拟猪之哼哼,以言“裹绞”之人愚蠢,似为穿凿。
滇言之称人、物的体量个子曰“个(guò)把”,例如,个把大力气大。但当读“个”(gè)时,就成了数量词,意思是少量,例如,个(gè)把两个馒头吃不饱!“个”字两读,普通话只有调变。

滇言“承”(shén),就是支撑。“有什么后果,我来承(shén)!”就是一句够担当的话,也就是“有什么责任我们必须承(担)起来的意思”。另一种是反过来用,作为(被)抓住的,警察抓了,叫“挨公安局承(shén)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