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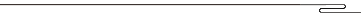
艺术是人类殷切企盼健全的梦,它以不断战胜狭隘性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点。艺术的灵魂,首先体现为一种充分释放、自由创造、积极赋型的人格素质。这种素质或多或少在每个人心底潜藏,因而每个正常人都能成为各种艺术深浅不同的接受者。
我国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刚刚展出时,许多观众徘徊不去,他们被一种赤裸的真实所惊动,而且,或多或少地感到了自己的浅薄与忘本。那么,看这幅画应该采取一个特殊的角度:半是画幅,半是观众。
在整个艺术创造过程中,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便是疏通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以开放,而不是以封闭的方式,完成创造。
接受美学标志着很多艺术家对于输出道口的重视,以致愿意反过来把它作为整体创造活动的基准。接受美学认为全部创造活动都应把接受者的接受状态包括在内。接受,参与了创造,延续了创造,完成了创造。
艺术的狭义本体只是成了一种诱发剂,一种推动力。这样,它的地位降低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要发挥那么大的组织功能和调动功能,它的职能提高了。它的自身形态也要随着职能的变化而变化,出现了各种召唤接受者参与其间的特殊结构。
我们可以写出长长一串艺术大师的名单,是他们,使人类适应了可以构成层累的各种美的气度、美的神貌、美的心绪、美的情境。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创造了一部使人类渐渐适应由低到高的文明的历史,即使是我们,身心之上也深深地留着他们塑捏我们的指印。我们短暂的一生,可看成是人类历史的缩影:从幼到长,一步步适应了各种层次的艺术作品,艺术的宝库在我们眼前横亘成一个有机系列,随着我们年岁增长,不断帮助我们创造适应,又突破适应。终于,我们成了一个比较健全的人。这也是人类的总体情景。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然而,当屈原有心绪吟咏《离骚》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获得了艺术化的自由心境。他的吟咏,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适应了华美的楚辞,也适应了审美的忧郁。他在一定程度上创建了中国人的某些心理素质。这一点,远远超过他现实的政治功绩。
就大范畴论,旧时代的中国文人,是逐次适应了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之后才总体缔造成的;就小范畴论,各种不同的文人又有自己具体的重点适应对象,例如在某些现代女作家身上,我们仍能依稀发现她们对李清照的远年适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创造,实在是在创造人。
我历来非常注意文学作品中隐藏的那股气,似乎不可捉摸,却又扑面而来。文章是生命的直接外化,这股生命气息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时时刻刻在诱导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气息。就像我们见一个人,直接感受的并不是他的档案资料和他的学术观点,而是从眉眼姿态中洋溢出来的那种气场。
艺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素质,是人们在误会与烦躁中进行美好的沟通的一种可能,是人类为使自身免于陷入浅薄功利而发出的一次次提醒。在远古,艺术使我们的祖先在难以想象的苦难中进入游戏,在游戏中融入群体、融入造型、融入宗教;在现代,艺术使我们从熙攘纷扰中超拔出来,领略宇宙,开掘生命,回归本真。艺术是贯通人类始终的缆索,是维系人类不坠的缰绳。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欧洲很多地方还是一片废墟的时候,还没有修复的音乐厅开始演出了。大量衣衫不整、家破人亡的幸存者聚集在一起,让音乐把自己拔离灾难。他们听的是贝多芬的音乐,他们没想到贝多芬其实和希特勒是来自同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艺术让他们恢复了心理的健康。从这些废墟音乐会,人们已可看到欧洲的今天。
到欧洲,主要是看他们城市的建筑。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有高水准的专业人员投入到公共空间的审美设计和审定中,其中就有米开朗琪罗这样的杰出大师,做了各种各样的公共雕塑和设计。当时是由贵族聘请他们的,其他人不一定懂得他们,但会模仿贵族,一模仿贵族就等于模仿了大艺术家所设计的房屋的样子。所以现在去看他们运用的色彩,他们的建筑形体,他们街道上各种各样的装潢,都符合规格,原因就在这儿。这种建筑本身变成了一个大学校,这个学校促进了一代又一代人审美意识的提高。
艺术欣赏中的思考,不是学术思维论文,不是智力游戏,不是强制领会,也没有预定答案。其结果,是意会,是神交,是顿悟,是心有所感而不必道之的那种境界。
最有意义的旅游,不是寻找文化,而是冶炼生命。我们要明白,人类的所作所为,比之于茫茫自然界,是小而又小的;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史,比之于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现,是短而又短的;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能力,是弱而又弱的。因此,我们理应更谦虚、更收敛一点。在群峰插天、洪涛卷地的伟大景象前,我们如果不知惊惧、不知沉默,只是一味叽叽喳喳地谈文化,实在有点要不得。如果这算是什么“大散文”,那宁肯不要。
旅途中的文化感受,不必如此拥挤、如此密集、如此迫不及待地表达出来。让自己的笔多描述一点自然景物本身,就会更大气,走在这样一条奇异的路上,我们的合适身份应该是惊讶而疲倦的跋涉者,而不宜是心思很重的读书人。
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年老的时候有记者问他:“爱因斯坦先生,你已经很老,死亡对你意味着什么?”爱因斯坦回答:“死亡对我意味着我再也不能听到莫扎特。”他讲出来的并不是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他讲出来的是一个艺术命题莫扎特。这就是一个人的程度。蒋介石去世的时候,宋美龄在他灵柩内放的是《唐诗三百首》,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看。
一个人的艺术素养,主要体现于他对审美形式的直觉敏感。人类要获得的艺术训练,也应该集中在这个方面。
到艺术博物馆去看看就知道,一般的参观者在认真地阅读说明、听着讲解,而真正高水平的艺术欣赏者和创造者却不会这样,他们只是打开自己的直觉之门,在各个展厅里寻找震撼自己的形式。找不到,就快步走过;找到了,就流连多时。塞尚说,一幅画,只是眼睛的节日、色彩的逻辑,其他逻辑也许包藏在里边,但艺术家不会去依顺,一依顺,他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