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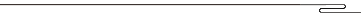
人间尊严的一个关键形态,是美。
美有可能被迫失去尊严,但尊严总会转化为美。
美之于人,集中了自信、教养、风度、见识,最终凝结成一种外化形态,举手投足气象非凡。这种气象,使尊严获得塑造,从此不再涣散。
当尊严释放成一种活泼的生态,美也走向诗化。
诗化的尊严是动态的天真,自由的率性。一切都充满着好奇,处处洋溢着幻想。这样的天地呈现出一种无邪,看似浑不设防,却完全无法侵犯。
诗人比美人更加自我,他们用诗情筑造了又一堵尊严的城墙。
美,不是外在点缀,而是人性、人情的精选形式。在社会上,政治和经济是在争取生命的强大和自尊;而美,则在争取生命的品质和等级。
美永不凝固。即使是处于凝固状态的雕塑,也会在变动的社会生活中缓缓地变易着它们的美学内涵,与不同时代的观赏者互通声息。许多希腊雕塑如维纳斯在近代世界上所焕发的美学内涵,与它们刚刚脱胎成形之时已有很大的不同。
我反复说明的一个道理,就是政治问题和美学问题之间的一般关系和终极关系。如果把这个道理放回到从前的历史中去,即便是当事人也未必明白。屈原不明白,他写的楚辞比他与楚怀王的关系重要;李白不明白,他写的唐诗比他成为李璘的幕僚重要;李清照不明白,她写的宋词比她追随流亡朝廷表明亡夫的政治态度重要。
连这些文化巨人自己都不知轻重,更不要说普通民众了。但是,我终究要告诉民众,他们有权利享受比政治口号更美的诗句,比政治争斗更美的赛事,比政治派别更美的友谊,比政治人物更美的容貌。
长期以来,国内外历史学家总是把物质进步、思想进步看成是一个时代的归结。其实,最终具有归结意义的是审美结构。也就是说,真、善、美这三元组合,以美为归结。这是我们所主张的“审美历史学”。美不是历史的点缀,而是历史的概括。商代历史的归结是青铜器和玉器,就像唐代历史的归结是唐诗,或者说,欧洲好几个历史阶段的归结是希腊神话,是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而不是那些军事政治强人。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归向,有的归向于宗教,有的归向于征战,有的归向于科学,有的归向于政治,有的归向于自然,而中国文化,则归向于艺术。孔子在《论语》中对于这个问题有两度概括。第一度概括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第二度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就是通过修身的方式获得人格享受。李泽厚先生把“游于艺”、“成于乐”说成是“人格的完成”,我很赞同。
在诗意上,人类有一种共同失落。几个伟大文明的开端都有一个史诗阶段,都以诗的语言来奠基一个民族的基础话语。遗憾的是,就像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所说的,大家越到后来越没有诗意了。中国的史诗传统与其他古文明有一点差别,那就是,中国的《诗经》主要是散篇抒情诗,特别在乎脚下的现实悲欢,在乎散散落落的亮点,而不太在乎叙事的整体结构。这也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和别的民族不一样。在我看来,西方民族诗情的宏伟性和整体性也许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生态方式有关,而中国的农耕文明则决定了诗情的真切、散落、随性。
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已经“以诗为经”,把诗当作族群精神的经典,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文明开端;发展了几千年之后,我们现在重新向往一种诗化的生活,希望在繁杂忙碌的尘嚣中升起袅袅诗意,使精神不再苦涩,使生活不再窘迫。这也就是连现代西方人也十分迷醉的所谓“诗意地栖居”。
我的《世界戏剧学》这本书虽然标着“戏剧学”的书名,但内容却广及艺术和美学。
原因是,世界各国的智者在很长时间内,把戏剧当作“最高艺术”来论述。他们的其他艺术观念也都汇集到了戏剧学。更多与戏剧关系不大的哲学家、宗教家、政论家、法学家也都挤到这里来高谈阔论,精彩勃发。因此,如果把《世界戏剧学》的书名改为《世界经典艺术学》或《世界感性美学》,也未尝不可。
以我自己为例,我写作此书那么多年,获得的精神成果就远远超出戏剧专业,使自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我被广泛认知的身份是中华文化的阐释者,但我的精神基座上,却牢牢地烙刻着亚里士多德、狄德罗、莱辛、歌德、黑格尔、席勒、雨果、尼采这些大名,都与这部书有关。从这个精神基座出发,通达对我更重要的康德、荣格、罗素、萨特,也不难了。
一个人,如果能够尽早获得全人类最高星座的审美默契,然后返视自己立足的土地,投入全新的创造,那就是真正的生命尊严。
人类早已跨越了纯实利的审美阶段,不仅早已能够欣赏一棵苍老斑驳、藤萝垂垂而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古松,而且还能把玩一截虬曲的树根。与此相应,在文艺创作上,人们也不愿意把一切创造活动都与现实需求直接挂钩,这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今天,我们还会兴致勃勃地吟诵几首唐诗、宋词,观赏几出杂剧、昆曲,也正体现着我们在审美领域所取得的自由。
即便如此,美的领域却也不应该主要由遗产组成,哪怕这些遗产确实是无价之宝。人类的文明需要不断前进,人类在审美领域所取得的自由需要不断开拓。因此,在美的领域里,应该流荡着生命的绿色、青春的气息。即使是那些极有保存价值的古松,也只有置身在遍是野花、苔藓、青草的山坡间,才能构成生命的比照,才能显现它们在年岁上的优势而分外威严。没有生机勃勃的氛围,也就没有古松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