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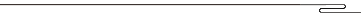
中外多数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都在研究常规。虽然它们也会频频举出一些伟大作品的例子,但也只是借用它们的名声来说明常规。
常规,对于科学、医学、法学、社会学来说都非常重要,但对艺术创造来说,这是平庸的另一种说法。
现代派文艺一旦被概括成理论,也就产生了差不多的毛病。那些理论话语初听起来很新鲜,但通过几十年的空洞重复,也就变成了一种表层概念。结果,模拟多而创造少,即便有创造,也已无涉伟大。
大学者弗兰西斯·培根曾用拉丁文为艺术下过一个定义:艺术是人与自然相乘。
陆机和刘勰把艺术家天人合一的创作状态写得淋漓尽致,尽管从概念到表述完全是东方古典形态,却能与培根的定义遥相呼应。他们的表述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座能够让“人与自然相乘”的“炼丹炉”就在艺术家心间,而艺术家抵达的这个创造境界又是一个极神秘的所在,外部力量很难介入。按照罗曼·罗兰的说法,这是一个“单房”。他说任何作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为自己保留一间单房,离开人群,单独幽居”。陆机和刘勰所说的一切,只能发生在这样的“单房”里。
在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中,唯有艺术的创造最为纯粹。美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一书中详尽讨论了这种特性。她认为,艺术创造和物质产品的创新有本质的区别。物质产品离不开特定的材料、形状、功能、名称,因此无论如何算不上纯粹意义的创造;而艺术则要构建一种原来并不存在的虚象,它即使与现实相关,也是一种主观经验和情感生活的表现,因此是一种真正的创造。
艺术创造的说服力,是要把培根所说的“人”,通过艺术家个人而抵达人类生态;还要把培根所说的自然,通过原始自然而抵达自觉形式。而这一切,又必须在虚设中实现。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定义了。
那就是——艺术,是一种把人类生态变成直觉审美形式的创造。
艺术要通过创造,把人类生态变成直觉审美形式,这件事的格局很大。
人类生态奇大无比,直觉形式则具体可感,两者之间距离迢迢。要完成中间的创造必须经过一层层严格的选择。选择的结果,人类的生态仍是人类的生态,不因经过选择而缩小;直觉形式仍然是直觉形式,不因经过选择而空洞。此间繁难,可想而知。
有些诗人、画家、音乐家,凭着自己的天赋把此间繁难轻捷消解,这是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常常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温习“人心之通天”的至高境界。
我坚信伟大是有秘密的。对艺术来说,伟大作品成功的秘密,除了人格原因外,也不排除方法上的原因。我花费七年时间仔细钻研了世界上十四个国家在美学、艺术学上的主要著作,并进而研究古今伟大作品,尤其是近一百年来的现当代伟大作品,终于发现,这些作品背后潜藏着两大隐秘结构,并由此建立了我自己的艺术创造论。
我要讲述的两大隐秘结构为:一、无结论的两难结构;二、半透明的双层结构。
人们普遍认为,正确的主题思想加上合适的艺术形式,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品。这种说法勉强也能成立,只不过,那是指常规的好作品,而不是指真正的杰作,更不是指伟大的作品。
伟大的艺术作品,没有清晰的主题思想,也没有简明的结论。现在我们似乎说得出几句它们的主题思想和结论,那是后人强加给它们的。后人为了讲解它们、分析它们、以它们谋生,就找了几条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拐杖,其实那些拐杖都不属于伟大作品本身。例如,人们常常会说《离骚》的主题思想是“怀才不遇的爱国主义”,说《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歌颂封建家庭叛逆者的爱情”,其实都是不对的。
在西方艺术中,《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几部最好的悲剧,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罗丹、凡·高、毕加索的绘画和雕塑,贝多芬、巴赫、莫扎特的音乐,也都不存在明确的主题和结论。讲得越清楚,就离它们越远。
这并不是说,杰出的艺术家在没有把事情想清楚之前就可以胡乱投入创作。更不是说,人们可以容忍艺术作品最后呈现出一团混乱和迷糊。恰恰相反,伟大作品不清晰、不简明的意涵,正是艺术家想得最多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的所在。世上想不出答案的问题有很多,但其中却有那么几个,一想就会搅动身心,卷入巨大的人生疑问。伟大的艺术家只要发现这样的地方,就会倾注自己最大的精力开始创作。创作的起点是两难或几难并存,此耶?彼耶?是耶?非耶?十分为难。创作的结果也是两难或几难并存,此耶?彼耶?是耶?非耶?继续为难。
两难结构有一个巨大的陷阱,让大量有可能问鼎伟大的作品失足其间,结果只能保持杰出,却与伟大无缘。这个巨大的陷阱,可称之为“两难的调解方案”。这种调解方案,是出于世俗心理而在万丈深渊上勉强勾画的安慰之桥。
勾画这种安慰之桥的,首先是评论家。他们首先要安慰的不是民众,而是自己,因为他们的天赋和心力理解不了万丈深渊。由于他们长年的连篇累牍,创造者也渐渐上当了。
有的时候,人们又试图用文艺作品来表现“真理”。在真理受到玷污的时代,艺术家和理论家呼吁让艺术皈附真理,是一种正义行动,是人类艺术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悲壮课题。但是,以现代艺术观念来看,真理不是一种僵死的条文,而是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艺术不应追随在早已发现的真理后面一味进行重复阐述,而应该置身于发现生活中一切奥秘的前沿,不管这种奥秘算不算真理。
艺术作品的诞生,并不是仅仅为了替公认正确的道理增添一个例子,而应该用艺术自身的方式,在公认正确的道理的外面、反面,或边缘地带,发现新的道理。
一切向着未知领域开发的艺术作品,都会在展现现场构成一种诱人的气氛,吸引你与它一起向着生活的深层探掘。相比之下,像小学老师引导学生一样来向观众转述一种既定常理,则失去了共同研讨的气氛。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
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
现代艺术向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与那种以验证常识为乐的文艺追求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常识,是人们普遍掌握的道理。不管到什么时候,艺术总难免要承担普及某些社会常识的任务,因为社会上总会出现大量违背常识的现象,人们需要通过谴责和纠正来获得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角色的自我确认。因此,那种以情节和形象来验证某种社会常识的文艺作品,如果写得好,也可以获得某种正面评价。但是,无可否认,这种作品的精神能量极其有限。一切精神能量的大发挥,总是产生在裂变和爆炸之中,总是产生在对常规空间的伸拓和突破之中,总是产生在对未曾知晓的领域的挺进之中。
艺术大师们的“直闯‘不可知’的禁地”总带着大量的超体验性质。这种超体验常常使艺术家和读者都或多或少地陷入慌乱的境地,但是,这不应该使我们退缩,而应该看成是无限对于有限的擢拔,永恒对于即时的擢拔,哲理对于庸常的擢拔。
海明威的作品确实饱蕴着这种强烈的探索精神。《老人与海》就是他对现代精神、美国精神、男子汉精神的一种探索。那位孤独的老人置身在茫茫大海中,与浪、与鱼、与自己的体力和意志进行着搏斗。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却找不到答案,这个老人,最后他到底胜利了没有?一个“未知数”。
海明威以《老人与海》等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有亲临颁奖现场,而是请美国大使代读了他的获奖感言。他的获奖感言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
给未知以起点——这是海明威对创作的基本观点。
现代艺术家特别重视探察未知,大半是由于现代生活的发展速率使以往规则的朽逝频率大为提高,未知天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不研究、不探察,只会使心头留存的幻影与生活本身越来越远。
有人会问:把自己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拿出来交给观众,不是太不负责了吗?现代艺术家回答:把生活中并未解决的问题在艺术上轻便地解决了,不是太不负责了吗?有人会问:还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有什么表现的必要呢?现代艺术家回答:已经找到了答案的问题,有什么表现的必要呢?
在这些现代艺术家看来,世界的意义,人生的意义,都不是某种事先的强加,而只能产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探索有结果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最大的那些未知课题与人类相始终,因此肯定不会找到答案,但却又永远充满着吸引力。于是,探索、开发、发现、创造,这就是二十世纪艺术的主旋律。
两难结构也是一种不知前途的结构,因此也可称之为“未知结构”。有的评论家生气了,说:“你自己还未知呢,为什么要写成作品?”那些艺术家回答说:“如果我已经搞清楚了,为什么还要投身创作?”
艺术创作之所要,就是曹雪芹所说的那种“痴”的其中深味,那种不仅自己不能“解”,连别人也不能“解”的状态,就是我所说的未知结构。《三国演义》有“解”,因此是优秀作品而不是伟大作品;《红楼梦》无“解”,因此不仅是优秀作品还是伟大作品。我们很多“红学家”试图给《红楼梦》提供各种各样的“解”,如果提供得非常非常好,那就是把伟大作品降格为优秀作品。可怕的是,他们提供的“解”常常不好,那就不知道把它折腾成什么作品了。
这就像评论《伽利略传》,评论家最常规的说法是,布莱希特创造了一个“既伟大又渺小的科学家”,伽利略是“科学上的巨人,人格上的矮子”,等等,硬是让一个人的“自身矛盾”来解释世间人生的共同难题。同样的道理,《红楼梦》所呈示的那种谁也无可逃遁的恢宏困境,也不能缩小为贾宝玉、林黛玉的“性格困境”。迪伦马特为什么故意要把罗慕洛放在罗马文明和中世纪的历史大拐点上?他正是要表明,所发生的一切都非常宏大,不是个人原因。
既然不是个人原因,那么,不少评论家就会寻找政治原因、历史原因,这是我们以前的教科书、学术著作的主流思路。例如,把《阿Q正传》试图解析“国民性”的努力,缩小为“辛亥革命前后浙东农村雇农阶层的生态和心态”,把《红楼梦》研究演变成清史研究。这种分析比“调解方案”更加糟糕,因为一旦把伟大的作品“锁定”在历史过程和政治事件上,它就成了一种已逝的陈迹,而且是一种“寄生的陈迹”,这就被抽去了那种穿越时间的生命力。不仅如此,历史过程和政治事件迟早可以由后人做出结论,从而体现后人居高临下的骄傲。因此,如果把伟大的作品曲解为历史和政治的寄生物,那后人对它们也可以倾泻居高临下的骄傲了。读这样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产生的心理效果,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隔”。也就是说,把作品与读者、观众隔开,让读者、观众取得一种浅薄的“安全”。
其实,在真正伟大的作品前,一切读者、观众都是无法“安全”的,因为它们与所有的人相关,又永远也解决不了。
记住了,朋友们,伟大作品的一个重大秘诀,在于它的不封闭。不封闭于某段历史、某些典型,而是直通一切人;也不封闭于各种“伪解决状态”,而是让巨大的两难直通今天和未来。一般说来,不封闭程度越高,也就越伟大。再遥远的作品,例如古希腊悲剧、《离骚》、《浮士德》,至今仍处于一种没有答案、无法解决的不封闭状态,而且把我们每个人都裹卷在里边。这就是伟大。
诸子百家是思想家而不是艺术家,因此他们的言论大多是一种结论式的宣讲。站得高,姿态也高。但是,这种格局到了大艺术家屈原那里就不同了。屈原没有结论,也不作宣讲。他只有没完没了的担忧、气恼、自问,而且永远找不到答案。他甚至还专门写了《天问》,问出一大堆最天真、最质朴、最终极的问题,也不企图获得解答。他完全像一个孩子一样睁着惶恐而好奇的眼睛问天问地;相比之下,诸子百家专门回答别人的提问,而且总是回答得斩钉截铁。这便典型地说明了大艺术家与总是给出结论的大思想家不同,他们所探询的总是那些无“解”的命题。
在艺术创作中,最怕“洞察一切”、“看透一切”的“宣教方位”。即便是好作品,一有宣教便降下三个等级。《三国演义》开宗明义,从“滚滚长江东逝水”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把书中的故事全都高屋建瓴地看透了,当然也不错,但一比《红楼梦》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高下立见。表面上,一个是俯视历史,把酒笑谈;另一个是连自己也觉得荒唐、辛酸、痴傻。但在艺术创作中,前者之“高”即是低,后者之“低”即是高。
在艺术领域里,凡是真正面对未知世界,在一些没有结论的问题上进行创作的作品往往是比较好的作品。而得出结论的作品往往不是好作品,因为逻辑战胜了感性,结论战胜了探求,这反而是一种封闭性的存在。我发现中华文化中的大量的未知其实只有放到更大的背景当中才会更有威力,我在不断的寻找过程中,找到了中华文化中那种最大的未知,她本身已经解决不了,观察不了,表述不了,必须要超越这个边缘,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析她。
世界的大部分是未知的,人生的大部分是未知的。但是,人类出于群体生存的惯性,不愿承认这一点,因此就用科学、教育、传媒、网络来掩饰,装扮成对世界和人生的充分“已知”,并把这种装扮打造成一副副坚硬的胄甲。实际上,大科学家会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宗教也会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各种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也会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装扮“已知”,使人类自以为是,颐指气使,并由此产生没完没了的争斗;承认未知,却能使人类回归诚实和诚恳。即使在发现太多的未知后人们会受到惊吓,变得疯疯癫癫,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领域的存在,更不能无视在这个领域中有着人性最慌张、最自省、最终极的部位。说到底,这就是伟大艺术的关键领域,也就是人类天天想掩盖又在内心不想掩盖的那方秘土。
艺术的秘土也就是人性的秘土,它比科学更贴近真实。
伟大作品的深刻追求,未必让多数读者和观众看“懂”。但对此我必须立即说明,艺术的伟大不同于哲学的伟大,在于即使不“懂”,也要尽可能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很多伟大艺术的覆盖面,远远大于能够真正欣赏它们的群落,就因为它们都具有一种正面的“泛化误读功能”。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少民众喜爱欧洲古典主义音乐,只觉得好听,而完全没有领会其中的宗教精神。同样,他们也会把凡·高的油画当作一种色彩亮丽的装饰画,而完全没有领会其中的生命挣扎。这种现象常常受到某些具有“伪贵族”气息的文化人嘲笑,而我却觉得很正常。这就像,即便文化层次很低的人也会觉得晚霞很美,尽管他们完全不知道光学原理和气象构成。在美的领域,“泛化感受”的天地很大,其中也包括“泛化误解”。而且,越是伟大,越容易泛化。
很多伟大的艺术作品有意无意间,构成了不同的泛化层次,和不同的接受者自由。甚至,有时也会故意提供“泛化误读”的层次,让接受者即使误读也没有脱离美的控制。
只有鼓励泛化感受,包容泛化程度,才能问鼎伟大。
伟大的作者总是在通俗层面和潜藏层面之间挖出一系列通道,树起一块块路碑,做出一次次暗示。从通俗层面看来,这也是一条条门缝、一道道豁口、一孔孔光洞,让一些有灵性的观众产生疑惑,急于窥探。当然,对多数通俗观众来说,这是一些情节之外的角落,难于理解的部件,也就不去注意了。这类艺术,照顾的是多数通俗观众,关注的是少数灵性观众。这些灵性观众,是伟大作者的精神知音,也是人类艺术的真正觉者。
这两个层面,前后并立,但前面一层又隐隐约约、影影绰绰地透露着后面一层的信息。我把这种艺术方式称为“半透明的双层结构”。
“半透明的双层结构”是造就杰出观众的秘径。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这样的观众,在年轻时发现了伟大作品表层的“门缝”,引起巨大好奇,在朦胧混沌中留下一个不断延伸的梦,结果提升了人格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