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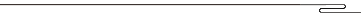
中国当代城市文化是我近来着重思考的若干课题中的一部分。较之其他任何方式,文化思考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它更善于进行时空上的整体把握。正如当我们置身于一千多年前已经人烟全无的新疆古城的遗迹时,其间巨大的震撼必然促使我们对城市文化的命运做出追索与探究。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少从城市文明的角度来论证自身的生态环境,而事实上城市文明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今中国在文化上所面临的时代性的重大命题。
文化争论极有可能将最终归结到城市文明的争论上,文化将被视作城市魅力最集中的发散点而受到强有力的关注。
如今,当我们走在各座城市中的时候,最大的困惑可能莫过于这些城市正在以极其相似的面目在我们面前不断地重复,致使我们无法把握到对城市的历史进行判断的依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要到哪里去?”这个哲理性的诘问同样适用于都市的文化,它逼迫着文化人必须怀着深切的热情为城市重新寻找、确认严重流失的自我性格。
连城市的普通生活形态也受到如此的抗拒和谴责,当然更谈不上对城市心理规则的弘扬了。中国历史上很难举得出一批真正的城市思想家。读古希腊、罗马文献,看到那些政治家、思想家一开口就朗声朗气地呼唤:“雅典城的公民们!”“罗马城的公民们!”在中国古代就缺少这种呼唤声。第一个真正具备城市意识的思想家,我觉得是龚自珍,那就出现得太晚了,而且他也未能让自己的声音占领任何一座城市。
中国也拥有过高水平的思想文化大师,但他们为了逃避无秩序的拥挤,大多藏身于草堂、茅庵、精舍,大不了躲在深山里讲学,主持着岳麓书院或白鹿洞书院,与城市关系不大。这个传统,致使我们直到今天还无法对城市文明做出高层面的把持和阐扬,而多数成功的艺术作品更是以农村或小镇为表现基点。
因此,突然热闹起来的中国城市,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它们天生的脆弱性。因此,我们还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完成了对数千年的封建观念和小农意识的战胜。
城市,还有被销蚀的可能。
在城市历史性的问题上,许多城市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表现得相当漫不经心。当人们用推土机轻而易举地推倒一座已经不再具有使用价值的井台时,几乎忽视了就是这座留下历史印痕的破落井台或许正值得后人驻足深思良久;当人们在一座经历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古迹前突兀地平添某些现代化的娱乐设施时,完全没有设想到就是这看似能招来顾客的一举将深藏的历史性扭曲得面目全非。历史性格意识的稀薄使我们付出的代价便是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变成没有年龄、没有后盾、没有根基的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并非只简单地以其长短来衡量。只有当我们真正珍惜历史时,我们才能充分地拥有自己的历史。散漫漠然的心态终究将使历史悄悄地流失。这使我不由又想到了关于城市魅力的话题。新加坡一家最豪华的旅馆大门前有一个特制的玻璃柜,其间放置着一本旅客登记本,上面记录了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经在一九三六年的某一天在这家旅馆住宿过一个晚上。仅仅是短暂的一个晚上,所有光临这家旅馆的人却因为这位文化名人的逗留而油然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敬畏感和崇高感。海明威也曾经到达过上海,爱因斯坦亦光临沪上。据说,当年爱因斯坦还是在上海获悉他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的。可是,关于这两位为人类文明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在上海的行踪,我们今天已所知寥寥。同新加坡郑重其事的做法相比较,由于缺乏必要的留存和梳理,我们同样拥有甚至远为辉煌的一段历史便这样悄然无踪了。
城市文化的哲学本质,是一种密集空间里的心理共享。
城市的密集空间,在政治上促成了市民民主,在经济上促成了都市金融,而在文化上,则促成了公共审美。
欧洲的文化复兴,并没有出现什么思想家、哲学家,而只是几位公共艺术家,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人在城市的公共空间进行创作,造就了可以进行集体评判的广大市民,从而使城市走向文化自觉。
保护重大古迹,其实也在建立一种公共审美,使众多市民找到与古人“隔时共居”、与今人“同时共居”的时间造型和历史造型。由此,增加共同居住的理由和自尊。
公共审美的要求,使城市文化肩负了很多艰巨的具体任务。
在这儿不妨做一个比较:在今天,我们可以不必理会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作品,但对于建筑和街道来说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种强制性的公共审美,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眼睛怎么也躲不过。因此,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审美课堂,市民天天都在上课。如果“课本”优秀,那么全城的市民也就获得了一种正面的审美共识;相反,如果“课本”拙劣,那么一代代市民也就接受了丑的熏陶,一起蒙污,造成文化上的沦落。欧洲有的城市曾经判定丑陋建筑的设计师应负法律责任,就是考虑到这种躲不开的祸害。
很多市长常常把哪个画家、哪个诗人得了奖当作城市文化的大事。其实,那些得奖的作品未必是公共审美,而建筑、街道却是。因此,在城市文化中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尤其是建筑,一楼既立,百年不倒,它的设计等级,也就成了一个城市文化等级的代表,成了全城民众荣辱文野的标志。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中国旅游者曾经由衷赞叹巴黎、罗马、佛罗伦萨、海德堡的建筑之美和街道之美,那就是在欣赏城市文化各项审美元素的高等级和谐。要做到“高等级和谐”很不容易,需要一些全方位的艺术家执掌。我们知道欧洲曾有不少大艺术家参与其事,其实中国唐代的长安、日本的京都也是如此。在当代中国,我的好友陈逸飞先生生前曾参与上海浦东世纪大道巨细靡遗的规划和设计,国内有几所美术学院的师生也做了类似的事情,都为城市文化的建设做出了切实贡献。
作为一种公共审美,城市文化的主要方面应该是可视的。城市里各所大学、研究所里的学术成果,严格说来并不是城市文化,至多只能说是“城市里的文化”。城市文化以密集而稳固的全民共享性作为基础,因此也必须遵守其他文化不必遵守的规矩。
公共审美必须遵守的一条重要规矩就是“免惊扰”。“惊扰”分两类,一类是内容上的惊扰,一类是形式上的惊扰。
何谓内容上的惊扰?由于是公共审美,审美者包括老人、小孩、病人,以及带有各种精神倾向的人。因此必须把暴力、色情、恐怖、恶心的图像删除。上海一个现代派艺术家曾把一具仿造的骷髅悬挂在窗下,直对街道,这就对很多市民造成惊扰。同样,巨蟒、软虫、蜥蜴的巨幅视频也不能出现在闹市。过于暴露的性爱镜头出现在公共场所,也会使很多领着孩子的家长、扶着老人的晚辈尴尬。
何谓形式上的惊扰?那就是艳色灼目、厉声刺耳、广告堵眼、标语破景。有人说,这一切是“现代自由”。其实,现代社会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享有惊扰他人自由的自由。这就像在一个安静的住宅社区,半夜里突然响起了意大利男高音,虽然唱得很美却违反了现代公共空间的规矩。
现在中国城市间最常见的艳色、彩灯、大字、广告和标语,人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只要多多游历就会懂得,这是低级社区的基本图像。就像一个男人穿着花格子西装,戴着未除商标的墨镜,又挂着粗亮的项链,很难让人尊敬。
公共审美的“免惊扰”原则,必然会使一座城市在图像上删除烦冗,删除缤纷,删除怪异,走向简约,走向朴素,走向本真。到那时,我们又可以在白墙长巷里打伞听雨声了,又可以在深秋江堤边静坐数远帆了。优秀的建筑设计也可以不受干扰、不被拥塞地呈现它们完整的线条了。
公共审美的最后标准,是融入自然。城市里如果有山有水,人们必须虔诚礼让,即所谓“显山露水”。这还不够,应该进一步让自然景物成为城市的主角和灵魂。不是让城市来装饰它们,而是让它们以野朴的本相楔入城市精神。柏林的城中森林,伯尔尼不失土腥气的阿勒河,京都如海如潮的枫叶,都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的谦恭。这样,前面所说的“免惊扰”原则,有了更重要的含义,那就是,既不惊扰市民,也不惊扰自然。现在全球都在努力地节能、减排,就是对两种“免惊扰”的共同遵守。
只要是公共审美,再小也不可轻视。例如我很看重街道间各种招牌上的书法,并把它看成是中国千年书法艺术在当代最普及的实现方式,比开办书法展、出版书法集更为重要。我在很多城市的街道上闲逛时曾一再生出疑问:这些城市的书法家协会,为什么不在公共书法这样的大事上多做一点事呢?
除此之外,街道上的路灯、长椅、花坛、栏杆、垃圾桶等,全都是公共审美的载体,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想想吧,我们花费不少经费举办的演唱晚会一夜即过,而这些元素却年年月月都安静地存在,与市民在构建着一种长久的相互适应。
这种相互适应一旦建立,市民们也就拥有了共同的审美基石。如果适应的是高等级,那么,对于低等级的街道就会产生不适应。这种适应和不适应,也就是城市美学的升级过程。
一切美丽都是和谐的,因此总是浑然天成、典雅含蓄。反之,一切丑陋都是狞厉的,因此总是耀武扬威、嚣张霸道。如果没有审美公德的佑护,美永远战胜不了丑。
正像美好是一所学校,丑陋也是一所学校;正像美好会传染,丑陋也会传染。这就雄辩地说明,审美是一种公德。
城市文化上层结构的代表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着整个城市的灵魂。普林斯顿的邻居们有多少人能理解爱因斯坦的学说?据爱因斯坦说,包括他本人在内,在当时整个美国了解相对论的不会超过四个人。令人欣慰的是,学术上的隔膜并不妨碍普林斯顿市民将爱因斯坦视作自己城市的骄傲。对于他们来说,只须明白爱因斯坦的贡献对于人类具有深远的意义,此便足矣。现在的广州时常怀有被认作“文化沙漠”的忧虑。倘若把历史倒回到三十多年前,广州城却大可不必为此担忧。一位老先生在此地的活动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小觑广州。这位老先生便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郭沫若曾称要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赶上陈老先生的学问,大多数人自然更是难以企及。一座城市便是由于容纳了这样的人类文化精英而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分量。
城市文化中层结构的代表者向普通市民走近了一步。人们在能够面对他们的前提下,对他们倾注了极为热情的关注,我们的艺术家多数可以属于此类。当我们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戏剧比较繁荣的那段时期时,我们首先引以为豪的未必是某些剧目,而是从广东的红线女、上海的袁雪芬到安徽的严凤英,更无须说梅兰芳、周信芳等一大批代表偶像的辉煌组合。人们对这一层次文化代表者的关注几乎达到了关爱的程度。他们的饮食起居、一举一动无不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甚至有许多事情希望要求他们做出表态。对于文化代表者个人来说,这种防不胜防的麻烦和失去个人空间的困扰确实相当不幸。然而,从一座城市的角度进行判断,这又何尝不失为一种幸运?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为何显得寂寞,这与我们目前缺乏人们普遍关注的生命体是密切相关的。
在城市文化的整体构造中,流行艺术作为完整范畴占据着它的下层结构。流行艺术偶像在少男少女中所受到的痴迷,往往被视为不可思议的现象。其实,这种崇拜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年轻的一代刚刚开始离开父母的怀抱,他们迫切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寻觅所能信任崇拜的对象。这个对象必然高于他们,但又必须在他们所能企及的范畴内,同时不带有任何涉及切身利益的功利色彩。在这些综合平衡中,流行艺术代表者成为青少年崇拜最理想的承担者。对此,我们不必有过多的指责。事实已经证明,真正能够立足的流行艺术必然是以传播真善美为主体的。以平心静气的眼光来看,这个层次并非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肮脏,它同样存在许多令人感动的生命关怀。
一个生命能够将几万个生命聚合起来,其间必然有艺术的理由,崇高的理由,这也提醒着我们对这个层次不妨采取更加宽裕与认同的态度。
城市文化的活体呈现,是市民身上的礼仪。
我曾不止一次阐释过荣格的一个观点: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重要的不是个体人格而是集体人格。荣格所说的集体人格带有“原型”的意思,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关键课题。我们在这里借用他的这个概念,并把这个概念缩小,说明一个城市的文化,也就是这个城市的集体人格。
优化一个城市的集体人格,是城市文化建设的目标。
礼仪的消失,初一看与兵荒马乱的时局有关,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在兵荒马乱之中,人们越来越企盼和平秩序的重建,而和平秩序的重要因素就是礼仪。因此,战后人们往往比战前更讲究礼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家破人亡的欧洲人走进了还没有来得及完全修复的音乐厅,用贝多芬、巴赫、莫扎特来修复心灵。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成了当代社会的礼仪载体。连我们熟悉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践踏了多少亚洲国家,自己也挨了两颗原子弹,精神面貌和城市面貌都是一片废墟。但很快,他们在废墟上建立起了让别国民众吃惊的礼仪。
须知,孔子心中的“君子世界”,是一个礼仪世界,而未必是一个觉悟世界。或者说,礼仪在前,觉悟在后,已是君子。
根据上述理由,我希望我们的城市,减少空洞的宣教,投入礼仪设计,试行推广步骤。
在集体人格上,谁也不会听从号召,谁也不会听从批判。
我们的祖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不信任“空对空”的说教,而是设计一套行为规范,以半强制的方式在社会上推行。这种行为规范,就叫礼仪。孔子一生最看重的事,就是寻找周朝的礼仪,并力图恢复。我们现在企盼的集体礼仪,应该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
正是礼仪,使文化变成行动,使无形变为有形,使精神可触可摸,使道德可依可循。教育,先教“做什么”,再说“为什么”。
文化代表者,其通俗化的表达方式即为文化偶像,只是“偶像”这个词汇往往容易引来人们微妙的反应。事实上,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根本性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一种高浓度化的组合,这样的组合方式在其代表层次上的表现必然要求以可感的生命体来完成。在一个都市中,某个文化代表者的生命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焦点,这种关心中包含着文化聚合的意味,其本身是令人感到温暖的。
长期以来,由于文化机制上的大锅饭体制和观念上的某些偏差,我们目前的都市文化正处在基本上没有代表者的尴尬境地中。当某个文化代表者的萌芽刚刚出现时,一些不健全的社会心理就在强有力的作用下轻而易举地将其消解殆尽。如此循环往复,我们所听到的只剩下无数明星梦的麻烦事。于是,能够凝聚无数人关注的生命体没有了,文化陷入一种难言的寂寞中。必须指出,任何一位文化偶像所承受的关爱都可能超过它本身的现实价值。我们对此不必过多地计较纠缠。文化偶像作为生命体的存在本身是真实的。缺陷部分的存在并不能否认关爱的价值。因为人们对其倾注关爱的部分亦同样是真实的,有价值的。我们完全可以对文化偶像的两个部分加以人性的区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到了建立起捍卫自己文化代表人物机制的时候了,这样才能避免和制止某种整体上的失落。
我们同样需要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崇拜。崇拜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然而,文化仰望在更大的程度上则包含着崇高的意味。因此,重建城市文化的生命体,并使其在一个和谐包容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生命力作为支撑城市文明的主干,其文化必然是散落的,缺乏凝聚力的,城市的魅力也由此而大为减损。可以设想,德国倘若没有造就贝多芬,这样的损失究竟属于贝多芬,还是属于德国?我以为艺术家个人的失落终究是有限的,最终承担这种遗憾的还将是文化的整体。
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文化吸引力的产生,未必大师云集,学派丛生。一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城市,万不可在这方面拔苗助长,只须认真打理环境。适合文化人居住,又适合文化流通的环境,其实也就是健康、宁静的人情环境。
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脚生根之前,虚张声势地夸张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牌号,反而会对流荡无驻的文化实力产生排斥。因此,好心的市长们在向可能进入的文化人介绍本市“文化优势”的时候,其实正是在推拒他们。这并非文人相轻,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气候的文化人都有自身独立性,不愿沦为已有牌号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选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灵”。
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而不是一堆已有的名字和作品。
几年前,我曾对急于清理家中旧物的人们发出一个倡议:大家在动手烧自己旧照片的时候,请千万手下留情,三思而后行。这些在一瞬间就可以被彻底毁灭的东西恰恰是永远不可能复制的。城市文化的历史亦是如此。一个城市历史厚度的显现,在于它善于留存值得纪念的一切人物和一切东西,现代都市文化的构建也由此而具备了基点。对此,我很赞赏新疆石河子市的做法。这个在沙漠上建造起来的年轻城市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建设大军们挖下第一犁的地方。因此,尽管这座城市的历史很短,它却能凭借自我历史性格的确认而在文化上矗立起来,发散自身独特的魅力。
在城市魅力的发掘中,我们无须过多地纠缠于历史的判断。我曾向合肥市人民政府提议,李鸿章的旧居最好不要轻易拆除。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但历史厚度的留存毕竟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纪念。当然,任何物质形态的文化遗迹所提供的只可能是某种表象。我们最终所关注的还是表象背后所凝注的东西,这便是一大群原本相互没有联系的人,由于共同拥有某种历史而被聚合起来,寻觅到共同的归属。城市历史性格确认的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