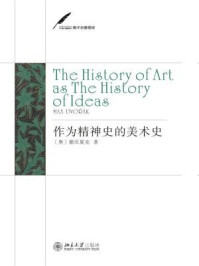北京地处华北平原的北部,是东北渔猎文明、西北游牧文明及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三种文明在北京地区持续碰撞、融合,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南海子就是这一共同体形成的见证,在其从辽至清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与天地参”的生态观、“礼乐复合”的社会观、“多元一体”的民族观、“以民为本”的民生观等共同文化意识。
皇家苑囿起源于先秦,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形。先秦、两汉时期,城市依河流选址,而与城共生的大型皇家苑囿多于水源处湿地营建,充分利用湿地生态环境效益,进而形成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苑囿承担着生态保护、物质生产、禽兽牲畜繁育、起居游赏仪式、狩猎与军事等多重功能,汉代的上林苑就是结合湿地环境营建皇家苑囿的典型代表。
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清楚地记载了上林苑以湿地环境为营建基础,通过水系划定苑囿范围:“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可见苑囿水源丰沛,生态环境优渥。文中,作者极力渲染描绘苑内林木花草、奇珍异果、飞禽走兽、离宫别馆的壮丽景象及汉天子游猎的盛大规模:“
 旄獏嫠,沈牛麈麋,赤首圜题……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借以讽谏帝王将如此肥沃的土地建为禁苑,是与民争利的行为。在《上林赋》一文的最后,天子反思:“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怕百姓被其尤也。”
旄獏嫠,沈牛麈麋,赤首圜题……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借以讽谏帝王将如此肥沃的土地建为禁苑,是与民争利的行为。在《上林赋》一文的最后,天子反思:“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怕百姓被其尤也。”
 强调苑囿营建要以民为本、与民共享,而这种民本思想对当今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和谐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强调苑囿营建要以民为本、与民共享,而这种民本思想对当今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和谐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根据《上林赋》中所描绘的情形,创作了《子虚上林图》(又名《天子狩猎图》)(图1),以精细的笔墨再现了天子于上林苑中游猎讲武、祭祀等恢宏画面,实际上这就是辽金以来,尤其是明代南海子的真实写照。

图1 《子虚上林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海子位于北京小平原南部的南潜水溢出带上,随着古永定河道的摆动,这里形成了一片水草丰美、湖泊密布的湿地,这片湿地就是南海子的生态环境基础。丰沛的水源造就了南海子北京生态屏障的历史地位,自辽金以来得到了持续的人文开发。辽将唐代的幽州城升为“南京”。辽太宗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设南北两院。辽世宗以后,辽主效仿中原诸王朝,接受朝见和处理政事,于皇帝的行在之所设朝廷,称为“捺钵”。
 到了辽圣宗时期,辽主张与北宋议和。在这种形势下,圣宗的春捺钵开始向南京地区移动,以处理与北宋相关的政务。同时,延续契丹民族传统,在候鸟北归之际举行水围活动。
到了辽圣宗时期,辽主张与北宋议和。在这种形势下,圣宗的春捺钵开始向南京地区移动,以处理与北宋相关的政务。同时,延续契丹民族传统,在候鸟北归之际举行水围活动。
 辽代捺钵的建筑形式以营帐为主,因而尚未见在南海子有固定建筑的记载。从宋人绘画中的契丹营帐,以及清代皇帝驻跸幄、大营,我们不难想象辽代帝王在南海子捺钵的场景(图2)。
辽代捺钵的建筑形式以营帐为主,因而尚未见在南海子有固定建筑的记载。从宋人绘画中的契丹营帐,以及清代皇帝驻跸幄、大营,我们不难想象辽代帝王在南海子捺钵的场景(图2)。

图2 《平定伊利回部战图册·邬什酋长献城降图》(《清史图典》)
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燕京,北京首次成为帝国的首都。金代帝王均尊崇儒学,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在吸收儒家文化的同时,也强调要延续渔猎民族的文化传统,遵循辽代皇帝四时巡守的旧俗:“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
 在城东南三十里,即今晾鹰台一带举行春水活动。金代“春水秋山”与辽代“捺钵”有所不同,皇帝行营不再是政治中心朝廷的所在,仅借春水之际体察民情:“天子巡狩当举善罚恶”。与契丹人相比,女真人的居住习惯也有所不同,“栋宇是居,不便迁徙”
在城东南三十里,即今晾鹰台一带举行春水活动。金代“春水秋山”与辽代“捺钵”有所不同,皇帝行营不再是政治中心朝廷的所在,仅借春水之际体察民情:“天子巡狩当举善罚恶”。与契丹人相比,女真人的居住习惯也有所不同,“栋宇是居,不便迁徙”
 。于是,最迟在明昌五年(1194)金章宗已在今晾鹰台一带修建别宫,作为春水期间驻跸之所,并于承安三年(1198),将其命名为“建春宫”,是为南海子行宫建设之始。
。于是,最迟在明昌五年(1194)金章宗已在今晾鹰台一带修建别宫,作为春水期间驻跸之所,并于承安三年(1198),将其命名为“建春宫”,是为南海子行宫建设之始。

从中都如春水的距离,以及清代舆图中的旧御道来看,晾鹰台一带就应该是金代春水的目的地,而旧御道穿越的小海子,地势略高,应为临时搭设帐篷的营地,这也是后来南苑机场选址于此的主要原因。这条御道至今依然部分留存,即今日的南苑西路、南大红门路。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听从刘秉忠的建议,取《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改国号为“大元”,并于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自认中华正朔。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将行围视为皇室的乐趣与荣耀之所在,在都城城郊设皇家猎场,称为“飞放泊”。此时,水草丰美的南海子一带成为离元大都最近的猎场,被称作“下马飞放泊”,内筑晾鹰台(呼鹰台),并将鹰坊这一专门饲养猎鹰的正三品衙署设在晾鹰台附近。至大元年(1308)二月元武宗下令立鹰坊为“仁虞院”。“仁”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虞”是古代掌管山泽之官,取名仁虞院来管理下马飞放泊,可见元代下马飞放泊虽无苑囿之名,已有苑囿之实。元代,官署的修建、帝王的狩猎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南海子的人文开发,此时为史料记载的建筑还有海中殿、幄殿、七十二桥等。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虽未在官方文件中申明国号出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但这在文人熟读《易经》的社会应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表达了大明对大元是中华正朔的认同与继承。作为中原农耕文化的代表,明代积极复兴传统文化,正如上林苑海子碑记中所述:“苑囿之设制乎,曰古制也,盖先王蒐苗狝狩四时示武于天下……盖以重王命利群黎也。”与前朝游牧民族四时迁徙、从不固守一地不同,农耕民族更加依赖土地。因此,明朝统治者下令对下马飞放泊进行扩建,建筑垣墙,明确范围,改称“南海子”,由上林苑监管辖,设海户种植粮食蔬果,豢养牲畜,成为京城重要的物质储备基地。除修建围墙,开辟苑门之外,明代南海子内辟二十四园,设四提督署,并修有庑殿行宫等建筑。
明成祖迁都北京初期,前朝蒙古贵族残余势力还未完全肃清,京城一带依旧居住着许多蒙古族后裔。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在苑囿功能上,南海子延续了辽、金、元时期皇家猎场的功能,成为明代皇帝行围演武的重要场所。明代商喜的《明宣宗行乐图》描绘了宣德皇帝出行游猎的场面,出宫苑入林郊,丘壑纵横、溪水潺潺、树茂花繁、飞鸟走兽成双结对的场景就是明初南海子景致的真实写照。经过明代历朝建设,南海子已成为颇具规模的皇家御苑(图3)。然而,由于海户制度的不完善,明后期南海子日渐荒废,一派“荒莽阻湿,宫馆不治”的衰败景象。

图3 明代的南海子
资料来源: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清朝入关后,全面继承明代的宫殿、园林遗产,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皇帝曾有谕:“思物力之限,罔敢过用,轸民生之疾苦,不忍重劳。”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渔猎民族,起源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行围骑射是满族人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但此时朝廷尚无财力新修皇家猎场以供行围。于是,顺治帝将明代凋敝的南海子重加修葺,作为猎苑,改称“南苑”:“仰惟开国以来,若南苑则自世祖肇加修葺,用备蒐狩。”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渔猎民族,起源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行围骑射是满族人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但此时朝廷尚无财力新修皇家猎场以供行围。于是,顺治帝将明代凋敝的南海子重加修葺,作为猎苑,改称“南苑”:“仰惟开国以来,若南苑则自世祖肇加修葺,用备蒐狩。”
 并在此长期驻跸、理政,使之成为与紫禁城互补的政务中心。历经康乾两朝,南海子全面复兴了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大型皇家苑囿的历史功能,在清代北京的城市生态、政治、文化、宗教、经济、军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在此长期驻跸、理政,使之成为与紫禁城互补的政务中心。历经康乾两朝,南海子全面复兴了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大型皇家苑囿的历史功能,在清代北京的城市生态、政治、文化、宗教、经济、军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城市生态角度看,作为京南重要的水源地,南海子水利工程承担了养源、清流、济运、蓄洪、匀沙的综合功能。乾隆时期通过对南海子内主要河流上下游泉脉、水道的梳理、调节,使凉水河(图4)与通惠河共同构成了京城漕运的“双保险”,保证了京城生命线——京杭大运河的通畅无阻,南海子是当之无愧的北京运河文化带上的明珠。

图4 凤泉凉水河图(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在政治与宗教信仰上,面对自明代以来日益兴盛的岳飞信仰,顺治皇帝采取存而不论、回避矛盾的策略,加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在全国推行关公信仰,弱化了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舆论。南海子在清代曾出现过6座关帝庙,它们是清代化解民族矛盾的政治智慧的见证。事实上,南海子内共有寺庙22座,堪称北京城南郊的宗教信仰中心。其中,南苑德寿寺的营建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见证。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首次入京朝觐,顺治皇帝于南苑设宴接见,并修德寿寺以表纪念。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自西藏赴京祝禧,于德寿寺拜谒乾隆皇帝。藏族宗教领袖的朝觐使藏族文化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德寿寺正是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
礼乐复合是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生活模式,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宫殿、坛庙是礼的场所,等级森严的礼制在传统建筑上体现为金碧辉煌、格局严整,屋顶多为庑殿顶和歇山顶;园林、行宫是乐的场所,乐旨在陶冶情操,因而园林建筑一般为白墙灰瓦,简洁朴素,屋顶多为硬山顶和悬山顶。目前,关于新旧衙门、南红门行宫的复原研究,受部分南海子总体性舆图中写意性建筑形式(图5)的影响,误以为其主要殿堂为歇山顶和庑殿顶。乾隆二年(1737)修缮档案中载:“南海子各行宫各主殿均为硬山顶”,其空间氛围与圆明园四十景之洞天深处(图6)相仿,这也比较符合中国传统园林的高尚文雅之风采。

图5 晚清《南苑全图》中的新宫(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图6 圆明园四十景之洞天深处(《圆明园四十景》)
《孟子》曾记载:齐宣王苑囿方四十里,因独享,则大;文王苑囿方七十里,与民同乐,则小。这种以民为本、与民共享的理念,直接影响了清代南海子的营建。“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南苑内设海户地,海户每人分田28亩进行垦荒耕种。为顺应农时,方便海户耕作出入,康熙皇帝曾下旨在苑墙上开洞14处,随开随堵。乾隆朝苑墙包砖时,会将这些必要的临时洞口改为角门。这些角门正是“人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体现,也是流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精神。

综上,南海子在持续的经营过程中,多民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与天地参”的生态观、“礼乐复合”的社会观、“多元一体”的民族观、“以民为本”的民生观,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核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