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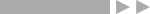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毕罗学着看账本、研究菜单、背菜谱,每天四时春和老宅两头跑,虽然饭菜都有专人负责,但人很快就瘦了一圈。
因为刚回四时春的第一天她就落了赵经理的面子,接下来有关饭店的全部营销策略和广告方案,都径直送到毕罗这里,好在毕罗在F国攻读学位时,为了锻炼自己,没少接大大小小的广告策划案,做起这种事倒是信手拈来。
清明主题的广告牌第二天就换了上去,清新的薄荷绿底色,古朴典雅的设计图案和一目了然的套餐介绍,刚摆在门口就吸引了许多老街坊的注意。对此朱大年是赞不绝口,赵经理原本想找碴儿,可一听后厨的单子短短两天数量又翻了两番,就知道这位毕家大小姐已经赢了先手。
凡是和艺术设计沾边的东西,毕罗动起手来都改得飞快。很快,全新的菜谱设计和整个4月份的营销方案也新鲜出炉。这些事情上,朱大年是个外行,毕克芳却越看越满意,几天下来,连精神头都好了不少。先生说好的事情,朱大年一向是最坚定的拥趸,又有朱时春这个能说会道的家伙在后厨大肆宣扬,很快,对于毕罗的种种赞语便在四时春内外越传越广。
谁都不知道,毕罗也有自己的烦恼。除了做设计、想点子这一套是她的擅长,她还有更大的不擅长。背菜谱、设计菜单,初看有趣,可越学越难,她在F国时虽然也经常自己开伙,但自己做菜只为贪嘴,要为整个饭店设计这些东西,背后可有着大学问。就拿一个清明饭的套餐来说,既要荤素搭配又要结合营养,四时春的许多菜还有着不一般的典故,不能胡乱填塞。一想到接下来自己还要进厨房掌勺,毕罗愁得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好在还有画画聊以慰藉。
睡不着,又静不下心,毕罗就画画。她先将四时春里这些熟面孔画了一遍,可画着画着,手里的笔不听使唤,就画成了心里最熟悉也最遥远的那个身影。俊朗斯文的面部轮廓,垂落前额的一缕发丝,再然后是眉毛、鼻梁、嘴巴,笑纹……最后才是那双眼。不知不觉,这样的画就叠成一沓,放在枕边,仿佛那个人真的陪在她身边,不知不觉也就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是毕克芳例行做检查的日子。毕克芳并不需要毕罗陪伴,只喊了朱大年一起,临走前,叮嘱毕罗在家好好钻研菜谱,务必在这两天内,把四时春4月份的菜单定下来。
这天本是个寻常的春日上午,院子里的鸟儿啾啁叫着,从窗口依稀能看到院墙外桃花纷飞,毕罗有一笔没一笔地画着,面前放着那本厚厚的《四时春录》。头一天晚上睡得太迟,这会儿她怎么都提不起精神看菜谱……手机传来“叮咚”一声响,毕罗一手撑着额际,另一手滑开手机屏幕,是一条微信消息。
“大小姐,微信求通过啊啊啊啊!”又是那个唐律发来的微信验证消息。
毕罗将手机一扔,懒得再看。
可没过几秒钟,手机又锲而不舍地响起来。她本以为是唐律打来的电话,不想去接,可目光一瞥,发现屏幕上显示的手机号是有名字的。她拿过手机,接通:“齐师兄,早。”
这些天她几乎每天都要去四时春点卯,也把大家伙儿的手机号和微信加了个遍。不过彼此联络都是工作上的事比较多,但这个时间段给自己打电话,而且是齐若飞,还是头一回。
电话那端传来齐若飞有点无措的声音:“大小姐……有个人,说想见你。”
“见我?谁?”毕罗在平城的朋友屈指可数,她实在想不出,除了那个讨人厌的唐律,还有谁会这么一大早地扰人清静。
“他说他姓沈,是你在国外留学时的同学。”
毕罗手里的铅笔“叮”的一声落在纸面上,她听到自己心脏“扑通扑通”越跳越急的声音:“他是不是叫沈临风?”
“嗯。”齐若飞问,“大小姐,他真是你的朋友吗?”
“是,是。”毕罗站起身,膝盖不小心磕到书桌下沿,可她丝毫没感觉到疼,“你说他跟你在一起?怎么会……”
手机那端传来两声短促的电流声,紧接着就是一道含笑的男声:“毕罗,想不到你也回平城了。有没有空,一块儿吃个饭?”
“这么早?”毕罗接起电话前才看过手表,早上七点半,这个时候相约,难道是吃早餐,“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嗯,想不到你也在平城啊。毕业典礼我没有去参加,都没能跟大家说一声……”
“这么巧,我也没参加毕业典礼。”沈临风的声音沉沉含着笑,“刚才跟朋友一起吃早餐,听人说起你,才知道你也在平城。刚好我们今天要去郊区的一个餐馆吃饭,一起吧?”
毕罗脑子一片空白,她知道自己此时说出的每一句话大概都很傻,可还是控制不住那种争着抢着从每个细胞渗透出的喜悦:“好啊!那个,沈……临风,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你认识齐师兄?”
“朋友的朋友。”沈临风听起来一直在笑,仿佛心情愉悦极了,“说起来也是巧。等见面聊。你家在哪,我去接你?”
“那个,其实我自己过去……”
“地址?”沈临风身边似乎还有人,他与对方低声交谈了两句什么,又说,“一块儿吃个饭,都不是外人,顺便介绍我另外两个朋友给你认识。”
“嗯……”毕罗轻声报出一个地址,是家门口外的一条主干道,“从金台路拐过来后有个小报刊亭,我在那等你。”
接下来的一切仿佛都在梦中。毕罗甚至都不记得自己怎么下的楼,锁的门,但还记得给自己化了个清爽的淡妆,又换上手头最漂亮的一身衣服,英伦风的连衣裙和一双短靴,这个季节不穿外套其实还有点冷,可她此时心里暖烘烘的,哪还感觉得到半分凉意。
临出门前,她看到枕头边放的那一沓画稿,略一犹豫,将整沓画稿收入怀中,又放进随身的包里。
在报刊亭旁等了约莫二十分钟,她看到一辆黑色辉腾朝自己驶了过来。她向前走了几步,隔着玻璃,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连忙踮起脚挥挥手。
对方似乎也看到了她,放慢车速的同时摇下车窗,对她喊:“阿罗,快上车,这边不让停车。”
几乎车子停下的一瞬间,副驾驶的车门就朝她打开,毕罗才坐上车,车门还没关妥,车子再次行驶起来。沈临风边掉转车头边说:“不好意思啊,一见面就让你跑。”
毕罗摇了摇头:“是我选的地方不合适。”她自己不会开车,许久没在国内生活,平时也没怎么留意什么路段不能停车。她看向空荡荡的车子后座:“你的朋友呢?”
沈临风勾着唇角笑:“咱们俩也有一阵子没见了,你一见面就问我的朋友,可真让人伤心。”
毕罗后知后觉,紧跟着又想起临上车前他喊的那句“阿罗”,这个称呼其实说不上特殊,要好的朋友都这么喊她,不知怎么的,一模一样的两个字,从沈临风的嘴巴里说出来,就显得格外动人心弦。
若是容茵在这,肯定又要笑话她花痴了。
毕罗偷偷瞄了一眼沈临风的侧脸,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也在看她,她才感觉有点降温的脸颊顿时又烧起来了。
沈临风说:“是不是有点热?刚刚害你跑得急了,给你开一会儿空调吧。”话音刚落,他的目光落在只被裙子遮住一多半的腿上,微微一滞,轻咳了声,“那个,我还是给你开会儿窗吧。”
毕罗连忙将腿往自己那边收,又将随身的包包放在大腿上,饶是如此,仍然感觉自己脸红得要冒烟了。
这件裙子从前她也穿过的,其实裙边并不太短,站立的时候是非常合适的膝上五公分,是她坐下来的动作太匆忙了,上车后又忘记整理裙摆,才显得有点暴露……毕罗越想越懊恼,这样会不会被他看轻,觉得自己是那种轻浮的女孩子……
沈临风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今天才听朋友说起,你是毕克芳的孙女儿?”
毕罗“嗯”了一声:“你的朋友,认识齐师兄?”
“算是吧。”沈临风说,“这么说你这次急着回国,就是为了继承四时春?”
毕罗不禁苦笑:“想不到连你都听说了这件事。”
“我怎么不能听说?”沈临风也笑了,“是你太过自谦。同学五年,都没听你说起过家里的情况。四时春在咱们平城也是响当当的老字号啊,要是上学时让咱们那些同学知道,肯定要撺掇你回国后请客。”
毕罗赧然一笑:“我也不是故意不说的……”她原以为以毕克芳的身体,加上如今四时春的发展,自己有可能不用继承这份产业,可以安安心心做自己设计师的工作,每天与纸笔打交道,才是她此前一直向往的生活。
“知道,你是低调。”沈临风说,“我听说现在四时春上下都管你叫大小姐,看来我也得入乡随俗啊。怎么样大小姐,即将接任四时春的感觉如何?是不是痛并快乐着?”
毕罗抬起眼,刚好遇上红灯,车子缓缓停下来,沈临风也正看着她,还伸手在她眼角飞快抚了一下:“黑眼圈都出来了,看来你这些天过得很辛苦。”
毕罗心里又酸又甜,她见沈临风正似笑非笑看着自己,忍不住别开视线:“你呢?听说你回来也是继承家族企业?”
沈临风回答得很坦然:“是啊。有很多东西都不熟悉,正跟我爸学着怎么上手。继承家业这种事,说起来好听,只有真正去做的那个人知道有多辛苦。”说着,他叹了口气,“不过我将来总要结婚生子的,早点闯出自己的事业,对父母对未来的妻儿都有交代。”
毕罗咬了咬唇,忍不住轻声问:“那个……安娜跟你一起回国了吗?”
“怎么可能?”沈临风一摊手,“我跟她,就像中餐和法餐,都很美味,也都能体味对方的好,但不可能真正在一块儿。”他摇了摇头,“刚在一起没多久我们就有了约定,只谈恋爱,不讲婚姻。”他扭过头,朝毕罗一笑,“说起来可能要被你唾弃了,回国前我跟安娜就已经分手了。”
毕罗轻轻摇头,什么话都说不出。这件事她回国前就已经听说了,否则也不会心心念念着要在毕业典礼上正式跟他告白……可一样的事亲耳听沈临风本人再讲一遍,又别有一番滋味。
曾经她和沈临风也走得很近过,尤其有一个学期,他们两个一起做小组作业,那可以说是他们两个真正对彼此熟知和了解的半年。本来她觉得就那样慢慢发展下去也很好,谁知道半路杀出个安娜,和沈临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好上了,听说两个人是在一个派对上认识的,当晚两人一见钟情,第二天就公开地出双入对了。
毕罗心里那点可怜的小火苗也在同时化为灰烬。
多少次,见到沈临风和安娜在一起说笑、约会、公开亲吻,她都劝自己,沈临风已经是有女朋友的人,他们未来甚至还有可能会结婚。这样在心里偷偷喜欢别人男朋友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可每当亲眼见到或听说他们俩吵架闹分手的消息,她心里那点已经熄灭成灰的小心思,又仿佛有隐隐复活的趋势……
是不是每个人都曾这样偷偷喜欢过一个人,藏在心间,掩于唇齿,是每晚睡前照在床头的白月光,是悄悄埋葬在青春岁月的不可言说。毕罗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会像她这样,偷偷喜欢着一个求而不得的人,谁都不敢说,更不敢主动去争取,唯一一次鼓起勇气,是在得知他与安娜分手的消息后,准备在毕业典礼上对他告白……却接到了朱大年打来的越洋电话。
世事无常,在F国读书时,谁都想不到临近毕业,自己的人生会铺开怎样绚丽的篇章,自然也更不会想到,会在朝夕之间发生怎样的变故。事故与巧合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往往让人目不暇接,只能被动去面对和接受……毕罗忍不住攥紧了背包的带子,不知道待会儿是否还有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她已经等得够久了,不想再平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沈……”
“阿罗……”
两个人几乎同时开口,沈临风不由得一笑:“你先说。”又说,“还有,阿罗,大家都是同学,你就叫我临风吧。”
毕罗点了点头,这两个字其实她已经在心里无声念了千百遍,可真的吐出口,仍因为紧张显得有点磕绊:“临风……咱们这是去哪?”
“噢,就在东郊一个新开的餐馆,地道的中餐,还挺有特色的。”他别有深意地看了阿罗一眼,“至于味道,你是行家,到了那一切你说了算。”
毕罗摇了摇头:“没有,我其实……”她想辩解,可看到沈临风望着自己的目光,又不知道该从哪说起。
毕业之后,他们两个的身份都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身处异乡努力融入大环境的留学生,而是各自都有了不得不遵行的轨道的成年人。尤其让她惊讶的是,看沈临风的样子,也是要在平城定居的:“我记得,你家乡是沪城?”
“就是那边的。”沈临风说,“不过家里的生意主要在平城这边。除了逢年过节去看看亲戚,也没什么时间回去沪城。”
大概也看出毕罗有些拘谨,沈临风故意讲了几个回国后跟朋友聚会的段子,逗得毕罗也露出笑颜。一说起话,路程也不觉得长。很快就到了他说的那家餐馆。他们来得早,到餐馆才九点来钟的光景,并不是吃饭的时间。沈临风的另外两个朋友也还没有到。两个人坐在雅间里,沈临风起身给毕罗倒了杯茶,正要说话,突然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掏出手机看了眼,神色微微一变:“家里的事,我接个电话。”
毕罗连忙让他请便,哪知道沈临风前脚走出房间,她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看到是朱大年的号码,毕罗先松了一口气,哪知道接起电话,听筒那边传来的却是毕克芳的声音:“阿罗,你在哪里?”
毕罗想起自己出门时太匆忙,连张字条都忘了留,不禁有点支吾:“我,我同学……”
毕克芳的声音听来异常严厉冷肃:“无论你现在在哪,都立刻给我回来!”
“可是,我才刚到……”
“家里进了贼,你的房间被搜得乱七八糟。”毕克芳说,“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有没有锁门?”
毕罗大脑一片空白:“门?我锁门了的……”可紧接着,她想起自己走前稀里糊涂的,压根忘记将那本《四时春录》放回柜子里收好。
书就放在临窗的桌子上。
“大年已经报警了,你房间里有没有放什么值钱的东西?”毕克芳问,“阿罗,你把菜谱放在哪里了?”
“我……”毕罗多余一个字都吐不出。
电话那端也是一片沉默,最后毕克芳说:“你还是先回来吧。”
沈临风推门进来时,刚好和拎着包往外冲的毕罗撞在一起。他见毕罗眼圈通红,顿时愣住:“怎么了阿罗?”
毕罗紧紧咬着牙:“对不起,我家里出了点事,不能跟你一块儿吃饭了。”
沈临风“啊”了一声,但他向来风度极佳,立刻反应过来:“那,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你约了朋友。”毕罗摇摇头,“不好意思,今天要放你们鸽子了,你们吃好。”
沈临风见她说完就不管不顾往外冲的架势,连忙将人拦住:“这个地方压根也不好打车啊。”沈临风有点无奈,拍了拍毕罗的肩膀,“而且我刚才进房间就是想跟你说,咱们两个被放鸽子了,我那俩朋友今天都来不了。看来我今天选的这个日子不大好。”
毕罗脑子里都是自己出门前的每一个举动,想到自己还特意将那沓画稿放在包里,却将菜谱那么随意摊开落在桌上,顿时恨不得抽自己一顿耳光。她几乎没去留意听沈临风说什么:“那我……我现在需要回去。我得回家。”
沈临风也看出她急坏了,连忙扶着人肩膀带她往外走:“我送你回家。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有出租车我也不放心你一个人这么回去。”
车子开出去好一段距离,沈临风见毕罗仍垂着头一语不发,只死死咬着自己手指的关节。趁着等红灯的时候,轻轻将她的手扳开:“阿罗,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如果信赖我,讲给我听听,好不好?”话音刚落,他看到毕罗已经将自己的手指咬出了血,也是一愣,“阿罗?”
毕罗垂着头,一滴泪从眼中滑落,刚好掉在已经被咬得血肉模糊的食指关节上,可她根本感觉不到疼。
她以为得知自己不能再画画的时候,心里的滋味称得上五味杂陈;不能回F国参加毕业典礼,也不能再见到沈临风向他告白时,那种感觉称得上心急如焚;可这些都比不上从朱大年口中听到毕克芳罹患绝症命不久矣时的茫然和震撼。大概当许多件倒霉事一块儿发生时,人的关注点总在最痛最可怕的那件事上,其他的什么自己给自己找一些借口,都被匆匆掩过。
可直到这个时候,她才知道,什么叫作天塌地陷。
明知道毕克芳没剩下多少日子,也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的是什么,却在这个时候,亲手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什么叫万死难辞其咎,此时此刻,毕罗亲身体会了。
那种恨不得将自己掐死的懊悔,那种恨不得全世界的一切瞬间停滞,让时间倒流的渴盼,那种根本不敢想象回家后要怎么面对所有人的恐惧,所有情绪和观感汇聚在一起,会让人恨不得直接杀死自己……毕罗深吸了一口气,说话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没有哭,可几乎每隔几个字,都会不小心咬到自己的唇舌,如果这时有人在旁边看着,就会发现,她整个人都止不住在发抖:“我把家里最重要的东西弄丢了,我……我外公……怎么办?”
其实前面的绿灯早就亮了,可沈临风一看她这个样子,根本没办法不管她,只能一踩油门紧急开出去一段距离,将车子在路边停妥,侧过身来握住她的双手:“毕罗,你清醒一点,慢一点说,到底怎么了?”
毕罗抬起眼,那双眼不像想象中含满了泪水,却比沈临风见过的所有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孩子都让人心里跟着一疼。毕罗一双眼睛都是红的,就像熬了三天三夜没睡过觉的人,目光虽然望着他,那里面却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有那么一瞬间,沈临风发现自己是哑的。然后他听见毕罗说:“如果你犯错了,这个错误是无法弥补的,会害许多人……”
“那就用尽全力去弥补它,无论付出多少代价。”沈临风清了清嗓子,说,“毕罗,如果是你犯了错,那就坚强点,想一想,你现在能做什么。”
毕罗紧紧抿着唇,将牙根咬得发酸,眼睛里却一滴泪都没再落下。她点了点头,松开沈临风的手:“麻烦你送我回家。”
如果她觉得自己罪无可赦,那毕克芳和朱大年呢?还有更多眼下还不知道真相的四时春员工呢?
现在不是自责和懊悔的时候,这些情绪能杀了她,却不能帮上谁的忙。
现在是赎罪的时候。
沈临风本打算将毕罗送到家门口,可车子开到早上接她的那个路口,就听到毕罗开口喊“停车”。这一路他两手都是汗,就连后背都微微汗湿,听到毕罗喊“停车”,下意识地就踩了刹车。眼看人一溜烟跑没了影,他坐在车子里,手机铃声响了两遍才回过神:“喂?”
“发什么呆呢?办成这么大个事儿,你小子今天回家等着你老子跪下管你叫爸爸吧!”手机那端帮他牵线的哥们儿哈哈笑着。
沈临风却觉得莫名烦躁。对方也觉察他情绪不高:“怎么了?事成了还不高兴?”
沈临风将车子停得远了一些,扒拉了下头发:“潘子,我觉得这事儿……我可能会后悔。”
“给我个你会后悔的理由?”
沈临风皱着眉,他的模样说不上多俊俏,看起来却非常斯文,用哥儿几个平时总打趣他的原话就是,跟他老子给他取的名字一样,往哪儿一站都人模狗样的,特招女孩儿待见。可沈临风此时却顾不上像平时那样保持风度,他解开两颗扣子,有点烦躁地扒拉两下头发,摇下车窗然后点上一根烟:“我那同学,就是你们说那个毕家老头儿的孙女,我这一路都陪着她……”
电话那头,潘子吐出一个烟圈,嗤一声笑了:“沈临风,你这小子就是不地道。”
沈临风紧皱着眉不说话。
虽然隔着电话,看不见人,潘子还是跟人就在眼前似的,边说话边用捏着烟的手指点了点屏幕:“没你这样办事儿的。想要你老子公司那继承权,把你那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挤开,求着兄弟几个给你想辙、找人、套资源。”他说着,又狠狠吸了口烟,皱着眉放下手机,去挽自己衬衫的袖口,继续教训沈临风,“现在东西到手了,你这未来沈氏太子爷的位子坐牢了,你又跟我扯那毕家的丫头。她是死是活,你从前在意过吗?”
沈临风闭着眼长出一口气,身边没别人,跟潘子又是从小一块儿玩到大的发小,他也懒得去装:“你没看见她刚才那个样子,潘子。她那个样子,跟要疯了一样……”
隔着电话,沈临风都能听到潘子嗤的一声又乐了:“这个事儿,不是现在她发疯,就是未来你发疯,你自己和一个外人,让你选,让谁疯?”他捻灭一根烟,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点上,“不是我说你,沈临风,你啊!对着女人,怜香惜玉的心思太多。”
沈临风闭着眼问:“就没别的办法吗?”
潘子又吐出一个烟圈:“你要真看上人家,接下来就盯着点毕家的动向。他们家现在保老本儿的东西丢了,接下来保不齐还有大难。这事儿怎么说也算是因你而起,你要喜欢人家,就帮两把。说不定一来二去的,人家对你心怀感激,还真就跟你成事儿了。”说到这,潘子舔了舔嘴唇,“你不是说这毕家丫头之前也喜欢你吗?”
沈临风睁开眼:“潘子,别打她的主意。她跟那些女孩不一样。”
潘子吊儿郎当地连连点头:“不一样不一样!你沈大少爷什么时候看上的女人,都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沈临风听得有点烦,干脆把电话挂了。车子在路边停了好一会儿,抽掉了半包烟,沈临风才打着方向盘掉头离开。心里存着事儿,当然也就没留意到不远处的后头,有人黄雀在后地一路跟着他。
另一边,毕罗一进老宅的堂屋,对着坐在当中那个身影就跪下了。
朱大年不在,只有毕克芳一个人坐在当中,手里仍拄着拐杖,从毕罗一路走进来直到扑通一声跪下,他如同一尊雕像,连眉毛都没动过一下。
许久之后,毕克芳说:“你起来吧。”
毕罗一声不吭地跪着。
其实从小到大,毕家从来没这条规矩。毕克芳虽然对她严厉了点儿,也仅限于穿衣和交友,在其他方面,他对毕罗称得上宽容,更从没有让毕罗对谁下跪过。
“毕罗啊。”毕克芳长叹了一声,他的声音透着一丝哑,“我已经是一只脚踏进棺材的人。四时春也好,那本菜谱也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等我两眼一合,什么也跟我没关系了。”他看着毕罗,眼睛里没有一丝埋怨,只透出一种很深的悲悯,“可你今年才二十四岁,你弄丢了祖传的饭碗,四时春倒了,大年也好那些师傅也好,不用他们开口,业内有的是人上赶着高薪挖人,你怎么办?接下来还有那么多年,没有人陪在你身边再看着你,你想过自己要怎么过活吗?”
毕罗熬了一路,直到这一刻,眼泪才无声地掉下来。
可她不敢让自己掉更多的眼泪。她跪在那儿,紧紧抿着唇,直到确定自己开口不会透出一丝颤音儿,才开口:“菜谱丢了,责任全在我,但四时春不会倒。我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会努力,让四时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
毕克芳望着她,半晌才说:“诺言说出来容易,但要说到做到……”
“我一定会说到做到!”毕罗站起来,看向毕克芳,“从今天起,除了看账本、整理菜谱,我会跟您学着怎么下厨。我不会再怕苦怕累了,您再信我这一次!”
毕克芳看着她熬得红彤彤的一双眼,终于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