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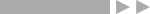
毕罗接到朱伯伯的电话,毕业证书都没来得及拿,便匆匆回国。
她回到平城时,正赶上一场春雨。
平城春天的雨向来下不太大。大城市都这样,一年到头城市上空都笼着霾,雨雪总下得不痛不痒,晴天的时候也不见蓝天,想看到蓝天,得靠大风吹。
这场春雨却让人措手不及,气象台都没预报,事先也不见有一丝风,便任性忘我地下了个痛快。毕罗从机场出来就赶上这场雨,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打到一辆车,赶到医院时,雨竟然还没停。
司机哼着小调,嘀咕了句:“这鬼天气!”没等毕罗将车门关妥,就踩了油门。车轱辘溅起的水刚好泼在毕罗烟灰色的风衣上。
毕罗顾不上骂人,拖着小号行李箱,马不停蹄地奔赴病房。
毕克芳的病房在同仁医院3号楼209。电梯上上下下,每次都挤满了人。毕罗拖着行李抢不过别人,只好将拉杆收回去,手提着行李箱爬上两层楼。走到病房门口时,她才喘匀这口气,霎时便被一种畏怯的情绪填满。若是按照老话,她此时的心情,大概叫作“近乡情怯”。可毕罗心里明白,她心里的为难和恐惧,不仅于此。
她不敢面对躺在病床上的那个老人。
病房里充塞着百合花的淡淡香气,毕罗害怕毕克芳,连带这些年也畏惧毕克芳喜爱的此种香气。她在F国留学时,路边花店常常摆出几束狐尾百合,概因这花花朵优雅、香气袭人,非常适宜招揽顾客。但每次毕罗见了,只会越发加快步伐。曾经有暗恋她的异国男生送她这花,卡片上写着优美的花体法文,内容既热忱又俗气:Laura,你的容貌就像这束百合,纯洁张扬,让我忍不住想拥你入怀……
毕罗看得头皮发麻,本是向来不喜得罪人的性格,也难得严酷一回,径直将花扔进公寓楼下的垃圾箱。
病房里充满了这个气味,毕罗心中紧张畏怯占了上风,一时有点怔住。她没认出躺在床上那个头发尽白的老人是毕克芳。
毕克芳正醒着,手里拿一本枣红色的册子,抬起眼来刚好看到她,向来严肃的面庞上透出一丝笑,朝她招了招手,示意她进去。
毕罗回神,硬是忘记行李箱的拉杆早被她在爬上楼梯后就抽了出来,拎着十五斤重的箱子一路走到病床边。她站在床边,一手拎箱子,另一手捏着自己因为雨水和汗湿摘掉的帽子,脸色微红,眼神懵懂。在毕克芳眼里,她和十五年前刚被人送到他面前时一模一样。
毕克芳在心里叹气,还是个孩子。
朱大年的到来打破二人的僵局。他一进门就先抹一把额头,又抖了抖伞上的雨水,蒲扇般的大手一拍大腿,将伞随便一扔,就朝毕罗冲过来。
毕罗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朱大年拢住肩膀,朱大年不住地说:“大了!漂亮了!我们阿罗是个漂亮的大姑娘了!”
毕罗扯出一抹有些僵硬的笑:“朱伯伯。”
不难看出朱大年是真的很激动,不仅脸膛是红的,眼圈也是红的,握着毕罗的肩膀不住地说:“这下四时春有指望了!大小姐回来了!四时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最后还是毕克芳咳了声,说了句:“大年。她这趟回来就不走了,你急什么。”
毕罗浑身一僵。目光不由得看向毕克芳。站得近些看,毕克芳不仅头发全白了,脸色也青中透白,和她印象里向来黑着脸膛的模样有些对不上号。若是不认识他的人见了,大多会以为这是个和蔼的老年人。可毕罗清楚地知道,这人严厉起来的面孔有多可怕。
朱大年总算松开了手,还有点不好意思地将手放在身后搓了搓。他注意到大小姐肩膀的布料被他的手沾湿了个五指印,不知想起了什么,竟然露出有点紧张的神情,慌乱中还朝毕克芳看了一眼。
毕克芳放下手上的册子:“大年,帮忙给阿罗搬把椅子。”
朱大年“哎”了一声,折身去门外找凳子。平时这间病房,有人来,但没人敢在毕克芳面前坐,也没人有这个资格,所以都是不放凳子的。
朱大年回来的时候,毕罗看了眼他手上,还真跟她预料的一样。毕克芳发话说让搬一张椅子,他真就老实地只搬了一张,然后就特别自然地站在床脚的位置,等待毕克芳的下一个指令。
这种气氛让毕罗再次紧张起来,坐在椅子上都觉得浑身冒刺。
毕克芳看着她,徐徐开口:“阿罗,这次回来,就别再回去了。”
毕罗猛地抬起头,可看进毕克芳的眼睛里,她就知道,这件事在他这里,没有转圜的余地。
毕罗垂下眼,双手交握放在膝上,腰杆挺得笔直,是非常端正的坐姿,可在场的三个人都知道,她姿态再端正,也没有半分底气:“可我毕业证还没有取。”
毕克芳说:“让学校寄回来。”
毕罗嗫嚅:“还有毕业典礼……”
朱大年在后面焦急得不得了,忍不住喊了声:“大小姐!”
毕克芳看着毕罗白净的面孔,她从进房间起就没怎么与毕克芳有过眼神交流,话还是那么少,神色是畏惧的、胆怯的,还有那么一点小女孩子的倔强……他叹了口气,生平第一次软和了口吻说了句话:“毕罗。”
他没叫她“阿罗”,也没像当着四时春里其他人的面时叫她“大小姐”“大姑娘”,而是叫她的全名,毕罗。
毕罗忍不住抬起头,就听毕克芳说:“我只有半年好活了。这半年,你必须把四时春撑起来。”
毕罗觉得自己可能幻听了。
直到跟在朱大年身后一块儿下了楼,又坐上车,她都没回过神。
毕克芳在她心里,一直是个强大到无法打败的形象。她畏惧他、躲避他,却也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偷偷崇拜他。这不奇怪,人对于强者,总是怀有某种不可动摇的崇拜的。无论是喜欢还是厌恶,都与崇拜这种情绪不相矛盾。可这个强势了一辈子的人突然有一天当着她的面说,他要死了。这种感觉既怪异又荒谬,好像她突然踏错一步,走进一场唱得荒腔走板的老戏里,所有人都那么认真,可她总觉得一切都是假的。
朱大年开的车子是辆车龄超二奔三的悍马。二十多年前在平城,开得上悍马的,都是一方顽主。朱大年这辆车开出去,不知得了多少老少爷们儿的口哨和口水,趁他不注意跑过来摸两把的半大小子也有的是。可这车放在如今的平城,不新鲜了。车身庞大、笨重,如同一位穿越到未来时空的超级英雄,看着是帅,却透着那么点落伍的二。
好在朱大年车技稳当,对车子也爱惜,大车嘛,坐着肯定舒服。
毕罗终于有点从医院的那种氛围中抽回神,一扭头,就对上朱大年一脸犹豫纠结忧伤悲痛的神情。
“……”毕罗在面对这位朱伯伯时,还是觉得挺亲切的。她有时也觉得奇怪,明明她和毕克芳才是有血缘承继关系的亲人,可面对毕克芳,她时常涌起各式各样的负面情绪,从未感觉到一丝亲近。朱大年可以说是看着她从小长到大的,她妈妈还在世时,就常把她放到朱伯伯家里玩,随着年龄增长,她明知道自己跟朱家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可每每看到朱大年,就打心眼里觉得亲切。
毕罗也觉得自己有点白眼狼,可人的情绪并不是能由自己控制的。
朱伯伯忍了又忍,也没忍住,他就这脾气,外人面前还能端着三分深沉,一见到毕家的人,就立刻成了一箱一箱倒豆子的竹筒,想到什么说什么,知道什么说什么,要他憋着,跟要他的命差不多。
于是朱伯伯就忍不住跟毕罗倒起了豆子:“大小姐,不是我老朱说,您这去国外读书,一走就是五年!五年,一次都没回来过!您说您也是先生看着长起来的,先生脾气是不那么和善,小时候对您也严厉了点儿,可那都是为了您好啊!您说您还真这么大气性,过年都不回来一趟!就连我家那小子,出国半年就忍不住往家蹿,您是真一点都不想家啊!”他看着毕罗白净玲珑的侧脸,看一眼,问一句,“真一点都不想?
“不想先生?
“不想家里?
“也不想我老朱和朱婶?”
毕罗满腔踟蹰愁绪,都被他这一句接一句地给冲散了,逗乐了:“朱伯伯……”
朱大年“哎”了一声:“大小姐!您这心真狠啊!您不知道这五年,您可想死老朱和你朱婶了!”
毕罗“扑哧”一声,又被他逗乐了。
她自小就发现朱大年特别有意思,毕克芳为人不苟言笑,喊四时春里其他人,都是喊个姓氏,诸如小张、小王、大李子等,简便,直观,好记。可唯独喊朱大年,是叫他名字后面的两个字。朱大年从十六七岁起就跟在毕克芳身旁打下手,被这么喊习惯了,竟也从未多想,随着年龄增长,还自己称呼上自己“老朱”了。
可听在别人耳朵里,总要想起四大名著中某部书里的那位“老猪”。
朱大年浑然不知毕罗的脑补,继续苦口婆心:“大小姐,您不要总觉得先生凶,其实先生心里是很疼您的……哎,这要我怎么说啊……”
朱大年虽是个憋不住话的性格,却并不是个舌灿莲花的主儿,要不也不会在毕罗心中落个“敦厚朴实”的印象。她默默听着朱大年将自己小时候的事翻过来调过去讲了个囫囵,其间并不插话。
别的不说,至少有一点朱大年说得没错。
若没有毕克芳,她早就饿死在外头了。
她妈妈毕舜华当年为了跟那个男人结婚,和毕克芳是公开断绝了父女关系的,毕舜华的母亲死得早,是毕克芳一个人将她拉扯长大。为了个男人和自小将自己养育成人的父亲断绝关系,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毕舜华都没脸再回去。
毕舜华眼光不太好。
那男人弄大她的肚子,又不见毕家给予任何经济支援,便跑了。毕舜华生活落魄,每天去玩具厂做工,一天要做满十六个小时。毕罗到上幼儿园的年纪前,常被她厚脸皮地塞到朱大年家里。那时朱大年还没结婚。
后来朱大年娶了朱婶,生了儿子,毕罗也顺利上了幼儿园。可毕舜华仍旧没时间去接她放学。这摊子事儿就又交托到了朱大年身上,一接就是六年。毕罗三岁上幼儿园,六岁半上小学,直到小学三年级的某一天,毕舜华出车祸过世,毕罗才第一次见到自己在这世上的另外一个亲人——毕克芳。
毕罗没有爸爸,所以随了母姓。长大之后她常常想,母亲给她取这个名字,沿用这个姓氏,大概一早就为她想好了出路。她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被一个男人欺骗玩弄拖累终生,也不会有好的未来,所以早就想好,等毕罗长到一定年纪,就送她回姥爷家里。
毕舜华经常把她送到朱大年家里,未尝没有试探毕克芳的意思。
朱大年不是个能瞒住事的人,有时为了接毕罗放学,还要跟毕克芳请个四十分钟的假,可毕克芳从来没有反对。这不就是默许的意思了吗?或者也是父女俩冰释前嫌的铺垫了。
可毕舜华没有料到的是,自己的寿命那样短,她的离世又是那样突兀。
所有人包括毕舜华自己都没有准备,所以毕罗被送到毕克芳家里时,所有人尤其这两位当事人,都要慢慢适应。
顺着朱大年的话头,毕罗脑海中浮起了许多儿时的回忆。朱大年却将她的沉默当作认可,越发起劲儿地煽动她要谅解毕克芳的脾气和作风。
直到车子在老宅的院子口停下来,毕罗一抬头看向外面,发现天不知什么时候放晴了。
这场春雨下得又急又大,竟然难得将平城的天空洗出了一片湛蓝。空气里飘浮着泥土和草木清香,毕罗下了车,跟在朱大年后头进了院儿,轻声说了句:“我可以留在平城,帮着把四时春撑起来。”
朱大年惊喜地扭头,毕罗轻声却执着地接下去道:“可我下周必须回一趟F国,我要去参加毕业典礼。”
朱大年蹙眉,犹豫着不敢点头。
毕罗说:“我只回去三天。”她用目光瞄了眼朱大年手里的行李箱,“况且我这次回来得匆忙,许多东西都没带回来。就这么扔在那太浪费。”
朱大年向来俭省,这次却没有轻易地点头表示同意。他只是沉默地将行李箱提进毕罗从前住的阁楼里,又“噔噔噔”地走下楼,进厨房忙活起来。
傍晚的天空映照出斑斓云霞,毕罗坐在院子里,望着四周。她五年没回来,这里却仿佛是被时间凝固的世外之所,与从前没有半分不同。
门口种着两棵枣树,往里走,是蔷薇、月季和芍药花,房子是个二层小阁楼,靠近阁楼的地方种着几丛忍冬并一棵柿子树,后院连着几畦菜地,打了水井,都供自家用的。这个时节,枣树还未抽芽,院子里种的花也都不到开花的时节,院墙外的桃花和杏花却长得很高,飘进粉白的花瓣来,落了一地。毕罗小时候最喜欢蹲在花瓣里面玩,那样的情景没有小女孩会不喜欢,穿一条裙子翩翩起舞,谁都觉得自己是不可一世的小公主。
九岁后的毕罗没有裙子穿了。毕克芳待她非常严苛,夏天也不许她穿裙子、扎辫子,总将她打扮得像个小老头儿,短头发、长袖长裤,身上的衣服永远只有黑、白、灰三色。
毕舜华没有死的时候,毕罗是穿过裙子的。毕舜华虽然穷,但总将她打扮得像个小公主,蓬蓬裙、花瓣裙、小旗袍还有花苞头,走到哪都是引人注目的娇娇公主。
这样强烈反差的生活经历对一个刚满九岁的孩子而言是困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毕罗入睡前独自躺在木头大床上,对着床里侧贴着的老式墙纸,无声掉泪。
她知道毕克芳不喜欢她的母亲,厌恨她的父亲,便由此推断,毕克芳是在她身上施展报复。
后来长大了,这样的念头随着成长渐渐淡了,可她对毕克芳的那种恐惧和排斥始终挥之不去,哪怕如今她已经二十四岁,即将大学毕业,哪怕毕克芳已垂垂老矣,半年后就要离世,她依旧没办法将这种感觉从自己心里拔除。
小院儿很美,充斥着童年的种种小小美好,也遍布着那些不堪的、畏缩的、茫然的童年回忆。
朱大年端着晚饭走过来时,毕罗本是背对着他的。听到熟悉的脚步声,鼻尖一抽,便闻到一股淡淡甜香。毕罗一笑,说:“朱伯伯,你做了桃花粥。”
朱大年声如洪钟,一开口就将整个小院儿都渲染得热闹了几分:“大小姐的鼻子还是那么灵!就是桃花粥!”他走到近前,将托盘里的几样食物一一放下。
毕罗坐了十个小时的飞机,腹内早就空空如也,可偏没什么胃口。一回到家里,别的不说,光闻到这香气便觉得被治愈了。中国人哪,中国胃,走哪都忘不掉这一碗粥的味道。
朱大年自小跟在毕克芳身边几十年,做起正经大菜,跟毕克芳本人的手艺相比还有一段差距,但也要看是什么人尝,一般人尝不出。许多家常小菜,尤其是毕罗自小常吃的那些,与毕克芳做的几无二致。
桃花粥这道粥品算是个古方儿。清朝时有个人叫孔尚任,写的《桃花扇》里,曾写过这么两句:“三月三刘郎到了,携手儿妆楼,桃花粥吃个饱。”可见桃花粥这道菜肴,是讲究时令的。过了春季桃花开的这个时节,哪怕有干花花瓣,怎么做都不是那个鲜味儿了。
毕家的桃花粥是依照四时春祖传的秘方儿做的,最讲究个“鲜”字,取新摘的桃花,用井水浸泡半小时,放在粳米粥里头小火慢熬。渐渐将米熬得浓稠,熬出一层厚厚的米油,盛一碗出来,香稠的米粥里点缀着星星样的粉色花瓣,就是一碗最风雅不过的桃花粥了。
然而这样的做法只针对外人。若做给毕家人自个儿吃,还有一道,会放一点毕克芳亲手腌制的桃花酱。
说是酱,但不是果酱类,更类似蜜,香气浓郁,放一点儿就得。可就是加了这一点儿桃花酱,才是《四时春录》里那道原汁原味的桃花粥。
桃花粥美颜、解郁、散燥热,像毕罗这样一路舟车劳顿回来,胃里面肯定有火气的。朱大年这碗桃花粥熬得心意十足。
再看另外几道菜,一道酒糟鱼、一道醉活虾,还一道山家三脆,鱼和虾虽是荤,却不是大荤,且都是滋味浓郁的菜肴。山家三脆清脆爽口,是用嫩笋、菌菇、枸杞菜做成,配粥吃最好。
毕罗看得食指大动,只顾说一句“朱伯伯你也吃”,便开动起来。
毕罗不是顶漂亮的模样,但肤白胜雪,眉目清爽,湛湛清灵,属于耐看型的女孩子。她平时斯文,可吃起东西来,并不像许多女孩子那样娇怯不敢下筷。相反,她吃得很快,眼睛微微眯着,看起来非常享受面前的食物,却并不显得粗鲁。
朱大年笑眯眯地去盛了碗粥,也坐在一旁跟着吃起来,一边吃还一边说:“大小姐不用让我。老朱每天守在厨房,嘴巴就没闲着过,喝这碗粥也就是陪着大小姐,要是让你朱婶见了,又得磨叨我贪嘴了。”
毕罗虽然也开口让他,但嘴巴和手指根本停不下来。毕家的《四时春录》并不拘泥南北菜系,书是从祖上传下来的,连同“四时春”这座酒楼。当时撰写这本书的人是毕家先祖,据说也曾做过大官,年少时就喜欢游历四方,遇到什么好吃的好喝的有趣的风雅的味道独绝的,就都记录下来。而且他读书多,看的杂书也特别多,每记录一样食物,总能旁征博引,大概撰写的时候又重新回去查阅过,凡是历史上记载过跟这样食物相关的,或杂文或诗句,他都一并收录进来。当时的人看了或许不觉得如何,但放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在毕家人乃至许多同行眼中,这本书就是无上珍宝了。
毕罗小的时候常在朱大年家蹭吃蹭住,九岁后搬进毕家老宅,穿着方面遭些刻薄,可吃上,毕克芳从不亏待她,因此也养刁了毕罗的一张嘴。这小嘴一张一合尝一口,一道菜里什么原料什么佐料便能说得比做菜的厨子还清楚,而且也养成了她饮食上不拘南北的习惯。
像今日朱大年为她准备的这几道小菜,酒糟鱼是江西一带的吃法,醉活虾则是沪城和宁波一带的名菜,都不在老平城人的菜谱上。桃花粥和山家三脆,按理说不在如今任何菜系的菜谱上头,这是古人的吃法,与其说吃的是滋味,不如说吃的是个雅趣。
但经过毕家人调制出的菜肴,味道就没有差的。
先说那酒糟鱼,这道菜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工夫能做得的。要选半斤左右的鲜鲫鱼,以盐腌渍再晾到半干,而后放进酿好的米酒坛子里封起来,放上十余日取出,放进锅子里,与酒糟同沸。酒糟鱼的关键在酒,酒要做得老一些,有烈性的酒味道才够浓醇。那酒糟的味儿渗入鱼肉,地道的酒糟鱼呈枣木红,酒香气可谓扑面而来,未尝先醉。
毕家的酒糟鱼,都是用野生鲫鱼做的,鲫鱼更小,肉更生嫩,米酒也不是从市面随便买的,是自家酿的纯米酒。朱大年掌勺的这道酒糟鱼,在锅子里煮的时候又放了头年采购后自家晾干的贵州七星椒,做出来的酒糟鱼糟香醇厚,又添辣味,吃起来别提多带劲儿了!
酒糟鱼这道菜,是道闲时菜,也是顶好的下酒菜。毕罗吃菜,有两个喜好,一爱食物新鲜,二喜菜肴原味。她并不在意这道菜是辣味还是甜味,一样喜欢,只要食材新鲜,做得地道,她就爱不释口。就拿这道酒糟鱼来说,她就爱吃这里面的酒糟味,更爱那如星子点缀夜空的一点辣,慢条斯理吃完一条小鲫鱼,直辣得神清气爽,齿颊留香。
再说朱大年做的另一道醉活虾。沪城和宁波一带的人最喜欢做这个菜。顾名思义,这道菜是将活蹦乱跳的鲜虾整个放进酒坛子里,虾不一会儿就醉了。毕家用的坛子不大,敞口窄底,最有特色的是这醉虾的坛子是玻璃质地,不会像平常材质那么闷。虾子刚放进去的时候还能看到在一跳一跳地动,不一会儿工夫就都老实了。
鲜虾是事先处理过的,在清水中滤过泥沙,又专门剪去须脚和虾枪。坛子里的也不是寻常的酒,与其说是酒,不如说是混着黄酒的调料。这醉虾的调料是毕家特有的秘方,一般人家,无外放点葱、姜、青红椒,朱大年放的调料都是毕克芳亲手调好保存在一个坛子里的,专门用作自家吃凉菜时放一些调一调味道,因此特别鲜香。
一小只玻璃坛子端上来,不过成年人的巴掌大小,里面的虾子各个醉倒着,个数不多,却足够毕罗吃。
酒糟鱼醇厚微辣,醉虾也带着酒香,咸鲜可口,吃得微醺辣口,就吃两口山家三脆爽爽口,一餐晚饭吃得毕罗脸颊红扑扑的,连眼睛里都有了几分精神气。
朱大年手脚麻利地将碗筷收拾了,又端上一只透明的玻璃小酒壶,并两只配套的玻璃小酒杯。
酒壶里的酒是淡青色的,毕罗一看酒液里的花蕾便知,这是雪梅酒,看成色,酒至少是三年陈。虽是三年陈,但并不辣,是特意酿给女孩子喝的花儿果子酒。
雪梅其实就是白梅,又称绿萼梅,气味清香,有疏肝和胃的药效,很适宜取一些酿酒。毕家的雪梅酒每年只在开春时对外售出,数量也是有限的,在平城的老饕们眼里,那是有市无价的东西。可在毕家人自己那儿,这东西不能说随便喝,也常有存储的。一年陈酒甘味甜,三年陈花香浓郁,要是五年陈,那就是一坛实实在在的老酒了,味道香醇、后劲儿大,并不适宜一般女孩子喝。
朱大年给毕罗准备的这雪梅酒,配上她刚吃进肚的那些食物,其实称得上是一壶养生酒。他觉得毕罗连着五年在外未归,看起来还是走时那么瘦,合该好好补一补。
春日的天黑得有些早,朱大年便将二人的小酒桌挪到了一楼的厨房里头。
毕克芳就是有这样的威严。哪怕他人不在,其余人来了这个家里,也没人敢乱了规矩,没人敢堂而皇之地跑去主屋坐下大吃大嚼。
朱大年跟了毕克芳这么多年,是有这个自由和资格的。可他仍从不逾矩,毕罗看得出来,他对毕克芳的敬重,是吃进心里刻在骨子里的,早成习惯了。
在厨房饮酒,并没有许多人想的那么糟。毕家的厨房很大,而且非常干净,干净得都有点不像厨房这种地方。桌子都是老式的,浸透着某种时光打磨的光泽,曾经有人来毕家拜访,见到厨房的长条桌子,非要出十万块钱买去。那时还是三十年前,十万块钱并不是个小数目,可被毕克芳一口回绝了,而且以后再也没允那人进过毕家的门。
朱大年和毕罗没在长条桌子上喝酒,那是厨子专用的。他俩用的是一张四方的小桌,长宽一米,平时不用就折起来靠墙壁摆着,虽然是张玲珑的小桌子,但木头材料和样式与那长条桌子是一套的,一看就是同一个工匠的手艺。
两人摆好了酒,门大敞着,从这儿望出去,能看到半个滚圆的月亮。白天下了大雨,夜晚的天空没一丝云彩,月亮又大又圆,仿佛也知道人终于团圆了。
毕罗可没这细腻的感悟,这话是朱大年说的。
雪梅酒喝了一壶半,朱大年才又开了口:“大小姐,您是不是心里头……还恨着先生?”
“没有。”毕罗回答得很痛快,因为是实话,所以不需要细琢磨,“是他把我带大的,没有他,我可能早就饿死了。”想起在国外的这五年,她有点出神,“而且后来出国读书,我说想学画画,他不喜欢,但也没反对,还给了我钱。”
朱大年又喝了一杯酒,这酒劲儿很柔,味道也甜润可口,并不醉人。他这样显然是为了借酒遮脸,说几句平时不敢说的话:“大小姐,先生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
毕罗苦笑:“这我知道。”毕克芳又不是傻子,谁愿意老了老了,还得这么个病受罪呢?
“先生其实一直想让您继承家业,但当年舜华小姐的事……”当年毕舜华没过世的时候,他一直喊她“舜华小姐”,后来毕罗搬回毕家,毕克芳就让所有人喊毕罗“大小姐”,仿佛从来没有过毕舜华这个人一样。朱大年咬牙,说:“舜华小姐心地善良,但自小被先生宠坏了,得不到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谁劝也劝不住。先生不想您再走舜华小姐的老路,才对您特别严格,不让您穿花裙子,不准您梳长头发,每天上下学无论您愿不愿意,都让老朱去接送,看着您,不让您跟别的男孩子说话……”
这些即便朱大年不说,毕罗已是二十四岁的成年人,又一个人在外生活五年,小时候的执拗和彷徨,总会随着岁月和阅历的砥砺,自己渐渐想清楚。
朱大年见毕罗端着酒杯垂眸不语,便又说:“先生的心结,您是知道的。现在您是毕家的唯一传人,如果先生去了,四时春和您,就是他最放心不下的。”
毕罗说:“我今天已经当着他的面答应了,我会留下来,帮他打理好四时春。我会说到做到。”
朱大年见毕罗仍不抬眼,就知道她还在坚持折返F国参加毕业典礼的事,咬了咬牙,说:“大小姐,您没回来的时候,先生已经下过两次病危通知书了。您知不知道,您不知道……”朱大年说着,又红了眼圈,“说是能活半年,其实都是吓唬外人的话,您不知道有多少人觊觎着四时春,先生随时可能醒不过来的……”
这就是朱大年甚至毕克芳这一次坚持不肯她再度折返F国的真正原因。
她有些茫然地抬起头:“朱伯伯,大夫到底怎么说的?”
朱大年说:“瘤子长在脑袋里,人随时有可能过去。不能大喜大怒,不能长途旅行,最好就这么一直在医院住着……”朱大年叹了口气,“大夫也不建议做手术,说做了手术也不保证能多活多久,手术失败的话,人当时就没了。让保守治疗。”
直到这时候,毕罗才仿佛大梦初醒,真正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实。
毕克芳随时会死。
她在这个世上唯一有血缘承继的亲人,随时有可能撒手而去。她又要变成孤零零一个人了。
毕罗,又做饆饠,始于唐。长安长兴坊有胡人开设饆饠店。蟹黄饆饠、樱桃饆饠、天花饆饠等,甚为著名。至宋,记饮食诸书皆无记载,或更名或失传。
《太平广记》卷二三四“御厨”引《卢氏杂说》:“翰林学士每遇赐食,有物若毕罗,滋味香美,呼为诸王修事。”唐段成式《酉阳杂俎.酒食》:“韩约能作樱桃饆饠,其色不变。”
今有四时春,樱桃饆饠、莲子饆饠、蟹黄饆饠、天花饆饠等,外皮分酥脆软厚二种,依四时不同而择馅料,滋味甜咸鲜美,制法如下……
——摘自《四时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