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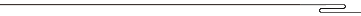
本书是诸位作者的观点的集合,各位作者都认同当前金融市场所存在的公平正义问题。本书共有三编,分别涵盖了有关金融市场正义的不同缺陷和失败。第一编讨论了所谓的“概念上的失败(conceptual failures)”,即没有使用足够广泛和细微的规范框架来思考正义和金融市场。这部分中的各章的共同之处在于拒绝了用过于简单的自由市场路径去分析金融市场,并将视野从纯粹的经济学扩展到了哲学和经济学的融合。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提出超越经济学家(甚至是非常成熟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有关金融市场的问题:金融市场与人权有何关系?金融市场是否支持个人行使其能力?金融市场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我们可以像某些经济学家所声称的那样,假设金融市场中的收入是应得的吗?第二编探讨了金融市场中的法律框架,并分析了该框架中各种不公正偏见的表现方式。这种偏见可以在使个人或公司对不法行为或过度冒险承担责任的法律制度和使金融市场成为可能的基础权利体系中找到痕迹。第三编探讨特定的机构和实践及其对正义各个维度的影响,无论是分配正义,还是对正义维度的认识,抑或是性别正义。这些分析被经济学家称为“局部分析(partial analyses)”,即他们从特定的角度看待特定的机构或实践。即使我们可以改变金融市场的一般概念,并纠正法律制度中的基本偏见,但这些章节提出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这个语境下本书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当前的一系列机构和实践,包括思维习惯和既得利益,是如何阻碍变革的。
罗莎·M.拉斯特拉(Rosa M. Lastra)和阿兰·H.布雷纳(Alan H. Brener)在第二章“正义、金融市场与人权”中重点关注社会机构获得和维持合法性的必要性。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是遵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人权框架。拉斯特拉和布雷纳追溯了人权思想史特别是在“萨拉曼卡学派(School of Salamanca)”的某些方面,强调了与市场概念和实践发展的殊途同归(parallel)。为了获得合法性,市场需要保持在正义的框架内,这可能需要谨慎的权衡和妥协,正如作者在简要讨论发薪日贷款(payday lending)监管的一些复杂性时所表明的那样。在国际范围内,联合国的“外债与人权问题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on foreign debts and human rights)”可以看作是如何弥合市场思维和实践与人权之间鸿沟的一个例子。拉斯特拉和布雷纳得出结论,只有确保金融市场与人权的兼容性,金融市场才能重新获得合法性和社会信任。
罗格·克拉森(Rutger Claassen)在第三章“金融市场监管的能力框架”中提出了一种评估和监管市场(包括金融市场)的统一方法。他回顾了市场监管的主流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它们将针对帕累托效率的经济考虑与针对父爱主义保护(paternalist protection)和分配正义的社会考虑分开了。这意味着当这些不同的目标发生冲突时,没有指导可供参考。克拉森建议转向另一种范式:由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提出的能力方法。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市场监管问题时,克拉森将参与能力、消费者能力和第三方能力进行了区分。最后,他展示了该方法如何阐明本书其他作者讨论的三个问题:德布鲁因(de Bruin)关于如何考虑评级机构的角色的建议,罗素(Russell)和维利耶(Villiers)关于金融市场中性别正义的讨论以及阿德玛蒂(Admati)对改革失败的分析。
谢默斯·米勒(Seumas Miller)在第四章“金融市场与制度目标:规范性问题”中为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但并非不相容的规范解释:一个“目的论(teleological)”解释。米勒拒绝接受诸如股东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之类的进路,而是认为在考虑制度的适当规制时应认真考虑其制度目标。制度应该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collective goods)。这种目的论的观点引发了许多问题:关于特定制度的制度目标(institutional purpose),实现这些目标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方案,以及这些制度所处的宏观制度环境。米勒将此种解释应用于金融系统的三个部分:银行部门、退休储蓄计划和资本市场。由此产生的争论和对改革的呼吁在直觉上似乎是合理的,以至于使人怀疑有些评论家是否本能地受到类似于米勒的目的论解释(teleological account)的指导。另一个可能性是,在涉及实际建议时此种解释与其他解释实现了会师。米勒的观点对我们提出挑战,要求我们调整思考一般制度以及金融市场中的特殊制度时使用的传统方式。
丽莎·赫佐格(Lisa Herzog)在第五章“金融市场中的收入是应得的吗?一个基于正义的批评”中,接受了在公众对金融市场的批评中经常听到的一个观念:在金融市场中产生的高收入可能不是应得的。相比之下,一些经济学家使用“应得(desert)”
 概念来为高收入辩护。在关于“应得”的哲学辩论的基础上,赫佐格采用了一个中性的、制度性的应得概念,并将其应用于金融市场。通过这样做,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市场运行的制度规则上,这些制度规则决定了市场是马基维利主义式(Mandevillian)的奖励恶的行为抑或是斯密式(Smithian)的奖励对社会有用的行为。现代金融市场,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以前,规则的设计并未能够实现这样一种理念,即奖励应当是由遵循规则的人获得。取而代之的是,这些规则曾经,而且可以说依然受到市场失灵和外部性问题的干扰,它们既没效率,也未将奖励给予任何值得捍卫的方面。因此,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可以就造成不当高收入的金融系统的许多缺陷达成共识,并共同推动改革。
概念来为高收入辩护。在关于“应得”的哲学辩论的基础上,赫佐格采用了一个中性的、制度性的应得概念,并将其应用于金融市场。通过这样做,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市场运行的制度规则上,这些制度规则决定了市场是马基维利主义式(Mandevillian)的奖励恶的行为抑或是斯密式(Smithian)的奖励对社会有用的行为。现代金融市场,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以前,规则的设计并未能够实现这样一种理念,即奖励应当是由遵循规则的人获得。取而代之的是,这些规则曾经,而且可以说依然受到市场失灵和外部性问题的干扰,它们既没效率,也未将奖励给予任何值得捍卫的方面。因此,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可以就造成不当高收入的金融系统的许多缺陷达成共识,并共同推动改革。
接下来的两章讨论与法律执行及其对金融市场正义的影响有关的法律问题。马克·R.雷夫(Mark R. Reiff)在第六章“管理层的罪与罚:道德责任、因果责任和金融犯罪”中,主张彻底重新思考金融市场中刑事正义的工作方式。关于正义的许多辩论都没有讨论刑事正义,而只是简单预设一旦某些规则被确定并同意,就有可能通过法律来执行它们。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此假设感到怀疑:尽管有一些令人发指的不当行为,并且至少有一些按照现行标准来看也是违法的,但很少有人入狱。金融机构被处以巨额罚款,但它们是否能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从而在将来确保更负责任的商业行为,这是令人怀疑的。雷夫认为,我们传统的将明知和故意作为犯罪定罪前提的思维方式太过局限。因此,他提出在道德上承担因果责任的概念,这需要根据公司高管的具体责任逐案确定。雷夫的讨论表明,实际起诉的案件数量远低于看起来应当起诉的案件数量,这种情况下不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看,都应当对关于入刑以及刑期的条款进行调整。
杰·库伦(Jay Cullen)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法律问责制的问题。第七章“无法修复的文化?金融伦理与制裁”,主要是指如何设计制裁,使制裁营造一种减少社会过度冒险的文化。库伦认为,银行在某些方面具有特殊性:它们由于其“太大而不能倒”的特征而获得隐性的公共补贴和担保,并且银行中还有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难以监管。这限制了自我监管的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和伦理作为调节行为的替代方法成为人们关注点的原因。但是,现代金融市场的匿名性和基于信息技术的交互性导致难以找到伦理责任的基础。因此,库伦建议仔细研究伦理与制裁之间的关系,强调后者在建立问责制(前者的关键组成部分)中的作用。他将英国新的“高级管理人制度(Senior Managers' Regime)”描述为一种有希望推动金融市场文化的基本假设发生变化的进路。
与雷夫相比,库伦倾向于更加系统和务实地从民法的角度寻求金融市场法律正义的路径。他比雷夫更加乐观地认为经济制裁可以是有效的,而对于在金融市场中刑法的适用则不那么乐观。但是,两人都同意需要加强个人责任,都强调不仅要制裁行为(actions)还要制裁疏漏(omissions),尤其是管理者在掌握和有效监管其团队成员行为上的失败。其指出的金融市场中的认知责任问题,德布鲁因在第十一章中也进行了讨论。
凯瑟琳娜·皮斯托(Katharina Pistor)开辟了政治哲学家很少走过的道路,但对他们而言更有趣:正义问题是金融社会本体的核心,即金钱的法律建构。在她的《金融的法律原理》(2013)一书中,皮斯托对金融的法律构造提出了有趣的解释。在第八章“货币的法律等级”中,皮斯托深化了这条路线,并探讨了这些法律结构对金融市场主流参与者和边缘参与者的不平等对待。正如支付手段的历史发展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有相反的说法,但金融市场绝非“公平竞争环境”,因为它们所依赖的法律上的追索权在强度上是有差异的。因此,皮斯托对“企业是分层的,而市场是平等的”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这种法律追索权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支付系统,还体现在可以实现资产隔离的信托法和公司法上。皮斯托最后指出建立更公正的金融系统的主要障碍之一,即是政府依赖于私人货币创造的政府融资(government finance)。这种理论进路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当前金融系统的法律不公正,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构性不公正。这些不是法律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层级控制及其分配后果的政治问题。
在第九章“臆想的投资者权利”中,亚伦·詹姆斯(Aaron James)质疑了近年来已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法律实践:使用为国际投资者提供特殊保护的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当今的金融市场可能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也许与有组织犯罪有关)。因此,支持它们的法律机制对于全球正义问题至关重要。投资条约赋予外国投资者(无论是对实物还是金融资本的投资)在特别仲裁庭面前起诉政府的权利。詹姆斯剖析了似乎支持这些条约的论点:无论是结果主义还是社会契约论的观点都无法证明这些条约赋予投资者大量权利的合理性。詹姆斯根据对国际贸易实践的解释,认为这些权利是基于对国际资金流动所支撑的社会实践的误解。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能够说明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权利是如何被撕裂,以及结构性正义问题,即金融市场并不公平,而是给予某些群体特权。揭露一些有缺陷的论点并否定支持这种法律框架的论证,是迈向变革的第一步。
第三编的前两章从正义的角度考察了两类特殊的机构,即中央银行和评级机构。彼得·迪特施(Peter Dietsch)在第十章提出了“中央银行的规范维度:金融市场的守护者如何影响公平”的问题,打破了似乎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他不是从技术角度而是从分配正义和合法性的角度讨论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在公共政策和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迪特施对货币政策进行了全景式的概述,区分了传统措施与非常规措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中央银行选择了后者,包括所谓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以试图推动经济。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些非常规政策加剧了不平等,这在(分配)正义的许多理论中都是有问题的。关于合法性,迪特施讨论了金融市场的反应如何成为可以影响货币政策的强大力量。这是很成问题的,不仅因为它使得资本能够对政策制定施加不当影响,而且还因其会破坏国家的经济自决权。
鲍德温·德布鲁因(Boudewijn de Bruin)在第十一章“金融市场正义中的信息条件: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中,讨论了金融市场正义的认知维度(epistemic dimension)。过去,金融市场中重要的认知任务被“外包(outsourced)”给信用评级机构。当这些机构未能准确评估复杂的结构化金融产品的风险时,对它们的批评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还延伸到道德层面。然而,德布鲁因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各国开始将评级视为可交易资产的正式认可标志,并在金融机构的监管中也依赖评级。德布鲁因基于对市场正义的最小假设,认为决策者应该采取步骤将金融市场中的认知责任(epistemic responsibility)归于原位,而不是试图通过“监管”消除寡头权力和利益冲突等问题。评估不同金融产品风险的责任必须由交易者承担,评级机构评级的附加价值不能成为对其判断的法律上的背书。这种说法与许多正义论者对市场问题所产生的本能反应背道而驰,即考虑更多的监管。关于金融市场的认知维度,德布鲁因认为,在错误的(允许认知责任外包)地方强化监管,本身就是问题,而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案。尽管这一结论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激进的,但它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金融市场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其交易往往反映了对于经济结果未来预期的不同预测,如果将认知责任外包给其他机构,则信息处理任务将会形同虚设。
最后两章讨论的不是当今金融市场中的特定机构,而是特定实践。在第十二章“金融市场中的性别正义”中,罗斯安妮·罗素(Roseanne Russell)和夏洛特·维利耶(Charlotte Villiers)讨论了一个本书前面一直未谈及但同样紧迫的正义问题:性别正义。男性在金融市场以及整个公司董事会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消失。尽管为增强妇女权能(empowering women)已采取了各种举措,但这些举措通常并不是基于对人权或性别正义的考虑,而是基于“多元化(diversity)”或女性参与的“商业考量”。罗素和维利耶指出,这些论点虽然缺乏可靠的基础,但是为了争取妇女和其他少数群体在公司界和金融市场中的公平代表权,没有必要吹毛求疵。她们呼吁在辩论中表现出更大的诚意,要认识到当前要求更多女性参与的呼吁通常是工具性的。这些呼吁只是关注了那些能够将照顾家庭的工作外包给其他女性的强势女性(privileged women),而没有挑战现有的权力结构。作为另一种选择,罗素和维利耶建议更加强调以社会正义为起点,克服个体主义观念(individualistic mindset)且与其他群体相容的女权主义(feminism),以实现可持续的结构性变革。
阿纳特·R.阿德玛蒂(Anat R. Admati)在第十三章“齐心协力维持一个危险的金融系统”
 提出了一个金融危机之后公众可能问过的问题:监管者和政治家将采取哪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否足够?根据她的早期研究(特别是Admati and Hellwig 2013),阿德玛蒂认为迄今为止采取的监管措施不足以解决金融系统固有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与银行的低资本比率有关。她将金融系统与航空业进行了比较:在航空业中,需要各岗位的共同努力以确保乘客和机组人员都能够安全到达。但是在金融领域,各市场主体的合作是相反:保持固有不稳定的系统并在必要时接受公共救助,而利润却被私人获取,这使其非常不公平。阿德玛蒂分析了在当前金融系统中无知、混乱、故意视而不见和缺乏问责制的痼疾。众多的利益冲突使得包括许多学者在内的那些应该更加了解的人无法向公众解释基本问题和机制。只能希望阿德玛蒂悲观的分析有一天会过时。正如她指出的那样,当其他行业(例如烟草行业)面临公众批评时,也可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改变是可能的,但也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来让它实现。
提出了一个金融危机之后公众可能问过的问题:监管者和政治家将采取哪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否足够?根据她的早期研究(特别是Admati and Hellwig 2013),阿德玛蒂认为迄今为止采取的监管措施不足以解决金融系统固有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与银行的低资本比率有关。她将金融系统与航空业进行了比较:在航空业中,需要各岗位的共同努力以确保乘客和机组人员都能够安全到达。但是在金融领域,各市场主体的合作是相反:保持固有不稳定的系统并在必要时接受公共救助,而利润却被私人获取,这使其非常不公平。阿德玛蒂分析了在当前金融系统中无知、混乱、故意视而不见和缺乏问责制的痼疾。众多的利益冲突使得包括许多学者在内的那些应该更加了解的人无法向公众解释基本问题和机制。只能希望阿德玛蒂悲观的分析有一天会过时。正如她指出的那样,当其他行业(例如烟草行业)面临公众批评时,也可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改变是可能的,但也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来让它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