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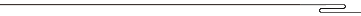
不论是从描述性的角度还是从规范性的角度,金融系统呈现给我们的图景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非常复杂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形式的批评似乎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例如,我们可能同时主张对某些市场的平等机会(例如性别平等),同时也从更广阔的角度批评其功能并要求其进行整体的结构性变革。
似乎很清楚的是,让金融系统保持原样是一个坏主意。实际上,已经有许多改革建议,其中一些已经在新法律或法规中实现。例如,已经提出了更高的银行资本比率(参见Admati and Hellwig 2013),对奖金结构的改革也有诸多建议并在一些地方得以实施。其他为稳定银行体系的关于透明度要求以及安全机制的新规则也已在欧元区建立。这些改革一般是从经济角度提出的,政治哲学尽管可以支持其中的一些,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都希望在考虑效率和稳定性之外还要考虑正义,并基于此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政治哲学可以从正义的角度思考需要作出什么样的改变。
在金融危机之后,此类改革工作的重点一直放在法律法规上,即改革金融系统的法律制度和监管规则。尽管其无疑是重要的,但人们想知道法律法规的这种变化是否足够,或是还需要社会思潮和市场文化的改变。在当今如此复杂的金融系统中,按规则进行治理需要正确地制定激励措施,但这绝非易事。
 从定义上讲,规则比较严格,可能不是理想的规制各种场景的唯一工具。如果情况发生改变,规则可能会过时而难以适应。规则需要应用于具体的案件,这可能需要对市场实践的判断和理解。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对规则遵守的控制也是耗时费力的。
从定义上讲,规则比较严格,可能不是理想的规制各种场景的唯一工具。如果情况发生改变,规则可能会过时而难以适应。规则需要应用于具体的案件,这可能需要对市场实践的判断和理解。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对规则遵守的控制也是耗时费力的。
各种因素反映了复杂系统不仅需要规则,而且非常需要参与者的共同精神特质来规范。在理想的金融系统中,有人希望市场参与者与监管机构合作,以最佳地制定规则,自愿放弃监管套利机会,并为整个系统运作建立共同负责的文化。有人希望市场参与者形成一种专业精神,为他们市场实践的隐性标准指明方向,无论是在分配资金、对冲风险还是为客户提供建议等方面(参见van de Ven 2011)。有人希望市场参与者能够组织和参加行业组织,在其中讨论和强化相应的道德规范,这些行业组织可以对某些风险或损害承担法律责任。有人还希望市场参与者共同建立和维护一种合乎行业责任(responsibility of an industry)的思潮(ethos),这种行业责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这种思潮是很微妙且难以琢磨的,而且尚不清楚如何在一个可以说具有截然不同的思潮的社会环境中实施。阿维里(Awrey)等(2013)讨论了“流程导向型监管(process-oriented regulation)”的理念如何设计具体步骤以期提高金融行业的道德标准。他们基于英国的“公平对待客户(Treat Customers Fairly)”倡议,提出了一种可以改善交易行为和减少“整个社会的过度冒险(socially excessive risk-taking)”的类似模式,这种模式关注对话和自上而下的统一思想,董事会层面的伦理委员会,内部控制和行为规范的改变。这意味着将期望于金融机构将某些监管任务内在化,而不再允许将其行为的负面影响外在化。
监管目标的确定,有特定方案(specific approach)和综合方案(integrated approach)的区分。
 特定方案倾向于具体的问题由具体的相应机构处理,其背后的假设是负责不同任务的不同机构之间进行分工是很有用的。这种观点与前面所提到的通常理解相呼应,即市场应当确保效率,关于公平等问题的监管考量应当是其他机构例如税务部门或其他福利国家所考虑的事。这种特定方案建议可以设立新的机构专司当前机构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巴拉达兰(Baradaran)提出的恢复美国的邮政储蓄银行业务的建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5)。该建议基于一项对当前金融市场排斥穷人群体的分析,以及对迫使逐利的银行为贫穷客户提供服务可能性的怀疑。尽管巴拉达兰也清楚地表达了她对于现有机构作出改变的欢迎,但她的建议并未关注现存的金融市场结构,而是试图通过设立新型机构来解决当前机构未能解决的问题。
特定方案倾向于具体的问题由具体的相应机构处理,其背后的假设是负责不同任务的不同机构之间进行分工是很有用的。这种观点与前面所提到的通常理解相呼应,即市场应当确保效率,关于公平等问题的监管考量应当是其他机构例如税务部门或其他福利国家所考虑的事。这种特定方案建议可以设立新的机构专司当前机构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巴拉达兰(Baradaran)提出的恢复美国的邮政储蓄银行业务的建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5)。该建议基于一项对当前金融市场排斥穷人群体的分析,以及对迫使逐利的银行为贫穷客户提供服务可能性的怀疑。尽管巴拉达兰也清楚地表达了她对于现有机构作出改变的欢迎,但她的建议并未关注现存的金融市场结构,而是试图通过设立新型机构来解决当前机构未能解决的问题。
综合方案侧重于机构间的相互联系,并试图将更广泛的目标纳入现有机构框架之中。例如,监管机构在对市场实施监管时,可能不仅追求效率最大化,而且还试图将分配正义的考量也作为监管目标之一,包括防止某些可能加剧不平等的市场交易(即使它们可能具有帕累托效率),或者按照消除贫困或减少不平等等制度目标的要求重新设计现有监管框架。例如,米安和苏菲(Mian and Sufi 2014)认为,抵押贷款目前的运作方式存在过多的风险,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最终落在了最缺乏抵押能力的人(即家庭)的肩上。这意味着,当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时,这些家庭将减少消费,从而导致总体需求下降,加剧经济衰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讨论了“风险分担抵押贷款(shared-risk mortgages)”的可能性,即住房抵押贷款的还款方案与当地房价指数挂钩,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人能与债权人分享一些未来的资本收益,从而也能避免未来的房价下降的风险(Mian and Sufi 2015,chap.12)。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建议非常雄心勃勃,因为它改变了金融市场所仰赖的核心法律基础架构。
没有先验的理由支持特定或综合的方案,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创建更多的特定机构也会对现有机构的工作方式产生影响,例如,因为客户现在有了其他选择,其可以选择退出现有机构,这意味着这两个类别之间的边界会趋于模糊。在某种意义上说,创建特定的机构似乎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因为它并没有涉及复杂系统对其核心变化的反应那么多的“未知数”,但它也似乎是无奈的次优选择,就像在需要手术的伤口上贴创可贴一样。综合方案可能具有更深远的影响,但也可能难以实施,因为它们会影响那些受益于当前系统的人的既得利益。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可以从金融危机和在其之前实行(或缺乏)的监管规则中学到的,那就是对于整个金融系统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细节,无论是在法规的设计中还是在指标的使用中。难怪这些技术细节是与变革利害攸关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紧张游说的重要目标。
尽管在如何更好地监管金融市场方面存在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人们一直视而不见的
 是政治家和监管者是否有实际意愿作出改变,以真正改善这种状况,或者说金融业是否成功抵制了真正的变革,并在最终被发现只是浮于表面的改革中逍遥法外。这最终是一个权力问题。关于游说问题和金钱在政治中的影响的文章很多(例如Hacker and Pearson 2010,Gilens 2013,Reich 2015)。当然,这个问题比它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影响要广泛得多,也更根本。但是后者是这个问题的含义变得特别明显的地方。另一个问题是金融市场监管的国际合作。毫无疑问,金融稳定已被概念化为一种全球性公共物品(Kaul et al. 1999;有关讨论另请参见Emunds 2014,272ff.),这激励了各国在其他国家的监管努力上“搭便车”。金融市场国际层面的问题也提出了其他正义命题,即正义理论家们刚刚开始探索的全球正义(global justice)。这些不仅涉及国际税收的结构和国际资金流动的合法性,而且还涉及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治理(参见例如Wollner 2014,Emunds 2014,Krishnamurthy 2014)。这些问题在本书中没有明确讨论,但是某些章节也对这些问题有所反映。
是政治家和监管者是否有实际意愿作出改变,以真正改善这种状况,或者说金融业是否成功抵制了真正的变革,并在最终被发现只是浮于表面的改革中逍遥法外。这最终是一个权力问题。关于游说问题和金钱在政治中的影响的文章很多(例如Hacker and Pearson 2010,Gilens 2013,Reich 2015)。当然,这个问题比它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影响要广泛得多,也更根本。但是后者是这个问题的含义变得特别明显的地方。另一个问题是金融市场监管的国际合作。毫无疑问,金融稳定已被概念化为一种全球性公共物品(Kaul et al. 1999;有关讨论另请参见Emunds 2014,272ff.),这激励了各国在其他国家的监管努力上“搭便车”。金融市场国际层面的问题也提出了其他正义命题,即正义理论家们刚刚开始探索的全球正义(global justice)。这些不仅涉及国际税收的结构和国际资金流动的合法性,而且还涉及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治理(参见例如Wollner 2014,Emunds 2014,Krishnamurthy 2014)。这些问题在本书中没有明确讨论,但是某些章节也对这些问题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