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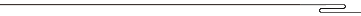
可以肯定,这个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鉴于许多人认为金融市场不同于卫生保健、教育或代孕市场,是运作良好且竞争充分的市场中的样板,因此这个问题值得一提。金融市场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特定的产品、特定的参与者和特定的均衡(或者失衡,例如泡沫)。
如前所述,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许多产品都是高度人为的法律建构,其中许多产品与实体经济相距甚远。
 因此,它们显然不能直接满足消费者的喜好。正如特纳所说:“没人早上起床,说‘我今天喜欢享受一些金融服务’。”在某些市场中,此类产品的交易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对实物产品市场的想象。在教科书中,通常假定参与者打算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产品的产权,即便他们出于投机目的而购买,他们也必须稍等片刻,直到价格朝某个方向移动为止。而在有些金融市场中,参与者从微妙的价格变动中获取利润,例如在计算机程序化交易中往往以毫秒为单位。目前程序化或“算法(algorithmic)”交易正在许多金融市场上发生,尽管人们对其尚未完全理解,例如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市场中发生的众多“亚秒级极端事件(subsecond extreme events)”与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究竟有何关系(Johnson et al. 2013)。
因此,它们显然不能直接满足消费者的喜好。正如特纳所说:“没人早上起床,说‘我今天喜欢享受一些金融服务’。”在某些市场中,此类产品的交易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对实物产品市场的想象。在教科书中,通常假定参与者打算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产品的产权,即便他们出于投机目的而购买,他们也必须稍等片刻,直到价格朝某个方向移动为止。而在有些金融市场中,参与者从微妙的价格变动中获取利润,例如在计算机程序化交易中往往以毫秒为单位。目前程序化或“算法(algorithmic)”交易正在许多金融市场上发生,尽管人们对其尚未完全理解,例如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市场中发生的众多“亚秒级极端事件(subsecond extreme events)”与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究竟有何关系(Johnson et al. 2013)。
金融市场上交易的产品的第一个特征(尽管与这些产品的一般特征相比不那么具体)是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绝对数量。随着资金在较小范围的交易者和金融机构之间转移,发财致富的诱惑远大于其他许多市场,尤其是在上行的市场中。正如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和阿列伯(Aliber)直白地指出:“腐败的供给以周期性的方式增加,就像信贷的供给一样”(2005,143)。腐败可能意味着市场参与者使用非法的欺诈手段来赚钱,但也可能意味着他们会加大努力来利用他人的脆弱性,例如他们的无知、恐惧或时间不一致的偏好。正如阿克洛夫(Akerlof)和席勒在其最新著作《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Phishing for Phools)中指出的那样,利用此类脆弱性(vulnerabilities)的倾向并非罕见的“外部性”,而是“竞争性市场的固有运作方式”(2015,166)。它当然不是金融市场所独有,但它们所涉及的巨大风险以及所交易产品的抽象性和复杂性可能使它们成为对“钓愚者(phishers)”特别有吸引力的池塘。
金融市场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参与其中的主体。标准市场模型假定经济主体承担其决策的向上和向下风险,这就是激励他们根据自己对风险和利润的偏好,在不同的选项之间进行谨慎选择的动机。在金融市场,责任以不同的形式受到限制,但价格却没有受到影响。就拿其中一个方面来说,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一般都是公司,这就意味着它们的股东能够享受有限责任,即只以其出资额为限而非以其私人资本承担责任(Ciepley 2013)。而金融市场的有限责任更为登峰造极。为了防止“银行挤兑”,银行存款通常都受到政府主导的存款保险体系保护。中央银行以“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身份为出现流动性危机的银行提供支持(Minsky 1986,chap.3; Kindleberger and Aliber 2005,chap.11)。正如金融危机中所暴露的一样,金融市场受到了“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和“太复杂而不能倒(too complex to fail)”的影响:如果金融机构对于整个金融系统太过重要,它们的失败将会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那么各国政府就会采取措施防止这种失败。这就意味着金融机构将会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从而造成一种“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如果有种更加冒险的策略能够带来更高收益,但风险是由纳税人去承担,金融机构何乐而不为呢?
人们对于金融市场中减轻责任的另一种方式关注不够,即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问题。在大型复杂机构(例如大型银行)中,存在掩盖不法行为或稀释责任的多种可能性。在银行中,许多任务是高度专业化的,并且需要很少有人具备的技术技能,这意味着其他人很难监控行为人的行为。而似乎许多银行的合规文化运作并不理想。对此的证据是,许多雇员的不当行为只有在造成巨大损失后才被发现,例如法兴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的杰罗姆·凯维埃尔(Jérôme Kerviel)的未授权交易。
 发现错误或可疑行为的可能性小,再加上与短期利润相关的高额奖金,导致了雇员受到鲁莽行事(behave recklessly)的诱惑可能要比在更透明、受到更好控制的环境中更大,更不用说他们不是用自己的钱在交易了。
发现错误或可疑行为的可能性小,再加上与短期利润相关的高额奖金,导致了雇员受到鲁莽行事(behave recklessly)的诱惑可能要比在更透明、受到更好控制的环境中更大,更不用说他们不是用自己的钱在交易了。
金融市场与其他类型市场不同的第三个方面是,它们是否能够自我稳定(self-stabilize),或者说它们是否还会产生破坏稳定的动力(泡沫)而不是市场均衡。如前所述,全球金融危机以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偏离市场均衡的走势会吸引理性的套利者,使市场回到均衡状态。但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以这种方式看待金融市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已经使用了“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一词,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和罗伯特·席勒在2009年的一本书以此为标题,它描述的是“一种本能地采取行动的冲动,它不是基于对收益和概率进行量化计算的理性衡量结果”(1936,161—162)。如果市场参与者遵循他们的“动物精神”,则市场可能不会均衡,而是造成非理性的上行或下行。这些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就像我们在2008年所看到的那样。
根据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的早期的成果(1986),金德尔伯格和阿列伯给出了关于金融危机的较好的描述。他们对历史的研究显示,金融危机可以由不同类型的资产引发,从郁金香球茎(1630年代著名的“郁金香热”,参见Dash 2001)到公司股票和房地产[参见Kindleberger and Aliber's Appendix(2005,256ff.)对史上泡沫的概述]。席勒将泡沫定义为“价格上涨的消息激发了投资者的热情,这种热情因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传染而传播,在此过程中,渲染可能证明价格上涨合理性的故事,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尽管对一项投资的真正价值存有疑问,但部分由于对他人成功的羡慕,部分出于赌徒的兴奋而被吸引”(2000,2)。这个定义强调了这种现象的心理因素,这在金德尔伯格和阿列伯的分析中也存在。
在上行(upswing)的过程中——金德尔伯格和阿列伯也称其为“狂热(mania)”——交易的增长不是出于长期投资或对冲实体经济风险的意愿,而是出于希望从短期价格变动中获利的动机。由于有赚容易钱的机会,许多投资者通常通过信贷资金加杠杆购买资产,然后在所有人都意识到资产被严重高估之前将其出售给愿意接手该资产的“更大的傻瓜”(Kindleberger and Aliber 2005,12)。一旦市场上行来临,乐观情绪就会扩散开来,投资者几乎无法抵抗它。甚至是经验丰富的投资者也可能会决定跟风,尤其是如果他们的雇主或客户将他们与趋势进行比较(另见Turner 2016,40ff.)。这可以为上行提供更多动力。正如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所说:“只要音乐在演奏,您就必须起身跳舞。”(Lomansky 2011,151)然而问题是:如果音乐停止了该怎么办?
正如金德尔伯格和阿列伯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狂热中,“资产价格在停止上涨后将立即下跌,没有平稳,没有‘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可言”(2005,10)。一旦价格开始下跌,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必须尽快摆脱困境,而在价格上行中推动价格上涨的机制现在则同样地将价格推低。因为当市场中卖方过多时,价格下降,这意味着其他资产所有者也希望在价格进一步下跌之前将其出售。当许多投资者用信贷资金购买资产时尤其如此。当他们有固定的债务需要偿还时,资产价值的下降将很快地使他们不堪重负。其中一些将被迫进行“火线出售(fire sales)”,另一些将破产,这会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在恐慌和幻灭的普遍气氛中,贷方几乎没有动力发放更多的贷款。明斯基尤其强调信贷在金融市场周期性不稳定中的作用。相反,主流经济学几乎没有关注信贷的作用及其扩张。
一些评论家认为,在银行监管方面的技术细节似乎进一步加强了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对于银行发放的每笔贷款,都要求银行在资产负债表中持有一定数量的资本。但是,这些资本的价值是根据这些资产在市场上的当前价值而不是历史成本来计算的。这意味着在市场上行中,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价值上升,这意味着它们有更多的可用资本来满足新贷款的监管要求。因此,它们可以为更多的投资者提供信贷,而这些投资者将用贷款来购买更多的资产,从而进一步推高价格。而在危机中,即使银行无意出售资产,资产价格下跌也将直接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因此,“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模型的使用起到了价格变动的顺周期放大作用(参见例如Turner 2016,102ff.)。莱因哈特和罗格夫(Reinhart and Rogoff 2009)记录,自1980年代以来数十年来助长金融危机加剧的其他因素是信贷证券化和结构化金融产品的使用,而资本在全球化经济中的自由流动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可能导致国际传染(Kindleberger and Aliber 2005,chaps 7 and 8)。
综上所述,金融市场具有非常特定的特征。也正是这些特征令此值得一问:我们是否应该将它们描述为“市场”?但是,为什么这很重要呢?读者可能会问: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上的问题吗?其他市场与教科书模型中所称的理想化、完全竞争市场难道没有很大不同吗?诚哉斯言。但是,如果我们将金融产品交易的领域称为“市场”,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将被转移到某些特征上,而其他特征就会被我们忽视。我们对这些领域公平监管的看法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关于如何规范市场公正性的广泛看法大致如下:市场应该具有公平的规则,可以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level playing field),并且它们还需要受到监管,以防止由于信息获取不平等,外部性或对完全竞争市场的其他偏离而引起的市场失灵。除了对正义的最低的、程序化的要求外,市场应该是自由的。这不仅使它们效率最大化,而且使人的自由最大化。随后出于分配正义考量的规制开始启动,通常是再次分配的税收形式,但这可能是以效率为代价的(例如参见Okun 1975;有关的批判性讨论,参见Le Grand 1990)。
关于这个问题的优点和缺点可以说很多,但在此不宜多言。因为应该明确的是,如果金融市场缺乏其他市场所具有的核心特征,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问一些更基本的、关于它们以及它们与正义的关系的问题。如果金融市场被视为市场的典型案例,就像在大金融危机之前人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这些问题就会被掩盖。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存在理想的“自由”金融市场,以至于所有与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背离都可以通过监管加以纠正。至少这样的理想是否会与我们目前货币由私人银行创造,而私人银行又得到中央银行背书的货币体系兼容,似乎就是令人怀疑的。
 易言之,指望通过监管来修复金融市场,以使它们更贴近苹果市场或橙子市场是徒劳的。我们不能指望“更自由的”金融市场也有助于增加个人的自由,事实上它们可能形成对个体自由的威胁,例如一个人在合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规划生活的自由。最后,我们不必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我们为正义而监管金融市场时,就必须要付出效率或经济规模的代价,这可能使为了正义的监管更加容易。
易言之,指望通过监管来修复金融市场,以使它们更贴近苹果市场或橙子市场是徒劳的。我们不能指望“更自由的”金融市场也有助于增加个人的自由,事实上它们可能形成对个体自由的威胁,例如一个人在合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规划生活的自由。最后,我们不必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我们为正义而监管金融市场时,就必须要付出效率或经济规模的代价,这可能使为了正义的监管更加容易。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提出有关金融市场制度结构的正义问题,而不必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正义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假设是否成立。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某些金融市场的某些方面,尝试使其尽可能接近教科书中的市场可能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在效率和平等之间也可能需要权衡取舍。从这些考虑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无论金融市场是不是市场),也许是要认真对待金融市场是什么或可以是什么的多样性:其产品、参与者和各自责任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出现泡沫的倾向。这意味着从正义的角度进行的评估也需要充分细化。并非金融市场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着同样的正义问题。一些市场运作良好,可以有效地分配资本和风险,而不会损害第三方或整个社会。实际上,在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市场的某些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影响地继续正常运转的。

金融市场有很多,它们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国家采取的不同的技术细节。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效率和公平的视角分辨出那些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
 并且可以淘汰关闭那些不好的。但是在实践中,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是高度关联的,各种关联又必须从效率和公平角度进行评估。这就是使得问题变得尤为复杂的原因之一。这也意味着针对不同的金融市场需要采用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改革方案。
并且可以淘汰关闭那些不好的。但是在实践中,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是高度关联的,各种关联又必须从效率和公平角度进行评估。这就是使得问题变得尤为复杂的原因之一。这也意味着针对不同的金融市场需要采用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改革方案。
 但是如果我们尝试简化这种复杂性,将会有可能停留在无法有效描述我们所面对的复杂社会现象的简单理论之中,而对于这种想要以过于理想主义的简单理论描述复杂社会现象的失败我们见得已然太多。
但是如果我们尝试简化这种复杂性,将会有可能停留在无法有效描述我们所面对的复杂社会现象的简单理论之中,而对于这种想要以过于理想主义的简单理论描述复杂社会现象的失败我们见得已然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