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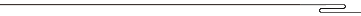
我们首先需要提供一个可行的社会制度解释。事实上,“社会制度”一词无论是在日常语言中,还是在哲学文献中都并不明确。然而,当代社会学在使用该词时却相当一致。通常,当代社会学家用这个词来指代那些自我复制的复杂社会形式,如政府、大学、医院、商业公司、市场和法律体系。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提出了一个经典定义:“社会制度是处于特定类型的社会结构之中的地位、角色、规范和价值观的复合体,并将人类活动组织为相对稳定的模式,针对的是生产维持生命的资源、再生产个体以及在一个既定环境中维持可行的社会结构等基本问题。”(Turner 1997,6)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制度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但有些并不是。
社会制度需要与公约、社会规范、角色和仪式等不太复杂的社会形式区分。后者是制度的构成要素之一。社会制度也需要与更复杂、更完整的社会实体区分,例如社会、政体或文化,任何一个特定的制度都是社会实体典型的构成要素。例如,一个社会或政体比一个制度更复杂,因为至少按照传统的理解,一个社会或多或少是自给自足的(例如满足其成员的各种基本需要的能力),而制度则不然。
社会制度通常以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更进一步讲,许多社会制度是组织体系。例如,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在现代,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特定组织形式形成的一个体系。此外,有些制度是元制度(meta-institutions):它们是组织其他制度(包括组织体系)的制度(组织)。例如,政府是元制度(Miller 2010,chap.12)。政府的制度目标或制度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包括组织其他制度(包括单独的或整体的),因此政府主要是通过(可强制执行的)立法来规范和协调经济体系。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世界,许多世界性的社会制度(例如全球金融系统)在各方面都超越了监管和协调其活动的元制度(例如各国政府)的边界和管辖权和/或执法范围。
根据对社会制度的目的论解释,社会制度的公共目的是公共物品,因为它们拥有以下三种属性(Miller 2010,chap.2):(1)它们是通过学校、医院、福利组织、农业企业、电力供应商、警察部门、银行、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养老信托等组织成员,即不同社会角色的共同行动而产生、维持或更新的;(2)它们是向整个社会提供的,例如清洁饮用水、清洁环境、基本食品、电力、银行服务、投资服务、法律服务、教育、健康、安全和安保;(3)它们应该被生产(或维护、或更新)并提供给整个社区,因为它们是可获得的(而不是仅仅是期望的),并且社会成员对其有共同的道德权利。
请注意,我们对公共物品(collective good)的定义不同于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对所谓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的标准概念。经济学家通常将公共产品定义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果一件产品是非竞争性的,那么一个人对它的享受并不妨碍或减少其他人享受它的可能性。例如,一个路标是非竞争性的,因为一个人用它来找路对他人同样地使用它没有影响。同样,如果一个人在享受这种产品,且其他人也都有权享受它,那么此产品即是非排他性的,国防就是如此。然而,我们对公共物品的定义并不是基于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而是基于其是联合创设的,以及其作为共同道德权利客体的规范性特征。因此,公共物品的概念在基于市场的社会制度和非基于市场的社会制度中都能适用。
这里一个重要的基本假设是,与许多经济理论相反,尽管自利是一个强大而普遍的驱动力,人类并非总是受个人理性自利驱动。
 然而,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强调的,道德信仰,是一种重要的额外的行为动机,特别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履行道德义务的时候,并且这不能被归于以牺牲他人目标为代价的自利(Sen 2002)(无论自利是如何被界定,例如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的目标或偏好)。在此必须指出,构成专业角色和制度性角色的义务往往也是道德义务,因此,履行自己的专业性和/或制度性义务往往也是在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此外,专业人员以及更广义的成熟制度践行者的标志是,他们能够将其身份的原则和目的内化,从而使他们能够超越其先前的、有限的、个人理性自利的目标和利益。
然而,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强调的,道德信仰,是一种重要的额外的行为动机,特别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履行道德义务的时候,并且这不能被归于以牺牲他人目标为代价的自利(Sen 2002)(无论自利是如何被界定,例如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的目标或偏好)。在此必须指出,构成专业角色和制度性角色的义务往往也是道德义务,因此,履行自己的专业性和/或制度性义务往往也是在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此外,专业人员以及更广义的成熟制度践行者的标志是,他们能够将其身份的原则和目的内化,从而使他们能够超越其先前的、有限的、个人理性自利的目标和利益。
理性选择模型(The rational choice model)假设理性的自利个体相互竞争,目前来看这似乎很对。但阿马蒂亚·森和其他人认为这一模型与现实还相差甚远(Sen 2002)。具体而言,它不允许个人为了集体自我利益采取理性行为,和/或根据社会产生的道德原则和目的而采取理性行动(参见Elster 1989,Miller 2001,chap.6),然而,这其实是人类集体生活的普遍特征,包括在经济领域。
在这层意义上,我们需要接受一个事实,即个体可以而且经常在个人行为决策中考虑集体目标和利益,对于这些作为团体或组织成员的个人而言,集体目标和利益是其铭刻于心并始终致力实现的。对于这种在个人行为决策中考虑公共目标和集体利益的情况,通常是基于行为人的职业身份或团体身份,例如作为银行家或者作为理财规划师的身份。简言之,个人将其所属职业团体或组织的集体目标和利益内部化了。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可以而且通常确实超越了拥有这些职业身份的个体先前的、有限的、个人理性自利的目标和利益。此外,有关个人的公众目标和利益可以而且经常被个人所接受,理由是从公正或至少公众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可取的。

关于个人理性自利模式的另一个观点是行为经济学家经常提出的,即人类在个人和集体自我利益方面往往是非理性的。例如股票市场上繁荣和萧条所展露的羊群现象(phenomena of herding)和认知偏差,以及那些不成熟的投资者缺乏知识,但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获得知识。
因此,制度设计需要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理性自利、非理性和道德都是人类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和动机,当它们发生冲突时,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一定会像通常那样支配其他动机。
基于以上分析,依据社会制度的规范目的论解释,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社会制度应当在其所存在的总体道德和法律框架中实现特定的制度目标。此外,它们是通过具体的制度结构和文化来实现的。因此,至少出现了三个突出的一般性规范问题,即:
(1)制度目标:各种金融市场的主要制度目标应当是什么?
(2)制度手段:
(a)结构,包括个人权利和义务:基于市场的产业结构是否能充分实现其制度目标。例如,是否存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机构?机构义务(如信托责任)和奖励(如薪酬待遇)的结构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更具体地说,这种结构是否符合相关的道德原则,是否有利于实现金融市场的主要制度目标?
(b)文化:组织文化是否存在道德问题?更具体地说,是否符合相关道德原则,是否有利于实现金融市场主要制度目标?
(3)宏观制度背景:所讨论的金融市场在更大的经济秩序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更具体地说,它应该与相关的其他社会经济制度有什么关系?华尔街应该为普通民众(Main Street)服务吗?
笔者认为,商业组织、金融市场或金融职业需要问的基本规范性问题与任何其他社会制度都是一样的,即:它的存在是为了提供什么公共物品?以资本市场为例,资本市场提供的最主要的公共物品,是以合理价格提供充足和可持续的资本供应。笔者在前面曾说明了直接的制度目标和最终的制度目标之间的区别:公共物品是社会制度的最终目的,但不一定是其最直接的目的。
就商业组织和市场而言,这些公共物品包括:(1)商品和服务买卖双方的协调;(2)一种产品或服务的数量足以满足有关人口的相关总需求。
 在这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无形”之手机制很突出(Smith 1776)。
在这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无形”之手机制很突出(Smith 1776)。
 “无形”之手运作的结果(公共物品)就是这个制度机制的最终目的(公共目的)(例如充足的住房、审计服务、退休储蓄或资本的充足供应等),利润最大化只是短期目的或者说直接目的。
“无形”之手运作的结果(公共物品)就是这个制度机制的最终目的(公共目的)(例如充足的住房、审计服务、退休储蓄或资本的充足供应等),利润最大化只是短期目的或者说直接目的。
在市场组织的案例中,利润最大化的存在增加了其复杂性,而在其他社会制度中则不存在。市场组织有三个公共目的:第一,组成性公共目的,例如汽车的生产,储户资金在银行的积累,用于投资的储蓄积累,以备将来使用的储蓄积累;第二,公共物品,例如运输、储蓄安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退休人员收入;第三,利润最大化。而这些公共目的并非其他社会制度所必需。
组成性公共目的不一定是公共物品。以所谓的有毒金融产品(toxic financial product)为例,一揽子次级抵押贷款就是如此。这些金融产品的生产是投资银行成员的公共目的。然而,事实证明,这些产品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对许多群体造成了巨大伤害,包括在持有这些资产的银行受到政府救助时,最终受到伤害的纳税人。因此,这一公共目的实现的并不是一种公共物品,反而是恰恰相反的。
此外,公共物品、利润最大化作为两大共同目标,两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竞争性。对公司而言,利润最大化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根据我们对社会制度的解释,利润最大化目标在“无形”之手的作用下最终会实现公共物品的目标。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对于“无形”之手作用的经验主义的主张是有争议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被证明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对于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的分析中所看到的一样。再例如,完全依靠市场机制为澳大利亚急需的基础设施提供投资资金的尝试显然也是失败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的是社会制度规范性的一个方面,即制度目标,特别是制度提供(或应当提供)的公共物品。然而,这里还有另外两个规范层面值得注意。第一,机构的活动存在着道德限制。在这个层面上,机构的活动与非机构的个人活动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对谋杀、欺诈和盗窃的禁止也能对机构的活动产生制约。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特定制度的结构,牢记制度目标应该为结构指明方向。在一般层面上,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一个制度是否应该是一个基于市场的制度。这不应该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以市场为基础的结构与非以市场为基础的结构,哪个最能实现制度目标?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和非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之间的区别并不一定是严格的二分法,还有可能是混合型的,即利用市场机制但不完全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强制退休储蓄体系和资本市场所依赖的金融基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例子。但重申一下:根据我们对社会制度的规范目的论解释,一种制度应该是完全以市场为基础的、非以市场为基础的,或者是两者的混合体,是一个需要借助于公共物品来解决的问题,该问题在于这三种模式中哪一种最有效地产生公共物品。
进一步的结构性问题涉及市场参与者的规模(例如“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利益的结构性冲突(例如评级制度对投资银行的金融产品进行评级,而投资银行又为评级机构提供资金)以及本身就是“游戏参与者”的监管者,例如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追求伦敦城的特殊利益,可能会牺牲其他金融中心的利益。同样,根据规范目的论解释,这些结构性问题应该通过求助于相关市场(包括全球市场)应该实现的公共物品来解决。“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们对国际金融系统构成了威胁,因此也对该系统应该实现的公共物品构成了威胁。出于同样的原因,利益的结构性冲突需要消除。关于不公正的监管者,需要指出的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集体利益不能仅仅是伦敦城的利益。
如前所述,存在着各种制度上相对的道德性权利义务(与先于制度存在的道德权利和义务,即自然的权利和义务,或以其他方式超越特定制度的道德权利和义务相反),这些权利和义务至少部分地来自社会制度生产的公共物品,事实上,这些权利和义务是特定制度性角色的构成要素,例如消防员、银行家、基金经理或财务顾问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制度性权利和义务(也是道德性权利义务)是由制度性角色构成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具体制度结构。既然制度结构是或应该是实现其制度目标的重要手段,那么,制度的道德权利义务则是手段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从制度的终极目标出发的,它定义了公共物品。因此,关于财务顾问是否有权收取佣金而不是服务费的争论,在这种观点下,应该从制度目标出发在对两个不同的职业权利义务的结构进行分析后予以解决。
这些结构化的道德权利和义务组合是在制度上相关的。即使它们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一直以来的优先人权(例如老年人对食物、衣服和住所的需求)。它们的确切内容、强度、适用范围(例如管辖权、国家领土、特定经济体)等只能参照其制度安排来确定,特别是根据它们对这些制度安排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贡献来确定。因此,当代澳大利亚老年人在退休期间获得一定金额报酬,这一基础权利与澳大利亚养老金和退休金系统(以及该老年退休人员在工作期间所作的具体贡献)一直以来都相关。
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区分个体的制度性(道德)权利和共同的(joint)制度性(道德)权利之间的区别。共同的道德权利是附属于个人的道德权利,但却是共同行使的。例如,房屋的共有人可能有对房屋的共有权利,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单独占有房屋的权利,但每个人只有在满足另一方也同样拥有这项权利的条件时拥有这项权利。共同权利需要与普遍的个人人权或自然权利(相对于个体的制度性权利)加以区分。生命权是普遍的个体人权的一个例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权。然而,由于个体生命权完全取决于个人,因此,一个人拥有生命权并不取决于其他人对该权利的占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时共同行动(joint action)实现的目的不仅仅是一个公共目的,它也是一个公共物品。这里所说的公共物品,只是指集体或共同生产的物品,而不是指它是由集体或共同来消费的——它可能是而且经常是被个人单独消费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联合行为很可能会生成一个共同权利。共同道德权利与公共物品的关系是什么?公共物品是一种已实现的公共目的,而实现这一公共目的的参与者,即生产这种公共物品的贡献者,拥有对这一公共物品的共同权利。
不难看出,为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会有权利得到这样的物品,因为他们是对公共物品存在或继续存在而负责的人。在这方面,可参考一家建造公寓楼并出售以获取利润的公司的股东、董事会成员、经理和工人(股东、高管和雇员)。董事会成员、经理、股东、建筑工人共同享有从共同生产公寓的销售中获得经济报酬的权利(尽管每个人有权取得的金额可能因人而异,取决于其个人贡献的性质和程度)。此外,如果他们共同享有的经济利益的一部分被输送到比如说退休基金中,那么他们对这些基金享有共同的权利(尽管同样,每个人有权取得的金额可能因人而异,这取决于他们个人长期以来的贡献程度)。同样清楚的是,如果一个参与主体对公共物品有权利,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他人也有权利。也就是说,对于公共物品的权利是相互依存的。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工人(提供劳动)、经理(提供领导)和投资者(提供资本):他们对所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拥有共同的权利。
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报酬取决于所签订的具体合同,包括雇佣合同。然而,这些共同的道德权利并不等同于或可还原为基于法律契约的道德权利。相反,从规范上讲,这些合同预设了有关的共同道德性权利。例如,正是因为一个建筑工人为公寓楼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所以他在道义上有资格获得工资。此外,当有人主张某项具体的合同给付公平或不公平时,合同与基本的共同道德性权利之间的这种规范关系就会成为证据。因为合同可能反映也可能不反映一个人对集体利益生产的贡献,这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因素(特别是权力关系)。例如一些公司异常慷慨地向管理层发放高额薪酬,包括不得不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的投资银行。在许多情况下,管理层薪酬与对公司生产的公共物品的贡献,甚至与公司创造的利润之间没有任何关联(Gregg and Tonks 2005)。
越来越多的监管者和其他人认识到,制度文化是个体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
 然而,这些讨论通常集中在不道德或非法的行为和对文化的有害影响上,例如最近基准操纵案例中的交易员文化。然而关于文化(包括文化的道德和不道德层面)与制度目标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却很匮乏。一个组织的成员是否将该组织理想的目标和原则内化,并且确立一些可取的目标和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结构问题,例如消除结构性的利益冲突,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制度文化的问题。制度文化反过来又取决于期望目标和集体道德责任(参见Miller 2015)的内化程度,即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明确的制度机制(例如,职业伦理方面的正式继续教育计划、举报人保护计划、不鼓励过度冒险的薪酬体系)和隐性做法(例如承认错误的经理、敢于表达担忧的雇员)在组织中嵌入实现期望目标和避免腐败行为的集体道德责任。
然而,这些讨论通常集中在不道德或非法的行为和对文化的有害影响上,例如最近基准操纵案例中的交易员文化。然而关于文化(包括文化的道德和不道德层面)与制度目标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却很匮乏。一个组织的成员是否将该组织理想的目标和原则内化,并且确立一些可取的目标和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结构问题,例如消除结构性的利益冲突,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制度文化的问题。制度文化反过来又取决于期望目标和集体道德责任(参见Miller 2015)的内化程度,即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明确的制度机制(例如,职业伦理方面的正式继续教育计划、举报人保护计划、不鼓励过度冒险的薪酬体系)和隐性做法(例如承认错误的经理、敢于表达担忧的雇员)在组织中嵌入实现期望目标和避免腐败行为的集体道德责任。
另外,一个组织中流行的风气或文化,或者一个部门核心的意识观念,可能会淡化预期的制度目标和其他伦理考虑,而只追求个人的私利。那么,当个人的私利凌驾于对伦理原则的遵守,甚至是法律所规定的原则时,也不应感到惊讶。尤其是在存在巨大诱惑而被发现和定罪的风险很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例如在监管部门存在结构性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银行交易员在巨额奖金的诱惑下操纵了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