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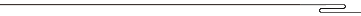
本部分首先介绍了能力方法的要点,然后说明能力方法的使用如何能够统一迄今为止一直困扰我们的三种监管理由。这部分内容将成为第五部分中所提出的市场监管具体能力框架的哲学基础。
能力方法的基础是能力和功能之间的区分。功能可以定义为“行为(doing)”或“存在(being)”:拥有健康的身体、受过良好的教育、写一本书、喝一杯咖啡都是功能的例子。能力指的是做这些事情或处于这些状态的能力。当一个人拥有一种能力,比如说喝咖啡,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把这种能力“转化”为“行为”或者“存在”,选择自己可以实现的行为方式。因此,一个基本要素是,当个人被社会或政府赋予某些能力时,他们有自由决定将哪些能力转化为功能。功能和能力这两个术语非常灵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定义这些能力时的概括程度。一般而言,每种能力都有内在(internal)和外在(external)两个方面的内涵。内在方面是指人以该能力所指示的方式发展的能力,包括人的生活能力、性情和技能。外在方面指的是对行为主体开放的机会,例如法律允许的接受高等教育或获得医疗保障的机会。这两个方面都可以有程度上的不同,所以当我们准备说一个人“具有某项能力”时,这是一个进一步的规范决策问题:这需要判断在该状况下给予多少能力和机会是必要的。
“行为能力”一词表明了这种衡量正义的标准。阿马蒂亚·森认为,任何关于正义的观点都为“什么样的平等(equality of what)”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Sen 1979,1992,2009)。与资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衡量标准(见下文)相反,能力方法提出将一个公正的社会设想为一个公民拥有“能力平等(equality of capabilities)”的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拥有一套基本能力的平等权利。然而,要将这一总体出发点发展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正义理论,还需要进行两个步骤。
首先,需要挑选出一套基本能力。玛莎·努斯鲍姆基于其新亚里士多德式(neo-Aristotelian)的人类繁荣(human flourishing)——后来称为人的尊严——主张十项基本能力,如生活能力、身体完整性、感官、想象力和思维、娱乐、实践理性、娱乐和其他能力(Nussbaum,2000,2006,2011)。也有其他学者提出了选择基本能力的其他标准。在其他地方,笔者主张使用自由和自主的标准作为能力方法的基础。这里的基本理念是积极的自由:如果个人要真正自由,他们需要拥有足够的能力和选择权去选择和实现他们自己的生活目标。这既需要他人不仅不干涉自己的选择,而且还需要作出积极贡献,以提高个人利用这些选择的能力(Claassen 2017a)。
其次,哪种分配规则能够与能力方法相适应?在正义理论中,已经有许多种分配规则被提出:(机会)平等主义、优先主义、充分性主义或最大化规则,这些理论都有无数变种。能力标准本身并不决定任何分配规则。尽管如此,许多作者将能力方法与“充分性原则(sufficientarian rule)”相结合(Nussbaum 2006,Schuppert 2014,Axelsen and Nielsen 2014)。每种能力的供给都应该达到一个阈值(thresholds)。如果低于这个水平,民众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如果高于这个水平,政府就没有必要介入了(这些都是对于能力的高级需要)。在其他地方,笔者已经为充分性原则的立场进行了其定性的论证(Claassen 2017b)。设置阈值对于能力方法下的监管理论非常重要。
如果论证得当,正义的能力理论将是其两个主要对手——资源主义和功利主义标准——的有力竞争者。能力方法应被看作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一方面,资源提供了能力的输入。个人所掌握的资源是决定这个人能力的主要因素。然而,各种社会的、个人的和环境的影响能力的转换因素,则决定着一个人达到某一能力水平需要多少资源。因此,一个身体残疾的人可能需要比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更多的资源才能达到相同的水平,例如行动能力。能力理论者认为,资源只是手段,而能力则是生活中的目标。因此,应从后者的角度来定义正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基于人与人之间在转换因素上的差异,一种纯粹的资源主义的方法,给人们同等的资源分配,最终会造成资源与其能力的需求之间不相匹配。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将某些能力转化为功能后,他会以某种方式对自己的功能产生幸福感、快乐感或满足自己偏好的满足感,因为他的功能是以某种方式附加的(“听音乐让我快乐”)。然而,这些效用水平(幸福感产出)也与功能有不同的关系。那些具有更悲观性格的人需要更多或更高层次的能力或功能,才能体验到与更乐观性格的人相同的效用水平。在这里,能力论者认为,人们应该对自己的主观幸福感负责。这一点尤其重要,否则有些人可能会声称他们需要比别人更高的能力水平(因此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达到同样的福利水平(要求过高的问题),而另一些人可能会要求得太少,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用很少的资源来满足(动态偏好问题)。因此,介于资源和效用之间,能力是衡量社会正义的正确标准。
现在让我们回到监管问题。能力理论者对社会状态的评价是关于基本能力的集合是否达到阈值水平的问题。与前面所说的经济方法不同,能力方法没有区分市场活动前的初始分配和基于市场运行的分配结果。充分性能力标准被用来评估两者的规范正确性。充分性的能力标准也确实建立了一种二元对立,即低于标准的分配和高于阈值的分配之间的对立。如果一个人或一群人低于能力标准,就需要政府采取某种形式的行动,使他们高于该标准。如果一个人或一群人在阈值之上,则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这意味着这些人可以在阈值之上自由行动。鉴于能力有助于促进人的自由和自主,因此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划分:一个人的能力在阈值以下,则不称其为自主能动的人,若其能力在阈值以上,他便达到了自主的能力标准。我们可以类比法律行为能力来思考这个问题,法律行为能力是赋予除了未成年人和严重精神障碍者之外的所有人的能力。同样,能力理论也着眼于自由和自主生活所需要的能力。低于这个阈值,个人仍需要发展自己的自主能力,高于这个阈值,他们就可以自由选择行使其能动性,这些活动给他们带来满足、福祉或他们希望的任何其他东西(Claassen 2016)。
 自主能动性的发展和行使的二元对立与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对立是相关的。能力理论并没有先验地认为市场是好的或坏的制度,而是从主体能动性的发展和行使的双重角度评估市场对能力提升的贡献。
自主能动性的发展和行使的二元对立与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对立是相关的。能力理论并没有先验地认为市场是好的或坏的制度,而是从主体能动性的发展和行使的双重角度评估市场对能力提升的贡献。
一方面,市场与其他制度一样,可看作是服务于能力正义的工具。市场可能是生产某些资源的最有效制度,而这些资源又是赋予人们基本能力所必需的。粮食市场可能是为民众生产粮食的最有效途径,因此,它能够实现人们获取营养的基本能力。如果某一特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实现一项或多项基本能力的必要条件,那么该市场便要受到监管。尤其重要的是,市场参与者(生产者、消费者)必须能够在市场制度下基于其市场角色取得自主性地位。要做到这一点,市场需要运转良好,而这需要解决经济学理论中常见的市场失灵问题。然而,从能力的角度来看,补救市场失灵的理由不是实现福利的最大化,而是实现市场主体的基本能力。由于规范标准不同,我们可以预期,这将导致对于这些市场失灵的诊断与主流经济学理论截然不同。市场需要能很好地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但如何认定“很好的参与”则取决于人们对市场活动结果的设想(更多的内容在第五部分)。
另一方面,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并非能力正义的必要工具,对于自由地行使自主能动性而言,社会领域才具有内在价值。在这个语境下,市场活动与私人领域其他活动(如家庭或民间行会的活动)是一样的。除了不损害其他人的基本能力(即使其他人的基本能力低于阈值)这一消极条件之外,对市场活动不应施加限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能力理论没有对高于阈值的行动提出任何积极条件,但关键是要有一个高于阈值的行动领域。如果没有,发展能力的全部意义就会变得多余。在这里,政府监管的作用不是干预市场,而是使市场本身的约束得以实现。所有捍卫经济自由作为基本自由的人都强调保护像这样一个平台的市场(Tomasi 2012)。在能力视角下,经济自由是保障人取得市场参与者这一社会角色的能力。因此,这一要求与前一要求不同,但两者都与能力理论相关。实际上,这两者都是特定市场中必须权衡的考虑因素。
本部分揭示了能力方法视角下的市场起始于对个体自主性形成的基本关注。这种关注能够整合分配效率、分配正义和父爱主义等经常被作为市场监管的理由而被提及的因素。对市场活动前的禀赋与偏好进行调整和矫正,被认为是实现基本能力之必需。基于同样的理由,提升市场效率——市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在这个层面上是有价值的。总的来说,相比于我们仅论证能力指标优于效用指标的常用理由,例如动态偏好和高级品味,关于监管的功利主义经济理论往往更为复杂且差异更大。这种差异主要在于不同的理论或者方法究竟如何理解人的自主能力的形成。对于功利主义者/经济学家来说,一个人的偏好和禀赋是主要的,因为这个人被认为已经成为一个具备完全自主能力的人。就能力理论而言,一个人的偏好和禀赋只能在他的自主能力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决定他的自由行为,然而在他参与市场交易的时候可能达到了这种情况,也可能没有达到。在没有达到这种情况时,需要允许对偏好和禀赋进行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