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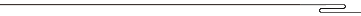
在当今我们理解和捍卫人权的同时,承认和保护人权已被广泛认为是法治的内在要素,但有关市场(包括金融市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辩论仍在继续。它是历史和当下政策辩论不能回避的议题,并影响着不同政党的选举议程。在建设一个公平和公正社会的过程中,正义问题是不能和市场问题相割裂的。这对于制定适当的国内和国际政策和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一种强烈的不公正感,引发了从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伦敦和西班牙的“愤怒运动”
 等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以及随后在欧元区一些国家崛起的政治运动或政党的发展,特别是希腊的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
等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以及随后在欧元区一些国家崛起的政治运动或政党的发展,特别是希腊的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
 这些都反映了整个社会从平等和不平等的角度对正义与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的重新审思。
这些都反映了整个社会从平等和不平等的角度对正义与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的重新审思。
虽然这些抗议与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密切相连,但其所涉及的问题并不新鲜。事实上,关于社会正义、团结、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的辩论贯穿20世纪欧洲福利国家建设的历史。
被称作英国“福利国家之父”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
 是1942年12月7日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又称《社会保险和联合服务报告》)的主要作者,该报告奠定了1945—1951年工党政府社会福利改革中立法方案的基础。从那时起,全面的社会保险(附带免费的全民医疗服务)就成为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的一大特色,瑞典、西班牙等西欧国家也纷纷效仿。然而,考虑到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负担渐重,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压力巨大,又鉴于人口、金融和财政的发展下公共养老金和福利体系的需求,这些社会保障制度在许多方面不得不进行削减甚至面临取消(参见Davis and Lastra 2016)。
是1942年12月7日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又称《社会保险和联合服务报告》)的主要作者,该报告奠定了1945—1951年工党政府社会福利改革中立法方案的基础。从那时起,全面的社会保险(附带免费的全民医疗服务)就成为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的一大特色,瑞典、西班牙等西欧国家也纷纷效仿。然而,考虑到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负担渐重,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压力巨大,又鉴于人口、金融和财政的发展下公共养老金和福利体系的需求,这些社会保障制度在许多方面不得不进行削减甚至面临取消(参见Davis and Lastra 2016)。
回到关于人权的辩论,从霍菲尔德(Hohfeldian)的意义上讲,人权存在于民族国家层面,国家对其公民授予或赋予权利,以换取其遵守相应的义务,如守法、纳税等(Hohfeld 1913,1917)。然而,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常常跨越国界。因此,人权与全球金融市场和机构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互动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随着经济学思维中“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理论的发展而更加突出。
经济人理论认为,在概念分析中可以将人视为纯粹经济理性的存在。
 虽然出于建模分析的目的,将理性“经济人”假设成代表现实中的某些方面可能是有用的,但也有必要退一步,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虽然出于建模分析的目的,将理性“经济人”假设成代表现实中的某些方面可能是有用的,但也有必要退一步,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从这一角度来看,就有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后一种观念包含了这样一种观点:每个人都有一系列的潜能,社会有责任发展这些潜能,既为个人的利益,也为社会整体的利益。
从这一角度来看,就有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后一种观念包含了这样一种观点:每个人都有一系列的潜能,社会有责任发展这些潜能,既为个人的利益,也为社会整体的利益。
 遗憾的是,正如本章第三部分所讨论的那样,这种更广阔的视角在经济和金融市场分析中常常被忽略。因这种分析而成的制度设计导致社会信任的丧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遗憾的是,正如本章第三部分所讨论的那样,这种更广阔的视角在经济和金融市场分析中常常被忽略。因这种分析而成的制度设计导致社会信任的丧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混乱,包括长期的低经济增长率、年轻人的高失业率、住房获取困难以及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这些共同造成了政治动荡,使得民众对现有的政治和金融体制产生了相当大的失望,并普遍转向支持更极端的政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幻想的破灭,对金融机构和市场越来越强的不信任感,特别是由于金融市场未能为整个社会创造财富。
某种程度上以上这些现象反映了任用技术官僚治理市场的范式在民众沟通和吸引民众参与上的失败。迄今为止,人们一直信任由一小部分专家来指导和管理经济和市场。金融危机及其后续的一系列问题暴露了这一范式的严重缺陷,而一些政治上的失败又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许多金融市场已经与其所属的社会失去了联系。证券交易本身很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敛财的工具,无法满足社会对于金融功能的需求(参见例如Turner 2016,42ff.)。这种后果已经体现在民众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感受以及共同体意识的丧失中。
许多公民认为自己受制于“不公正”力量。通常,这种看法来源于阴谋论和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臆想。这种归咎于“他人”的认知错位,往往会导致不满和极端主义的增长,以及对个体价值的忽视。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担忧可以形容为一种“失控(loss of control)”的感觉。有一种看法认为,市场交易已经失去了可预测性和选择自由。一直存在的强大的市场和经济力量似乎突然被释放出来。市场经济带来的变化中许多是有益的,在几十年间让许多人受益,例如使印度和中国的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推动了卫生和医疗方面的进步,改善了农业和城市发展,为许多人提供了更多选择。然而,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并不平衡,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在许多地区,来自社区或福利国家机构的确定性和支持已经瓦解。这导致人们对经济变革的性质及其与人的尊严和社会平等的关系产生了疑问。

罗纳德·德沃金试图将“平等”划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要求按照“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对待个人,其二是与“具有发展和实现能力的人的属性”相关的形式(Guest 2013,197)。前者是通过获取资源的自由来解决的,而后者则让个人自由选择他们希望的生活方式(Dworkin 2011,356—363),在这里,他考虑的是有关“资源平等”的问题。德沃金认为追求正义需要一种“包容的伦理和道德理论”(Dworkin 2011,419)。评估人们应当如何生活,包括他们在经济中的关系,需要“一些有效的道德信念……它们对于生活中的责任至关重要”(Dworkin 2011,420)。
为了与上文相联系推进这一讨论,我们需要考虑哪些人权与这一分析最为相关。人权通常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绝对权利(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身体完整权);另一类是相对权利(如受免费教育的权利、获得清洁水的权利、获得充足食物的权利等)(例如参见Raz 2015,225 and 229—231,拉兹在其中质疑第二类权利是否真的是“人权”)。第二类权利被描述为需要“共存义务(compossible duties)”作为权利的相对方,因为绝对权利可以通过限权和约束来满足,而相对权利则需要承担义务的人采取“积极行动”(O'Neill 2015,77ff.)。后一类权利可被称为“愿望性的”,而满足这些权利的义务则取决于相关机构实现这些权利的相对能力。但是,这种形式的概念化可能太过局限,它似乎立足于模糊了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什么是可行的经济分析来认识这一问题。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提出了类似批评,认为尽管从经济角度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析固然重要,但只关注收入和财富的经济效果是不够的。森主张创造“人们过上他们期待的生活的能力”更为重要(Sen 1999,18)。个人和团体的能力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自由”得到提高,包括疾病防治、健康改善、教育机会以及参与政治经济活动等(Sen 1999,15—17)。
 这能够给予人们选择:能力的提升能够为个人和社会提供机会,以帮助他们获得尊严。他们个人能力的提升,又会回过头来影响与他们有关的社区或领域(Sen 1999,15)。能够参与市场本身就是一种“自由”,是人权的一个方面,应被视为一种解放。
这能够给予人们选择:能力的提升能够为个人和社会提供机会,以帮助他们获得尊严。他们个人能力的提升,又会回过头来影响与他们有关的社区或领域(Sen 1999,15)。能够参与市场本身就是一种“自由”,是人权的一个方面,应被视为一种解放。

因此,无论是金融领域还是其他方面,参与市场的权利和能力是个人能力和人权的基础。如果市场不能让个人和团体参与,不能支持他们的能力发展,可能就会滋生对于市场的不信任和疏远。如前所述,金融危机后的金融市场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市场对于其所在的社会而言,需要被认为是公平、连通且有益的。这意味着,市场中的个人需要遵循道德操守,市场也需要形成对社会目的、透明度、社会关联度以及责任承担等进行清晰易懂解释的文化。这些核心要素在我们即将讨论的2012年联合国“外债与人权问题指导原则”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