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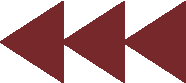
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宗教与经院哲学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人类的探索精神被扼杀了。古代科学的萌芽刚刚破土而出,就遭到了中世纪严寒的摧残。
391年罗马皇帝下令禁止一切异教,禁止学习数学、天文学。415年女数学家、天文学家海帕西娅被基督教暴徒袭击,暴徒们用贝壳剥掉了她的皮肤,然后把她烧死。教会还宣布数学是“魔鬼的艺术”,下令把数学家当作异教徒驱逐出境。从此神学坐在最高的宝座上,理性、科学都成了它的婢女。科学一旦超出了神学规定的范围,就立即成为镇压的对象,而经院哲学则是神学的帮手。教皇庇护十世说:“全部圣经中都有神的灵感,因此里面每一处都不可能有不正确的地方。”他们鼓吹盲目信仰,反对人们研究自然。奥古斯丁说:“在家里坐着的时候,与其将注意力被蜥蜴抓住苍蝇或者蜘蛛用网套住苍蝇这些小事吸引过去,莫如不要忘记赞美无所不能地创造出万物的神。”德奥图良更直截了当地说:“在基督以后,我们不需要任何求知欲,不需要作任何研究。”
经院哲学一方面用抽象、烦琐的推理来论证神学教条,一方面又引诱人们从概念到概念,沉溺于玄想空谈之中。天使是否要睡眠?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这些荒唐的问题居然成了长篇论文的主题。他们可以就鼹鼠是否长眼睛的问题,引经据典,争论不休,却没有人亲自捉只鼹鼠来看个究竟。
教会还用暴力来统治人们的思想。1220年教皇洪诺留三世下令设立宗教裁判所,这是宗教审判科学、愚昧审判理性的法庭。宗教裁判所规定:只要有两人作证,控告即可成立;一切有利于被告的证词都不能成立,证人若想收回证词,就视为同谋;被告不认罪,就反复用刑拷问,再不认罪就处以火刑;认罪后终身监禁;被告也可不经审判就处死。1327年意大利的阿斯科里认为地球是球形的,就被用火烧死。1611年有一个主教说虹是水滴反光的结果,就被开除教籍,死于狱中后,尸体还被砍碎。有人甚至因为说事物会变化,过去人们的生活同现在不同,也被割了舌头以后烧死。15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官托尔奎马达一人就判了1万多人火刑,在他几十年的一生中,平均每天都要烧死一个“异教徒”。
伴随着神学与经院哲学而来的,就是无知与愚昧。博韦在《史鉴》中说:“一切聪明的知识,如果不加进神的知识,都是没有用的。”535年基督教徒科兹梅在《以基督教徒所不容怀疑的圣经证据为基础的基督教的宇宙形象图》中写道:“我们要跟先知者伊萨耶同样地说,笼罩着宇宙的天具有圆穹的形状;我们要跟约夫同样地说,天和地是连成一片的;要跟莫西同样地说,地球长比宽大些。”这已经倒退到了毕达哥拉斯以前的水平。亚里士多德《论天》的注释者亚普利契则说:行星的真正运动是不可能认识的,人们所看到的那些运动只不过是幻影而已。许多修道院把古代学者写在羊皮纸上的著作刮去,以便抄写圣经。到7世纪末,西班牙首府托利多的主教图书馆内,古希腊罗马的著作只剩下西塞罗一个人的作品了。教会甚至反对人们学习文法。有个教会人士想学点这方面的知识,罗马教皇知道以后,就写信发出警告说:“你好像在学习文法——我不能不脸红地重复这句话。我很悲哀,我在叹息。请你证明你不是在学习无聊的庸俗的科学吧,这样,我们就将赞美我们的神。”992年在罗马举行宗教会议时,竟找不到识字的神职人员来做记录。
在神学的粗暴干预下,医学本身似乎也成了奄奄一息的病人。6世纪下半叶法国格列戈里主教说:敬拜死去的圣徒能治百病,吃神龛上的一撮土能治胃病,舐圣徒墓前的栏杆能治喉痛,任何东西只要放在圣徒墓周围,就能得到神奇的能力,能治百病,驱百邪。中世纪的欧洲流行病非常猖獗,每年死于天花的就有150万人,人的平均寿命只有25岁。
再看看著名学者阿尔伯特的“研究成果”吧:“取一克蔷薇、一克芥子和一只老鼠腿,把它们挂在树上,树就不再长果子了。假如把上面这些东西放在鱼网的附近,那么鱼就会聚集到网里来。”
但是到了11、12世纪,随着城市的形成,一批世俗大学出现了。除1100年建立的巴黎大学培养神学人员以外,著名的世俗大学有:波伦亚大学(1100年)、帕多亚大学(1222年)、牛津大学(1229年)、布拉格大学(1348年)、维也纳大学(1365年)、海德堡大学(1386年)、科隆大学(1388年)、爱尔福特大学(1392年)、莱比锡大学(1409年)等。为了满足人们追求世俗知识的需要,许多古希腊著作的阿拉伯译本和评注本,通过西班牙人传入了欧洲,陆续被翻译为拉丁语。1200~1225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被重新发现了,大批的翻译家也把它陆续译成拉丁语。由于他们的工作,欧洲人才重新读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物理学》、《动物学》,托勒密的《至大论》和《光学》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中世纪的欧洲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世界。他的著作中的深奥哲理和丰富内容,使多少年来一直缺少精神食粮的欧洲人大开眼界,惊叹不已。教会感觉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个威胁,1209年巴黎的教会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列为禁书。可是人们追求世俗知识的愿望是不可遏制的,于是教会改变了策略,1225年巴黎大学把亚里士多德著作列为必读书目。1231年教皇格里戈利九世下令重新修订与评注古希腊的著作。神学家与经院哲学家根据教皇的旨意,就尽量把古希腊的著作加以歪曲,使其能同神学的教义一致。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就抓住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消极的东西,加以歪曲利用。列宁说:“僧侣主义扼杀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活生生的东西,而使其中僵死的东西万古不朽。”
 经过这番“加工”的亚里士多德,也被奉为基督教世界的思想权威,一个“仅次于上帝的人”。
经过这番“加工”的亚里士多德,也被奉为基督教世界的思想权威,一个“仅次于上帝的人”。
12世纪的欧洲学者把古希腊著作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在一些学校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科学和哲学著作被当作主要教材。可是神学家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观点(如世界永恒、自然变化有规律、灵魂不比肉体活得更久等)同教义相悖。1210年桑斯地方宗教会议颁布命令,禁止在巴黎阅读亚里士多德著作,违者开除教籍。根据教皇约翰二十一世的命令,1277年巴黎主教坦皮尔经过调查,列出219条禁止讨论的命题。例如,第9条:“没有最初的一个人,也没有最终的一个人;相反,永远是人类繁衍的后代。”第34条:“第一因(即上帝)不可能创造多个世界。”第35条:“除非作为一个父亲和一个人,上帝(单独)不可能造人。”第49条:“上帝不可能使宇宙(即天空和整个世界)作直线运动,因为这会留下真空。”第153条:“懂了神学,什么也懂不好。”第154条:“世界上唯一有智慧的人是哲学家。”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1255年巴黎大学的教材目录还是包括了当时所有能得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牛津大学一直可以注释和研究亚里士多德著作。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1255年巴黎大学的教材目录还是包括了当时所有能得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牛津大学一直可以注释和研究亚里士多德著作。
世俗知识的传播,必然给沉闷的欧洲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欧洲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经院哲学不满了,他们要求从经院哲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投入大自然的怀抱。罗吉尔·培根就是他们的代表。
罗吉尔·培根(约1214~约1292),牛津大学教授,是一位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尖锐地批判了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及其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指阿奎那的体系。他说阿奎那的体系是在圣经与亚里士多德著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庞然大物,但并未真正懂得圣经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这个体系是摇摇欲坠的,因为它缺少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他认为盲目地崇拜无根据的权威,是认识真理的一个巨大障碍。显然阿奎那的体系以及被阿奎那歪曲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权威。
他大声疾呼:实验胜过一切思辨,实验科学是科学之王。他说,对于前人的说法,无论它的推论如何有力,都不能盲从;判定前人说法是否正确的方法只有实验,因为实验是认识现象的原因,只有实验才能把自然界所产生的效果、人工所产生的效果和欺骗所产生的效果区别开来。他提出研究学问的原则是:不盲从权威,不轻信别人,真理来自实验,一切皆应有证明。
他认为科学的基础是几何学与光学,曾提出过关于望远镜、自动船、潜水艇、飞机等设想,但均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他曾做过一些实验,尽管这些实验大部分是关于炼金术的,但也引起了教会的惊恐。他们说罗吉尔·培根要把魔鬼释放出来了,叫嚷要“打倒魔法师”。教会说彩虹是上帝的手指在天空中划过时留下的痕迹,他却说是阳光照射小水滴的结果。他的这些言行是教会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便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把他关进了裁判所。他在受审时说:“不能因为你们不懂得这些东西,就说是魔鬼的工作。”他在监狱里被关了14年,释放后不久就离开了人间。罗吉尔·培根的思想是战士的呐喊,犹如雄鸡破晓的啼鸣。
这次以世俗大学的出现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为标志,以罗吉尔·培根为号手的小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经过教会、经院哲学的歪曲,原来起着开阔人们眼界、活跃人们思想作用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却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这一历史命运的变化以及罗吉尔·培根所受到的挫折,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次曲折。它生动地说明了封建思想意识的顽固性,说明了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没有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中世纪的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思想统治是不可能彻底摧毁的。但这次小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毕竟是即将到来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前奏。它庄严地向人们宣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科学只可能沉寂,但不可能死亡。在黑暗的中世纪,仍有人以不同形式在思索自然之谜,提出了一些零星的科学思想。虽多为思辨产物,但对后人不无启迪。
运动学是中世纪科学的主流。从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有人提出了“内阻力”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物体都是水、土、火、气四种元素的混合物,占优势的一种元素决定物体自然运动的方向。中世纪则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自然运动的方向是由轻元素的合力与重元素的合力之比决定的。所占比例大的合力是动力,所占比例小的力是阻力。对向下运动的物体来说,重为动力,轻为阻力;对向上运动的物体而言,轻为动力,重为阻力。阻力存在于物体之中,称内阻力。若两个物体的内阻力相同,则它们以相同速度下落。14世纪的布雷德沃丁等人认为,两个重量不同的同质物体在虚空中以同等速度下落。因为是同质物体,所以每一单位的物质都有同样的重与轻之比(动力与内阻力之比),在这种情况下物体自由下落的速度同物体的重量无关。
中世纪运动学的主要贡献是冲力说。6世纪的菲罗波诺斯最早提出冲力的概念,认为力给予物体的冲力可使物体运动。冲力可使飞箭穿过真空,无需亚里士多德所假定的空气在填补真空时对物体所产生的排挤。冲力说在13世纪开始流行。14世纪的波内图斯对冲力的理解是:“在一个强制运动中,一些非永久的、短暂的形式注入到运动体内,因此只要该形式持续存在,虚空中的运动就是可能的;当它消失时,运动便停止。”
 巴黎大学校长布里丹(约1300~1360)认为冲力是由初始推动者传给运动物体的动力,其强度用物体的速度和质量量度。“基于这个正确的假设,他解释这一事实:如果同样形状和体积的一块铁与一块木头以同样的速度运动,铁块将运动较长的距离,因为它的较大质量能接受更多的冲力并保持更长的运动时间以对抗外部阻力。……正是同样的量(质量和速度)在牛顿物理学中被用来定义动量,尽管在牛顿物理学中动量通常被设想为一个运动的量或一个物体的运动效果的量度,而冲力却是运动的原因。”
巴黎大学校长布里丹(约1300~1360)认为冲力是由初始推动者传给运动物体的动力,其强度用物体的速度和质量量度。“基于这个正确的假设,他解释这一事实:如果同样形状和体积的一块铁与一块木头以同样的速度运动,铁块将运动较长的距离,因为它的较大质量能接受更多的冲力并保持更长的运动时间以对抗外部阻力。……正是同样的量(质量和速度)在牛顿物理学中被用来定义动量,尽管在牛顿物理学中动量通常被设想为一个运动的量或一个物体的运动效果的量度,而冲力却是运动的原因。”
 布里丹认为物体向上运动时,由于重力和阻力的作用,冲力不断减小。自由下落时重力使冲力逐渐增大。他暗示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冲力使物体永远做匀速运动。可以推测这是匀速直线运动,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它的运动方向和速度会改变。布里丹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空气填补真空对物体产生排挤的说法,指出陀螺旋转时并未排出空气,末端为平面的标枪并不比两个尖的标枪运动得更快。
布里丹认为物体向上运动时,由于重力和阻力的作用,冲力不断减小。自由下落时重力使冲力逐渐增大。他暗示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冲力使物体永远做匀速运动。可以推测这是匀速直线运动,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它的运动方向和速度会改变。布里丹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空气填补真空对物体产生排挤的说法,指出陀螺旋转时并未排出空气,末端为平面的标枪并不比两个尖的标枪运动得更快。
14世纪早期牛津大学梅顿学院的学者还对匀速运动和加速运动作了定义。匀速运动是在任何相等的时间间隔内通过相等的距离,匀加速运动是在所有相等的任意长度的时间间隔内获得相等的速度增量。他们还提出了平均速度原理。奥里斯姆(1323~1382)也主张冲力说,并用几何方法证明平均速度原理。
美国的格兰特说:“有关运动的一些最基本概念和定理,伽利略并未优先于他的中世纪先驱。人们一度认为运动学完全是伽利略的创造。无疑,这种说法夸大了他的贡献。这主要是由于17世纪到19世纪提出的对伽利略成就的传统解释,是在对中世纪成果几乎完全无知的基础上作出的。”“历史记录的修正并没有贬低伽利略的天才,也没有剥夺他被誉为现代力学奠基者的地位。”

冲力说者还用冲力说来讨论一些天文学问题。菲罗波诺斯否认神灵推动天体的观点,认为天体和地下物体皆由冲力推动。布里丹说:“我们不可能在《圣经》里找到什么神灵负责天球作正规运动。由此可见,并没有假定这种神灵存在的必要。事实上,我们不妨说,上帝给予每一天球以一种冲力,使天球从此就一直走动着。”
 布里丹还说,一个在运动着的船上的人,就会觉得静止的船在动。所以我们既可以想象地球静止太阳运动,也可以想象地球运动太阳静止,这两种想象都能解释一些现象。设想小小的地球在运动更为合理,因为这种说法更简单、容易理解。可是布里丹又说地球运动的假说不能解释向上发射的箭又会垂直下落到发射点的现象。他不同意空气会带动着箭一块随地球转动的说法,因为冲力能使箭抵抗空气的横向运动。
布里丹还说,一个在运动着的船上的人,就会觉得静止的船在动。所以我们既可以想象地球静止太阳运动,也可以想象地球运动太阳静止,这两种想象都能解释一些现象。设想小小的地球在运动更为合理,因为这种说法更简单、容易理解。可是布里丹又说地球运动的假说不能解释向上发射的箭又会垂直下落到发射点的现象。他不同意空气会带动着箭一块随地球转动的说法,因为冲力能使箭抵抗空气的横向运动。
奥里斯姆指出,若地球从西向东转动,我们不会感到有东风吹来,因为我们随地球一块转动。垂直向上射出的箭又垂直下落,这同地球转动没有什么不协调之处。他说,航行船内的运动与静止船内的运动完全一样。所以究竟是天动还是地动,不可能由经验来判定。但是奥里斯姆还是选择了地静说。
布里丹与奥里斯姆都为地动说作了辩护,但又宣布赞同地静说,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大约他们内心倾向于地动说,但没有勇气表白。“尽管布里丹和奥里斯姆都断言地球并没有转动运动,但他们的许多论点却支持地球的转动,其中一些论点还出现在哥白尼捍卫日心说……的辩护之中。这些论点包括:由船的运动所说明的运动的相对性;让地球用一个非常小的速度完成一个日转动比起让巨大天体以巨大的速度来完成一个日转动要更优越一些;空气与地球一起作日转动;上升和下落物体的运动是由直线和圆周分量合成的结果;以及既然静止是比运动更高贵的状态,让低贱的地球转动,比起让高贵的天球转动更为合宜。哥白尼是否借用了布里丹和奥里斯姆的部分或全部论点呢?布里丹、奥里斯姆的著作在东部欧洲人们是知道的,或许15世纪晚期在克拉科夫大学还被人们研究过,其时哥白尼正是那所大学的一名学生。”

中世纪欧洲这些运动学、天文学的思想,在客观上向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发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