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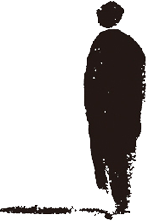

二〇一二年秋天,在秦岭河南段一个叫黑山的矿区,我和一群老乡工作了两个月。黑山是秦岭西峰华山以东,海拔高度近于老鸹岔的区域,有资料显示高两千一百米,植物只绿四个月,每年大部分时间里树木植被呈黑褐色,故名黑山。它的北面是陕西洛南县陈耳镇,南面是河南灵宝市豫灵镇,平地拔起一堵屏障,陕豫由此分隔。金矿开采在这里已有数百年历史,传说李自成兵败潼关商洛养锐时曾开掘采金,为后来东山再起蓄下军资。一九八〇年至二〇一〇年三十年间,秦岭在此被数度打穿,造就出许多亿万富翁,也使无数人倾家无归。如今资源枯竭,这里已成一片废墟。日升日落,雾断云续,唯有群峰苍茫如幕。
大巴整整走了十二个小时。
早晨上车时,凌晨四点整,天还没有亮,天空中星星点点如豆。中秋刚过几天,空气已显出冷意。小镇上的人们大多还在睡梦中,偶有亮起的窗户,有大人起来为上学的孩子准备早餐了。
这是我的家乡小镇峦庄镇。它离我老家的村子有二十里。我们是步行赶过来的,走得太急,个个汗水淋漓。赵大头他们几个人,昨晚先过来了,在小旅馆住着,这会儿倒显得哆哆嗦嗦的。
这是我们经常的出行方式,十几年间,这样的场景一幕幕循环往复,而负担长途客运的大巴换了几回颜色与车主。
下车时,大家的脚都有些发胀,踏在地上,使不上力的感觉,趔趔趄趄,头也有点儿晕乎,耳道胀疼。一路翻山越岭,车太颠簸了。大巴丢下一堆人继续向前,距终点还有五十里,那里是灵宝市朱阳镇。我们开始翻山。这是通往此行目的地黑山的唯一近路,相比另一条容易些的大路,可以节省一天时间和八十元车费。
这里叫庙嘴,一个弹丸小村子。紧依山脚,开着几家饭店和几家小旅馆。看得出,它们因矿山需求而生,这里是最后的中转站,来去的人们在此停顿或出发。
秦岭就在眼前。远眺峰岭,影影绰绰,犬牙交错。凭经验判断,距离应该不近。已经是下午四点半,天光留给我们八个人的时间不多了。
这里是秦岭北坡,秋天来得比山下要早一个节拍。杂草正枯,树木差不多已落光了叶子,只有坚韧的青杠树还顶着一头枯黄,一阵风,摘下几片,再一阵风,再摘下几片。越往上,树木越稀少,一律向下倾斜着身子,这是长期风力和雨雪的结果,高山的风是由上往下刮的,雨雪也是由山顶向山下铺展的。而杂草和小灌木反倒随山势更加茂密,高山特有的小野花一片一片,开满了山坡、路边。
道路盘旋蜿蜒,忽东忽西,路途因而被无限拉长,山体实在太陡峭了。不远一段,就有一个矿坑,有的还在生产,有的荒废多年,渣坡上已生出杂草树木。生产着的矿口一律铺着长长的铁轨,灯泡下,它们向山体里延伸,仿佛永无尽头。污浊的流水、矿车、工人,从那一端流出来。
驮运矿石的骡队从山顶嘚嘚地下来,有的高大,有的瘦小,腰身一律被装矿石的袋子压成深深的凹形。常年如一日地驮运,铁掌把小路开凿出一道深槽,有的达半人深。险峻陡峭的地方,下面是万丈深壑,赶骡人在这里要紧紧抓住牲口的缰绳,以防连骡带矿跌落下去。
八个人都走得大汗淋漓。开始时,相互还开着玩笑,打嘴仗、吃东西,渐渐地,越走话就越少,个个都老实了。力气要用在腿上,大家沉默不语,只有脚步声与呼呼的喘气声。赵大头虚胖,走得东倒西歪,索性把背包甩给了延安。延安老家的黄土高坡上出苹果,年年往坡下扛苹果箱,扛出了一身蛮力。
终于到达山顶了。
这是一个垭口,仿佛刀劈开的一道石门,只是少了一道门楣。前方就是河南地界。苍山无涯,雪白的裸崖仿佛从天空垂下来的瀑布。太阳快要落山了,金色的余晖打在我们汗淋淋的脸上、身上、小路的石子上。岭下不远处就有洞口,可以听到机器声隐约不绝。有人远远地向岭头上眺望着。
回身后望,庙嘴村小得仿佛乌有。那里,暮色正在落下。骡队收工了,赶骡人的吆喝声、骡铃声,一点点低下去、低下去。
坑口叫黑山十八坑。
这是一个濒临废弃的洞口,工棚东倒西歪,机器锈迹斑驳,从洞里流出的水异常清冽,它汪汪汩汩,在渣坡下边的岩根与别的洞口污浊的流水汇合,向山下流去,最后归于黄河。显然,这里已经很久没有生产了。
老板早已在洞口等着我们。他一口外地口音,显然不是当地人,也不是陕西人,这种口音此前听过很多,它吸纳掺杂了太多成分。他五十岁上下,有些胖,头发稀疏。加上炊事员,他们一共五人。攀谈中,知道他是河北保定人,以前开过铁矿。他也不是真正的老板,从矿主手里以每年四十万元的价格将坑口承包过来,只能算包工头。
一间蒙上了新的彩条布的工棚是我们的新家,虽然霉味浓重,还算宽敞、干净,床板上已经铺上了新被。一溜儿长铺,正好可以睡八个人。单间里有一张桌子,铺着一张塑料布,桌上、地上散落着麻将牌。上一拨儿人留下了一圈没有打完的麻将。
吃饭。没有什么比疲惫与饥饿时的饭菜具有更大的召唤力,更能慰藉人了。
早晨推开门,地上、石头上、树上落了一层薄霜。这里,秋天已显出杀气,早起的赶路人嘴上呼出一团白气来。
早饭正在做着,炒菜的热气从棚顶飘出来,被附近洞口的一阵阵爆破声震得一抖一抖,变成一段一段,仿佛被快刀腰斩了几回。老板说,先开一个会。
我们才知道,洞口是今年四月承包过来的,半年过去了,一直找不到工人。老板着急了,天天催促工头上马。着急的原因是上下左右的坑口都打出了新矿脉,有的矿体品位还相当高,量相当大。再错过机会,坑口就要彻底报废了,因为整个黑山山体里的实体部分已经不多了,每天都在互相打穿。
“肉要大家吃,我们按五五分成,打出来的矿石,拉下山去选炼,收入一人一半。爆破材料、电费、生活费、矿石运输费、选矿费,在你们那五成里扣除。”胖胖的工头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五成,打出了一窝好矿石,发财就是一夜间的事情。别的坑口都是三七分呢。”
我们知道,这就叫打分成,老板的坑口,工人的劳动,双方都冒一把险。在矿山,这是普遍的经营方式。也的确有发财的人,打出一窝高品位矿石来,一场活儿干下来,开上了小车、盖了新房。当然,更多的是空手无归。
离家时,老板电话中已经把条件说得很清楚了,这会儿不过是再重复一遍而已。大家都没有异议,但干不干、怎么干,还得进洞看情况。事到紧要处,所有人都有些凝重。这种活儿,一旦上手,中途很难再退出来,挣也罢,赔也罢,都得硬着头皮干到底。重要的一条是,没有谁来承担安全风险,所有的意外结果都需要自己消受。
在坑口的神龛前,新来的人向山神、土地和财神爷爷烧起一炷香。开始吃早饭。
整个矿洞并不太深,从坑口到最远处有两千米。洞里布满了岔道、向上的天井、向下的斜道,向下的斜道里蓄满了水,清幽幽的,不知道有多深。有一些岔道被石块堵住了,封了水泥,这是打穿的地方。有些地方用木头做了支护,上面的石头龇牙咧嘴,只要轻轻一碰就要垮下来。支护的木头上,长满了白花花的树菌。
崭新的小型螺杆式空气压缩机安装在大约离洞口一千米的一个岔道口,这里空气通畅,可以缓解机器的发热问题,也方便左右作业使用。空气开关上通着电,红色的指示灯一闪一闪。
在向东的岔道尽头,露出了一道矿体,裸露出来的部分有三四十米长,二十厘米厚,呈四十五度倾斜状。矿体上,前人打出的一朵梅花状掏心孔还在,一个巴掌就能盖住,这么密集的孔位,看来石头的硬度不小。这是整个洞内我们发现的唯一矿体。看矿石的色泽,可以判断品位并不高。
大家找来了锤子,沿矿体敲打下一片片矿石,用食品袋包装起来。它将被送到山下的化验室检验成分和含量。大家一致的想法是,如果矿石有价值,就在这地方开干,如果品位太低,就拉倒散伙。用掘进的方式在洞内寻矿,那是严重不现实的事情,每掘进一米,成本在三四千元,失败的风险和成本谁也担不起。
按照直线距离计算,矿体所在的地方应该过了山体的轴心,也就是说这里算陕西地界了。但地下矿洞从来的规则都是谁先力量所及就算谁的,从来没有一个分界的定论,因此也就经常发生地下争斗,互相伤害和破坏。好在据炮声判断,相互离得还很遥远。这里暂时还是实体,可以支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开采作业。
出洞口,天已经擦黑了,风从山顶刮下来,碰在高空的缆索上,发出吱吱的声响。这里不通车路,所有的物资需要高空索道运输。缆索在高空布出一片天网,可以想见矿山生产巅峰期的壮观和忙碌。眼下,除了少数偶尔使用,大部分已经废弃了。
带出来的矿石样品,按照不同位置来源被分成三份,由徐明明带到山下的豫灵镇化验,这是必做的环节。结果出来大约需要三天时间。他是我们八人的小头目,打分成这种活儿,他有经验。
在等待结果的时间里,大部分人除了吃饭就是睡觉,或者接着上一拨儿工人打剩的麻将打一阵。
我和徐明明的弟弟,清洗、安装破烂不堪的风钻和高压水泵。这是将来工作时必用的家伙什儿。他叫徐亮亮,我此次的搭档。
我们八人来自不同的小地方,大多数也算是乡邻,只有大胡子延安来自陕北。他曾和徐明明搭过伙。
第一份化验报告单拿上来的那天,大家差点儿散了伙。矿石含金量太低了,计算下来,除去各种消耗,连每天饭钱都挣不出来。这也佐证了当初的判断,上一拨儿工人也不是傻子,为什么掘进那么远打出矿石却不开采,当初一定是化验过了,没有开采价值。
徐明明最后说:“既然来了,就拼一把,如果三茬炮过后,矿还是老样子,咱们再撤!”看来,搞对了!这种情况也叫捡漏,靠的是运气。
第一茬炮效果太不理想了,透过炸药释放的滚滚浓烟,出现在我和徐亮亮矿灯光柱下的矿石连一架子车都不到,不但矿石没有爆破下来,反倒带落下来很多黑色的毛石。毛石是不含金的,掺和在矿石里,将大大拉低矿石的含金量。打分成,追求的就是一个精字,运输和选炼的成本太高了。
第二茬炮效果就好多了,矿体被爆破的破坏力掏进去深深一条槽。矿体异常硬,并且与天地板粘得非常紧密,我们采取了“人”字形炮位排列法。炮孔密集,且个个炮位排列在矿体中央部位,这样就不至于伤到天地板,大大提高了矿石的纯度。
更重要的是,钻头进入到矿体,明显感觉到了矿石的变化,钻孔流出的水阵阵发黑,伴随着一股股淡淡火药味。这是矿石中的含硫量在变大,硫金共生,有硫才可能产生高含金量的矿石。
开矿行业有一句话说,穷和富就隔着一层板。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一个老板,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矿坑打了几千米,实在耗不下去了,把矿坑便宜卖了,下一个接手的人,一茬炮就打出了高品位的矿石,一夜暴富了。穷和富之间,成功与失败之间,就差着一茬炮的厚度。这样的传奇,今天在我们身上再现了!
爆破过后,细碎的矿石明亮亮、黑乎乎,手捧起来沉甸甸的,有一种润泽感。再看爆破过后的矿体断面,石英石上一条条乌黑的硫线,宛若群迁的蚂蚁,盘绕、绵延。在硫线周围,出现了小若针尖的金粒,细细密密。
我俩还没有走到洞口,他们六个就拉着架子车哐哐啷啷进来了。我俩见了他们的第一句就是:“我们发财了!”
阳光从东边的豁口上投过来,它明净得纤尘不染,正是早饭时间。豁口那边叫东闯,公路就通到了那里,网络信号也在那边戛然而止。所有的日用品,煤、粮、菜、矿用物资,都由那里用人工背转过来。东闯公路尽头开着一家小商店和一家小饭店。传说,那里曾是闯王部下驻兵采金的地方。而黑山的西边,就叫西闯,曾驻过闯王的另一支采金部队。小说《李自成》里,“石门平叛”一节隐隐有提及。
我细数过,整个黑山还在生产的坑口有十二个,每个坑口有工人十到几十个不等,算起来,有一二百人。一二百人每天需要的生活生产物资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一支背脚队承担着转运任务,他们来自四川大巴山,这支队伍有一半是女人。
我和亮亮没有顾上吃饭和换衣,拿着矿样直奔东闯。那里有下山的拉矿车,司机可以直接把要化验的矿石样品送到山下的化验室,化验室会用电话告知化验的结果。
大家都太需要一份提振精神的矿石化验报告单了。
“重阳一过无时节,不是风来就是雪。”季节可一点儿都不会作假。
刚过了重阳节第三天,天空密密匝匝落下一场大雪来。雪似乎是从东边来的,又似乎是从西边落下来的。白天还晴得好好的,半夜起来撒尿,地上就见了白,待到天亮,推开门一看,漫天遍地,已经没有别的颜色。树枝还是黑色的,但显然粗壮了许多,沉重了许多,仿佛那些树啊草啊一夜间都低矮了一截。
电线承受不了冰雪的重荷,停电了,整个黑山上下安静了下来。突然的安静,反倒让人有些不适应。
我们爬上岭头去打电话。打电话的,不打电话的,都跟了上来。刚下过雪,反倒没了风,空气也不太冷,就是雪白得让人眼疼。
在垭口,一览众山小。左边和右边,苍岭绵延,不知道它们延伸到了什么地方。陕西地界,也是白雪茫茫,看不到一支骡队,雪天路滑,它们可能在家歇息了。坑口上,有黑的、红的人影,显然这边并没有停电,也就没有停工。按照这个季节太阳的轨迹,这边属阳坡。庙嘴村的房子像丢弃了一地的麻将牌。
豫灵镇遥远得怎么也看不到,只见亚武山白晃晃一片,分不清是崖是雪。通矿公路在峡谷里断断续续,像一条毛线。
大伙儿都抱着电话一通乱打,给自己人,也给外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更多的内容还是向家人和天南地北的同行们报告自己眼下的收成。
第二次的化验报告单写着:金18,铜6,铅10。这是一组叫人睡不着觉的数字。按照当前金、铜、铅价格计算的结果是:18×200=3600元,6×40=240元,10×100=1000元,就是说每采下来一吨矿石,会产生4840元毛收入。除去包工头那部分和各种支出,收入不少于2000元。而我们每天的开采量有八吨多。
矿体的结构也在变化,倾斜度由四十五度变成了六十多度,工作中需要一架架铁梯来借力了,还要穿上防水衣,全副武装。行话说,矿直有金,意思是矿体的结构形状呈直角状就是最理想的含金矿石生成体。
一道六十度的斜槽每天夹着我和徐亮亮,石壁上打出一排铆桩用来垂挂铁梯,用以风钻作业。而出矿工们需要用塑料拖斗将爆破下来的矿石一节一节转拖到宽敞些的巷道上,再装上架子车拉出坑口。赵大头太胖,总是被卡在狭窄处,有时越拽卡得越紧,他就负责专门拉车。吃饭时大家就欺负他,开他的玩笑,让他少吃点儿,再胖下去就只能被开除了。赵大头就认了真,每顿饭真的就少吃一碗。赵大头不傻,少吃一碗,留下来的机会就多一些。而留下来,对于还没娶到媳妇的小伙子来说意义重大。
矿石太招眼了,引起了各路人马的眼红。背脚队、收破烂的、挑小担的、别的坑口的工人,晚上都来偷矿石。一晚上矿堆能偷出一个大坑,弄得大伙儿晚上都不敢睡安稳觉。特别是矿管科更牛,三天两头要安全整顿,各项检查,来一回就要意思一下,这是一个无底洞,越填越深,谁也填不满。
大家就又开会,商量办法。有人说,先把这些矿石发运下山去选炼了,有了收入再接着干;有人说,正是大好时机,每天的炮声早已惊动了四面八方的眼睛,别的洞口正往这儿赶来,说不定哪天就被人打穿了。最后,我们采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不停产,矿石也不出洞,堆在岔道里。仅仅向东的一条岔道就可以堆几百吨矿石,它有三百多米深。当然,这样也增加了工作成本。
背脚队大部分时间有十个人,有时候有十二三个,有时候剩下八九个,人头随农忙农闲而变化。
领头的叫老伍,或者叫老乌,四川话里的“伍”和“乌”听不出区别来。他四十岁还是五十岁,也看不出来。这支队伍在这里扎根有十年了,十年不长也不短,约等于黑山金矿现代化开采史的三分之一长度。此前有很多支背脚队伍,随着资源的枯竭、活路的减少,就剩下了老伍这一支。剩下一支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四川人。
四川人看着和别的地方的人没啥区别,区别是他们特别能爬山路,称得上小说中写的“穿山岭如履平地”,这都是被蜀道一辈辈逼出来的,就像秦淮河逼出了画舫和侬曲。还有一条别人没法比的,他们的背篓特别能负重,往山下背矿石,好劳力能背四百斤,差点儿的也能背二百斤,一支手拐,行走中当杵,歇脚时当顶,支在背篓下,对天喊一嗓子解口气。那速度,那稳当劲儿,不差于一匹骡子。
老伍的背脚队长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抢来的,是背出来的。四川人能背,但能背四百斤的也不是很多,老伍算一个。主要是他不知道累,别人一天背四回,他能背六回,别人一顿吃二斤肥肉,他有一瓶老村长就行了。
老伍有没有老婆谁也不知道,没人见他老婆来过矿山,也没人见过他回老家,一年四季他都在矿上,黑山就是他的家。但老伍有一个情人,陕西华阴人,秦东镇上的,过了风陵渡大桥就是山西,那是杨贵妃的老家,它们就隔着一条黄河。
老伍的情人叫玲,有杨贵妃的容颜,但没贵妃的命,她也背脚,就在老伍的手下。
我到过他们的家,那是一个废弃的矿坑,在一棵松树下。家不大,有十米深、两米宽、一米七八高,地上、屋顶上和四壁都贴了彩条布,不但干爽还干净。门口有一株山丹丹。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是歌里唱的,其实有一种山丹丹花开不红也不艳,它是粉里透着红的。玲说,夏天开放时,那颜色,找不到词语描述。
玲有一个女儿正在上小学,有一个丈夫,几年前在山西煤窑上死了,有人说是跑了,反正再没有回来。
玲大概三十岁,那眉眼看着比三十岁小点儿,唇角有点儿上翘,带着自然笑。老伍舍不得让玲背脚,那不是人干的活儿,本来是骡子干的活儿。但玲一定要背。她背不过一个劳力,一趟只背八十斤,路上歇十几回。
事情就出在玲身上。
那一天,玲背了两箱炸药。炸药的规格是一箱四十八斤,加上背篓,就超过了一百斤,加上前一天下了点儿毛毛雪,路有些滑,不敢放开腿脚走,玲就多歇了几回,落下好远。
炸药是背给我们坑口的,我们每天使用的炸药,都是玲背过来的。专用的爆破材料运输车把材料运到东闯,剩下的运输就得靠人的肩膀,几十年一直是这样。
那天玲喝多了水,不时要小便。她把背篓放在路边,去树林里方便去了,树叶都落光了,天明晃晃的,更遮不住人,只能跑远点儿,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大石头遮住了路人的视线,也遮住了玲的视线。
解完手回来,背篓里只剩下了一箱炸药,另外一箱不见了。
炸药的管理非常严格,每一箱从生产到运输再到使用都有登记。什么东西一严,小事就成了大事。但玲谁也不敢告诉,包括老伍在内。我们以为少买了一箱,也没放心上。
几天后,一伙偷矿的在一个大坑口偷矿,那是一家国营的坑口,矿好,招贼。他们胆大,用炸药炸一个矿柱。炸药还没点燃,被巡逻的矿警人赃俱获,炸药事大,结果被交到矿山派出所。一夜审下来,他们交代了炸药的来历。
偷矿本不是啥大事,可以说很多黄金都来自偷来的矿石。但炸药得落到实处,查到最后,查到了玲身上,被拘留十五天。十八坑对炸药材料管理登记不严,也难辞其咎,被罚款五千元,坑门被永久贴上了封条。
沿着河西林场的玻璃房子往西闯走,是一条绝壁栈道,栈道没有古陈仓那条兵事纷扰的栈道有名,走的人也少,但比它险峻多了,也好看多了。夏天一到,栈道上下就开满了杜鹃花,有的红,有的白,有的又红又白。很多地方的杜鹃花是假的,托杜鹃之名,只有这儿是真的。
栈道没有栏杆,别的车不敢走,只有一种嘎斯汽车敢,只是嘎斯汽车一旦坠落山涧,也就不用下去看了,看也白看,都成了纸一样的碎片。
在栈道的某处,一处长着一丛高大杜鹃树的崖下,赵大头也成了碎片。那天,他负责押车,那是最后一辆车,拉着最后一趟矿石。
那天,已经不胖的包工头说:“算了,也不用下去看了,我卡上还有四十万,你们给他家里带回去。我也该回去了。”
翻过西闯的千尺梁,会出现三条小路,沿中间的一条走四里,有一个矿坑,渣石铺展出一片气势。那就是黑山十八坑。铁门上的封条大概早被风吹雨打去,但一把大铁锁一定还在。
进入坑口三百米,向东,有一条岔道,里面有一筒子矿石,如果运到山下,能值一百万。
只是,如今大约早没了下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