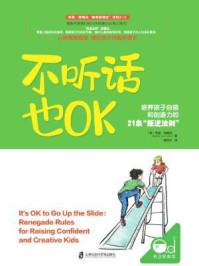帕斯卡·艾特尔、史蒂芬妮·欧森、乌法·延森


巴斯蒂安·巴尔沙札·巴克斯一直是个焦虑、不快乐的胖男孩。在母亲去世后,由于父亲始终处在哀悼状态走不出来,他简直是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不过,就在巴斯蒂安为了躲避平日霸凌他的同学们而闯进一家二手书店那天起,一切都改变了。书店里有一本奇特的书迷住了他,他偷走那本书,躲在学校荒废已久的阁楼里开始阅读。富有想象力的故事总是吸引生活在幻想中的巴斯蒂安:
有关人的不可抑制的热情事儿总是那么神秘莫测,这对孩子来说与成年人并没有什么两样。那些陷进这类事情的人无法作出解释,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类事情的人也无法理解这些事情。为了征服一座山峰,有些人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人,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解释。还有些人为了赢得某个人的心而毁掉自己,而这个人一点也不想知道有关他们的任何事情。有些人为了在赌博中赢钱,押上了自己的全部财产……总而言之,正像有形形色色的人一样,天下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可抑制的热情。对巴斯蒂安来说,他的热情就是看书。
 [1]
[1]
读着读着,男孩逐渐进入由孩童女王统治的幻想国,那是个充满了奇异景色与古怪生物的世界。孩童女王的生命维系着幻想国的存亡,而现在她生了重病,她的性命得靠一名人类儿童前去救援。于是,小书虫巴斯蒂安还真的就被拉进了书中世界:“他,巴斯蒂安,正是这本书里的一名角色,而直到刚才他还以为他只是在阅读着书中故事。天晓得此时此刻是否也有人正好读到这,并同样以为自己不过是一名读者罢了。”

在幻想国里,巴斯蒂安变成英俊、刚毅又强壮的男孩。在经历重重冒险与难关以后,就在他差点忘掉真正的自己时,他终于成为更棒的人重返人世间,并带回一样新本领:爱别人,同时也爱自己。
米切尔·恩德(Michael Ende)的《永远讲不完的故事》(1979年德语版;1983年英译版)再版了无数次,销售量超过一千万本。这本书已翻译成四十种不同语言,不仅赢得许多奖项,也启发了多部电影。书中的英雄之旅发展成一种“情感教育”
 ——也因此,这本小说涉及许多本书将要讨论的议题。《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凸显了一些得以理解“激情”(passions)或“情绪”(emotions)在儿童文学中的重要性之方法:书中奇特且迷人的世界诱惑儿童拿起书本、儿童透过书籍可获得对于自身与其所处世界的知识,还有透过阅读别人的痛苦与喜悦而获得情绪体验。从许多方面说来,本书观察的是儿童透过阅读能够感受到什么——就像我们能观察到巴斯蒂安阅读着他自己成为其中一部分的故事一样。
——也因此,这本小说涉及许多本书将要讨论的议题。《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凸显了一些得以理解“激情”(passions)或“情绪”(emotions)在儿童文学中的重要性之方法:书中奇特且迷人的世界诱惑儿童拿起书本、儿童透过书籍可获得对于自身与其所处世界的知识,还有透过阅读别人的痛苦与喜悦而获得情绪体验。从许多方面说来,本书观察的是儿童透过阅读能够感受到什么——就像我们能观察到巴斯蒂安阅读着他自己成为其中一部分的故事一样。
关于儿童与其情感的研究已有很长一段历史,早从18世纪末以前就开始了。刚开始时很缓慢,接着,19与20世纪见证了儿童情绪的研究逐渐出现史无前例的活跃、潜力、深思熟虑、理解与描述,以及对儿童情绪的塑造、调教、训练或治疗。在家庭或学校变化多端的方法下、在给儿童与成人的教养手册(advice manuals)里、在后来出现的电视或自助团体影响下,儿童变成情绪训练与情绪最适化
 的对象,同时也是情绪自我发展的主体。
的对象,同时也是情绪自我发展的主体。
反观上述,人在描述情绪时可能已经将它们自然化了:情绪往往被视为某种非常基本、人性本质的东西。在一般人看来,儿童有情绪似乎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不是出生以后才有,根据一种流行假设,甚至当儿童还在子宫里尚未出生以前就有情绪了。此说法认为胎儿的情绪罗盘会对母亲怀孕时所受的压力及荷尔蒙水平做出反应。心理学家还表示,我们出生后头几年的情绪体验对于我们整个人生平衡以及往后的人际关系具决定性影响。
这种观点的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当时儿童情绪成为心理学上备受瞩目的话题,后来变成神经心理学与生物社会学的研究及讨论话题,甚至是公众讨论的话题。 [2] “情绪”变成教育专家的职权范围,他们提倡各种身体与社会文化情绪学习法来教育年轻人。不成熟及幼稚的情绪得透过各种社会化或惯习化进行栽培、培育与最适化。因此,父母与整个社会都被奉劝要非常小心地照顾这些需要专业人士帮助和教育谏言的儿童。
19与20世纪期间,儿童与其教育成为许多社会试图了解并由此塑造它们自己情绪数据库的其中一个核心区域。到了20世纪60与70年代,来自专家、公众与政治加诸在父母与其他成人身上的压力大幅增加,并鼓励实现儿童的情绪自我发展。 [3]
与此相伴而来的是心理学家、教育专家和社会学家等人的历史面关注,他们对儿童情绪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并且这股兴趣持续至今。其结果是,众人很容易受诱导而得出一个错误结论,即认为儿童的情绪没有历史;而事实上,儿童的情绪对于研究过往来说,应该被视为一个值得迎接的挑战。总的来说,儿童的情绪在历史研究中尚未占有一席之地,这多少教人感到意外。

然而,在快速扩展的情绪史领域中,这是个极其重要的主题。情绪史学家仔细审视情绪的建构与其社会框架,以及唤起这些情绪的方式。 [4] 他们不仅追寻关于情感表达方式的变化,同时也质疑我们无法观察到“真实的”情感和“纯粹的”表现规则这种传统区分,或是对特定的情感学(emotionology)提出质疑。他们十分关注情绪是“自然的”此一概念,原因不只是情绪的再现、感知与分类会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化,更重要的是,情绪为历史发明的具体结果及社会产物,以及(本书即要论证的)一道实践性知识的问题。 [5]
在此背景下,本书试图重建被认为是儿童情绪社会化的关键要素,尤其关注它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晚期的变化,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传统西方焦点以外的地方。我们将探讨前人透过教养手册与童书提供什么样的情绪给儿童,并详述种种涉及学习如何感觉的过程、具体论述与其多重实践行为。故事里的年轻主角是如何学习的?童书给小读者提供什么样的框架?而在那框架下,有什么改变是能够跨越时空被我们观察到的?有哪些特定情绪被儿童学习到了,或至少被教导说这些情绪对他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而这些儿童指的是哪些儿童?年龄、性别、种族和阶级背景在这里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在现代社会大规模发展背景下(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期),童书与教养手册提供给儿童的情绪数据库呢?
上述问题都设置在广大的童年与儿童历史框架内,故引起一些关于年龄层以及年龄层如何影响情绪学习的基本问题。“儿童”无疑没有一个固定范畴,不能单纯用生命周期的生物或生理阶段来定义。
 认知或情绪发展指数固然可以令人更好地理解年龄分层,但也正是当一个人被标示为儿童、青少年或成人时,会对他们在自主、自我、权力关系以及情绪发展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虽然儿童、童年与青春期的定义并不明确,但都是历史分析的重要范畴。在19与20世纪期间,童年本身的概念在地理与时间上都展现了显著的变化,这点或许不言而喻。所谓的一名儿童、一名青少年和一名年轻人等意涵已经大幅度转变。这些改变是透过政府立法、教育、私人倡导、科学知识与大众媒体而产生的,大大影响童年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意义。
认知或情绪发展指数固然可以令人更好地理解年龄分层,但也正是当一个人被标示为儿童、青少年或成人时,会对他们在自主、自我、权力关系以及情绪发展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虽然儿童、童年与青春期的定义并不明确,但都是历史分析的重要范畴。在19与20世纪期间,童年本身的概念在地理与时间上都展现了显著的变化,这点或许不言而喻。所谓的一名儿童、一名青少年和一名年轻人等意涵已经大幅度转变。这些改变是透过政府立法、教育、私人倡导、科学知识与大众媒体而产生的,大大影响童年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意义。
历史学家已将看似有明确范畴的“儿童”与“童年”视为待解决的问题。 [6] “青春期”(youth)、“少年期”(adolescence)和“青年期”(young adulthood)这些用语在历史上都是不精确的术语,并且经常交互使用。尽管“少年期”这术语存在已久,但它的现代用法(为介于童年与成年中间那段棘手的时光进行分类)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出现,并且在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的著作《少年期》(1904)推广下而普及。 [7] 就法律层面来说,少年期的结束意味着进入成年,一般这是落在18至21岁;但是就行为与情绪方面来说,此阶段则可以延长下去。比如在霍尔的《少年期》里,这段时光是介于14至24岁之间。 [8] 至于现代,儿童则预期会在6岁进入学校学习识读能力,16岁时少年期正活跃,但再过个两三年就到了法定成年期。为了定义出一个明确的起点,本书将“童年”定位在6至16岁的年龄范围来引导其研究,不过作者群在阐述儿童与童年的多样化及其不断变化的定义时都十分谨慎,包括那些缺乏具体概念的时代背景亦然;至于在具体定义已存在的时代背景下,本书则研究这些时代里的儿童是被解释为小大人还是天真、理想化的存在,看看他们是依照自己的才智来发展的主体,还是等着转变为成人的教育对象?
在西欧与北美,伴随着以“正确的”方式塑造儿童而来的,通常是对童年定义的窄化。儿童的社会化与文化适应,以往主要发生在家庭与宗教环境下,对下层阶级的儿童来说还包括工作环境;后来这些逐渐由教育机构取代,最后则反过来由同侪团体所取代。 [9] 在18世纪与大半的19世纪里,负责儿童教育的主要是男性精英。不过,让儿童获得基本识读能力的目标开始渗透阶级与性别界限,尤其是福音派为主的地区,因为传福音需要信徒透过阅读宗教册子与《圣经》来建立与上帝的个人关系。渐渐地,识读能力的训练变得较有系统。几乎所有本书研究的国家的识字率在19世纪末都有明显提升,不过印度的识字率相较之下提升得较慢,其女性识读能力更是欲振乏力。俄国的识字率在19世纪期间有明显提升,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最佳估计也只有百分之四十五的男性能够阅读,识字能力最高的年龄层则落在11至20岁之间,且和印度一样,女性识读能力也比较落后。不过,到了1950年左右的苏联,有九成的男女都能够阅读了。 [10]
西欧与北美在推动普及识字时恰逢大众教育大幅增长,这些大众教育经常是先由宗教或其他非政府机构带头进行的。到了19世纪末,免费的义务教育变成国家的职责。不过,在印度,虽然有些省试图建立初等义务教育,但英属印度时期(1858至1947年)并没有普及教育制度出现。印度独立后才有组织地为所有14岁以下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11] 在苏联,直到20世纪30年代教育才完全受国家所掌控,并且直到50年代后期,8年的学校教育才变成义务性质。 [12]
普及识字与教育的无数努力扩大了阅读市场,不分男女与阶级。源源不绝的读物稳定供应到市场上,其中包括童书与教养手册。特别是童书,在情绪建构与产出的过程中已被证实为相当重要的一门文类。正如本书所表明的,至少到20世纪末为止,童书在直接塑造儿童情绪这方面有着独特与显著的功能。今日,其他媒体涉入了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为学习如何感觉引进新的技术。比如说,电影院从20世纪20年代起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漫画则从40年代开始,接着要到70与80年代其他媒体才开始有更广大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电视、有声书以及过度生产的计算机游戏。
为了让本研究考察的时代保持一致性,本书重点将只会放在童书以及指南文学上。本研究团队的共同成果建立在60本左右经过精挑细选、非常成功并广受好评的童书上,每一本在它们所属时代都是所谓的经典。这些作品大多为国际畅销书,有许多至今仍在市面上,其中包括:《蓬蓬头彼得》(1845德语版;1850英译版)、《丛林之书》(1894)、《彼得与温迪》(1911)、《长袜子皮皮》(1945瑞典版、英译本)、《世界第一少年侦探团》全系列(1942—1962)以及《纽扣战争》(1912法语原版;1968英译本)等等。其中一章将研究重点放在多种跨类型改编版的《彼得·潘》上,以凸显爱情观的转变,以及各版本对于角色关系的不同强调。每一章都会针对它们所研究的特定情绪参考若干部童书以及写给成人与儿童的大众教养手册,详细选书清单可见于附录的参考书目。
本书重点与其说是“以写作来教学”,不如说是“以阅读来学习”。我们不将历史读者看作是各种教条式或社会化的被动接收者,相反,我们认为全神贯注与热情的阅读是一种主动体验,读者可透过阅读来探索他们的想象力、参与文本意义的生产,并行使不同程度的自主权。
 阅读史学家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与马丁·里昂斯(Martyn Lyons)等人在重建读者历史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读者史。
[14]
最重要的是,阅读行为现在也公认为会参与并产生出情感的了;文本不仅是诠释的,同时也是“感受”的。
[15]
一如瑞秋·艾布洛(Rachel Ablow)的主张:“在19世纪中后叶,众人普遍认为阅读至少和情感体验一样可贵,因为阅读是一种传达信息或增进理解的方式。”
阅读史学家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与马丁·里昂斯(Martyn Lyons)等人在重建读者历史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读者史。
[14]
最重要的是,阅读行为现在也公认为会参与并产生出情感的了;文本不仅是诠释的,同时也是“感受”的。
[15]
一如瑞秋·艾布洛(Rachel Ablow)的主张:“在19世纪中后叶,众人普遍认为阅读至少和情感体验一样可贵,因为阅读是一种传达信息或增进理解的方式。”
 本书要问的是作家与读者如何看待阅读体验,而非检验提供情绪处方笺的规范。其他学者已越过文本的意义去研究读者如何响应文本:是什么导致这名读者心生怜悯,另一名读者却心生愤怒?同一个文本也许能使某位读者感动落泪,另一位却无动于衷。苏珊·费金(Susan Feagin)从“鉴赏”的角度解释了对于虚构文学的情感反应,她将其描述为行使一套能力。
[16]
这些情绪反应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评断特定文本的呢?
本书要问的是作家与读者如何看待阅读体验,而非检验提供情绪处方笺的规范。其他学者已越过文本的意义去研究读者如何响应文本:是什么导致这名读者心生怜悯,另一名读者却心生愤怒?同一个文本也许能使某位读者感动落泪,另一位却无动于衷。苏珊·费金(Susan Feagin)从“鉴赏”的角度解释了对于虚构文学的情感反应,她将其描述为行使一套能力。
[16]
这些情绪反应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评断特定文本的呢?
要描述儿童与青少年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阅读些什么是个难题。在19世纪初,大多数德国、法国与英国的儿童在学习阅读时,都会借助一些简单的初级读物与宗教文本,通常是《圣经》或教义问答手册。 [17] 比较世俗的书籍只在中产阶级家庭里看得见,这些书在18世纪末时首先以儿童周刊杂志的形式出现,接着再以专门写给儿童的文类形式出现。从19世纪末起,尽管每个国家国情有所不同,但各个阶级的儿童都愈来愈容易接触到儿童文学了。
与此同时,要描绘儿童读书时的阅读情境对历史学家来说更是困难重重。毫无疑问,各种儿童阅读场景都曾存在过,就与成人的阅读经历相类似。
 有时候,只要儿童与青少年年纪够大并接受过必要的教育,他们就会独自阅读。在19世纪英国与德国中产阶级家庭里,儿童的房间至少要有一个与房间主人等高的书架才算布置齐全。
[18]
有时书籍则是在团体里、在公开场合或在私底下读给儿童听的。19世纪中叶起,枕边故事、《圣经》故事或其他故事变成许多家庭的习惯。在其他情况下,老师会要求儿童念书给父母听,好让父母见识一下这项新技能的价值。在下面一则中产阶级家庭的例子里,当女儿被说服倾听父亲朗读时,阅读的情感(甚至于神圣)意义显而易见:
有时候,只要儿童与青少年年纪够大并接受过必要的教育,他们就会独自阅读。在19世纪英国与德国中产阶级家庭里,儿童的房间至少要有一个与房间主人等高的书架才算布置齐全。
[18]
有时书籍则是在团体里、在公开场合或在私底下读给儿童听的。19世纪中叶起,枕边故事、《圣经》故事或其他故事变成许多家庭的习惯。在其他情况下,老师会要求儿童念书给父母听,好让父母见识一下这项新技能的价值。在下面一则中产阶级家庭的例子里,当女儿被说服倾听父亲朗读时,阅读的情感(甚至于神圣)意义显而易见:
当他对你朗读一些东西,当他向你述说一些他的成就,当他透过歌唱——透过一日将尽时的晚祷——发送温暖的情感,当他的天职使他能够对你朗读《圣经》或其他好书——那么就放下手上所有干扰你的事,并与自己的心灵、精神和感觉完全同在吧。

同一本书也可以在许多读者手上流传,让大部分儿童容易取得也负担得起阅读文学作品。这不是中产阶级独有的习惯。举例来说,根据罗伯特·罗伯茨(Robert Roberts)的社会历史自传,劳工阶级的青少年经常阅读校园小说,而且那些校园小说带给他们的影响比什么都还大(包括像童军那样有影响力的团体)。比起宗教与非宗教领袖的谆谆教诲,小说反而更容易让男孩子将公学的风气内化。 [19] 反之亦然,中产阶级儿童也可能会阅读到劳工阶级的角色,并根据他们从阅读材料中得到的灵感,想象自己化身为不同阶级和种族的样子。
可是,本书作者群真的能够借由探索儿童文学与教养手册,就能重建并分析学习历程吗?若不去探索小读者对于这些文本的具体接收效果与不同诠释,有可能深入了解儿童的情感吗?换句话说,这本书所要描述的内容,是否能超越单纯的教学过程与某种特殊的现代情感学呢?
本书并不打算强调并夸大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科学知识与大众知识,或“真实”情感与“单纯”情感规则之间的传统区分(二元区分之所以备受批评不是没有原因的)。相反地,本书要强调的重点是儿童的特殊性与儿童的情绪社会化。跟成人相比,儿童更明显是透过模仿、仿效与适应的方式来进行学习。
[20]
此说法适用于当代儿童身上,而我们主张类似过程也作用在19与20世纪的西欧与北美儿童身上,在一定条件下,这些作用在印度与俄国的儿童身上也没有完全不同。
 这假设了在本书所研究的时代,儿童主要是透过试着以身体的实践、模仿和姿势,复制或重现他们在别人身上观察到的情绪来学习情绪的。由于这些情绪绝非“自然”的,所以儿童必须在具体的与情境式的感知中融合并且——借布尔迪厄的丰硕思想来说——惯习化这些情绪才行。
[21]
一如克里斯多福·沃尔夫所说:“模仿学习……创造了实践知识,而这种知识组成了社会……行动。”
这假设了在本书所研究的时代,儿童主要是透过试着以身体的实践、模仿和姿势,复制或重现他们在别人身上观察到的情绪来学习情绪的。由于这些情绪绝非“自然”的,所以儿童必须在具体的与情境式的感知中融合并且——借布尔迪厄的丰硕思想来说——惯习化这些情绪才行。
[21]
一如克里斯多福·沃尔夫所说:“模仿学习……创造了实践知识,而这种知识组成了社会……行动。”

从本书作者群的观点来看,真正重要且具建设性的问题,并非童书和教养手册是否呈现了关于儿童情绪或学习过程不断变化的知识体以外的东西,而是它们向儿童提供了何种知识。举例来说,与通俗的百科全书或工具书相较,童书不会将官方或正规知识总结成简洁的文章段落。相反地,童书传授及分享的是情境知识与实践知识,它们未必会告诉孩子该感受些什么,但会以某些细节来说明这种或那种情绪是如何发生的、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以及该情绪实际体验起来的感觉。 [22]
这种实践知识呈现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冲突、故事与结构当中。从19世纪中叶起,愈来愈多童书不是只从成人视角来讨论规范与其伴随的情绪或道德问题,也开始让成为故事要角的儿童来告诉读者关于儿童与儿童之间的严重冲突、改变和长期摩擦等问题。这些童书为争执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来自儿童,而不是爱批评又爱纠正人的大人。不论孩子是否真的经历过这些特殊情境,他们都可以把自己的情绪知识应用到故事里,从而扩展这方面的知识。
有鉴于接收理论的分析贡献,我们不能假定儿童总是会在儿童文学或教养手册里学到作者或其他成人想要他们学习的东西。因此,本书不会探讨儿童究竟从童书或教养手册里具体学到什么。除了上述原因,另外也考虑到儿童,尤其是年幼的儿童,要以历史观点重现他们对实践知识的接收是非常困难的。相反地,本书提出以下论点:童书提供大量的经验、表达与情绪实践数据库给读者,让读者在没有预设结果的情形下就很大程度上以模仿的方式学习到了。模仿学习总是受制于变化,多少也受制于另类诠释。
 复制的过程也会不断产生差异。因此,阅读或听故事的情境在这里的理解比较像是在“尝试情绪”(trying),而非一致同调的“做情绪”(doing)。
复制的过程也会不断产生差异。因此,阅读或听故事的情境在这里的理解比较像是在“尝试情绪”(trying),而非一致同调的“做情绪”(doing)。

本着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的精神,或者说本着叙事学领域的精神,本书作者群认为是各色各样的故事与其往往复杂的叙事结构(这些故事在某些历史点上也见于教养手册中)给了儿童重新感受特定情境的可能性与所需的时间。透过模仿、仿效的方式来阅读童书或手册里的故事,小读者能够由下往上实践或发展出相应的情绪,并从故事“主角”或“反主角”身上学习如何感觉。 [23] 当故事人物有所成长,读故事或听故事的儿童亦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童书和许多教养手册所提供的实践知识可以由儿童以有别于成人的方式所采纳,比如说,儿童不会像成人阅读大众百科全书那样收集实践知识。尤其是童书,除了给予规范以外,也提供书中角色情感的详细讯息。因此,可以假定阅读或聆听的情境本身已经产生体验;它可能启动并行的学习过程,有时对儿童与其身体都产生强烈影响,让他们从大哭、大笑到颤抖。童书这文类在19与20世纪期间有了巨大转变,尤其在西欧与北美,随着童书的市场成长,叙事也变得愈来愈多元,创造出能使这些经验发生的空间。就这意义上来说,本书作者群并不认为模仿学习过程在情绪史里是“较低”或“较高”的发展阶段,而认为是一种学习如何感觉的社交机会,不同类型的书籍与叙事结构在不同的时期与社会底下所赋予的空间也会有所不一。虽然本书聚焦在比较私密环境下的阅读情境,也就是儿童独自阅读或由儿童与照顾他们的人组成的小团体,不过模仿学习的过程同样也可能在更大的、较不亲密的团体聆听情境中开启。
相关研究指出,儿童文学特别有助于儿童处理他们的问题与困境,心理学实验似乎也如此暗示。阅读可以增强儿童的情绪能力,提升他们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意识。
[24]
这个结果符合了过去的主张,即认为阅读会对儿童与青少年有所(正面或负面的)影响。19世纪的指南文学经常强调书籍作为强大“共同教育者”的重要性,并推荐“会在心头上留下有益印象”的文本。
[25]
这些作者同时也不断警告所谓伤风败俗的读物有破坏儿童道德之嫌,会“污染心智”
 并“对心灵造成败坏”。
[26]
尽管这是否定之词,不过诸如此类的告诫只证明了大家从很早以前就认为书籍对儿童的情绪教育有显著影响。
[27]
并“对心灵造成败坏”。
[26]
尽管这是否定之词,不过诸如此类的告诫只证明了大家从很早以前就认为书籍对儿童的情绪教育有显著影响。
[27]
虽然儿童文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8世纪,但直到19世纪“童年”才开始被强调为生命周期里“天真无邪”的独特阶段,再加上儿童识读能力大规模扩张,这才促进了针对这群独特人口的文学作品激增。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经常被视为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 [28] 这个时期也为此文类创造了多样模式。纯说教与宗教文学由针对儿童和青少年应具有之特性的故事所补充,并逐渐被取代,而这些特性是由此领域日渐增多的专家提供。
尽管难以划分其范畴,儿童文学及其演变仍然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通道,让人有机会可得知众人对青少年的期望如何随时间、地点而不断改变。儿童文学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为特定类型的读者而书写与改编的,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 [29] 无论给年轻人阅读的内容如何具有颠覆性,儿童文学仍受成人掌控。 [30] 本书所调查的许多书籍都是成人权威人士认为“恰当”的,这些人包括家长、教师、评论家、学者、出版者、图书管理员以及各种图书奖委员会。有些是特意写给特定政治、宗教或社会受众,有些则是为了满足儿童玩耍或逾矩的欲望。还有很多同时作用在多重层面上,这使得要对它们的说教目的和预期成效或影响做简单分析是不可能的。但话又说回来,作者(以及他们的预期读者)能够掌控文本被阅读与理解到何种程度呢?作者运用了哪些文学手法来传达他们的情感教学,而这些文学手法又如何影响读者的学习?
起源于18世纪英国与德国的儿童文学,在19世纪中叶发展为一门独特文类,不仅在英国与德国拥有庞大商业市场,也横跨整个西欧与北美市场。 [31] 刚开始时,此文类中有许多书并无意只写给儿童阅读,而是打算让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拿来朗读;有些专门为儿童而写的作品也深受成人喜爱(《哈利·波特》系列是近代的例子);有些书原本是为成人而写的,后来到了19与20世纪则变成儿童文学名著,例如《鲁滨孙漂流记》(1719)、《格列佛游记》(1726)或较晚出版的《蝇王》(1954),这些作品经常为年轻读者而推出改编版或精简版。这些经典名著的历久不衰与适应力表明了它们的重要性。
19世纪中叶起,童书加入了许多复杂且多元的叙事、情绪与道德冲突,还有挣扎奋斗的主角,并且在此情况下,学习过程与过渡情感往往也被表达得非常详尽。与通常以强势口述传统为特征的童话故事或寓言相反,儿童文学主要是较多散文式、较少象征性叙事组成,呈现与讨论具体、实用的情感知识。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童书与教养手册并非探索儿童情绪社会化的唯一可能来源,我们也可以检验教科书、宗教布道讲章、教育者的报告或父母日记。不过,再也无其他文类或媒介在学习过程与变换体验上能提供如此丰富的洞见,同时又是其年轻受众可独立参与其中的——至少,当他们年纪大到可以随心所欲选择时间和场所,以及尽可能在不受制度压力下阅读时,是如此。
不过,关于这类文学作品,有些最简单的问题却是最难找到答案的。
 尽管儿童文学有丰富的研究传统,可供本书作者群知道哪些作品在哪些方面有引人注目的影响力,但大多数文本的销售量相关数据却十分稀少,直到20世纪下半叶以前的作品大多是如此。为数不多的一个销售数量指标是畅销书排行榜,但这些排行榜往往是有问题的,另外也必须考虑到这些排行榜背后错综复杂的历史。
[32]
这些排行榜无法提供读者实际接受畅销书的任何洞见,最多只能提供关于图书普及程度的模糊信息。《读书人》杂志的美国总编辑哈利·瑟斯顿·佩克(Harry Thurston Peck)在1895年发明了第一份畅销书排行榜,他会按月编制全美各个书店的销售数据排出前六名最畅销的书籍。至于在其他国家,这种透过商业成功来评判文学的想法则招来大量反对。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曾有些人尝试建立畅销书排行榜,但很快就因强烈反对的声浪而中断。英国刊物《学院期刊》在1896至1899年间有出过一份畅销书排行榜,但随后消失不见,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再也没有类似的排行榜出现过。
尽管儿童文学有丰富的研究传统,可供本书作者群知道哪些作品在哪些方面有引人注目的影响力,但大多数文本的销售量相关数据却十分稀少,直到20世纪下半叶以前的作品大多是如此。为数不多的一个销售数量指标是畅销书排行榜,但这些排行榜往往是有问题的,另外也必须考虑到这些排行榜背后错综复杂的历史。
[32]
这些排行榜无法提供读者实际接受畅销书的任何洞见,最多只能提供关于图书普及程度的模糊信息。《读书人》杂志的美国总编辑哈利·瑟斯顿·佩克(Harry Thurston Peck)在1895年发明了第一份畅销书排行榜,他会按月编制全美各个书店的销售数据排出前六名最畅销的书籍。至于在其他国家,这种透过商业成功来评判文学的想法则招来大量反对。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曾有些人尝试建立畅销书排行榜,但很快就因强烈反对的声浪而中断。英国刊物《学院期刊》在1896至1899年间有出过一份畅销书排行榜,但随后消失不见,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再也没有类似的排行榜出现过。
就连美国也是,除了1909年至1914年的《读书人》与1930至1932年的《出版者周刊》这两个短命的少儿畅销书榜之外,儿童与青少年文学的畅销书排行榜也是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出现。《纽约时报》从1952年开始刊载儿童与青少年畅销书排行榜,起初一年刊载一到两次。其他国家的畅销书相关数据更为罕见。尽管如此,凡事起了头就会留下痕迹,专门写礼仪书的美国作家埃米莉·波丝特在其著作《儿童也是人》(1940)中建议家长:
当他到了可以阅读的年纪时,别让他错过《爱丽斯漫游奇境》《原来如此的故事》和A. A.米尔恩(Milne)的作品等所带来的喜悦与熏陶……去找一张儿童研究协会推荐的书籍清单吧,从里面选出几本吸引你孩子的书。 [33]
为了替儿童与青少年读者找到合适、有价值的书籍,成人简直不遗余力,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在德国、英国与美国,各式各样的推荐书单是为了指引家长与教育者挑选合适的文学作品而拼凑出来的。有时(成人)读者只是被要求列出他们自己最喜欢的童书,接着书单就这样发表出去了。当然也有一些推荐书单是由专家提供的。除此之外,每年新上市的童书也会获颁各种奖项作为获得认可的证明。
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同时也是比较跨国际的文类。在《纽约时报》的儿童与青少年畅销书排行榜上,来自美国以外的书目逐年增加。1953年的时候,排行榜上每十六本书中只有一本出自非美国作家;到了1973年的时候,在两份独立的排行榜上,二十本书里头有十一本是非美国作品,大多来自英语世界,有少数几本来自法国与德国。德国的“图书库索引”登记了1971年最热门的书籍,前五十名当中就有二十九本是儿童与青少年读物,其中有十五本为外来作品,绝大多数作品要不是出自瑞典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之手,就是出自英国作家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此文类跨国际面向的另一个指标,是英国杂志《时间与潮流》于1938年的推荐书单里首次出现孟加拉国作家达恩·葛帕·默克奇(Dhen Gopal Mukerji)的儿童小说《花颈鸽》(1927)。这本书在1928年就已得到美国纽伯瑞奖,默克奇同时也成为美国最早成名的印度作家之一。还有其他几位作家的作品也获得不止一个国家的赞誉。
毫无疑问,儿童文学已变得相当国际性,这点在世界其他地区皆然,比如本书将从跨国际与跨文化视角来讨论的俄国与印度。这种跨国际视角相当重要,因为它的重点将会放在儿童情绪社会化的过程中,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翻译方式以及逾越改写(不论是全面改写或局部上的修改)等变化。有特定童书在跨国际或跨文化背景下比其他童书做得更好、更成功吗?有某些情绪在此背景下会起不同作用吗?有什么特定情绪是在英国就跟在印度一样,或在俄国就跟在德国一样,都是儿童能够也应该要学会的吗?同样的方式是否也发生在殖民母国与(前)殖民地上,而程度是否也相当呢?
除了童书外,本书也探讨以儿童教育与儿童情绪为题的教养手册(有时则拿来与童书做对比)。教养手册是重要的资源,提供童年以及儿童情绪的规范与实际框架。虽然无法假设父母与其他成人对这些教养建议都照单全收,不过此文类经久不衰证明了它们对读者仍然是有帮助的。
这部分的研究来源涵盖了约三十本最有影响力和最常被引用的指南文集,这些手册也经常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这些书主要是用来指导或提供消息给家长与教师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书也会直接写给儿童与青少年阅读。作为一门文类,教养手册的内容与形式几乎和儿童文学一样丰富,包含了性、婚姻、教育、工作、礼仪和烹饪。
[34]
“以阅读来学习”的方法就是从近代早期此文类出现时建立的,这种学习法深深改变了知识生产、散播与教育的过程。
 尽管养育儿童向来是此文类的重心之一,但是并没有什么精确的方法可以确认这种谈论童年的指南文学读者群是谁。
[35]
许多书明显是写给成人阅读的,尤其是为人父母者。同样道理,关于抚养婴儿或幼童(通常到3岁,有时会到7岁)的书也是给成人阅读的。
[36]
不过也有一些书打算由年轻读者自己阅读,这些书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最常见到。这里有些不错的例子,比如说德国医生暨性学专家马克思·霍丹(Max Hodann)与美国基督教路德派牧师西凡纳斯·史达尔(Sylvanus Stall)这位备受欢迎的多产作家,这两个人都曾经为年纪较大的孩子出版过一系列的教养手册。
[37]
就整体而言,这些文本几乎都认定幼儿期与青春期是童年最重要的时期,所以比较少强调童年中期(5岁至12岁)。
尽管养育儿童向来是此文类的重心之一,但是并没有什么精确的方法可以确认这种谈论童年的指南文学读者群是谁。
[35]
许多书明显是写给成人阅读的,尤其是为人父母者。同样道理,关于抚养婴儿或幼童(通常到3岁,有时会到7岁)的书也是给成人阅读的。
[36]
不过也有一些书打算由年轻读者自己阅读,这些书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最常见到。这里有些不错的例子,比如说德国医生暨性学专家马克思·霍丹(Max Hodann)与美国基督教路德派牧师西凡纳斯·史达尔(Sylvanus Stall)这位备受欢迎的多产作家,这两个人都曾经为年纪较大的孩子出版过一系列的教养手册。
[37]
就整体而言,这些文本几乎都认定幼儿期与青春期是童年最重要的时期,所以比较少强调童年中期(5岁至12岁)。
和儿童文学一样,指南文学的性质已经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改变。这既是童年的本质不断变化的原因也是结果,而教育、讨论和提供儿童方面建议的成人也对此有所察觉。虽然卢梭的小说《爱弥儿:论教育》(1762)是受洛克与其他教育改革者所启发,但可以将这本书看作是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儿童教养手册之一,书中很具体地对童年提出了浪漫主义式的理解。卢梭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为情感教育所做的特定年龄划分,以及为了让儿童按自然成长而坚持推迟儿童的发展。根据卢梭的说法,阅读甚至对儿童有害,在12或15岁以前都不应该引导儿童阅读。 [38]
19与20世纪,将童年与其相关知识的学科专业化的驱力促成了许多新进展。掌握儿童情绪文化适应的知识主体也随着时间改变了。长期以来,人可以遵循宗教对于道德与教育的理解,然而自19世纪末起,心智科学逐渐侵占了宗教的位置,尤其是心理学与教育学。大部分写给父母、儿童与青少年的指南文学主要讲的还是道德教育,只不过教学内容是以心理学术语呈现;相反地,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学家反而经常依赖宗教所留下来的对童年较老旧的认识。
斯坦利·霍尔是站在儿童的道德与科学建议分歧点上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之一。其著作《少年期》充分体现了19世纪末的社会科学专业化,而霍尔本人正是这种专业化的主要宣传者。有神学背景的霍尔是科学心理学以及童年与青少年期相关问题的先驱。他对于以心理学的新理论为基础的教育学与儿童教育的改革也很有兴趣。
 霍尔在1906年的时候出版了精简版的《少年期》并命名为《青春期》,是一本告诉父母与教育者如何处理年轻人的教养手册。
[39]
他除了在自己的科学领域里精益求精以外,也将此科学领域推广普及化到家长与年轻人身上。他的著作在欧洲很畅销、有一大票追随者,而且他对问题的观点很快就被欧洲的社会科学家采纳。尽管如此,就许多方面而言,霍尔在处理儿童与青少年的方法上并不是一个创新者,而只是走从前宗教与德育的回头路。
霍尔在1906年的时候出版了精简版的《少年期》并命名为《青春期》,是一本告诉父母与教育者如何处理年轻人的教养手册。
[39]
他除了在自己的科学领域里精益求精以外,也将此科学领域推广普及化到家长与年轻人身上。他的著作在欧洲很畅销、有一大票追随者,而且他对问题的观点很快就被欧洲的社会科学家采纳。尽管如此,就许多方面而言,霍尔在处理儿童与青少年的方法上并不是一个创新者,而只是走从前宗教与德育的回头路。
在20世纪的历程中,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与教育学的学术专业化大幅度地改变了儿童指南文学的领域。心理学的影响在幼儿期与婴儿期的手册里显而易见,它不一定会取代宗教或道德价值观,但是经常会改造它们。儿童心智与情绪的知识变得以科学为导向也开始深深影响了父母的角色。就许多方面来看,指南文学其实助长了它们承诺要减轻的负担。这些书宣称,除非家长开始听从来自学者与专业人士所给予的建议,否则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名誉扫地的传统育儿知识了。一般而言,像这种亲子教养手册与咨询文类的运作方式就是把熟悉的事物变陌生。不过,在迈向20世纪下半叶时,同类型的指南文学对于科学方法育儿则予以强烈批评。一些书像查尔斯·安德森·奥德里奇(Charles Anderson Aldrich)和玛丽·奥德里奇(Mary M. Aldrich)夫妇合著的《宝宝是人类》(1938)鼓励父母再次相信自己的本能。
[40]
虽然这本书也表示科学知识仍然是有用的,但首要任务是教育父母了解他们角色的自然性。然而,如果养育儿童的相关知识是本能的,那为什么还要阅读教养手册呢?指南文学没有意识到这种方法是自打嘴巴的。此外,也有证据表明某些父母是多么有批判性地接触与使用这些材料。就以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的名著《婴幼儿保健常识》
 (1946)为例,一些母亲还真的就按照“斯波克声称的信念,认为她们应该要依靠自己的常识来抚养孩子”而停止听取他的建议。
[41]
(1946)为例,一些母亲还真的就按照“斯波克声称的信念,认为她们应该要依靠自己的常识来抚养孩子”而停止听取他的建议。
[41]
接下来的十二章,即将探讨儿童文学与教养手册这两种性质相异的文类,提供给儿童的情绪数据库之变化。每一章都集中讨论单一的情绪,这些情绪分别是:焦虑、信任、虔诚、同情心、同理心、爱、羞耻、痛苦、恐惧、勇敢、思乡病以及无聊,每一种情绪都会连结至其他情感,并置于19世纪中叶起更广泛的历史转折与变迁中讨论。
本书作者群在童书与教养手册里辨识出至少六大趋势与重大论题:(一)众人愈来愈重视情绪,情绪也因此而多元化;(二)尽管道德的作用不停变化,但仍然是儿童文学与教养手册不变的特色;(三)成人与儿童以及儿童彼此之间都在争夺更加民主的关系;在此背景之下,(四)性别、种族、阶级或物种等不断变化作用的社会区别也会影响教导与学习如何感觉;(五)同侪团体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最后,虽然将这些转变与变迁解释并描绘成一部单纯的成功故事很吸引人,本书仍然得揭示(六)过去一百五十年来,儿童要为自己的情感与自我发展承担的责任也愈来愈大。
(一)本书并非主张19世纪中叶以前的指南文学或童书完全没有把儿童的情绪当成主题过,因为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就已经有几位主要倡导者观察到了,其中包括德国教育家、出版商以及儿童畅销书作家约阿希姆·海因里希·坎珀(Joachim Heinrich Campe)。在近代,大家不仅接受了儿童本身就有情绪,也同意了儿童体验与学习到比以往更加多样化的强烈而认真的情感,几乎就和成人一样发达。 [42] 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文类在情绪方面以及处理情绪的方式上有很出色的扩展,尤其是它们的多元化——也就是说,关于学习如何感觉,它们提供了不断在改变以及更加详尽的实践知识。尤其是西欧与北美洲,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已经有日益重视儿童情绪的明确趋势。部分章节将重现众人对儿童情绪日益增加的兴趣,特别是在教育与家庭的脉络下。比如说,我们可以观察到某些情感如何将儿童与青少年连结到家庭里,同时却又有其他情感似乎想将他们与家庭拆离。在这方面,教养手册除了告诉家长有关于儿童情绪的知识以外,同时也会造成家长出现某些情绪——主要是焦虑感和责任感。
(二)在这两种文类里,说教话语一旦减少,往往也就表示大家对于儿童情绪更加重视。确实,在本书所讨论的时期里有种明显的趋势,即以不同的、较不严格的方式来处理道德难题,这个趋势比较强调儿童而非成人的问题和情绪或其他能力。尽管如此,这并不表示童书或教养手册完全无视道德或政治话题。儿童的教育与娱乐在19世纪末甚至直到20世纪末,偶尔还是会以相当教化与说教的模式来运作,在公领域以及私领域中都具有明确的目标和强硬的行为准则,强调宗教在这些方面独特而又不断变化的作用。举例来说,有些章节阐明了童书与教养手册是如何处理暴力、折磨与惩罚,它们是让道德判断变得显著的场域。不过,发生这种情形的方式也是会变化的,这些书给予更多空间让人理解暴力与折磨,不论是受害者或加害者皆然,即使目的几乎总是为了减少并控制这些灾难。
(三)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改变是这两种文类在19世纪末时,可以发现其趋势是走向较少阶层关系、更多民主关系,并强调赋予儿童权力,在西欧与北美尤其如此。以前的概念是小孩必须要大人来教如何感觉,现在反而是大人有时必须从小孩身上学习“正确”的感受事物的方式。就这样,两种文类都深深嵌入了一些19世纪末与20世纪的主要社会趋势,也就是社会阶层愈来愈多的冲突、解放运动与民主党派出现,以及不同领域的政治参与到来——不只殖民母国如此,被殖民地多少也有这种现象。这种趋势可以透过典型男女主角的转型而观察到,比如说,他们的恐惧开始有了正当性。有些章节强调了儿童性别角色的转变。不过,儿童不论是与成人或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愈来愈平等化,这点是有争议的。由于这些发展与趋势的冲突性质,若看到为了减少等级制度而出现强烈的反对趋势也不令人意外。
(四)不过,一般说来在整个19世纪和大半部分的20世纪,不论是作为文学角色、读者或教育对象,儿童的性别对于他们预期要根据传统、学习所谓未来男女分别该有的恰当情绪的方式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从19世纪末开始,作为一个更广泛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性别区隔在童书与教养手册里逐渐失去了压倒性的影响力,至少在西欧与北美洲是如此。 [43] 其他通常与性别区隔有强烈关系的社会区隔,比如说阶级、种族或物种,在这段期间内也往往变得不那么不言而喻。有时这些社会区隔在尝试未知关系上,会比做为复制传统二元化的平台更具挑战性。举例来说,有些章节说明了学习如何与他者同感(不论这个他者是人类或动物),在殖民母国与(前)殖民地都大大地获得了重要的历史意义。
(五)另一个非常重要也与这两种文类密切相关的转变,是青少年同侪团体关系的重要性提高了。在赋权给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儿童的这种更大转变中,以及在幼儿园、中小学或寄宿学校等不断变化和扩大的教育体制背景下,其他孩子、兄弟姊妹、伙伴、朋友或作战团队在童书与教养手册的儿童情绪社会化上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即使家庭(特别是父母)在儿童的生活与教育中从未失去应有的关键作用,仍然有不断增加的故事与教育主张,提供了关于儿童如何学习或应该学习如何感觉与对待他人的另类叙事。比如说,本书某些章节展现了寄宿学校(尤其是在英国)的作用,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儿童文学的一种独特比喻,与儿童的同侪关系情感社会化特别相关。在20世纪后期,特别是在1968年以后,“左翼”儿童文学证明了赋予儿童权力这一方面变化的程度。在当时,儿童赋权是一个中心目标;他们的情感、愿望与担忧,都必须根据每一个孩子的个人需求以“真诚的”的方式“表现出来”。
(六)可以说,这种“真诚的”情感标示了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进程之成果,并且应该解释为一种赋权与民主化、或解放与参与的成功故事。虽然本书辨识出一些主要趋势与历史转变,作者群也赞成下述论点:第一,这些进程既非线性也非同质的。它们缺乏明确的、历史决定的目标,并且在整个调查的时间框架内可发现明显的反趋势与矛盾;第二,作者群想要强调,赋权与民主化进程不应该仅仅被解读为是一种毫无条件的成功故事。成为具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和优势的情绪主体,而非情绪客体,意味着童书与教养手册里描绘的儿童也必须对自己的情绪、情感健康,以及连带的整体行为与个人自我发展要更加负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的数据源也让我们能够本着米歇尔·福柯的精神,分析并问题化所谓的儿童情绪治疗或灵活度。 [44] 因此,有些章节将重点放在“情绪”如何成为教育学的难题与心理治疗的任务上。这般情绪主要被看作是这些受影响儿童的调适问题,并认为揭示了一些关于儿童被假设的心理与情绪发展。
因此,从19世纪中叶起,童书与教养手册中的情绪明显扩展与多元化,不仅表现为故事主角与读者的机会,而且这些多样的机会和愈来愈多的可能性也变成了一种新的义务。儿童与成人之间更加民主的关系,也让儿童面临到在情绪上或心理上的自我成长和学习如何以“真诚的”方式去感受的要求。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情绪以及如何感受其他行为者之间,有愈来愈多的可能性可以选择,而这打开了一个永无休止的自我改善与自我最适化的大门。该过程要求个人情感要有更多的灵活性。不过这两种文类都不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儿童的情绪问题,而是试图让儿童能够适应各种挑战,随时为他们生活中的每个新问题做好准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书作者群认为这两种文类对许多19、20世纪的儿童来说,在情绪社会化上都扮演着重大且亲密的角色。在童书与教养手册里,学习如何以“对”的方式感觉,或许是变得比较不那么说教、等级制度或社会性别化了,但同时也明显变得更加矛盾与复杂。
以下十二章探讨的六大趋势与重大主题,是否在20世纪末依旧存在并进入21世纪,这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童书和教养手册一样,在儿童情绪社会化上的社会功能已经有所改变,尤其在1980年至90年代以后。电视和电影院、儿童广播剧和计算机游戏的重要性从量化观点来看不仅持续提升,这些媒体试图呈现的关于情绪或激情的叙事也变得愈来愈复杂。因此,同样的,计算机游戏,这项对今日儿童与青少年来说成长最快速的全球娱乐与教育市场也能够启动模仿学习的过程,就跟童书与教养手册一样。本书作者群并不认为童书与教养手册对现代儿童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不过,当我们调查这些文本在儿童文学“黄金时代”之外扮演何种角色时,都必须研究它们与现代儿童用来学习如何感觉的众多媒体之间的关系。
[1] Ende, Neverending Story , 9—10.
[2] 关于近期的情绪研究,可见Lewis,Haviland-Jones,and Barrett, Handbook of Emotions ;Gross, Handbook of Emotion Regulation .另见第一章《盖斯凯尔夫人的焦虑》。
[3] 尤其是1968年的事件后。可参见Bookhagen et al., Kommune 2 。
[4] 近期的综述可见Frevert, Emotions in History ;Frevert, Geschichte der Gefühle ;Plamper,“History of Emotions”;Plamper, Geschichte und Gefühl ;Biess et al.,“History of Emotions”。
[5] 可参见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Frevert, Emotions in History 。更具体的观点可见Eitler and Scheer,“Emotionengeschichte als Körpergeschichte”;Gammerl,“Emotional Styles”;Scheer,“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6] 虽然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对童年的“发现”进行历史分期现在被视为是有问题的,但其著作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1960;Eng. Centuries of Childhood ,1962)仍然是这块领域的开创性文本。至于历史学家为何不应该继续仰赖阿利埃斯的理论,具说服力的理由见Heywood,“Centuries of Childhood”。
[7] “Adolescence”; Hall, Adolescence .
[8] Hall, Adolescence , i, x.
[9] 例如Gebhardt, Angst vor dem kindlichen Tyrannen 。
[10] Cipolla,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 72, 93.
[11] Biswas and Agrawal,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India , 835.
[12] Anweiler and Meyer, Sowjetische Bildungspolitik 1917—1960 , 44—51.
[13] Feagin, Reading with Feeling .
[14] Darnton, “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Lyons, History of Reading and Writing ; Lyons, Readers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 Rose, “Arriving at a History of Reading”; Ros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 .
[15] Ablow, Feeling of Reading , 4.
[16] Feagin, Reading with Feeling , 4.
[17] Schenda, Volk ohne Buch , 73—85.
[18] Budde, Auf dem Weg ins Bürgerleben , 127—128.
[19] Roberts, Classic Slum , 160—162.
[20] 对该主题不同的视角可见Saarni,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 ;Suzuki and Wulf, Mimesis,Poiesis,and Performativity in Education ;Nadel and Butterworth, Imitation in Infancy .关于模仿与模仿学习的概念,有个很好的讨论是Gebauer and Wulf, Mimesis 。跨学科的综述可见Spariosu, Mimesis in Contemporary Theory ;Garrels, Mimesis and Science 。关于文学与社会科学中,模仿与仿效的(现代)概念“起源”,见奥尔巴赫(Auerbach)的经典之作 Mimesis ;Tarde, Laws of Imitation 。
[21] 事实上,“习癖”(habitus)与“模仿”的概念有诸多共同之处,详见Gebauer and Wulf, Mimesis .关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脉络下的情绪惯习化可参见Zembylas,“Emotional Capital and Education”。另见Scheer,“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2] 关于实践知识与模仿概念的关系,见Bourdieu, Logic of Practice 。
[23] 尤见Girard, Deceit,Desire and the Novel ;Girard, Mimesis and Theory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esp. vol.1。
[24] Trepanier and Romatowski,“Classroom Use of Selected Children's Books”;Kumschick et al.,“ Sheep with Boots ”.至于利用故事与戏剧来衡量与培养学龄前幼儿的道德情绪,见Malti and Buchmann,“Entwicklung moralischer Emotionen bei Kindergartenkindern”。
[25] Newcomb, How to be a Lady , chapter 16, quotation 158; Newcomb, How to be a Man , chapter 16; Blackwell, Counsel to Parents , 44—45; Anon., Boys and Their Ways , 199—233; Hughes, Notes for Boys , 121—130; Matthias, Wie erziehen wir unsern Sohn Benjamin , 168; Klencke, Die Mutter als Erzieherin ihrer Töchter und Söhne , 425—426.
[26] Klencke, Die Mutter als Erzieherin ihrer Töchter und Söhne , 572.
[27] Vallone, Disciplines of Virtue , 4.
[28] Green, “Golden Age of Children's Books”; Carpenter, Secret Gardens .
[29] Hunt,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 1—2.
[30] 见Rose, Case of Peter Pan ,2。
[31] 全面综述见Grenby and Immel,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Carpenter and Prichard, Oxford Companion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
[32] Eyre, British Children's Book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Faulstich, Bestandsaufnahme Bestseller-Forschung ; Vogt-Praclik, Bestselle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5—1930 ; Ego and Hagler, Books at Shaped Our Minds ; Ferrall and Jackson, Juvenile Literature and British Society ; Justice, Bestseller Index .
[33] Post, Children are People , 182.
[34] 20世纪可得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性方面的教养建议:Bänziger et al., Fragen Sie Dr. Sex ;Putz, Verordnete Lust 。关于自我建议在现代历史上的影响,见:Maasen et al., Das beratene Selbst 。
[35] 更全面的综述请见:Hardyment, Dream Babies ;关于美国的文献可参见:Grant, Raising Baby by the Book ;Hulbert, Raising America ;关于德国,见:Fuchs, Wie sollen wir unsere Kinder erziehen ;Gebhardt, Angst vor dem kindlichen Tyrannen 。
[36] 例如Isaacs, Nursery Years 。
[37] Hodann, Woher die Kinder kommen ; Hodann, Bub und Mädel ; Stall, What a Young Boy Ought to Know .
[38] 唯一的例外是《鲁滨孙漂流记》(1719),这本书在卢梭看来可当作儿童一生的指引。关于卢梭对于19世纪儿童心智的影响,有个有趣的讨论可见Shuttleworth, Mind of the Child ,4—6。
[39] Hall, Youth .
[40] Aldrich and Aldrich, Babies are Human Beings .
[41] Grant, Raising Babies by the Book , 225.
[42] 可比较Campe, Robinson the Younger (1781/1782);Campe, Ueber Emp ndsamkeit und Emp ndelei in pädagogischer Hinsicht (1779)。
[43] 例如Clark, Regendering the School Story ;Flanagan, Into the Closet 。
[44] 例如Martin,Gutman,and Hutton,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Rose, Governing the So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