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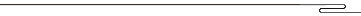
人类社会进化的事实和性质,以及相关的争议;家庭或族团层次的社会向部落的过渡;介绍血统、宗族和其他人类学基本概念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年)发表之后,涌现出大量涉及人类早期制度起源的理论。首先在19世纪末,新兴人类学的首创者,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收集积累了尚存原始社会的实证资料。 [1] 摩尔根对日益减少的北美洲土著进行实地勘察,发明了解释其亲戚关系的详尽分类,并将此推及欧洲的史前。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阶段——野性、野蛮、文明,他认为,所有人类社会都须一一经历这三个阶段。
卡尔·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读了摩尔根的书,运用该美国人类学家的民族学研究,发展出私人财产和家庭的起源理论,之后变成共产世界的福音。 [2] 马克思和恩格斯携手推出现代最著名的发展理论:他们设置一系列的进化阶段——原始共产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全部由社会阶级的基本矛盾所驱动。马克思主义这一错误和从简的发展模型,误导了后来数代的学者,或寻找“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试图在印度找到“封建主义”。
早期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第二动力,来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于1859年的《物种起源》,以及其自然淘汰理论的进一步阐述。将生物进化原理应用到社会进化上,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在20世纪初所作的,在逻辑上讲得通。 [3] 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都要参与生存竞争,优秀的得以支配低劣的。欧洲之外社会的发展,或受到阻妨,或停滞不前。达尔文之后,进化理论在辩护当时的殖民秩序上确实取得成功。全球等级制度的顶端是北欧人,通过黄色和棕色皮肤的深浅不同,一直降至身处底部的黑色非洲人。 [4]
进化理论中褒贬和种族的特色,酿成20世纪20年代的逆反回潮,至今仍在影响世界上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部门。优秀的人类学家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主张,人类行为受到社会彻头彻尾的改造,并不植根于生物学。他在一项著名研究中,以移民头颅大小的实证资料证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归因于种族的东西,实际上却是环境和文化的产物。博厄斯还认为,早期社会的研究需摒弃对各式社会组织的高低评估。在方法论上,民族学家应放弃自己文化背景的偏见,全身心投入他们所研究的社会,评估其内在逻辑。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倡“深描”(thick description);他认为,不同社会只可解说,不可互比,不分轩轾。 [5] 博厄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则把文化人类学科继续引向非评判性的、相对的、绝无进化的方向。
早期的进化理论,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还存有其他问题。它们的社会形式,往往是相对直线的,有严谨的等级,前阶段必须早于后阶段,某元素(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决定整个阶段的特征。随着对尚存原始社会的知识积累,大家愈益清楚,政治复杂性的进化不是直线的。任何指定的历史阶段,往往包含前阶段的特征。将社会推至下一阶段,又凭借多重的动态机制。事实上,我们可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前阶段并不被后阶段完全替代。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便由基于亲戚关系的组织过渡至国家层次。但时至今日,复杂的亲戚关系组织,仍是一部分中国社会的特征。
人类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由文化的比较研究总结出真正的普遍规律。发现了违反所谓社会发展规律的冷僻社会,人类学家常常感到兴奋。但这并不表示,不同社会中没有进化形式中的规则性和同类性。
以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背景,博厄斯派的文化相对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在比较人类学的领域里,留下了政治上求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持久遗产。严格的文化相对论,有悖于进化论,因为后者明确要求厘清社会组织的不同层次,并确定后一层次取代前一层次的原因。人类社会随时间而进化,这是显而易见的。生物进化的两个基本组件——变化和选择——也适合人类社会。即使我们细心避免后期文明“高于”前期文明的评判,但它们确实变得更为复杂、更为丰富、更为强大。因应成功的文明,常常战胜因应不成功的,恰似个体有机体之间的竞争。我们继续使用“发展中”或“开发”的名词(如“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佐证了下列共识:现存的富裕国家是上一阶段社会经济进化的结果,贫穷国家如有可能,也将参与这一进化过程。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政治制度借文化而获得传递,与借基因的生物进化相比,则面对更多的悉心设计。达尔文的自然淘汰原则与人类社会的进化竞争,仍有很明显的类似。
这一新认可导致了进化理论在20世纪中期的复兴。人类学家如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
[6]
、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
[7]
、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
[8]
、莫顿·弗莱德(Morton Fried)
[9]
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0]
认为,各式社会在复杂、规模、能源使用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升级。
[11]
根据萨林斯和塞维斯,人类群体都经历所谓的“特别进化”,以适应他们所占居的生态环境,其结果便是社会形式的多样化。对社会组织的普遍问题,不同社会往往采取类似的应对方法。由此表明,相交相汇的“普遍进化”在生效。

人类学家的难题是,没人能直接观察,人类社会如何从早期模式发展到较复杂的部落或国家。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假设现存的狩猎采集或部落社会是早期模式的实例,再通过观察其行为来推测引发变化的力量,如部落何以演变为国家。可能是基于此,对早期社会进化的推理,已从人类学移至考古学。不像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可通过不同文明在数十万年间留下的物质记录,追踪其社会活力的伸张。例如,考古学家调查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人住宅和饮食的改变,得以了解战争和环境压力对社会组织的改造。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缺乏民族学研究的丰富细节。太依赖考古学记录,会导致对唯物主义解释的偏爱,因为史前文明的精神和认知世界,其大部已永远丢失。 [12]
泰勒、摩尔根、恩格斯之后,对社会发展的进化阶段的分类系统,也经历了自身的进化。放弃了具强烈道德色彩的词句,如“野性”和“野蛮”,而改用中性的描述,如点明主要技术的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另一系统则点明主要的生产方式,如狩猎采集、农业、工业社会。进化人类学家,以社会或政治组织的形式来排列阶段。这是我在此所选用的,也是我的主题。埃尔曼·塞维斯发明了四个层次的分类,即族团、部落、酋邦、国家。族团和部落中
 ,社会组织以亲戚关系为基础,成员之间相对平等。相比之下,酋邦和国家等级分明,不以亲戚关系而以领土为基础来行使权力。
,社会组织以亲戚关系为基础,成员之间相对平等。相比之下,酋邦和国家等级分明,不以亲戚关系而以领土为基础来行使权力。
很多人相信,原始人类社会组织是部落的,这一见解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比较人类学家,如努马·丹尼斯·甫斯特尔·德·库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和亨利·梅因,认为要在复杂的亲戚团体中去理解早期的社会生活。
[13]
但部落组织的兴起,要到九千年前定居社会和农业出现时。这之前,狩猎采集社会历时数万年,由类似灵长目族团的流浪家庭集居而成。这样的社会,至今尚存于合适的边缘环境,如爱斯基摩人、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ushmen)、澳洲的土著。
 (也有例外,如美国太平洋西北部的土著,属狩猎采集者,却生活于可支撑复杂社会的富饶区域。)
(也有例外,如美国太平洋西北部的土著,属狩猎采集者,却生活于可支撑复杂社会的富饶区域。)
卢梭指出,政治不平等起源于农业的兴起,他在这点上是基本正确的。出现农业之前的族团层次社会,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的私人财产。就像黑猩猩的族团,狩猎采集者居住于他们守卫的领土,偶尔为之争斗。但他们不像农人,犯不上在一块土地上设立标志,说“这是我的”。如有其他族团前来侵犯,或有危险猎食者渗入,由于人疏地广,族团层次的社会有移居他方的选择。他们较少拥有像已开垦的耕地、房子等投资。

族团层次的内部,类似现代经济交易和个人主义的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这个阶段没有国家暴政,更确切地说,人类只体验到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所称的“表亲的专横”。 [14] 你的社交生活囿于你周遭的亲戚,他们决定你做什么,跟谁结婚,怎样敬拜,还有其他一切。家庭或数户家庭合在一起打猎和采集。特别是打猎,与分享直接有关,因为那时没有储存肉类的技术,猎到的动物必须马上吃掉。进化心理学家纷纷推测,现代流行的进餐分享(圣诞节、感恩节、逾越节),都起源于长达数千年的猎物分享传统。 [15] 此类社会中,大多数的道德规则不是针对偷人财产者,而是针对不愿与人分享者。在永久匮乏的阴影下,拒绝分享往往影响到族团的生存。
族团层次的社会高度平等,其主要差别仅在年龄和性别上。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男人打猎,女人采集,繁衍一事自有天然分工。族团内,家庭之间仅有极小的差别,没有永久领袖,也没有等级制度。个人因突出的品质,如力大、智慧、可信,而被授予领袖地位。但该地位是流动的,很容易移至他人。除了父母和孩子,强制的机会非常有限。如弗莱德所说:
简易平等社会的民族学研究中,很难找到某人要求他人“做这做那”的案例,却充满了某人说“如能完成此事,那真太好了”之类的话语。之后他人可能照办,也可能不予理睬……因为领袖无法迫使他人。在我们的叙述中,领袖扮演的角色只牵涉权威,无关乎权力。

此类社会中,领袖因群体的共识而浮现。但他们没有职权,不能传予子孙。没有集中的强制力量,自然就没有现代意义的第三方执法的法律。

族团层次的社会围绕核心家庭而建,通常奉行人类学家所称的异族通婚和父系中心(patrilocal)。女人嫁出自己的社会群体,搬到丈夫的居所。这种习惯鼓励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增加基因的多样化,创造群体之间发生贸易的条件。异族通婚也在减轻冲突中发挥作用。群体之间有关资源或领土的争议,可通过女人的交换而获得谅解,就像欧洲君主为政治目标而安排的战略性联姻。
 群体的成员组成,与之后的部落社会相比,则更为流动:“任何地域的食物来源,不管是派尤特人(Pauite)的松果或野草籽的丰收,冬春猎场上海豹的数量,还是中部爱斯基摩人在内陆峡谷遇上驯鹿群的迁移,都是不可预测的,且分布太疏,以致任何一代的亲戚,即使想组成凝聚排外的群体,也屡屡遭挫。因为生态机遇时时在诱惑个人和家庭采取机会主义。”
群体的成员组成,与之后的部落社会相比,则更为流动:“任何地域的食物来源,不管是派尤特人(Pauite)的松果或野草籽的丰收,冬春猎场上海豹的数量,还是中部爱斯基摩人在内陆峡谷遇上驯鹿群的迁移,都是不可预测的,且分布太疏,以致任何一代的亲戚,即使想组成凝聚排外的群体,也屡屡遭挫。因为生态机遇时时在诱惑个人和家庭采取机会主义。”

农业的发展,使族团层次过渡到部落层次变得可行。九千到一万年前,世界上很多地区出现农业,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大洋洲、中美洲,常常位于肥沃的冲积流域。野草和种子的驯化逐一发生,伴以人口的大增。新兴的产粮技术促使人口繁密,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但埃斯特·博塞鲁普(Ester Boserup)认为,这样讲是因果颠倒了。 [16] 无论如何,它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取决于气候,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1到1人,而农业的发明,则允许人口密度上升至每平方公里40到60人。 [17] 至此,人类的相互接触更加广泛,便会要求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部落、氏族、家族、宗族”,被用来描绘高于族团的新层次社会组织,但用得不够精确,甚至靠此吃饭的人类学家也是如此。其共同特征是:第一是分支式(segmentary)的,第二是以共同的老祖宗为原则。
社会学家涂尔干以“分支”一词来解释由小型社会单位自我复制而成的社会,如蚯蚓的分段。这样的社会以添加新的支系而获得扩展,但没有集中的政治机构,没有现代的分工,也没有他所描绘的“有机”团结。发达社会里,没有人是自给自足的,每个人都要依赖社会中大批他人。发达社会的多数人,不知道如何生产自己的粮食、修理自己的汽车、制造自己的手机。在分支式社会中,每个“支系”都是自给自足的,都能丰衣足食,都能自我防卫。因此,涂尔干称之为“机械”团结。 [18] 各支系可为共同目的聚在一起,如自卫,但他们不依赖对方以获生存。在同一层次上,每个人只能属于一个支系。
部落社会里,支系以共同老祖宗为原则。其最基本单位是宗族,成员们可追溯到好几代之前一名共同老祖宗。人类学家使用的术语中,后裔可以是单传(unilineal),也可是双传(cognatic)。单传系统中,后裔追随父亲,被标为父系;追随母亲,被标为母系。双传系统中,后裔可追随父母双方。稍作思考便可明白,分支式社会只能是单传。为了避免支系的重叠,每名小孩只可分给一个后裔群,或是父亲的,或是母亲的。
在中国、印度、中东、非洲、大洋洲、希腊、罗马曾经流行的宗族组织是父系家族。它是最普遍的,也存在于战胜欧洲的野蛮部落。罗马人称之为 agnatio(族亲),人类学家遂称之为aganation。父系家族只追踪男性的血脉。女人结婚时,便离开自己家族,转而加入丈夫家族。中国和印度的男系家族制度中,女人几乎彻底切断与自己家族的联系。所以,婚姻之日变成妻子的父母悲伤时,只能在女儿的聘礼上获求补偿。女人在丈夫家里没有地位,直到生下儿子。其时,她彻底融入丈夫的宗族组织,在她丈夫的祖先坟前祷告祭祀,保障儿子将来的遗产。
父系家族虽是最普遍,但不是单传的唯一形式。在母系社会里,后裔和遗产追随母亲家族。母系社会(matrilineal)不同于女性掌权得以支配男性的女家长社会(matriarchal)。似乎没有证据显示,真正的女家长社会真有存在。母系社会仅表示,结婚时是男子离开自己家族,转而加入妻子的家族;权力和资源,基本上仍掌握在男子手中;家庭中的权威人士通常是妻子的兄弟,而非孩子的生父。
 母系社会远比父系社会罕见,但仍可在世界各地找到,如南美洲、美拉尼西亚、东南亚、美国西南部、非洲。埃尔曼·塞维斯指出,它们通常建立于特殊环境,如依靠女人劳作的雨林园艺区域。但该理论无法说明,为什么美国西南沙漠地带的霍皮人(Hopi),也是母系社会和母系中心的(matrilocal)。
母系社会远比父系社会罕见,但仍可在世界各地找到,如南美洲、美拉尼西亚、东南亚、美国西南部、非洲。埃尔曼·塞维斯指出,它们通常建立于特殊环境,如依靠女人劳作的雨林园艺区域。但该理论无法说明,为什么美国西南沙漠地带的霍皮人(Hopi),也是母系社会和母系中心的(matrilocal)。

宗族有个神奇的特点,只要追溯到更早祖先,便能进入更为庞大的宗族组织。例如,我是追溯到我爷爷的小宗族成员,邻人的爷爷便是外人。如作进一步的追溯,到第四代、第五代甚至更早,我们两个宗族又找到亲戚关系。如情况合适,大家就有可能携手合作。
此类社会的经典描述是爱德华·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对努尔人(Nuer)的研究,他的著作《努尔人》为数代人类学的学生所必读。 [19] 努尔人是居住在苏丹南方养牛的游牧民族。20世纪末,他们和传统对手的丁卡人(Dinka)联合起来,在约翰·加朗(John Garang)和苏丹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下,向喀土穆的中央政府展开长期斗争,以争取南方独立。但在20世纪30年代,埃文斯—普理查德进行实地考察时,苏丹仍是英国殖民地,努尔人和丁卡人仍生活在传统中。
根据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部落是分支式的。我们把最大的支系,称之为主要部落。它再一步步分割成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部落……第三层次由数个村庄组成,其居民相互之间都有亲戚和家庭的关系”。

努尔人的宗族组织彼此经常打架,通常是为了在他们文化中占中心地位的牛。同一层次内,血统之间互相打斗。但他们又能联合起来,在更高层次作战。到了最高层,全体努尔人同仇敌忾,向以同样方法组织起来的丁卡人开战。埃文斯—普理查德解释说:
每个支系,本身也是可分的,其成员互相存有敌意。为反对同样层次的邻近支系,支系的成员会联合起来;为反对更高层次的支系,又会与同样层次的邻近支系联合起来。努尔人以政治价值来解释这些联合原则,他们会说:如果娄(Lou)部落的郎(Leng)第三层次支系与努阿克瓦科(Nyarkwac)第三层次支系打仗——事实上,两支系之间战事频频——组成这两支系的各个村庄都会参战;如果努阿克瓦科第三层次支系与鲁莫乔科(Rumjok)第二层次支系发生争执——不久前,为了用水——郎和努阿克瓦科将团结起来,以反对共同敌人鲁莫乔科。鲁莫乔科也将组成其各支系的联盟。

各支系能在较高的层次汇总。一旦联合的原因(如外部威胁)消失,它们又倾向于迅速瓦解。可在众多不同的部落社会中,看到多层次的支系。它体现在阿拉伯的谚语中:“我针对我兄弟、我和我兄弟针对我表亲、我和我表亲针对陌生人。”
努尔人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执行法律的中央权威,没有制度化的领导等级。像族团层次的社会,努尔人社会也是高度平等的。男女之间有分工,宗族之内有分代的年龄级别。所谓的豹皮酋长,只扮演礼仪的角色,帮助解决成员的冲突,但没有强迫他人的权力。“在整体上我们可以说,努尔人酋长是神圣的人,但这神圣并没给他们带来特殊场合之外的权力。我从未看到,努尔人特别尊敬酋长,或在谈话中把他们当作重要人物。”

努尔人是分支世系组织获得充分发展的范例,其宗族系谱的规则严格决定社会的结构和地位。其他的部落社会,则更为松散。共同老祖宗,与其说是严格的亲戚规定,倒不如说是建立社会义务的借口。甚至在努尔人中,仍有可能把陌生人带入宗族,视之为亲戚(人类学家称之为虚拟的亲戚关系)。很多时候,亲戚关系只是政治联盟的事后理由,并非构建社团的原动力。中国的宗族往往有成千上万的成员,整个村庄使用同样的姓,这显示中国亲戚关系的假想和包容。当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把自己称作“家庭”时,它的血誓仅是血亲的象征。现代的种族划分,把共同老祖宗推到很远,使宗族系谱的追溯变得异常艰难。我们把肯尼亚的卡冷金(Kalenjin)或基库尤(Kikuyus)称作部落,该称呼是非常松散的,因为他们各自的人数,少至数十万,多至数百万。

实际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曾经组成部落。因此,很多人倾向于相信,这是自然的情形,或有生物学上的原因。但弄不清,为什么你想与四圈之外的表亲合作,而不愿与非亲的熟人合作。难道,这只是因为你与表亲分享了六十四分之一的基因。动物不这样做,族团层次的人也不这样做。人类社会到处建立部落组织,其原因是宗教信仰,即对死去祖先的崇拜。
对死去祖先的崇拜开始于族团层次社会,每个族团内都会有巫师或宗教人,专司与死去祖先联络的工作。随着宗族的发展,宗教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建制化,反过来又影响其他制度,如领导权和产权。相信死去祖先对活人的作用,才是凝聚部落社会的动力,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生物本能。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提供了有关祖先崇拜的最著名描述之一。他的《古代城市》初版于1864年,给数代欧洲人带来启示。欧洲人习惯于把希腊和罗马的宗教与奥林匹克的众神挂起钩来。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则揭示更古老的宗教传统,其他印欧群体,包括移居印度北部的印度—雅利安人,也在遵循这一古老传统。他认为,对希腊和罗马人来说,死者的灵魂并不飞上天国,却住在葬地的底下。基于此,“他们总是陪葬他们认为死者需要的东西——服装、器皿、武器。他们在他坟上倒酒以解渴,放置食物以充饥。他们殉葬马匹和奴隶,认为这些生命将在坟里为死者继续服务,就像生前一样”。
 死者的精灵——拉丁文是manes——需要在世的亲戚不断的维持,定期供上食物和饮料,免得他们发怒。
死者的精灵——拉丁文是manes——需要在世的亲戚不断的维持,定期供上食物和饮料,免得他们发怒。
在最早期的比较人类学家中,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的知识领域远远超出欧洲史。他注意到,灵魂转世(死时灵魂进入另一肉体)和婆罗门宗教的兴起之前,印度教徒奉行类似希腊罗马的祖先崇拜。亨利·梅因也强调这一点,他认为,祖先崇拜“影响着自称为印度教徒的大多数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在多数人的眼中,自己家神比整个印度万神庙更为重要”。
[20]
假如库朗日的知识领域涉及更远,他很有可能发现古代中国相似的葬礼。那里,崇高地位人士的墓穴填满了青铜和陶瓷的三足鼎、食物、马、奴隶、计划陪伴死者的妾。
[21]
像希腊和罗马人,印度—雅利安人也在家里供养圣火。圣火代表家庭,永远不得熄灭,除非家族本身不复存在。
 所有这些文化中,圣火被当作代表家庭健康和安全的神而受到崇拜——这里家庭不仅是现存的,而且是死去多年的列祖列宗的。
所有这些文化中,圣火被当作代表家庭健康和安全的神而受到崇拜——这里家庭不仅是现存的,而且是死去多年的列祖列宗的。
部落社会中,宗教生活和亲戚关系紧密相连。祖先崇拜是特定的,不存在整个社群都崇拜的神。你只对自己祖先有责任,对你邻居或酋长的祖先则没有责任。通常,祖先并不久远,不像所谓的罗马人祖先的罗慕路斯(Romulus)。祖先只是三或四代之前的人,家中老人可能还记得。
 根据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它丝毫不像基督教对圣徒的崇拜:“葬礼的礼仪只容最亲近的亲戚做虔诚表演……他们相信,祖先不会接受他人的奉献,只接受家人的;祖先不需要崇拜,除非是自家的后裔。”此外,每人都渴望有男性后裔(父系家族),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其死后照料他的灵魂。因此,结婚和育有男性后裔变得非常重要。大多数情形下,独身在早期希腊和罗马都是非法的。
根据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它丝毫不像基督教对圣徒的崇拜:“葬礼的礼仪只容最亲近的亲戚做虔诚表演……他们相信,祖先不会接受他人的奉献,只接受家人的;祖先不需要崇拜,除非是自家的后裔。”此外,每人都渴望有男性后裔(父系家族),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其死后照料他的灵魂。因此,结婚和育有男性后裔变得非常重要。大多数情形下,独身在早期希腊和罗马都是非法的。
这些信念的结果是,除了现存子女,每个人与死去的祖先和未来的后裔都有关联。裴达礼(Hugh Baker)这样解释中国的宗族关系,一条绳子代表血脉,“两端是无穷尽的,经过一把象征现在的剃刀。如果绳子遭到腰斩,两端就会自行掉离,绳子不复存在。如果一名男子死而无后,其祖先和后裔的连续体便跟着一起消亡……他的存在是必须的,因为他是整体的代表。除此之外,他又是无关紧要的”。 [22]
部落社会中,以宗教信仰形式出现的思想,对社会组织有极大影响。对先祖的信仰得以凝聚众人,其规模大大超过家庭或族团层次。该“共同体”包括的,不仅是宗族、氏族、部落现有成员,而且是祖先和未来后裔的整条绳子。甚至最疏远的亲戚都会觉得,他们之间有牵连和职责。这种感受,借共同体共同遵循的礼仪,而获得加强。对如此的社会制度,成员不相信有选择的权力。说得确切些,他们的角色在出生之前已被社会预定。 [23]
军事上,部落社会远比族团层次社会强大。一获通知,他们可动员数百乃至数千名的亲戚。第一个以祖先崇拜来动员大量亲戚的社会,很可能享有对付敌人的巨大优势。一经发明,它就会刺激他人的模仿。因此,战争不仅造就了国家,也造就了部落。
宗教在促进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很自然,人们要问:部落组织是既存宗教信仰的结果呢?抑或,宗教信仰是后添的,以加强既存的社会组织?很多19世纪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涂尔干,都相信后者。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它是精英们发明出来以巩固其阶级特权的神话。据我所知,他没有对部落社会的祖先崇拜发表过任何意见。但也可推而广之,说家长在操纵死去祖先的愤怒,以加强自己在活人中的权威。另一解释是,需要帮助以对抗共同敌人的族团领袖,为赢得邻人支持,而求援于传奇或神话中死去多年的共同祖先。虽是他的首倡,但这想法蔓延滋长后自成一体。
很不幸,我们只能推测思想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无人目睹从族团层次到部落社会的过渡。考虑到宗教观念在后来历史中的重要性,假如因果关系不是双向交流的,人们反而会感到惊讶。宗教创意影响社会组织,物质利益也影响宗教观念。但要记住,部落社会不是“自然”的,不是其他更高社会崩溃时回归的首选。它出现于家庭和族团层次社会之后,只在特殊环境中繁荣昌盛。它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靠某种宗教信仰获得维持。如若新宗教引入,原有信仰发生变化,部落社会就会分崩离析。我们将在第19章看到,这就是基督教挺进野蛮欧洲后所发生的。随时间流逝,部落社会被更有弹性、更易扩张的社会所取代,但其缩了水的变种从未消失。
[1]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 Ancient Society );或《人类进步研究:从野性、野蛮到文明》(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纽约:Henry Holt出版社,1877年);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Language, Art, and Custom )(纽约:G. P. Putnam出版社,1920年)。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Light of the Researches of Lewis H. Morgan )(纽约:国际出版社,1942年)。
[3] 赫伯特·斯宾塞,《生物学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Biology )(纽约:D. Appleton出版社,1898年)和《社会学原理》。
[4] 例如参见Madison Grant,《伟大种族的消逝》(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或《欧洲历史的种族基础》(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 )修订第4版(纽约: Scribner出版社,1921年)。
[5] 这一经典之句出自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73年)。
[6] Leslie A. White,《文化的演变:罗马崩溃前的文明发展》(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 )(纽约:麦克劳希尔出版社,1959年)。
[7] Julian H. Steward,《文化变迁的理论:多线性演化的方法学》(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伊利诺伊州乌尔班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3年)。
[8] Elman R.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第2版(纽约:兰登书屋,1971年)。更早尝试进化思路的是V. Gordon Childe,《人类自己创造自己》( Man Makes Himself )(伦敦:Watts出版社,1936年)。
[9]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纽约:兰登书屋,1967年)。
[10] Marshall D. Sahlins和Elman R. Service,《进化与文化》( Evolution and Culture )(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0年)。
[11] 有关进化理论的背景,参见Henri Claessen和Pieter van de Velde,《社会进化概论》(Social Evolution in General),载Henri Claessen,Pieter van de Velde和M.Estelle Smith编,《发展和衰落: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变》(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The Evolution of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马萨诸塞州南哈德利:Bergin and Garvey出版社,1985年)。
[12] Jonathan Haas,《从领袖到统治者》( From Leaders to Rulers )(纽约:Kiuwer Academic/Plenum出版社,2001年)。
[13] 甫斯特尔·德·库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古代城市》( The Ancient City )(纽约州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5年);亨利·梅因,《古代法》(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3年)。
[14] 参见Ernest Gellner,《民族主义与复杂社会的两种凝聚形式》(Nationalism and the Two Forms of Cohesion in Complex Societies),载Ernest Gellner,《文化、身份与政治》( Culture, Identity, and Politics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6—28页。
[15] Adam Kuper,《中选的灵长目:人性与文化差异》( The Chosen Primate: Human Natur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227—228页。
[16] Ester Boserup,《人口与技术变化》(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40—42页。
[17]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 A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 )(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7年),27页。
[18]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的分工》(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3年),特别参见第6章。涂尔干所用的分支式比我的更为广泛,事实上,也许太广泛了,以至不能通用。他将之用于已有高级政治发展水平的国家层次社会。有关批评,参见Ernest Gellner,《民族主义与复杂社会的两种凝聚形式》。
[19] 爱德华·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40年);《努尔人的亲戚关系和婚姻》( Kinship and Marriage Among The Nuer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1年)。
[20] 亨利·梅因,《早期法律和习俗》( Early Law and Custom: Chiefly Selected From 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 )(德里:B. R. Pub. Corp出版社,1985年),56页。
[21]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年),165页。
[22] 裴达礼(Hugh Baker),《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26页。
[23]
像努尔人那样的部落社会,对政治学的理性选择提出了挑战。这些团体中的很多行为,似乎并不基于个人选择,而基于复杂的社会规范。促成努尔人社会组织的,很难想象是社会成员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更像是社会学的解释,让社会组织植根于宗教信仰,譬如祖先崇拜。
政治学家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接受了这一挑战。依他看,社会学传统,无论是涂尔干式的,马克思式的,还是韦伯式的,都认为秩序源于道德、强制或权威的规范。他继续以理性选择理论来审阅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努尔人》,该理论认为人们行为植根于彻底的个人主义。他认为,努尔人家庭或分支所作的彼此交往的选择,反映了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通常与牛资源的效用最大化有关。他列举各种方法,以个人主义的前提来模拟家庭团体之间的争端处理。努尔人的制度可被视作应付互相配合的有效方法,也可通过博弈论来得到模拟。他总结道:“它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政治社会学的问题在于它太偏向社会学,为了强调社会的至高无上,根本不想知道集体行为能否来自个人的决策。此外,它极力坚持方法论的基本假定,如‘社会事实的独立有效性’,或‘各层次分析’的严格分离,进一步显示它实在无法解决问题。它确信社会生活没有疑问的文化高姿态,不鼓励他人去审查私人选择和集体行为之间的联系。然而社会秩序的问题,恰恰需要如此的检验。”罗伯特·贝茨,《无政府社会中的秩序维持:重新解释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The Preservation of Order in Stateless Societies: A Reinterpretation of Evans-Pritchard’s
The Nuer
),载罗伯特·贝茨,《非洲乡村的政治经济》(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Africa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19页。
然而,贝茨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作了错误的两分法。不管是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人类学的角度,既不要求所有行为都基于规范,也不要求个人的理性选择在最终决策中没有发挥影响。总是有某种层次上的互动—通常在最高聚合的社会单位—在那里,理性选择是社会单位所作所为的最好解释。与欧洲相比,奥斯曼帝国具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但在外交政策中,它仍遵循熟悉的规则,作出现实政治的选择来促进自己利益,而不是宗教的选择。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难以解释的是低层次社会单位本身。努尔人为何组成后裔团体,而不是宗教互助会,或像美国年轻人那样的自愿协会?理性选择不可能提供社会动员的理论,因为它故意忽略了思想和规范的作用。后者可能反映出进化更深刻的理性,所考虑的是团体利益,而不仅是个人利益。进化生物学家们正在讨论,基因能否编入程序,从而塑造促进团体适存性的行为,而不仅是个体适存性(就像包容适存性)。没有特别理由证明,社会规范不能促进此类的行为。像自杀爆炸那样的现象,单单它的存在就表明,这并非天方夜谭。参见David Sloan Wilson和Elliott Sober,《为他人:无私行为的进化和心理》(
Unto Others: The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of Unselfish Behavior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David Sloan Wilson,《集体选择的论争:历史和现状》(The Group Selection Controversy: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载《生态系统年度评论》(
Annual Review of Ecological Systems
)第14期(1983年):159—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