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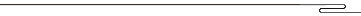
不同于部落社会的国家层次社会;国家的“原生”形成和竞争形成;国家形成的不同理论,包括此路不通的灌溉论;国家为何仅出现于部分地区
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层次社会具有下列重要差别: [1]
第一,它们享有集中的权力,不管是国王、总统,还是首相。该权力委任等级分明的下属,至少在原则上,有能力在整个社会执行统一规则。该权力超越领土中所有其他权力,这表示它享有主权。各级行政机关,如副首脑、郡长、地方行政官,凭借与主权的正式关联而获得决策权。
第二,该权力的后盾是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体现在军队和警察上。国家有足够权力,防止分支、部落、地区的自行退出。(这也是国家与酋邦的分别。)
第三,国家权力是领土性的,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因此,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时期,法兰西还不算国家。其时,统治法兰西的是法兰克国王,而不是法兰西国王。国家的疆土可远远超越部落,因为其成员资格不受亲戚关系的限制。
第四,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更为等级分明,更为不平等。统治者和他的行政官员,常与社会中的他人分隔开来。某种情况下,他们成为世袭的精英。部落社会中已有听闻的奴役和农奴,在国家的庇护下获得极大发展。
第五,更为精心雕琢的宗教信仰,将合法性授予国家。分开的僧侣阶层,则充任庇护者。有时,僧侣阶层直接参政,实施神权政治;有时,世俗统治者掌管全部权力,被称作政教合一(caesaropapist);再有时,政教并存,分享权力。
随着国家的出现,我们退出亲戚关系,走进政治发展的本身。下面几章将密切关注中国、印度、穆斯林世界以及欧洲如何自亲戚关系和部落过渡到非人格化的国家机构。一旦国家出现,亲戚关系便成为政治发展的障碍,因为它时时威胁要返回部落社会的私人关系。所以,光发展国家是不够的,还要避免重新部落化(tribalization),或我所谓的家族化。
世界上,不是所有社会都能自己过渡到国家层次。欧洲殖民者出现之前,19世纪的大部分美拉尼西亚,由群龙无首的部落社会组成(即缺乏集中的权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一半,南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 [2] 缺乏悠久国家历史的事实,大大影响了它们在20世纪中期独立后的进展。与国家传统悠久的前东亚殖民地相比,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中国很早就开发了国家,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直没有,尽管人类抵达后者更早。为什么?这就是我希望回答的问题。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把国家形成分成两种,“原生”和“竞争”。国家原生形成是指国家在部落社会(或酋邦)中的首次出现。国家竞争形成是指第一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与周边的部落社会相比,国家通常组织得更为紧密、更为强大。所以,不是国家占领和吸收邻里的部落社会,就是不甘被征服的部落社会起而仿效。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竞争形成的案例,但从没观察到国家原生形成的版本。政治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只能猜测第一个或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有众多解释,包括社会契约、灌溉、人口压力、暴力战争以及地理界限。
国家源于自愿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洛克、卢梭,一开始并不想提供国家如何出现的实证。相反,他们只是试图弄清政府的合法性。但最先的国家是否通过部落成员的明确协议而建立集中权力,弄清这一点还是很值得的。
托马斯·霍布斯如此解说有关国家的“交易”:国家(即利维坦)通过权力的垄断,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安全,公民放弃各行其是的自由以作交换。国家还可向公民提供无法独自取得的公共服务,如产权、道路、货币、统一度量衡、对外防卫。作为回报,公民认可国家的征税和征兵等。部落社会也可提供一定的安全,但因缺乏集中的权力,其公共服务非常有限。假如国家确实源于社会契约,我们必须假设,在历史上的某一天,部落群体自愿决定将独裁的统治权委托给个人。这种委托不是临时的,如部落酋长的选举,而是永久的,交到了国王和其后裔手中。这必须是部落中所有支系的共识,因为如有不喜欢,每一支系仍可出走。
若说主要动机是经济,即产权的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国家源于社会契约似乎是不可能的。部落社会是很平等的,在密切相处的亲戚团体中,又很自由自在。相比之下,国家是强制、专横、等级分明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把国家称作“最冷酷的怪物”。我们想象,自由的部落社会只会在极端逼迫之下才出此下策。譬如面对即将来临的异族入侵和灭绝,委托一名独裁者;或面对即将摧毁整个社团的瘟疫,委托一名宗教领袖。实际上在共和国期间,罗马独裁者就是这样选出的,如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后,汉尼拔(Hannibal)对罗马造成了切实的威胁。这表明,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暴力,或暴力的威胁。社会契约只是有效途径,并非终极原因。
国家源于水利工程
社会契约论的变种是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工程”论,前人为此花费了很多不必要的笔墨。魏特夫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蜕变成反共产主义者。他发展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专政出现于非西方社会提供了经济解释。他认为,大规模的灌溉需求,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方能满足,从而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墨西哥的国家兴起。 [3]
水利工程的假设要解答很多疑问。新生国家的地区,其早期灌溉工程多数都是小型的,地方上自己就能应付。像中国大运河这种大工程,是在建立强大国家之后,只能算是结果,不应该是原因。 [4] 魏特夫的假设若要成真,我们必须假设,部落成员聚集起来说:“我们将心爱的自由交给一名独裁者,让他来管理举世无双的大型水利工程,我们将变得更加富有。我们放弃自由,不仅在工程期间,而是永远,因为我们的后代也需要卓越的工程主管。”此种情形如有说服力,欧洲联盟早已变成一个国家了。
密集人口
人口统计学家埃斯特·博塞鲁普主张,人口的增加和密集是技术革新的主要动力。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江河流域的密集人口,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业。它涉及大规模灌溉、高产作物、各式农业工具。人口密集允许专业化,允许精英和百姓的分工,从而促进国家的形成。低密度人口的族团和部落社会,为减少冲突可分道扬镳;如发现不能共存,便自立门户。但新兴城市的密集人口并无如此的选择,土地匮乏,如何取得重要公共资源,这一切都可触发冲突,从而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
即使人口密集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仍有两个未获答案的疑问:一开始是什么造就了密集人口?密集人口与国家又是怎样互动的?
第一个问题似乎有简单的马尔萨斯式答案:如农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大大提高了土地产量,导致父母生育更多孩子,从而造成密集人口。问题是,有些狩猎采集社会的利用率,远远低于当地环境的富饶能力。新几内亚高地居民和亚马孙印第安人开发了农业,尽管在技术上做得到,却不愿生产余粮。有了提高效率和产量的技术,可以增加人口,但并不保证这一切确实发生。
[5]
人类学家表明,在某些狩猎采集社会,粮食供给的上升反而导致工作量的降低,因为其成员更在乎休闲。按平均来说,农业社会的居民比较富庶,但必须工作得更加努力,这样的交换可能并不诱人。或者说,狩猎采集者只是陷入了经济学家所谓的低平衡。那是指,他们掌握了转移至农业的技术,因为面对他人分享盈余的前景,旋又打消了转移念头。

这里的因果关系,可能被颠倒了。早期社会的人们不愿生产盈余,除非挥鞭的统治者强迫他们这样做。主人自己不愿辛苦工作,却很乐意压迫他人。等级制度的出现,不在经济因素,而在政治因素,如军事征服或强迫。埃及金字塔的建造,顿时浮现在眼前。因此,密集人口可能不是国家形成的终极原因,只是中间的变数,其本身又是尚未确定原因的产物。
国家源于暴力和强迫
经济解释的弱点和空缺,把国家形成的来源指向暴力。部落到国家的过渡,涉及了自由和平等的巨大损失。很难想象,为了灌溉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部落社会愿意这么做。所以,牵涉的利害关系必须更大,威胁生命的有组织暴力比较可信。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实际上一直参与暴力,尤其是在部落层次。一个部落战胜另外一个时,可能出现等级和国家。为了在政治上控制战败部落,战胜者建立了集中的强迫机构,渐渐演变成原生国家的官僚系统。如果两个部落在语言或种族上是不同的,战胜者可能建立主仆关系,等级制度慢慢变得根深蒂固。异族部落前来征服的威胁,也会鼓励部落群体建立起更永久、更集中的指挥中心,如夏安和普韦布洛的印第安人。

部落征服定居社会的案例,在历史记载中屡有发生,如党项、契丹、匈奴、女真、雅利安(Aryans)、蒙古、维京人(Vikings)、日耳曼人,他们都是以此建国的。唯一的问题是,最早国家也是这样起家的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苏丹南部的部落战争,历时数世纪,却一直没能建起国家层次的社会。人类学家认为,部落社会自有平衡的机制,冲突之后会重新分配权力。努尔人只收纳敌人,并不统治他们。于是,解释国家的兴起似乎还要寻找其他原因。彪悍的部落群体,从亚洲内陆草原、阿拉伯沙漠、阿富汗山脉向外出征时,才会建立更为集中的政治组织。
地理界限和其他环境因素
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注意到,就国家形成而言,战争虽然是普遍和必要的,但还不够。他认为,生产力增长,如发生于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或发生在敌对部落的有效包围中,才能解释等级制国家的出现。在非环绕地区或人口稀少地区,衰弱的部落或个人可随时跑掉。夹在沙漠和海洋中间的尼罗河峡谷,以沙漠、丛林、高山为界的秘鲁峡谷,都不存在逃跑的选择。 [6] 地理界限也能解释,由于没人搬走,生产力的增长只会导致人口密度的增加。
新几内亚高地的部落也有农业,也住在被环绕的峡谷。所以单凭这些因素,也是无法解说国家兴起的。绝对规模可能很重要,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峡谷、墨西哥峡谷,都是相当规模的农业区,又有山脉、沙漠、海洋的环绕。他们可以组成较大、较集中的军队,尤其是在马或骆驼已获驯养的情况下,可在广阔地区施展威力。所以,不仅是地理界限,还有被环绕地区的大小和交通,决定国家的形成与否。地理界限尚可提供额外的帮助,暂时保护他们免遭峡谷或岛屿外敌人的攻击,让他们有时间扩军备战。大洋洲的酋邦和雏形国家,只在斐济、汤加、夏威夷那样的大岛上出现,而不在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Vanuatu)、特洛布里恩群岛(Trobriands)那样的小岛。新几内亚虽是大岛,但多山,被分割成无数个微型的生态环境。
国家源于魅力型权威
推测政治起源的考古学家,偏爱唯物主义的解释,如环境和技术;不大喜欢文化因素,如宗教。这是因为,我们对早期社会的物质环境,已有较多了解。
 但宗教思想对早期国家的形成,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部落社会丧失自由,过渡到等级制度,都可从宗教那里获得合法性。在传统和现代理性的权威中,马克斯·韦伯挑出了他所谓的魅力型(charisma)权威。
[7]
这是希腊文,意思是“上帝碰过的”。魅力型领袖行使权力,不是因为部落伙伴推崇能力而选他,而是因为他是“上帝选中的”。
但宗教思想对早期国家的形成,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部落社会丧失自由,过渡到等级制度,都可从宗教那里获得合法性。在传统和现代理性的权威中,马克斯·韦伯挑出了他所谓的魅力型(charisma)权威。
[7]
这是希腊文,意思是“上帝碰过的”。魅力型领袖行使权力,不是因为部落伙伴推崇能力而选他,而是因为他是“上帝选中的”。
宗教权威和军事威武携手并进,让部落领袖得以调度自治部落之间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它也让自由的部落成员,将永久权力委托给领袖和其亲戚,这比经济利益更有说服力。之后,领袖可使用该权力建立集中的军事机器,战胜反抗部落,确保境内的和平和安全,在良性循环中再一次加强宗教权威。祖先崇拜等宗教受到其固有规模的限制,因此需要一个有的放矢的新宗教。
展示此一过程的具体案例是正统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Patriarchal & Umayyad caliphates)时期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兴起。数世纪以来,部落群体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属埃及、波斯、罗马、拜占庭等国家层次社会的边缘地域。他们的环境恶劣,不适合农耕,所以没有遭遇他人的侵占,也没遇上仿效建国的军事压力。他们只在附近定居社会之间充任中介和商人,自己不能生产相当的粮食盈余。
公元570年,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城镇的麦加,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根据穆斯林传统,穆罕默德40岁那年获得上帝的首次启示,随即开始向麦加部落布道。他和追随者由于受到迫害,在622年搬至麦地那。麦地那部落的争执需要他的调解,他便草拟所谓的麦地那宪法,为超越部落忠诚的信徒团体(umma)定位。穆罕默德创立的政体,尚无真正国家的所有特征。但它脱离了亲戚关系,不靠征服,而靠社会契约,这全凭他作为先知的魅力型权威。新成立的穆斯林政治体经过数年征战,赢得信徒,占领麦加,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中部,一举成为国家层次的社会。
在征战国家中,创始部落的领袖血统通常开创新朝代。但在穆罕默德的案例中,这没有发生,因为他只有女儿法蒂玛(Fatima),没有儿子。新兴国家的领导权因此传给穆罕默德的同伴,他属倭马亚氏族,也是穆罕默德的古莱什部落(Quraysh)中的支系。之后,倭马亚氏族确实开创了新王朝。倭马亚国家在奥斯曼(Uthman)和穆阿维叶(Mu‘awiya)的领导下,迅速战胜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在这些现存的国家层次社会中实施阿拉伯统治。 [8]
就政治思想的重要性而言,先知穆罕默德促使阿拉伯国家兴起是最好的证明。之前,阿拉伯部落只在世界历史中扮演边缘角色。多亏穆罕默德的魅力型权威,他们获得统一,并把势力扩展到整个中东和北非。阿拉伯部落自己没有经济基础,但通过宗教思想和军队组织的互动,不但获得经济实力,还接管了产生盈余的农业社会。 [9] 这不是纯粹国家原生形成的案例,因为阿拉伯部落已有周边如波斯和拜占庭等现成国家,先作为仿效榜样,后予以征服。不过,其部落制的力量非常强大,后来的阿拉伯国家不能完全予以控制,也建不成无部落影响的官僚机构(参看第13章)。这迫使后来的阿拉伯和土耳其朝代采取特别措施,如军事奴隶制和招聘外国人充当行政官,以摆脱亲戚关系和部落的影响。
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创立,昭示了宗教思想的政治力量。这是非常突出的案例,但几乎所有国家,都倚靠宗教使自己获得合法地位。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创始传说,都把统治者的祖先追溯到神灵,或至少一名半神半人的英雄。如弄不清统治者如何控制宗教礼仪以取得合法地位,就不能理解早期国家的政治力量。请看中国《诗经》中,献给商朝创始者的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天帝任命燕子降,入世生下我商王,居衍殷地广且强。古时帝命神武汤,整顿边界安四方。)
另一首颂诗《长发》称:
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睿智的商君,早现朝代的祯祥。洪水滔滔,禹来治理大地四方。) [10]
我们似乎在接近国家原生形成的齐全解释,它需要若干因素的汇合。首先,那里必须资源丰富,除维持生活,还有盈余。这类丰裕可以是纯粹自然的,太平洋西北地区充满猎物和鱼,其狩猎采集社会得以发展成酋邦,虽然还不是国家。但更多时候,创造丰裕的是技术进步,比如农业的兴起。其次,社会的绝对规模必须够大,允许初级分工和执政精英的出现。再次,居民必须受到环境的束缚,技术机遇来到时,其密度会增高;受到逼迫时,会无处可逃。最后,部落群体必须有强烈动机,愿意放弃自由来服从国家权力。这可通过组织日益良好的团体的武力威胁,也可通过宗教领袖的魅力型权威。上述因素加在一起,国家出现于像尼罗河峡谷那样的地方,这似乎是可信的。 [11]
霍布斯主张,国家或“利维坦”的产生,起源于个人之间理性的社会契约,以终止暴力不断和战争状态。在第2章的开头,我曾表明,全部自由社会契约论都有一个基本谬误:因为它假设在史前自然状态时期,人类生活于隔离状态。但这种最早的个人主义从没存在过。人类天生是社会的,自己组成群体,不需要出于私心。在高层次阶段,社会组织的特别形式往往是理性协议的结果;但在低层次阶段,它由人类生物本能所决定,全是自发的。
霍布斯式谬误,还有其另外一面。从蛮荒的自然状态到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从来未见干净利落的过渡;而人类的暴力,也从未找到彻底的解决办法。人类合作是为了竞争;他们竞争,也是为了合作。利维坦的降临,没能永久解决暴力问题,只是将之移至更高层次。以前是部落支系之间的战斗,现在是愈益扩大的战争,主要角色换成了国家。第一个国家问世,可建立胜利者的和平。但假以时日,借用同样政治技术的新兴国家将奋起提出挑战。
我们现在明白,国家为何没在非洲和大洋洲出现,部落社会又为何持续存在于阿富汗、印度、东南亚高地。政治学家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认为,非洲很多地区缺乏自生国家,原因在于各式因素的聚合:“非洲的建国者——不管是殖民地的国王和总督,还是独立后的总统——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人口稀少且不适居住的领土上行使统治权。” [12] 他指出,与大众的想象相悖,非洲大陆上仅8%的地区处于热带,50%的地区降雨不够,难以支撑农业。人类虽在非洲起家,却在世界其他地域繁荣昌盛。现代农业和医学到来之前,非洲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其在1975年的程度,刚刚达到欧洲在1500年的水平。也有例外,如非洲肥沃的大湖区和东非大裂谷(the Great Rift Valley),养活了高密度的居民,并出现集权国家的萌芽。
非洲的自然地理,使权力的行使变得艰巨。非洲只有很少适合长途航行的河流(这一规则的例外是尼罗河下游,它是世界上最早国家之一的摇篮)。萨赫勒地区(Sahel)的沙漠与欧亚的大草原迥然不同,成为贸易和征服的一大障碍。那些骑在马背上的穆斯林战士,虽然设法越过这道障碍,却发现自己的坐骑纷纷死于孑孓蝇传染的脑炎。这也解释了,西非的穆斯林区为何仅局限于尼日利亚北部、象牙海岸、加纳等。 [13] 在热带森林覆盖的非洲部分,建造和维修道路的艰难是建立国家的重要障碍。罗马帝国崩溃一千多年后,其在不列颠岛上建造的硬面道路仍在使用,而热带的道路能持续数年的寥寥无几。
非洲只有少数在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统治者因此而遇上极大的困难,将行政管理推入内地,以控制当地居民。因为人口稀少,通常都有荒地可开;遇上被征服的威胁,居民可轻易朝灌木丛做进一步的撤退。非洲的战后国家巩固,从没达到欧洲的程度,因为战争征服的动机和可能性实在有限。
[14]
根据赫伯斯特,这显示,自部落社会向欧洲式领土政体的过渡从来没有发生于非洲。
 非洲的被环绕地区,如尼罗河峡谷,则看到国家的出现,这也符合相关规则。
非洲的被环绕地区,如尼罗河峡谷,则看到国家的出现,这也符合相关规则。
澳洲本身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与非洲雷同。大体上说,澳洲非常贫瘠,而且甚少差别。尽管人类在那里已居住良久,但人口密度总是很低。没有农业,也没有被环绕地区,由此解释了超越部落和宗族的政治组织的缺乏。
美拉尼西亚的处境则不同。该地区全由岛屿组成,所以有自然环境的界限,此外,农业发明也在很久以前。考虑到多数岛屿都是山脉,这里的问题与规模大小和行政困难有关。岛屿中峡谷太小,仅能养活有限人口,很难在远距离行使权力。就像较早时指出的,具大片肥沃平原的大岛,如斐济和夏威夷,确有酋邦和国家出现。
山脉也解释了部落组织为何持续存在于世界上的高山地区,包括: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老挝和越南的高地,巴基斯坦的部落区域。对国家和军队来说,山脉使这些地区难以征服和占领。土耳其人、蒙古人、波斯人、英国人、俄国人,还有现在的美国人和北约,都试图降伏和安抚阿富汗部落,以建立集权国家,但仅有差强人意的成功。
弄清国家原生形成的条件是很有趣的,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国家出现的物质条件。但到最后,有太多互相影响的因素,以致无法发展出一条严密且可预测的理论,以解释国家怎样形成和何时形成。这些因素或存在,或缺席,以及为之所作的解释,听起来像是吉卜林的《原来如此》(Just So Stories)。例如,美拉尼西亚的部分地区,其环境条件与斐济或汤加非常相似——都是大岛,其农业能养活密集人口——却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无法复原的历史意外。
找到这样的理论并不见得有多重要,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是原生形成的,而是竞争形成的。很多国家的形成是在我们有书面记录的年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开始得很早,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与地中海和新世界(New World)的国家兴起几乎同时。早期中国历史,有详尽的书面和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细致入微的中国政治纹理。但最重要的是,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中国人发展出了明确反家庭的政治原则,其早期统治者刻意削弱豪门和亲戚团体的力量,提倡非人格化的行政机构。中国投入建国大业,建立了强大且统一的文化,足以承受两千年的政治动乱和外族入侵。中国政治和文化所控制的人口,远远超过罗马。罗马统治一个帝国,其公民权最初只限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少数人。最终,罗马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从不列颠到北非,从日耳曼到叙利亚。但它由各式民族所组成,并允许他们相当可观的自治权。相比之下,中国帝王把自己称作皇帝,不叫国王,但他统治的更像王国,甚至更像统一国家。
中国的国家是集权官僚制的,非常霸道。马克思和魏特夫认识到中国政治这一特点,所以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词语。我将要在后续章节论证,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政治上现代国家的早熟出世。在中国,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之前,后者可以是拥有领土的世袭贵族,组织起来的农民,以商人、教会和其他自治团体为基础的城市。不像罗马,中国军队一直处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从没对政治权力构成独立威胁。这种初期的权力倾斜却被长期锁定,因为强大的国家可采取行动,防止替代力量的出现,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要到20世纪,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才能出现,打破这种权力分配。强大的外敌曾不时占领部分或整个中国,但他们多是文化不够成熟的部落,反被中国臣民所吸收和同化。一直到19世纪,欧洲人带来的外国模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途径提出挑战,中国这才真正需要作出应对。
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主要表现在:其他建制化的力量,无法抵消这早熟现代国家的发展,也无法加以束缚,例如法治。在这一方面,它与印度截然不同。马克思最大错误之一是把中国和印度都归纳在“亚细亚”模式中。印度不像中国,但像欧洲,其建制化的社会抵抗力量——组织起来的祭司阶层和亲戚关系演变而成的种姓制度——在国家积累权力时发挥了制动器作用。所以,过去的二千二百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统一帝国,缀以内战、入侵、崩溃;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弱小政治体的分治,缀以短暂的统一和帝国。
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不是为了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在魅力型宗教领袖,而是无情的战争。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一千八百年内,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治体凝聚成大一统的国家。它创立了永久且训练有素的官僚和行政阶层,使政治组织脱离亲戚关系成为可行。就像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评论后期欧洲时所说的,“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就是中国。
[1] 有些人类学家,如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和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在部落和国家中间再分出一个层次,即酋邦。酋邦很像国家,它也等级分明和中央集权,并从建制化的宗教那里获得合法性。它与国家的不同处在于,通常不维持强大的常备军,也无权防止属下部落或地区的出走。埃尔曼·塞维斯,《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第5章;罗伯特·卡内罗,《酋邦:国家的先驱》(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载Grant D. Jones和Robert R. Kautz编,《新大陆向国家的过渡》(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
[2] 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和埃文斯—普理查德编,《非洲政治制度》(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0年),5—6页。
[3] 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参见Henri Claessen,Pieter van de Velde和M. Estelle Smith编,《发展和衰落: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变》,130—131页。参见Henri Claessen和Peter Skalnik编,《早期国家》( The Early State )(海牙:Mouton出版社,1978年),11页。
[4] 参见Michael Mann的讨论,《社会力量的来源》第1卷:《从开始到公元1760年的权力历史》(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1760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94—98页。另请参阅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127—129页。
[5] 参见Kent V. Flannery的讨论,《文明的文化演变》(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载《生态学和生物分类学年度评论》(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 )第3期(1972年):399—426页。
[6] 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国家起源的理论》(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载《科学》第169期(1970年):733—738页。另请参阅罗伯特·卡内罗,《人口密度和社会组织复杂性的关系》(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ze of Population and Complexity of Social Organization),载《人类学研究杂志》(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第42卷,第3期(1986年):355—364页。
[7] 这三种权力为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经济与社会》第1卷( Economy and Society , Vol. I)(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212—254页。
[8] 如需背景资料,参见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章。
[9] 如需背景资料,参见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章;Joseph Schacht编,《伊斯兰教的遗产》( The Legacy of Islam )第2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187页。
[10] 引自F. Max Muller 编,《东方圣典》第3卷(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 Vol. Ⅲ)(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79年),202页。
[11] Robert C. Allen,《古埃及的农业和国家起源》(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tate in Ancient Egypt),载《经济史研究》(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第34卷(1997年):135—154页。
[12] Jeffrey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 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11页。
[13] Jack Goody,《非洲的技术、传统和国家》( Technology, Tradition,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37页。
[14] Jeffrey Herbst,《非洲的战争和国家》(War and the State in Africa),载《国际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第14卷,第4期(1990年),117—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