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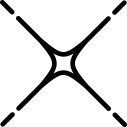
热爱大自然通常被看成是日本人审美观的基础。据说,在中国和日本,人和自然融为一体,不像西方,二者呈对立关系,人倾向于对抗自然界的力量。这一观点时常能在传统画卷或水墨画中得到印证。画中人十分渺小,有时甚至难觅其踪。自然风光可不是映衬人的背景板;相反,人倒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在艺术和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喜欢运用自然界的形象表达人的喜怒哀乐。在将自然界的隐喻和形象织入故事结构这一方面,日本小说家堪称大师。日本人的书信和明信片也总以对季节的简短描述作为开头。
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传统的日式住房建得不像是能经受住风吹日晒的石头堡垒,而是一栋看似十分单薄的木屋,且四面都有出口,看上去就和四季本身一样稍纵即逝。
传统画中既无定点,也无灭点。若俯视观之,画中物体越高,景反而越远。这给观者造成了一种纵深感上的错觉,而不是立体的错觉;没有阴影部分,画中物没有一样是独立存在的:不管是人、屋还是自然,所有一切都相互融合,浑然一体。
这种世界观植根于神道教传统和佛教信仰:在神道教中,世间万物都具有潜在的神性。而在佛教徒看来,人只不过是大自然生死轮回中的一分子。人来世投胎可能是只青蛙,或者是只蚊子。
人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是否令其显得自然呢?我们不妨再打个比方:大自然仿佛一位繁殖力旺盛的母亲,赐予我们吃的喝的,可问题在于,它也蕴藏着可怕的破坏性力量;其会随着毁灭性的地震、凶猛的台风和洪水被释放出来。这就好比女人这类神秘力量,会爆发出可怖的狂热,因此自然必须被降服,或者至少也要得到控制。
因此,日本人对自然的态度不单是爱,还混杂着对不可预知力量的深深恐惧。没错,它受到膜拜,但仅仅是在得到人类双手重塑之后。所有那些与日式住家“自然地”融为一体的美丽园林完完全全都是人造的。一棵野草也别想长出来——某些最受推崇的园林则全部由石块堆砌而成。日本人爱自然,但原生态的自然要除外,因为这似乎并不太招人待见。
这一“自然”当然也包括了人的自然状态,即人性。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箴言“女人是自然的,也就是说是令人厌恶的”恰恰与日本传统思想相呼应。人,尤其是女人,需要重新打扮,培养仪式感,并且尽可能地改造成艺术品。当然了,出于类似的原因,无论我们身居世界哪个角落,做任何事时都很讲究形式。而且,西方社会的一部分人同样表现出过——现在有时仍表现出——对风格的执著。然而,退一万步说,包括日本近邻中国和朝鲜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文化都比日本文化更包容个体的自我性。
日本传统的审美意识往往体现为一种人为的、默默无闻的美。谷崎在小说《各有所好》(‘蓼喰う虫’,1928)中谈到这点时提及了文乐木偶戏 [*] :
真正的小春(剧中一艺伎名)生活在元禄时代 [†] ,可能就像一个娃娃;哪怕她其实不像,人们也会想象她在剧中就是这般模样。那时理想中的美太过含蓄,不足以衬托出她的个性。当个娃娃就已经绰绰有余了,因为任何使她有别于其他人的东西都属于多此一举。简言之,这个木偶版本的小春完美地呈现了日本传统中“永恒的女性”。
谷崎在这部小说里还写到另一位娃娃般的女人阿久。她是京都当地一位品味考究的老淫棍的情妇。用她女婿的话来说,是他“藏品中的一件古董”。老头儿让她穿上旧的丝绸和服,“又沉又呆板,跟链条一样”。她只被允许看传统木偶戏,只被允许吃分量不足的日式菜肴。老头儿把她精心打造成自己的“头号宝贝”。女婿有几分羡慕岳父。想到自己面临的棘手问题,他把“阿久这一类型的女人”视为逃避现实的办法。“最好是能爱上那种可以像娃娃一样被疼爱的女人……老头儿的生活状态似乎显示出他内心十分坦然,而且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要是我也能过上这种日子就好了。”
这种人偶的审美观在川端康成的小说《睡美人》(‘眠れる美女’,1961)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家收费高昂、提供专门化服务的妓院里,年轻姑娘被人灌下迷药后陷入昏睡,然后送去给阔老头当一言不发、百依百顺的床笫伴侣。“对于掏了那么多钱的老头们而言,睡在这样一位姑娘身旁实在是好福气。由于他们不能弄醒姑娘,也就不必为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感到难为情。另外,他们可以浮想联翩,尽情地回忆昔日伊人。”
川端在书里几次将这些睡美人比作佛教里的神祇,拯救并宽恕老翁们的罪过。“没准她就是佛祖的化身,”老头暗自想道,“没准就是这样。毕竟,有传言说佛祖会佯装成妓女。”这些被迷晕的姑娘和佛祖一样,不光形似玩偶,同神秘佛像那样全无个性,而且纯真无邪。她们可以被人玩弄,但终究不可玷污,因为她们虽是供人睡的对象,但清清白白。川端似乎在说,只有依靠这样的单纯,人才能获得拯救,并接受死亡。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若松孝二拍摄的《无水之池》(‘水のないプール’,1982)一片中。一个地铁站的年轻检票员发现了强奸女青年的绝佳办法。他在夜间潜入她们家中,用皮下注射器在房间里喷洒氯仿。待姑娘适度昏迷后,他就能为所欲为了。其中有一幕,他将三个熟睡的裸女放在布置得如同节庆般的餐桌旁,然后仔细地用口红和胭脂为她们化妆。他手中的宝利来相机的闪光灯不时闪动,凸显出这组奇异、无声的景象中透露出的灵异之美。这在日本算不上最离奇的电影。无名强奸者在日本娱乐作品中可谓司空见惯的形象,可以想见,对于隐姓埋名的幻想在日本一定很有群众基础。我们清楚地感受到,这部片子对匿名强奸者怀有深切的同情。在最后一幕定格画面中,他向我们吐舌头:他藐视这个世界。这或许可以从社会角度得到解释:在日本很难独自生活,在传统住房里就更加不可能。再说了,在一个如此看重颜面的社会里,人际关系充斥着责任和义务,纷繁复杂,要参透这点可不容易。
另一方面,日本人普遍害怕孤独,担心与人疏远。克服这点的办法似乎是隐姓埋名地混迹于人群中。人们通过合群,却又不真正与人交流来获得心理宽慰:于是,我们每日在东京见到数以千计张毫无表情的面孔,人们在柏青哥弹珠机前流连忘返,或静坐在一排排长椅上,像是神情恍惚的流水线工人。匿名强奸者的幻想也是由此而生的。
对玩偶式女性的偏爱也有许多不那么反常的表现形式。举例而言,“玩偶女”是百货商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被训练得尽可能和木偶一样。这些开电梯的姑娘身穿漂亮的制服,戴着洁白的手套,用做作的假声迎接顾客,继而再按照规定摆动手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活像玩具兵,动作一成不变,总是指向电梯运行的方向。
这些姑娘不仅被训练得像舞台上男扮女装的演员那样说话,而且还像从事高雅艺术那样练习礼仪性鞠躬,务求精准无误。一位自豪的人事经理曾带我参观一座训练中心,他向我解释怎么用机器教这些姑娘正确鞠躬。这是台不锈钢制的新鲜玩意,立在一尘不染的房间中央。一条钢臂顶着姑娘们的背,将她们推到理想的角度:15度、30度、45度,电子屏幕上精准地记录着这一切。“您知道么,这不光是给新人练习用的,”经理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边说还边用手杖戳了戳一位年轻职员,“老员工也时不时喜欢用它来练习一下鞠躬。”更有甚者,部分商店为了省钱,还决定采用真正的人偶替代活人,可是此法不通:顾客抱怨说机器人没有人情味儿。
说到展示玩偶式女性,电视可谓一面琳琅满目的橱窗,比方说深夜档节目里登场的所谓“吉祥物姑娘”,她的唯一用处就是坐在椅子里,对着摄像机挑逗式地眨眼,而且自始至终不能说话。在西方也能见到这类人:譬如展会上站在车顶的模特。这些身着比基尼的尤物至少还装得有事情可干,哪怕只是把道具递给问答竞赛主持人。但在日本,姑娘们只是杵在那儿,打扮得漂漂亮亮,但神情漠然。
少年“偶像明星”往往是玩偶。在经过精心规范、再三指导和千锤百炼之后,他们身上起初可能存在的任何自发性都将荡然无存。每个动作、每个手势、每个笑容、每句话都是彻底训练的结果。近年来最极端的一例是一对叫“粉红淑女”(ピンク·レディー)的演唱组合。两位有着大长腿的姑娘风靡大街小巷,红了几乎有三年之久。她们不仅唱歌跳舞时动作完全一致,就连讲话也是异口同声,而且始终带着电梯间姑娘的那种假声。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数年,之后,尽管十分偶然,但塑料般外表的背后开始透射出一缕人性的微光。这一细微暗示,说明“粉红淑女”其实是人,而不是聪明的机器人。恰恰从这时起,她们在青少年中的女神地位开始动摇。当两个娃娃身上的生命力充分苏醒后,她们谢绝了一档久负盛名的新年大联欢电视节目的邀约,会过气也就势所必然了。
很明显,许多所谓的“名流”,比方说美国电视节目上的那些人,和日本演员一样也经过精心雕琢,与他们的“真我”已是相去甚远。不过表演方式不尽相同:在美国,演员训练是为了显得自然,不拘一格,一句话,得真实。演戏就要演得“自然”;不能让人看出这一切都是假的。怎么说电视表演者也是名流。
在日本,情况往往相反。人们对“真我”不那么感兴趣,也不尝试掩饰假象。相反,人们对矫揉造作的表演倒是很欣赏。演员不会刻意装得不拘一格或贴近真实,因为只有外在形式,或者也可以说是伪装之道,才是表演的奥义。这倒不是说日本的专业电视演员都会表现得很不起眼,事情往往是反过来的:电视给一些人撒泼胡闹大开便利之门——像疯癫的小丑那样大喊大叫——毕竟这不是个真实世界。不消说,这和一本正经的那一派同样做作。
以传统木偶戏为例,文化差异便十分明了。西方的戏台上,操纵木偶的人不会露面,为的是让木偶尽可能显得真实。而在日本,表演者会手提木偶一道登台:没有理由把他们藏起来。观众想要看到他们,好欣赏其技艺,这就好比早期日本电影观众既对银幕上闪烁的画面如痴如醉,也对放映员深深着迷一样。这样说来,美国名流和日本达人或许都是木偶,但普通美国观众不希望有人道破这一点,日本人则并不介意。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社会生活。一个社会越重形式,人们扮演的角色也就越鲜明。从这点来看,日本这个民族就很好理解了。表演,即有意识地按照规定模式表现自己,这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痴迷于故作“率真”,以至于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不是在演戏,而是……本来即是如此。极端的暴力被视作是“忠于自我”,值得赞扬。在日本,多数情况下,个人意愿仍得服从于社会形态。日本人是个礼貌的民族,因此多数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戏。
当然多数日本人都能意识到这点。个人在公开场合和私底下的形象差距之大,往往令人震惊。开电梯的姑娘一下班,嗓门就会低几个八度: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很显然,日本人同其他人一样也有独立人格。但个人情感也只有在需要亲昵的场合(通常是酒桌上)才能得到发泄,这种时候迸发出的情感也许常常显得过于伤感,但那又是另一番做戏了。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日本的生活在外人眼里极具戏剧性,甚至连人们的穿着往往都很做作。总而言之,日本人所崇尚的身份与他们所处的团体及所从事的职业挂钩,而不是仅仅被视为个体。没有哪位称职的日本厨师会愿意被人瞧见自己没有戴高高的白帽;“知识人”都戴贝雷帽和墨镜,如同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巴黎左岸的流亡人士。文身的帮派分子穿着艳俗的条纹西服。简言之,所有人的穿着都视其角色而定:就连无业游民也像极了舞台上的流浪汉,衣衫褴褛,头发像打了结的绳子一样垂至腰际。
这种顺应规范化模式的倾向也许在传统艺术中最为突出。这些模式,或者形式,在日语里叫“形”。举例而言,歌舞伎就以“形”为基础:演员从小就通过模仿师父,学到了一整套传统的姿势和动作。因此,除名伶自己添加的、只有内行才看得出来的元素外,戏中每个人物的动作编排,小到最小的细节,几个世纪以来从未变动。有意思的是,歌舞伎中的不少姿势和手势是直接从木偶剧中照搬而来的。
但是“形”也有着更加现代的面貌。日本厨子不同于法国或意大利同行,一般不会自行创造菜谱。相反,在经年累月地模仿师父的动作后(还真就是模仿,因为日本烹饪更多考验的是刀工,而不是对各种佐料的搭配),他就学到了自己这一行的“形”。说到底,学做生鱼片跟学习空手道的腿法是一回事:都是靠不断地模仿既有套路。
无论是切鱼、摔倒柔道对手、插花,还是社交中的做戏,“形”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理应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对于“形”的学习,日语里有这样一句话:“体で覚える”,也就是说要身体力行地去学,用身体记住;像小孩子学游泳,甚至是学鞠躬,他们还在母亲背上时就已开始这种学习。这一过程时而还要伴随师父和师兄的不少欺凌,这被认为是一种精神锻炼,像极了旧式英国公立学校里以大欺小的现象。只有长时间忍下来的学徒才能指望当上师父。很显然,一位厨师学徒将一生中的三年时间用来学习如何正确地将饭团砸进左手掌后,是不会揭穿这种劳形伤神的学习方法的:他经历的磨砺已经太久、太严酷了。
有意识的思考被认为是臻于完美的阻碍。日本师父从不做解释,询问为何要做某事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形式。人们常能看见生意人在拥挤的月台上练习高尔夫挥杆的动作,或者看到学生反复练习投掷棒球,不过也仅仅是做做动作而已。棒球和高尔夫很难算得上是日本的传统技艺或非常崇尚精神的活动,但是学打棒球和高尔夫的过程完全是传统的。人们认为,只要肯苦练规定动作,自会有如神助一般击中来球。同理,著名禅宗射手拉了几年弓后,闭着眼睛也能射中靶心。基本上可以说,理想情况是形式左右人,而不是人左右形式。
一位著名的日本文化批评家曾将这种以“形”为主的文化——他称之为“艺道”——与另一种重内容、轻形式的较为轻松流行的文化作了清楚的区分:依照他的观点,“艺道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充斥着武士阶级的贵族思想。另一种文化蔚为大观时,脱离了宗教,继而以庶民百姓的玩乐精神(遊びの精神)为基础”。
在大多数国家都能作类似区分,但其是否真的合理呢?答案只能是仅仅部分合理。贵族艺术和民间“玩耍”之间显然有差别,但这两种传统的确能互相影响,彼此反哺。因此,把一种归为形式艺术、另一种算作实质艺术的说法是令人生疑的。不过,日本人即使是沉浸在最通俗、最忘情的玩乐之中,仍不忘遵守“形”的规则,这点着实令人称奇。
[*] 文乐又称“人形净琉璃”,是用木偶(人形)演出,搭配“太夫”的道白和三弦的音乐表演的艺术形式。——编注
[†] 元禄为日本的年号之一,指1688年到1703年的期间。——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