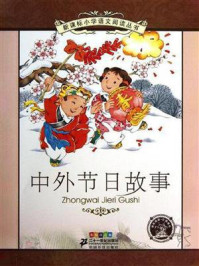出普林斯顿大学朝向拿骚街(NassauSt.)的大门,在街的尽头拐上默瑟道(MercerSt.),步行约十五分钟,在红绿灯处向左一转,就上了那条破破烂烂的老街(OldenLane)。老街路面斑驳,年久失修,不过,静卧在古木与老宅中间的这条旧道与周围幽深雅静的氛围到底还是协调的。也许,此地的主人有意保持这样的状态,以挽留几许旧日情趣,或者,他们是怕游客如织,破坏了这里的清幽。
走过几个街口,眼前豁然开朗,右面一大片圆形草场,绿茵中间,两列白皮梧桐辟开一条“大道”,“大道”尽头是由一座带钟楼的乔治亚式建筑率领的小建筑群。远远望去,钟楼在阳光下烨烨生辉,红砖砌成的楼宇庄重而典雅。转向左面,一幢幢的二层公寓,一色仿包豪斯式建筑,散落于树木和草地中间。最让人称奇的是那些纵横左右的便道小径,不起眼的小路,居然顶着响当当的名号:麦克斯韦(Maxwell),冯·诺依曼(von Neumann)……自然,最响亮的还是福德楼(FuldHall)前那条环绕圆形草场的路名:爱因斯坦路( Einstein Drive )。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了。
高等研究院声名远播,据说它在欧洲的名气比在普林斯顿更大。不过,知道高研院大名的人大多对它也不甚了了。人们提到高研院时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把它径直接在“普林斯顿大学”后面,结果,生来便睥睨傲世的高研院竟屈尊成了普大的一个部门。这也难怪,高研院太小,且地处一隅,夹在一大片高尔夫球场和更大一片森林之间,若不是在林中迷路,一般人或许还发现不了这片学者的清修之地。更重要的是,高研院的设计者和创建者从一开始就想把这里建成一个最最崇高的学术殿堂,纯而又纯的象牙之塔。如此遗世而独立,世间的令名美誉又何足道哉。

从林地望福德楼(背面)
高研院建于 1930 年,是两位实业家兼慈善家的慷慨、远见同一位大教育家的大胆奇思相结合的产物。1929 年,新泽西富商班伯格(Bamberger)兄妹卖掉生意,有意捐一笔巨款在当地建一所医学院,这时他们遇到了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这位弗莱克斯纳当真是一个教育界的异人。他是美国著名的大学教育改革家,对医学院的改革贡献尤大。不过,当他在“耳顺”之年得此天赐良机,能够将毕生探索得来之理念付诸实施,办一所理想的大学时,他心中想到的却不是什么医学院,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一所独一无二的顶尖级学府,一个目标单纯、旨在推进尖端知识的“学人社会”( society of scholars)。他写道:“它必须是个自由自在的学人社会。要求自由自在,乃是因为成熟的人,出于知识的目的,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去达成他们的目标。也必须具备单纯的环境,尤其重要的是宁静——不必受俗世的干扰,也毋须负责教养那些不成熟的学生族群。”弗莱克斯纳写这段话时想到的乃是法兰西学院和牛津的万灵学院。那是在 1929 年,当时他决计想不到,一年以后会有可能梦想成真。
班伯格兄妹首批捐献的款项约有 3 千万美元之巨,如此坚实的经济基础,足以令世间最大胆的奇想付诸实现。但这些都还是第一步。接下来须要选址建院,更要网罗贤能,礼聘大师。最后,经过一番准备筹划,院址定在美丽幽静的新州小镇普林斯顿,与著名学府普林斯顿大学为邻。不过,直到1930 年代末院所建成、全体教职员迁入现址之前,高研院主要借用普大数学系所在的范氏馆。显然,这也是人们常常错把高研院叫成“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一个原因。
高研院聘请的第一位教授是爱因斯坦。请到这位物理学教宗无疑是高研院历史上最成功的举措之一。直到七十年后的今天,公众仍习惯于把高研院同爱因斯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径以“爱因斯坦研究院”相称。爱因斯坦成为高等研究院的象征,但这不只是因为他享有崇高声望,也是因为,他所探求的知识,以及他探求知识的方式,无不表明高研院建院的宗旨。
1933 年爱氏初入高研院时,他的三位同事分别是拓扑学之父詹姆斯·亚历山大( James Alexander)、现代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和数学家奥斯瓦尔德·维布伦(Oswarld Veblen)。同年进高研院的还有一批来此深造的“工作者”,他们多数获得博士头衔不久,在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且发表过有潜力的学术论文。其中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哥德尔。这些人,教授和工作者,物理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都研究高深而抽象的学问。他们探问宇宙的奥秘,大至星体,小至粒子,无不在其观照之下。不过,与普通科学家不同,他们没有实验室,也不借助天文望远镜、显微镜或者高能加速器,他们的工具是方程式,是他们的笔和脑。相应地,他们最关心的并非知识的应用,而是知识本身。就像数学家莫尔斯(Harold Marston Morse)说的那样:“虽然我研究的是天体力学,但是我对登陆月球可没什么兴趣。”尽管偶有例外,这种醉心于抽象理论和纯粹知识的好尚确实表明了高研院立院之本。
要保持这样一种知识情趣,维持高研院建院宗旨于不辍,须要满足若干条件。

从林地望社科与人文图书馆
首先是经济条件。高研院虽无实验设备之需,但是建院之前的征地建屋、大兴土木,建院之后的招贤纳良、管理运作,在在都需要坚实的财政支持。而且,欲使院内研究人员心无旁骛、一心问学,丰厚的薪俸必不可少。至于那些大师巨匠,不用说更要重金礼聘,终生奉养。幸运的是,高研院自成立始,从不曾为金钱所苦,有时,问题竟是因为付酬太丰而起。当年,爱因斯坦要求年薪 3000 美元,弗莱克斯纳认为太少,最后以 1 万美元(按:约合 1994 年的 8—9 万元人民币)定案。爱氏最早在高研院的同事维布伦的年薪更高达1.5万美元,外加退休金 8 千美元。据说仅是这笔退休金就相当于甚至超过当时普大一些极杰出教授的全职薪水。如此优厚的薪俸为高研院带来了“高薪研究院”的雅号,自然,也曾引起院内院外的不平之声(关于高研院教授的薪俸,社会科学部教授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评语是:“对凡人很多,对半神半人却太少”)。1980 年代中期,高研院终身教授年薪约为 9 万美元,现在应该水涨船高,在 10 万以上了。当时全院年度预算大约 1000 万美元,占高研院资产的十分之一不到。而据高研院去年的报告,截至 2000 年年底,院净资产为 3 亿 6570 多万美元,当年各部门支出总计则是 2800 多万美元。
其次,研究人员应无行政与教学之累,专心学术,这正是当初创立“学人社会”的构想。高研院成立之初,曾将颁授博士学位事项载明其组织章程,但又旋即改变初衷,宣布只有已获博士学位或具相等程度资历者方可申请进入高研院。这项安排并非没有争议,但已成为定制,延续至今。当年弗莱克斯纳在解释这一改变时说:“我不打算颁授博士学位,因为我不想把教职员卷入论文审核、考试以及杂七杂八的相关行政工作上。世上多的是提供学位的地方,我们志不在此,而是有更崇高的理想。”撇开其他方面不论,这一制度确实为高研院教授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令他们可以专心于自己的研究和履行他们在高研院的另一些重要职责,比如指导后进、组织学术活动、确定新的研究方向,等等。
高研院终身教授人数不多,加上已经退休的荣誉教授也不过三十来人。整日在办公楼进出的,除行政人员之外,便是每年更新的研究员和访问者。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通常保持在一百八十人左右。说起来,最轻松自在的还是这些暂驻的访客。他们享有高研院提供的金钱、住所和一应便利,唯一的“义务”,只是在访问期间驻院。驻院有利于学者之间的切磋与合作,增强“学人社会”的群体认同。更重要的是,高研院刻意营造这种物质环境和知识氛围,正是为了给来访的学者们提供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彻底摆脱俗务,一心问学。生活在这样一个学者乐园当中,与大师和同侪们朝夕相处,智慧生长、学术精进,岂非指日可待?
然而,要建设一个学者乐园,还有一项条件不可缺少,那就是学者们生活和工作的物质环境。高研院最初的章程曾经载明院址应选在新泽西州纽沃克市内或市郊,幸而这一条最后并未付诸实行,否则,高研院绝不会有今日的魅力。美国的一些名校,如纽约的哥大、费城的宾大、纽黑文的耶鲁,皆因为所在城市衰落、环境恶化而面临种种问题。普林斯顿是小地方,风景秀丽,环境清幽,绝无大都市的嘈杂拥扰,但也并非偏远闭塞之所。从普林斯顿到纽约或者费城,只需一个小时,再远一点到北面的波士顿或南面的华盛顿,也只需半天时间。因此,普林斯顿的居民无需忍受现代都市病,却可以享受大都市的种种好处。自然,与普林斯顿大学为邻也很重要。两三所学术机构连在一起也能自成气候。
大环境好,小环境也要适宜。尤其是以学者乐园相标榜的地方,一定要让它的居民生活无忧、乐不思“俗”才好。自然,不思“俗”的意思不是要人做苦行僧,而是让人完全不为俗务所累。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要解决的便是“住”。
高研院终身教授人数不多,而且长居此地,住房自然不是大问题。相比之下,每年来访者人数众多,其中多数还携有家小,这些人的住所真正是个问题。美国许多大学,尤其是在东西海岸的名校,通常无力也无意为访问学人提供住房,而这些地方从来人满为患,房价高扬。找一个合适的住所,即使是对本国学者来说,也总是一件让人头疼不已的事情。花几周时间安顿下来是常事,前后折腾几个月的也不乏其例。在这方面,高研院同样与众不同。它有自己的能容纳约二百户的公寓区,足以满足每年到访者住房之需。这些公寓设计美观,实用大方,内部设施一应俱全,不但配有全套家具和餐具,就连电话也已经装好。新人到来,即使是孓然一身,也不致有生活匮乏之虞。院内还设有幼稚园,有接送学童的校车和来往于普大和镇上的班车。每年新学期之前,有关部门会把载有详细说明的相关材料寄给来访者,让他们事先了解与在高研院生活和工作有关的详情,并帮助他们选定住所。这样,早在搬入高研院之先,这些人就已预先知道了自己新居的地址、电话号和电子信箱地址。我在美国游学数年,这种经验是绝无仅有的。
安顿下来马上要考虑的问题是“食”。高研院有自己的食堂,不过,这可不是我们在听到“食堂”两个字时通常想到的那种场所。长方形的宽大厅堂,足有两层楼高,一面连着有喷水池和白桦树的庭院,另外两面装饰有大幅的抽象派油画,还摆放着对本院具有纪念意义的铜塑胸像。这里是饭厅,也是高研院同仁们日常交际之所。此外,高研院还在这里迎来送往,宴宾客,开舞会。食堂每周五天供应早餐和中餐,外加两顿晚餐。普林斯顿是国际性的社区,小镇上有各种不同风味的饭馆和食物。不过,美食家绝不会错过高研院食堂。这里食物的丰富与精美,用美酒佳肴四个字来形容也不过分。请来访的朋友在那里用餐,肯定不会让人感到失望。

社科与人文图书馆一角
安居然后乐业。接下来便要坐办公室、钻图书馆了。凡是高研院的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教授们有自己的秘书,办公室宽大明亮。研究员的办公室自然小很多,但是电脑、电话、书橱、书桌等基本设施却也一应俱全。在我访问的社会科学部,打印机、复印机和传真机是“公共财产”,此外,另有一间公用办公室,一位秘书为大家服务。想来其他几个部的情况也大体不差。
高研院有两座图书馆,一座设在福德大楼正中,古色古香,专供自然科学研究之用。另一座建在历史和社会科学所在的“西楼”和一片池塘之间,造型现代,专门收藏人文和社会科学文献。这些图书馆规模不大,藏书有限,但是自有特点,独具魅力。人文社科图书馆是我在高研院时常去的地方。两层楼的图书馆,设计现代,布局雅致,极舒适而亲切。二楼采光最好,书架之间摆放着宽大的书桌,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走在上面悄无声息。与那些迷宫一般的大学图书馆相比,它更像是一座私人图书馆,属于高研院的每一个成员。没有出纳员,也没有看门人。“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使用者可以自由出入,随意取阅(书刊),且数量不限,甚至时间也没有限制。如果不是碰巧收到图书馆应其他读者要求而发出的还书催单,很难意识到还有别人同你一道分享这座图书馆。这种经验使我了解到什么是真正自由的“学人社会”。
高研院诸同仁享有如此优异的服务,自然会戮力本业。这时应当有适当的精神调剂,益增其乐。高研院的娱乐活动多种多样,从舞会、聚餐、读书会到电影展播、音乐会和观光游览,应有尽有。而比这些更加重要的是,高研院本身就是一片无忧的田园,鸟语花香,恬淡悠然。人之所至,尽是美地,目之所及,皆成胜景。一棵树,一片草,一泓水,无不透着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空中飞鸟,林中麋鹿,在在显示了这片乐土的欢乐与自在。无怪乎新到的同仁们聚到一起,异口同声把高研院说成是“天堂”(paradise)。
天堂是人人向往的极乐至福之地,但是做一个天堂居民却不一定没有烦恼。当初弗莱克斯纳请来爱因斯坦,为确保爱氏不受外界干扰,以不辱其创造伟大理论的使命,竟然常常截留爱氏往来信函,甚至代为回复。有一次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爱氏夫妇参加一个在白宫举行的晚宴,弗莱克斯纳获悉此事之后,立即回电给白宫,不客气地说爱因斯坦很忙,没有时间赴白宫的晚宴。接着他还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信给白宫,其中说“爱因斯坦教授应聘来普林斯顿,为的是能与世隔绝,专心从事科学工作”。信的结尾说:“我们绝对不可能开此恶例,免得使他无可避免地成为公众人物。”对这类事,爱因斯坦忍了又忍,终至忍无可忍,最后只好向高研院理事会提出申诉。有一则记载说,爱氏当年致信友人时,曾经自我调侃地把信封上的地址写成“普林斯顿高等集中营”。自然,这些都是旧时故事,今天的高研院要有人情味得多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什么问题不是因人而起呢?弗莱克斯纳早年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要把高研院建成“学者的天堂”( aparadise for scholars),这位朋友却向他泼冷水说,这种想法可当不得真,“对一个人来说,天堂肯定是个好地方,但再加哪怕一个人,那可就要命了”。“我们还是试着认识人性吧”,这位朋友最后说,“因为我们打交道的是人,而不是天使”。弗莱克斯纳任院长职不过十年,就因为刚愎自用行事专断而尽失人心,终于在一场教授们发动的“政变”中丢了位置。实际上,高研院自建院以来,各种各样的紧张(教授与院长之间、院长与理事之间、理事与教授之间,以及所有这些人与捐助人之间)和纷争(任命之争、设系之争、薪俸之争)从未停止过。
记得一次晚会上与在高研院已经整整三十年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闲聊,内子说到我们都非常喜欢的高研院,随口说出“paradise'这个词。老人听了微微一笑,把这个字重复了一遍,正要说些什么,却被下面的节目打断了。后来我读到格尔兹的学术自传《追寻事实》(after the fact)“,读了其中专门讲高研院的几页,于是明白了那个微笑的意思格尔兹在 1970 年由芝加哥大学转来高研院,很快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最不同寻常但又极为艰难”的学术环境之中。这种艰难在两年后的“贝拉事件” (The Bellah Affair) 中暴露无遗。当时,格尔兹在院长卡尔·凯森(CarlKaysen)支持下提名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Bellah)为高研院教授,不料遭到各方阻挠甚至攻击。教授中早有人对经济学家出身的院长不满,对设立永久性的社会科学部不高兴。种种不满,加上以往的积怨和矛盾,借此机会一并发泄出来。提名之议演成一场公开冲突,更有人私底下串联媒体,将事态扩大。一时间,“乐园”之内的阋墙成为一些报纸的卖点,且看这些冷嘲热讽的标题:“天堂里的麻烦事”,“象牙塔里的内讧”,“奥林匹斯山上的晦日”。这场风波,据格尔兹说,几乎令高研院分崩离析。后来凯森院长虽然力排众议,强行通过了对贝拉的提名,但是饱受内心创伤的贝拉对高研院兴味索然,没有赴任。凯森院长和格尔兹教授也都感到深受伤害。自然,到世纪之交我有幸造访高研院的时候,所有这些陈年旧事都已经烟消云散,不为人知。院内各研究部门和睦相处,遇有活动,大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无论如何,高研院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学术建制也已经牢牢确立,纵有人际之间的纠葛纷争也不足为虑。尤其是,高研院大多数研究人员来此只是暂驻,不大受校园政治影响,却最能享受这天堂乐园的种种乐趣。
当然,要在这样的地方硬挑出点“毛病”也还是可能的。天堂好处多多,只是“高处不胜寒”,难免寂寞之苦。大抵携配偶同来、与家小同住的,尚不致孤独难耐,若是孤男寡女,一人独处,有时不免会觉得百无聊赖。我在高研院认识的一位单身朋友,在自然科学部作博士后研究,一住三年,到了周末便四处活动,不是去镇上“吃早茶”,就是找什么地方看电影;这个月去参加本地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下个月到邻州另一个朋友的婚礼上充摄影师。自然,有机会他也会把天下豪杰拉来高研院,先在大饭厅聚餐神聊,然后到他在林边的住所玩猜字游戏。他是非常出色的青年,研究很前沿的超弦理论。像前辈爱因斯坦一样,他也不靠实验设备,只用纸、笔和脑(现在加上了电脑)。6 月的某个中午,我看见他跨卧在图书馆前的石条上,竟似睡着一般。事后问他,他说原来是坐在那里思考,想着想着就躺了下去,觉得那样更舒服一点。我看着他,心想他躺在石条上究竟是睡过去了呢,还是真的在闭目凝思。也许,睡与不睡没那么大区别,反正他当时是在神游太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