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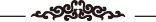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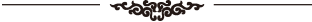
在讲中世纪哲学之前,我要引用两段话,分别是近代哲学史上的两个大家赫尔德与卢梭说的。
赫尔德说:“每一个民族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一个阶段,并成为另一个民族的准备阶段。把这一观点应用到西方历史上,就意味着决不能把中世纪看作是最黑暗的野蛮时期。中世纪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对于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从它自身出发来加以理解。”

卢梭说:“没有信仰的哲学是错误的,因为它误用了它所培养的理智,而且把它能够理解的真理也抛弃了。”

赫尔德在这里指出了中世纪的历史意义,卢梭则指明了信仰对于哲学的意义,而中世纪哲学一个最根本的特点恰恰就在于它是一种有信仰的哲学。也许这就是中世纪哲学最大的特点与优点。
说完这两段话之后,我们开始来讲中世纪哲学。
中世纪哲学对于我们而言称得上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当然先是熟悉它的名字,并且也知道它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和宗教即基督教关系密切,甚至被称为“神学”——关于神的学问,陌生指对它的具体内容陌生。
一直以来,中世纪哲学都称得上是西方哲学中比较另类的,被从西方到中国的许多哲学家与著作忽视甚至蔑视,究其原因有二:
首先与对中世纪整个的态度有关。
一直以来,中世纪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黑暗世纪”,这是他们对于中世纪一个总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无疑是贬义的,就像文艺复兴是褒义的一样。在西方人,主要是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与近代时期的西方人看来,中世纪整个儿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的文化没落了,从光辉灿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堕入了一片黑暗之中,这一片文明的暗夜就是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到来之后,西方文明才从黑暗重新走向光明。
我们甚至可以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名字看出它们的贬义与褒义,中世纪意思就是“中间的世纪”,文艺复兴意思就是“文学与艺术的复兴”,这里的复兴指的是复兴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与艺术。这也就是说,对于西方人而言,中世纪只是一个中间的世纪、一个过渡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伟大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衰落了;后来,这个中间的、过渡性的时期终于过去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也终于复兴,那就是文艺复兴。
由于有了这样的整体认识,其结果便自然而然地将中世纪的所有方面——从文学到艺术到哲学——都认为是黑暗一片,不值得学习与认识的。这就像中国古话所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其次,正是基于对中世纪历史的整体认识,使得西方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轻视中世纪的一切思想成果,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哲学都是如此。这其中就包括中世纪之后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如笛卡尔与培根,他们对中世纪哲学是相当轻蔑的。例如培根——他可以说既是中世纪最后的哲学家同时也是文艺复兴的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认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把亚里士多德建立的体系勉强同神学结合起来,并且将之视为百分之百的真理、神圣的教条。当经院哲学家们研究哲学时,总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查找出某些教条,然后以之为不言而喻的公理去思考一切,包括自然。这是十分错误的,他说:
“就现在的情形而论,由于有了经院学者们的总结和体系,就使得关于自然的谈论更为困难和更多危险了,因为那些经院学者们已经尽其所能把神学归成极有规则的一套,已经把神学规划成一种方术,结局并还把亚里士多德的好争而多刺的哲学很不相称地和宗教的体系糅合在一块了。”

在这里,培根将神学看成了是一种类似于方术的东西。这是一种十分明显的蔑视态度。
由于笛卡尔和培根都是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态度自然也就影响了之后的哲学家们,使得他们也一样地蔑视起中世纪哲学来。就像柯普斯登所言:
“一般人之所以对中世纪哲学家存在着侮蔑的态度,必须负起一些责任的,无疑地是像培根和笛卡儿这些人在评论士林哲学时所使用的措辞。就好像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容易以亚里士多德的批判来评价柏拉图主义。同样地,由培根和笛卡儿所启导的运动的信徒,自然而然会透过他们的眼光来看中世纪哲学。”

这里的士林哲学就是经院哲学。正是由于培根与笛卡尔这些哲学史上的大人物蔑视中世纪哲学,使得他们之后的哲学家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甚至尤有过之,对之充满了蔑视、批判与轻忽。
这样的结果就是中世纪哲学在中世纪之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被打入了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的另册,面目可憎。不妨打这样一个比喻:我们可以将西方哲学史比喻成一串珍珠项链,项链里有很多美丽的珍珠,却有一个例外,就是中间夹杂着几颗小石头而不是珍珠,这些小石头就是中世纪哲学了。或者用另一个更时髦的比喻:西方哲学史是一群人,绝大部分不是高富帅就是白富美,唯独中间站着一个矮穷丑,就是中世纪哲学了。
这种蔑视的结果就是忽略,也就是说,在许多哲学史著作中,中世纪哲学所占的比重都是很少的。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也来个东施效颦,将中世纪哲学随便说上几句就算了,就像黑格尔所说的一样“穿七里靴尽速跨过这个时期”呢?

当然不行!绝对不会!这样的原因很简单:人们过去对于中世纪哲学的蔑视与忽视是不对的,中世纪哲学完全并不如过去人们设想的那样不堪,甚至恰恰相反,在西方哲学的珍珠项链里,它也是一颗同样闪闪发光的珍珠。
事实上,那些过去的老观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现在大多数西方哲学史对于中世纪哲学的地位都给予了应有的尊重与肯定,这正如卢汶大学高等哲学研究所所长卡洛斯·斯蒂尔教授在为赵敦华教授的杰作《基督教哲学1500年》之序言中所说的:
“这种否定中世纪哲学的态度流行了若干世纪。直至本世纪,人们才终于理解了这个长达一千多年的时期对于欧洲思想,包括世俗化、理性化的思想的形成,所起到的重大作用。造成这种认识的部分原因是新经院主义运动和更完好的历史知识。人们现在更好地理解了存在于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思想之间的连续性。没有一个严肃的哲学家会提出应该撇开中世纪的理由。”

我们也理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