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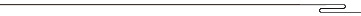
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的首都北京仍处在八国联军的占领下,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小朝廷只能在西安继续过他们的流亡生活。经过一年的谈判(背后实际上是侵略中国的八国之间对如何分赃的反复协商),清政府终于在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这一年的漫长过程中,列强考虑的首要问题是要不要乘此瓜分中国。由于义和团强烈反抗的事实使列强认识到难以对中国进行直接的统治,不如通过已完全屈服的清政府来实行对中国的统治,也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它们最后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打算。《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一是规定中国对各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要承担一两白银。这笔赔款在四十年内分年还清,加上利息和地方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至少十二年的财政总收入,使清政府的财政更加陷入绝境。二是规定列强有权在北京至渤海地区驻军。这一条关系重大。以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使用的军队就是根据这个条约早已盘踞在平津铁路沿线的“中国驻屯军”。三是所谓“惩办祸首”,实际上就是严厉警告清政府以后只能乖乖地顺从他们的意旨办事,不得稍有违抗。这样,中国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又大大跨进了一步。
看起来,中国在《辛丑条约》后的不短时间内没有再遭到像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那样的外国大规模军事进攻,瓜分中国的声浪也不像前一阵那样叫得凶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民族危机暂时得到了缓和?不是。恰恰相反,民族危机向着更加深刻的方向发展了。
列强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已大大加强,这一点下面将着重谈到。
更突出的事实是:为着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建筑铁路,开掘矿藏,兴办工厂,设立租界,经营航运业,牢牢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要是说,一九〇一年以前,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攫取了各种投资的特权,但一时还来不及消化这些果实、直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活动;那么,一九〇一年以后,他们就以空前的规模来实现这种投资特权,来消化、巩固和扩大前一时期获得的侵略成果。这是帝国主义深化对华经济侵略的重大进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华投资和正常的国外投资不同:它是在中国丧失国家独立主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外国资本享有垄断权利,是不妨害而且有利于帝国主义利益的半殖民地化发展工业的道路。投资的重点,是利润最优厚并便于资源掠夺的兴筑铁路和开掘矿藏。
从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一年间,完工的铁路,有东清铁路、东清铁路南满支路、京汉铁路、株萍铁路、胶济铁路、粤汉支路、道清铁路、正太铁路、滇越铁路、沪宁铁路、潮汕铁路、漳厦铁路、广九铁路、津浦铁路;正在兴筑的有京奉铁路、粤汉铁路、京绥铁路、陇海铁路、新宁铁路、沪杭甬铁路、南浔铁路、吉长铁路。旧中国的铁路干线,除浙赣铁路、同蒲铁路和粤汉铁路的株洲韶关段等以外,几乎都是这个时期内完成或开工兴建的。
 喷吐着浓烟的火车像一个怪物,风驰电掣地奔过中国内地的广大原野。这对促使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起了重要作用。俄、法、德、英、日等国,经过剧烈争夺,采取借款或强行承租等方式,控制了中国的铁路。它们的主要着眼点是在把它们的商品大量运送到中国内地和把从中国掠夺的原料运送出去,并获得一定年限内对某些铁路事业的管理权,获得优厚的借款手续费、利息和红利,并且使铁路通过的区域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因此,它不可能像美国西部大铁路建筑那样,有力地促进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喷吐着浓烟的火车像一个怪物,风驰电掣地奔过中国内地的广大原野。这对促使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起了重要作用。俄、法、德、英、日等国,经过剧烈争夺,采取借款或强行承租等方式,控制了中国的铁路。它们的主要着眼点是在把它们的商品大量运送到中国内地和把从中国掠夺的原料运送出去,并获得一定年限内对某些铁路事业的管理权,获得优厚的借款手续费、利息和红利,并且使铁路通过的区域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因此,它不可能像美国西部大铁路建筑那样,有力地促进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外国对中国矿业特别是煤矿的攫夺,是这时非常突出的现象。“因为,无论是外国在华设立的工业企业,或从西方来华的远洋轮船和在中国沿海以及埠际之间航运的大小轮船,都十分需要就近获取燃料动力,以支持它的生产和运转。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煤炭是第一能源,它是现代工业和航运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外国资本对中国矿冶业,特别是煤矿业的开发和投资,便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重点。而以煤矿为中心的矿业攫夺,就成为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内容。”
 重要的有:日本资本对抚顺煤矿和辽阳县的烟台煤矿的掠夺,英国势力对开平、滦州煤矿的兼并,德国资本对淄川、坊子煤矿的侵夺,英资福公司对焦作煤矿的侵夺,日本对辽宁鞍山铁矿开始勘查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英国借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机会,以欺诈手段霸占中国经营多年的开平煤矿,随后又兼并滦州煤矿,在一九一一年成立英国控制下的开滦矿务总局;另一件是日本在一九〇六年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锐意“经营满洲”,而以经营南满铁路及开发沿线煤矿资源为中心,“满铁”日后成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急先锋。
重要的有:日本资本对抚顺煤矿和辽阳县的烟台煤矿的掠夺,英国势力对开平、滦州煤矿的兼并,德国资本对淄川、坊子煤矿的侵夺,英资福公司对焦作煤矿的侵夺,日本对辽宁鞍山铁矿开始勘查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英国借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机会,以欺诈手段霸占中国经营多年的开平煤矿,随后又兼并滦州煤矿,在一九一一年成立英国控制下的开滦矿务总局;另一件是日本在一九〇六年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锐意“经营满洲”,而以经营南满铁路及开发沿线煤矿资源为中心,“满铁”日后成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急先锋。
除路矿两项外,西方列强在其他方面的投资也急剧增加。甲午战争前,虽经过五十多年积累,一八九四年外国在华企业资产总额还只有约一亿零九百万美元,而到一九〇二年已增至四亿七千八百万美元。与此相应,外国银行也积极扩大经营范围,加强控制中国的工矿交通事业,垄断中国的财政金融。
这些纷至沓来的经济掠夺活动,特别是它深入中国内地,对一切爱国的中国人起了强烈的惊醒作用。当时,许多人突出地认为:外国人一旦掌握了我国的铁路和矿山,就是握住了我们的命脉。在二十世纪初年出版的留日学生刊物《江苏》《浙江潮》等上面,到处可以读到这类沉痛、激烈的词句:
呜呼,铁路之于人国,犹经脉之于人身也。是故一县失其权则一县死,一省失其权则一省死,况全国南北(粤汉铁道)、东西(蜀汉铁道)交通之大关键乎?

经济上之竞争,其祸乃更毒于政治上。何以故?譬之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警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其由,未几乃病瘵以死矣,此言其术也。若夫于政治上,则未有经济上之权既占、而政治上之权乃犹能以人者也。盖其资本所在之地,即为其政治能力所到之地,征之于近代,历历有明征也。

这些认识,比起十九世纪末年,显然要深刻痛切得多了。
资本输入的激增,并不排除列强对华的商品倾销。相反,又为商品的进一步输入打开通道。通商口岸是西方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据点。甲午战前开设的通商口岸共三十四处,战后到清末新设的口岸有四十八处,其中包括苏州、杭州、梧州、南京、岳阳、秦皇岛、长沙、济南、南宁、长春(宽城子)、哈尔滨、齐齐哈尔、奉天(今沈阳)、昆明等,大多处于中国内地。
 由于列强取得海关管理权、扩大内河航行权和铁路修建权,并享有免除子口税等远优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特权,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五年的短短五年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陡增一倍以上,而出口却大幅度萎缩。许多以往还很少或没有见到外国人的地方,这时闯进了高悬外国旗帜的轮船,出现了许多高视阔步、耀武扬威的“洋人”。他们俨然以主子的姿态,君临到中国的国土,把中国人看作下等人。上海外滩公园高悬的“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告示,便是一个突出例子。他们的势力每伸到一个地方,立刻激起这些地方民众的极大愤怒,进一步提高了民族自觉。
由于列强取得海关管理权、扩大内河航行权和铁路修建权,并享有免除子口税等远优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特权,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五年的短短五年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陡增一倍以上,而出口却大幅度萎缩。许多以往还很少或没有见到外国人的地方,这时闯进了高悬外国旗帜的轮船,出现了许多高视阔步、耀武扬威的“洋人”。他们俨然以主子的姿态,君临到中国的国土,把中国人看作下等人。上海外滩公园高悬的“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告示,便是一个突出例子。他们的势力每伸到一个地方,立刻激起这些地方民众的极大愤怒,进一步提高了民族自觉。
与此同时,列强为了争夺特殊权益,在中国展开了严重的斗争。其中最剧烈的是日俄在东北的争夺和英俄在西藏的争夺。沙皇俄国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出兵占领东北。《辛丑条约》签订后,他们仍不撤兵,一九〇二年四月才同清朝订约分期全部撤兵。到一九〇三年四月,原来规定的第二期撤兵期限届满,沙俄不仅不肯履行条约,反而提出新的要挟。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给沙皇的备忘录中,还提出“把北满归并俄国”的要求。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就抱着对中国东北的极大野心,力图排除沙俄的势力,为它们自己控制东北打开大门。一九〇四年一月,日本不宣而战地对驻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了。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大规模厮杀竟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进行,中国居民惨遭屠戮,房舍化为灰烬,带来巨大灾难。而腐朽的清朝政府居然声称“中立”,置战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这怎么能不使众多的中国人感到寒心?日俄战争进行了一年零八个月。结果,确定东北的北部保留为沙俄的势力范围,而东北的南部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英俄之间也展开着剧烈的争夺。一九〇三年冬天,英国悍然发动对西藏的军事进攻。第二年八月,攻陷拉萨。但在西藏民众的坚决反抗下,只停留了一个多月就被迫撤出拉萨。
这时,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十九世纪初维也纳会议后最剧烈的变化,旧的世界格局已被打破,新的角逐正在激烈地进行。一九〇五年春季和秋季在摩洛哥发生冲突事件后,英、法同德国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化。它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欧洲和地中海区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日益临近。为着集中力量对付德国,英、法在外交上采取一系列主动行动,调整同各方面的关系。一九〇七年,先后签订了英俄协定、法日协定和俄日协定。第二年,日美之间也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在这些协定中,包括秘密商定双方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一切连个招呼也不同中国打。当时留日学生刊物《河南》痛心地写道:
今则吾国内不问何省,省不问何地,一草一木,一沙一礁,非皆已于他国之最近协商时而默于意中互相认许耶?……以吾四万万之同胞,脑量不减于人,强力不弱于人,文化不后于人,乃由人而降为奴,是稍有人血人性者所不甘,而谓我志士而忍受之耶?以此原因,睹外患之迫于燃眉,遂不能不赴汤蹈火,摩顶断脰,以谋于将死未死之时。

不久,又一个事件给了中国人重大的刺激,那就是日本在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强迫朝鲜签订所谓《日韩合邦条约》,正式吞并朝鲜。中朝两国历来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已能陈兵鸭绿江边,虎视眈眈地把目光集中投向中国的东北。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写道:“夫其于朝鲜,则既已奏凯而归矣,而彼之挟此优胜之技,以心营目注者,岂直一朝鲜而已。是故吾睹朝鲜之亡,乃不寒而栗也。”
 朝鲜亡国后民众的悲惨遭遇,更使中国人目击心伤,受到强烈刺激。
朝鲜亡国后民众的悲惨遭遇,更使中国人目击心伤,受到强烈刺激。
“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中国人成了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个人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只是空谈,都将化为泡影。许多爱国者不惜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来拯救祖国于危急之中。这不是哪个人任意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
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够带领民众抵抗外来侵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就会被民众所抛弃。这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政府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呢?人们期望的是一个能够痛定思痛、锐意革新、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府。清政府恰恰相反,宁肯大量出卖国家的权益,以换取外国列强的支持,压制民众的爱国行动,维护它在国内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这个极端腐朽的政府,事实上已失去锐意革新的可能。
清王朝原来虽早已日趋衰败,但外表上仍仿佛是个威严显赫的庞然大物,使人望而生畏。甲午战败,对外屈辱到如此地步,内部的腐败也暴露无遗,使一向把自己装扮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王朝在人们心目中顿时丧尽了尊严。军事和财政力量的极端空虚也使它的统治无法保持稳定。它的覆亡已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甲午战后的清政府不过是在苟延残喘中勉强再维持了十多年。
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又有新的变化:成为外国列强统治中国的更加驯服的工具。这以前,清政府虽早已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同它们相互勾结,但毕竟在统治权力和利益上还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因而在各种条件凑合下,即使表现得十分被动和动摇,并且很快以屈服告终,但多少还参加过一些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这以后,连这样的抵抗也不再看到了。
一九〇一年二月,当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立刻发出一道煌煌上谕,宣布政府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且厚颜无耻地说:“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辛丑条约》签订后,一九〇二年一月,清政府从西安回到北京。他们从郑州到正定这一段路,坐的是火车。进宫那天,“当西太后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轿中欠起身来,以非常和蔼的姿态向他们回礼”。当一月二十八日各国使节受接待时,“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帘幕后面。二月一日,她接待外国使节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
 这些,看起来都是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却很具有象征性,显示出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间的政治关系上的微妙变化。
这些,看起来都是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却很具有象征性,显示出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间的政治关系上的微妙变化。
这以后,清政府在各方面变本加厉地执行对外屈服的政策。它一再传谕保护外人权益,竭力压制民众爱国行动,聘请外国人担任财政、军事等顾问,连地方大吏的任命也要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各级地方官更加战战兢兢地一意媚外,竭力维护外人在华的特殊权益。“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

既然清政府把自己同外国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毫不奇怪,民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结论。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
 “洋人的朝廷”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被陈天华一语点破后,立刻不胫而走,在爱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洋人的朝廷”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被陈天华一语点破后,立刻不胫而走,在爱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不仅如此,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对民众经济上的榨取也进一步加重。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两个:首先是对外支付巨额的赔款。清朝的财政在甲午战败后本已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辛丑条约》后受到更加重大的打击,除了采取对外大举借债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外(在政治上也因而更加俯仰随人),只有加紧对百姓的榨取;其次是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在国内的统治而加紧扩军,袁世凯练成北洋六镇(镇相当于师),每个省也计划各编练新军一个镇,这自然又需要加紧对民众进行更残酷的搜刮。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迟滞,政府的财政收支一向难以有过快的增长。直到甲午战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支大体上都稳定在八千万两左右。但到一九〇三年,岁入已达一万万零四百九十二万两;到一九〇八年,岁入达二万万三千四百八十余万两。
 而一九一〇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度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为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两,岁出达三亿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十几年间,国家的财政收支竟剧增到四倍左右。这在人们生活中是从来不曾经历过的。所谓岁入的逐年猛增,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来自竭泽而渔的掠夺和搜刮。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田赋、厘金、盐税等旧税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从中中饱,任意诛求,造成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使人民到了再也无法忍受的地步。
而一九一〇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度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为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两,岁出达三亿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十几年间,国家的财政收支竟剧增到四倍左右。这在人们生活中是从来不曾经历过的。所谓岁入的逐年猛增,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来自竭泽而渔的掠夺和搜刮。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田赋、厘金、盐税等旧税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从中中饱,任意诛求,造成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使人民到了再也无法忍受的地步。
汉族人民中传统思想,这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满族统治者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民众之间的矛盾重新突出出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话,到处被引用着。许多人把清政府种种倒行逆施,包括它所以毫不顾惜地出卖国家和民众的权益,统统归结为“异族”统治的结果。连同前面所说的种种,汇合成一个共同的观念:必须推翻这个清朝政府的统治。
在民怨沸腾、革命高潮日益逼近的时候,为着应付这个已越来越驾驭不住的局势,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宣示“预备立宪”。这道上谕说了一大堆空话,实质内容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一句话。也就是说:庶政尽可以让各方面发表一点“舆论”,这也算是一个让步,但“大权”只能“统于朝廷”,一点也放松不得。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两天内先后死去。三岁的溥仪继位,年号“宣统”。醇亲王载沣作为摄政王监国。清朝最高统治集团陷入一片混乱。
一九一一年春,已是全国大起义爆发的前夜,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担任。“十三个大臣之中,汉人仅得四个,满人得了八个,而八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五个,蒙古旗人一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假使那些皇族人才确是人才,犹有可说,实际上都是一些骄纵无度、不知世务的糊涂虫。”
 靠这样一群昏庸骄横的“糊涂虫”,能指望他们把国家引导到哪里去呢?
靠这样一群昏庸骄横的“糊涂虫”,能指望他们把国家引导到哪里去呢?
为什么清政府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还要那样倒行逆施?根本原因在于:一切反动统治者历来都把权力看得最为重要,总要尽力把一切权力牢牢地集中在自己手里。越当他们统治地位不稳,越当他们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况中,他们就更加惴惴不安,对周围一切人都不放心,唯恐权力有什么分散,更要把它紧紧地攥在手里。这是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病态心理,但在这个没落阶级的统治集团看来,却仿佛是生命攸关的头等大事。
对“清末新政”,不能离开这个大背景来考察。
他们推行的“新政”中,“奖励设厂”和“废科举、兴学堂”这些措施,在客观上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这件事,虽已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如此,但它对推进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毕竟不能小看。在各省设立的咨议局也使当地士绅多一点发发议论的权利,受到一点初步的民主训练。但由于清政府拒绝任何根本的社会变革,而且把政权紧紧掌握在那群极端腐败无能的权贵手里,又怎么能给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呢?“奖励设厂”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给自己开辟财源。前面说过,那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罗掘皆尽的地步。石头中已榨不出多少油来,要另辟财源就使他们的眼光也转到工商业上来。它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口头上鼓励你们从事工商业,使你们努力谋求生财之道,然后从你们身上狠狠地勒索出大笔钱来,解决我的财政困难。这在闽浙总督李兴锐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取于民者既不能不加于前,则为闾阎筹生利之源,以救目前财用之困,非讲求商务,无从措手。”
 因此,所谓“奖励设厂”的政策最初很使一些人高兴了一阵,对他们投资新式工业起过激励作用。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那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上海《时报》上有篇文章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事实的真相:“自商部设立,而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赠巨金,即曰招徕南洋富商责令报效。”“自有商部,而我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天下名实不相符之事,乃至如此。”
因此,所谓“奖励设厂”的政策最初很使一些人高兴了一阵,对他们投资新式工业起过激励作用。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那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上海《时报》上有篇文章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事实的真相:“自商部设立,而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赠巨金,即曰招徕南洋富商责令报效。”“自有商部,而我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天下名实不相符之事,乃至如此。”
 其实,病商更甚的还有一道又一道处处留难、任意增抽的厘卡。难怪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要说:清政府“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的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
其实,病商更甚的还有一道又一道处处留难、任意增抽的厘卡。难怪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要说:清政府“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的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

孙中山在一九〇四年写道:“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清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

海外有些学者对“清末新政”作了过高的评价,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革命,让清政府继续把“新政”推行下去,中国的现代化仿佛将能更顺利更快地实现。客气一点说,这些学者对中国的情况实在太隔膜,所作的论断很难说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民众对清政府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人从冰冷的事实中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推翻这个腐败的卖国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是现实生活迫使他们得出的结论。
到辛亥革命前夕,人们的这种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不加掩饰的地步,并且在社会上相当普遍。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二日和十六日,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两封信中忧心忡忡地写出他所看到的民众普遍心态:
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中国(引者注:指清政府)的前途似乎非常黯淡。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

他说得不错:一场革命大风暴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绝不是少数人的意旨所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