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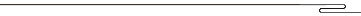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改变了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
对日本来说,学者远山茂树这样概述:“以甲午战争走向帝国主义早熟的步伐加速了。凭战争得到的巨额赔款(收到的是英镑),成为一八九七年三月确立金本位制的准备金。此外,第一抵补了甲午战费的百分之三十(七千九百万日元),第二用作准备下次更大规模战争(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充军备费用(约二亿日元),第三用来设立钢铁厂和扩充铁路、电报、电话事业(三百八十万日元),第四用来充作经营台湾殖民地的费用(一千二百万日元),第五用来充作皇室费(两千万日元)和水雷、教育、灾害准备的三种基金(五千万日元)。就是说,以赔款的杠杆和天皇制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日本资本主义确立起来了。资产阶级也积极地热衷于对外侵略政策,叫嚷所谓‘国旗飘扬的地方,贸易随之’。甲午战争并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矛盾而爆发的战争,但在完成帝国主义世界体制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开端上,却是划时代的。”
 从此,日本军国主义便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对中华民族的主要威胁。
从此,日本军国主义便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对中华民族的主要威胁。
在中国方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急速衰落已经暴露无遗,成为谁都看得清楚的事实。西方列强把它看作一艘快要沉没的破船,争先恐后地扑上前来,想尽快从这里多捞取一把,掀起了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图景:甲午战争结束后两年,德国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借口德教士两人在山东巨野被害,出兵占领胶州湾。十二月,沙俄军舰佯称助华抗德,驶入旅顺港。一八九八年三月,清政府同德国公使签订胶州湾租借条约,租期九十九年;准许德国修造从胶州湾至济南的铁路,铁路附近三十里内的煤矿由德国开挖;山东境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德国有优先权。取得铁路建筑权,往往同时就是取得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这就是五四运动时“山东问题”的最初由来)。同月,清政府又同沙俄签订旅顺、大连租借条约,租期二十五年;南满铁路由俄方控制的东省铁路公司建造。法国本已取得云南、广西、广东的开矿优先权和越南至中国境内建筑铁路、架设电线权,接着又取得广州湾(今广东湛江)的九十九年租借权。英国得到中国长江流域永不割让给他国、永任英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承诺,又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和威海卫。日本获得清政府不将福建让租他国的认可。后来,英、德、俄之间索性撇开清朝政府自行协商,分别达成协定,划分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起步稍晚的美国政府只能提出“门户开放”的主张,承认其他国家势力范围的划分,但要求与其他国家在华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和待遇。
中国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过去所说的强或弱,而是更加冷酷的存或亡了。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人们一旦发觉自己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便不能不对过去的传统信条进行深刻的反思,尽力以新的眼光去审视外部世界,力图从中汲取足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寻求国家的新的出路。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救亡成为近代启蒙运动的真正动力和起点。
知识分子,在被压迫民族中通常是政治上最敏感、最早觉醒起来的部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大体上还是旧式的士大夫。他们受了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浸润,“君臣之义已定,天泽之分难越”“食毛践土,莫非臣子”之类的观念在头脑里根深蒂固。甲午战后流行过一部时论选集叫《普天忠愤集》。“忠愤”两字并提,是当时一般爱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他们目睹祖国面临沦亡的严重危险,满腔悲愤地起来奔走呼号,但一时却还突不破“忠君”精神枷锁的束缚,把忠君爱国看作一回事。康有为的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最容易打动他们的心。光绪皇帝支持变法的态度,更使他们欢欣鼓舞,产生巨大的幻想。康有为等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能够在国内掀起一股巨大浪潮,成为当时爱国救亡运动的主流,是很自然的。
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进程,是一步紧扣一步地同当时民族危机的逐步激化相应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劈头就写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
 这里说得很清楚:维新变法运动,作为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兴起,是甲午战败强烈刺激下的产物;而戊戌变法高潮的出现,又是列强公然在华争夺并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迅速激化的产物。
这里说得很清楚:维新变法运动,作为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兴起,是甲午战败强烈刺激下的产物;而戊戌变法高潮的出现,又是列强公然在华争夺并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迅速激化的产物。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值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应试的时候。康有为倡议举人们聚议,共同上书。聚议的结果,推康有为起草,有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署。书中慷慨陈词,要求拒和变法。这次上书,由于都察院拒绝代递,并没有送达光绪皇帝。但这一千二百多名举人联署的“公车上书”,在有清二百多年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书稿很快被坊间翻刻流传。各省举人返回各地,更使这个事件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留在北京,联络社会各方,特别注重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他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并推动开设强学会于北京、上海。第二年,又出版《强学报》。不久,强学会遭封闭。梁启超又和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销行至万余份,成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一八九七年,康有为等创办《广时务报》(后改名《知新报》)于澳门,江标、唐才常等创办《湘学报》于长沙(第二年又出版唐才常主编的《湘报》),严复、夏曾佑等创办《国闻报》于天津。同年十月,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支持下开设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有了这些据点,维新变法运动就在全国逐步高涨起来。
德国强占胶州湾时,康有为本来在北京筹划移民美洲的事,闻讯后再次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局势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
他在这次上书中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俄”指彼得变法,“日”指明治维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三策,并且强烈地警告说:“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发愤与否,在于此时。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一切不行,则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刲,欲为偏安,无能为计;圈牢羊豕,宰割随时,一旦脔割,亦固其所。”“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这些话是很大胆也很有震撼力的。
这些话是很大胆也很有震撼力的。
随着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纷纷在华攫取势力范围,情况越来越危急。四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他在第一次集会上发表了沉痛激昂的演说,“座中人有为之下泪者”。他说:
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吾四万万之人,吾万千之士大夫,将何依何归何去何从乎?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

在这前后,各地学会、报馆等纷纷成立。据不完全统计,三年内,全国共设立学会八十七所、学堂一百三十一所、报馆九十一所。这是中国社会中以前没有过的新现象。他们议论局势,鼓吹新学,抨击时弊。以往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至此国内风气为之大变。
在亡国的威胁和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下,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分化。由于慈禧太后把持着朝内一切大权,光绪帝名为皇帝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他对慈禧太后推行的对外屈服的政策不满。这时,借着慈禧表面上允许他“亲政”的机会,就在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接着,陆续颁发许多诏书,准备自上而下地实行一些改革。从光绪下诏变法,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随后遭到软禁、变法停止,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号称“百日维新”。
尽管“百日维新”的那些谕旨,由于皇帝没有多少实权,并没有真正得到执行,但由于它用皇帝“圣旨”的名义下达,在国内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当时远在四川的吴玉章回忆道:
甲午之前,在我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思想。……那时四川还很闭塞,新书还未流行,因此我还没有接触到什么“新学”。不过,我对当时国家危亡的大势是了解的,我正在为祖国的前途而忧心如焚。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激发了我的救国热忱,我需要找寻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我知道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因此,对“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不感到惊奇。但是,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有些茫然。正当我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传来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我于是热烈地接受了它。
“戊戌变法”的那些措施,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曾经震撼人心。我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所以感受得特别深刻。那时我正在四川自(自流井)贡(贡井)地方的旭川书院读书,由于热心于变法维新的宣传,人们给了我一个外号,把我叫做“时务大家”。当变法的诏书一道道地传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赞成变法的人,真是欢欣若狂。尤其是光绪帝三令五申地斥责守旧派阻挠上书言事,更使我们感到鼓舞,增长了我们的气势,迫使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守旧分子哑口无言。现在看来,我们那时对光绪帝的迷信,是何等的幼稚可笑,但在当时,尤其是在我的家乡,我们的思想要算是最进步的了。

戊戌维新运动的重大历史贡献,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它所以能在一向闭塞的中国社会中激起如此巨大的思想波澜,根本的一条,是因为它适应着当时众多的苦苦寻求救国出路的人们的需要,给了他们一个新的答案。它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变化,最重要的有:
第一,它帮助广大知识分子认识万国大势,看清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提高了民族觉醒的程度。本来,许多人虽然痛切地感受到“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但由于长期处于闭塞状态,对世界整个局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变到底会怎么发展,还是茫无所知的。世界知识的缺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维新派这时通过报纸和学会,宣传他们当时所知道的一点万国大势。《时务报》“译欧美报纸,载瓜分之说,以激厉人心,海内为之震动”。
 “天津报馆刊布瓜分中国图说,远近震恐。”
“天津报馆刊布瓜分中国图说,远近震恐。”
 湖南的南学会每七天举行演讲会一次,“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湖南的南学会每七天举行演讲会一次,“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它以广泛的规模宣传西方近代文化,即所谓新学,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鸦片战争以后,这种新学虽然早已渐次传入中国,但在很长时间内,一般士大夫认真关心这种新学的很少很少。直到中法战争以前,仍然是“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经过中法战争,“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斥。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盖渐知西学而莫肯讲求”。
 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一般士大夫看来,仍不能在所谓“大道”中占有半点地位。封建文化依然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这种状况,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运动,把提倡新学和人们救亡的迫切要求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对当时许多人日夜焦虑、寝食为之不安的问题,它给以一个看起来比较实际的回答:只要实现新学,中国就可以从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摆脱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西方文化为什么在短时期内忽然被那么多人所关心和向往,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有这种客观需要。
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一般士大夫看来,仍不能在所谓“大道”中占有半点地位。封建文化依然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这种状况,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运动,把提倡新学和人们救亡的迫切要求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对当时许多人日夜焦虑、寝食为之不安的问题,它给以一个看起来比较实际的回答:只要实现新学,中国就可以从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摆脱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西方文化为什么在短时期内忽然被那么多人所关心和向往,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有这种客观需要。
在救亡的强烈要求下,国内出现了一个学习西学的空前热潮。各地新成立的学会,纷纷译印图书,刊布或推销报纸,举办讲演会,展览新式仪器,宣传新学。他们把学习西方看作救国的唯一途径,只要是西方的东西都想学过来。这构成当时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百日维新”时,科举考试中废八股、试时务的措施也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在广西的雷沛鸿回忆知识界风气大变的情景时写道:
从此我就从八股文中解放出来,再不用墨守朱子章句而改做另一文体的策论了。策论是不受什么格式限制的,而内容要求丰富,议论则要求纵横捭阖,这就非多读书不可,非打开思路不可,于是学风文风为之丕变,一改过去废书不读为大读其书,上至周秦诸子,下至三教九流,稗官野史、杂书禁书,无所不读。当时我们只要看见书就抢来读,书店来了新书就抢来买,买不到就借来看,甚至借来抄。这样,我们的胸襟眼界就大大开拓了。

第三,它初步宣传了民权思想,给知识分子灌输了一点初步的民主意识。这种“民权”思想的宣传,同样是和救亡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汪康年写道:“若夫处今日之国势,则民权之行,尤有宜亟者,盖以君权与外人相敌,力单则易为所挟;以民权与外人相持,力厚则易于措辞。”“且夫民无权,则不知国为民所共有,而与上相睽;民有权,则民知以国为事,而与上相亲。”
 从这点出发,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书中一再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张,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课艺批语中一再强调“兴民权”的重要性,严复在《辟韩》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痛快淋漓的阐发。谭嗣同在《仁学》中发出“冲决网罗”(包括冲决“利禄之网罗”“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等)的呐喊,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之谈。各地学会团体纷纷成立,对知识分子中民主意识的初步养成也起了一定作用。
从这点出发,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书中一再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张,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课艺批语中一再强调“兴民权”的重要性,严复在《辟韩》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痛快淋漓的阐发。谭嗣同在《仁学》中发出“冲决网罗”(包括冲决“利禄之网罗”“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等)的呐喊,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之谈。各地学会团体纷纷成立,对知识分子中民主意识的初步养成也起了一定作用。
第四,有力地宣传了“变”的观念,对许多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变化起了巨大作用。
前面说过,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占着支配的地位。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变”的观念在宣传中占着突出的位置,成为变法主张的理论基础。康有为等力图从中国传统古籍中寻找这种宣传的依据。他们一再引述《周易》中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并附会《公羊传》中“张三世”的说法来解释他们的变法主张。梁启超在他《变法通议》中有一段名言:
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的发表。这是第一次将西方近代重要学术著作比较完整地直接介绍到中国来。它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它替当时求进步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同传统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新观念:进化论。《天演论》一开始就引导人们去深思:我们眼前的世界在几千年前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成今天的?支配这种变化的力量是什么?书中用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的丰富材料,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与“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充满着矛盾冲突和变化的物质世界的图景:世界万物都充满着蓬勃的生气,彼此间进行着异常剧烈的斗争。“数亩之内,战事炽然。”世界就是在这种剧烈斗争中,不断开辟着自己前进的道路。整个宇宙间充满“不可穷诘之变动”。“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这些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话,对当时许多人来说,却是石破天惊之论,大大打开了他们的眼界。
《天演论》把“物竞天择”看成支配世界发展的法则。它认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凡是同它周围的环境相适应的,就能生存,能发展;反过来,凡是不相适应的,就会被淘汰,会灭亡。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说的这种适应不是消极的、宿命论式的,而是积极的、激励人们去奋斗的。究竟是人胜天,还是天胜人?严译《天演论》作出“人胜天”的回答。它强调发挥“群治”的作用,“与天争胜”。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不甘心祖国长期处在听任外国列强宰割的地位,迫切要求救亡图存,奋发图强。严译《天演论》在卷终按语中语重心长地点出:生当今日,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
 。这就点明了严复所以要在这时翻译发表《天演论》的原因所在。
。这就点明了严复所以要在这时翻译发表《天演论》的原因所在。
严译《天演论》所宣扬的进化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没有任何其他书籍能同它相比。鲁迅回忆自己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的情景时说:“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这在那时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支配了中国的进步思想界。
这在那时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支配了中国的进步思想界。
戊戌维新运动推动的变法活动却是注定要失败的。原因在于:在当时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足以支持变法取得成功的社会力量。在朝廷内部也好,地方上也好,旧社会势力仍然占着绝对优势。维新派希望依靠一个并无多少实权的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某些重要改革,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对那些无拳无勇的书生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缺乏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就终究只能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运动还有不少严重的弱点:他们鼓吹的“民权”被限制在君主立宪(也就是康有为所说的“君民合治”)的范围之内,只是要求将原来的绝对君权稍稍开放一点,“参用民权”而已,还声明“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他们宣传的“变”只讲渐变,不讲突变。在清朝政府和它代表的旧社会制度已经腐朽到如此地步的时候,已不可能指望它把中国从迫在眉睫的深重危局中解脱出来,更谈不上靠它来实现什么现代化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正确地指出:“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一八九五年的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一八九八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革命变革。”

尽管如此,绝不能因而抹杀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特别是思想启蒙方面起过的巨大进步作用。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得很对:“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清朝统治者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失去头脑的作用,驯服在腐朽统治之下。”“当时一整套毒品,受到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
 只要比较一下戊戌维新运动以前和以后中国思想界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别,就不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摆脱陈旧的思想牢笼的束缚极不容易。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蒙下跨出了一步,又从这个运动的失败中再向前跨出一步。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索的爱国者们,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只要比较一下戊戌维新运动以前和以后中国思想界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别,就不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摆脱陈旧的思想牢笼的束缚极不容易。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蒙下跨出了一步,又从这个运动的失败中再向前跨出一步。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索的爱国者们,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